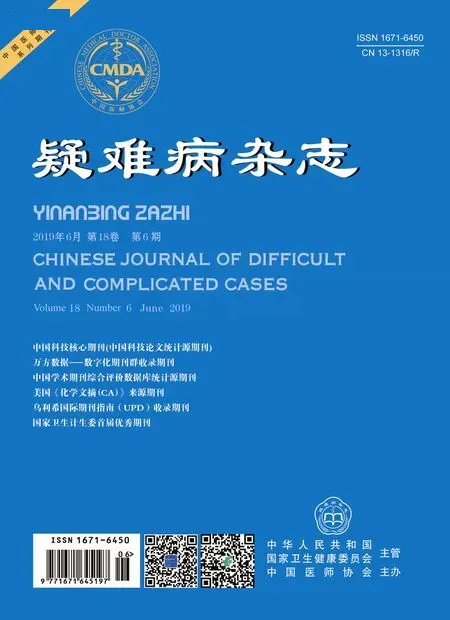巨噬細胞遷移抑制因子對腫瘤微環境影響的研究進展
陳其冰,李芬綜述 陶澤璋審校
腫瘤的發生發展受到眾多因素的影響,而腫瘤微環境(tumor microenvironment,TME)對腫瘤的影響極為密切而重大;腫瘤微環境中存在大量細胞因子,每時每刻都在對環境本身及瘤細胞產生或多或少的作用。其中巨噬細胞遷移抑制因子(macrophage migration inhibitory factor,MIF)對腫瘤微環境的影響越來越受到重視,研究表明巨噬細胞遷移抑制因子在不同的疾病模型中發揮的生理作用大相徑庭。本文就MIF對TME中幾種主要的免疫細胞、內皮細胞、成纖維細胞的作用作一簡單概述。
1 巨噬細胞遷移抑制因子與腫瘤微環境
1.1 巨噬細胞遷移抑制因子(MIF) MIF是一種以促炎作用為主的多功能細胞因子,通常也被認為具有促瘤作用。目前已被學界證明可與包括CD77/44、CXCR4、CXCR2、IL-2/6/8、MMP成員及EGFR在內的多種細胞因子相互作用,并在多種腫瘤的形成、侵襲和轉移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1]。事實上MIF的作用并非一直促瘤,而是隨生理環境變化而變化,這點可以從MIF的結構角度解釋:MIF的四級結構由3個同源單體組成,每個單體由115個氨基酸構成,其中有多個氨基酸殘基容易發生翻譯后修飾從而影響最終的四級結構,所以MIF的生理作用及活性受到具體生理環境影響[2-3]。
1.2 腫瘤微環境(TME) 腫瘤的發生發展與其所處的生理環境密切相關,腫瘤細胞所處的細胞環境和細胞外基質(extracellular matrix,ECM)環境統稱作腫瘤微環境。腫瘤微環境是一個包含邊界、血管、淋巴管等復雜結構的生理環境,它可發揮促瘤作用也可發揮抑瘤作用。它的細胞成分包括大量正常細胞,如血管內皮細胞、成纖維細胞和免疫細胞[如T淋巴細胞、B淋巴細胞、自然殺傷T細胞、腫瘤相關巨噬細胞(tumor-associated macrophages,TAMs)]等[4-5]。而基質部分則指以上細胞及腫瘤細胞自身分泌的細胞因子、各類大分子物質及相關復合物[6]。其中免疫細胞可被腫瘤細胞從外周循環中招募并浸潤到瘤體中,并通過旁分泌作用參與細胞外基質環境的改造,從而為原發腫瘤創造更好的生長環境,促進腫瘤發生發展[7]。
2 MIF對腫瘤影響
MIF主要來源于單核細胞、巨噬細胞、中性粒細胞、T細胞、B細胞和樹突細胞等多種免疫細胞以及血管內皮細胞,其作用主要表現為對巨噬細胞遷移的抑制和增強局部炎性反應[8]。而在腫瘤狀態下,MIF還來源于腫瘤細胞,大量文獻證實腫瘤來源MIF可對腫瘤的癌變、腫瘤細胞增殖、侵襲及疾病預后產生重要影響。如在鼻咽癌細胞系中,Liu等[9]發現針對MIF的siRNA可顯著減少鼻咽癌細胞(SUNE-1、CNE-2)的克隆形成并抑制其侵襲能力,提示MIF可能會促進鼻咽癌的形成、侵襲甚至轉移。除此之外,MIF在黑色素瘤、消化系統惡性腫瘤和宮頸癌等多種人類癌癥中的表達水平均顯著高于健康對照組,提示腫瘤狀態下MIF水平雖然上升但機體對腫瘤的局部免疫并沒有增強[10-12];同時也有學者的研究結果支持高水平MIF對應更好的疾病預后。Castro等[1]發現MIF水平的降低會導致惡性膠質瘤瘤體邊緣的M2樣巨噬細胞浸潤增加,引起免疫抑制、增加腫瘤對貝伐珠單抗的耐藥性,進而促進腫瘤生長。Presti等[13]在治療膠質母細胞瘤時發現新輔助治療可顯著增加患者體內MIF的表達,提出MIF的相對高表達與相對較低的總體存活率缺乏相關性,反而表現出增加總體存活率的趨勢。
這些截然相反的研究結論提示:MIF的作用并非一成不變,不同腫瘤意味著不同的腫瘤微環境,不同腫瘤微環境下MIF的功能和活性發生變化,該現象可能與蛋白質的翻譯后修飾密切相關[7]。
3 MIF對TME中主要細胞的作用
免疫細胞是MIF對腫瘤產生影響的重要媒介之一。所有實體瘤都包埋在有免疫細胞參與組成的微環境中,如巨噬細胞和淋巴細胞;另外還有一些非免疫細胞,如成纖維細胞[11]。在TME中,有的免疫細胞如樹突狀細胞(DC)、自然殺傷T(NKT)細胞、CD8+/CD4+T淋巴細胞等被激活后會包圍腫瘤細胞,進行免疫殺傷,延緩疾病進展;而另一些免疫細胞如TAM、調節性T細胞(regulatory T cells,Tregs)、髓源性抑制性細胞(MDSC)等則會促進腫瘤生長、侵襲、血管生成并抑制抗腫瘤免疫反應[14]。因此,TME中免疫細胞的組成直接影響腫瘤的預后,富集T淋巴細胞的TME與較好的腫瘤預后相關,而富集TAMs的TME則與腫瘤預后不良有關[15-16]。
3.1 樹突狀細胞及效應T細胞 MIF作為促炎因子會增強DC的聚集和抗原提呈作用,激活巨噬細胞、T細胞和B細胞并抑制免疫細胞的壞死從而加強腫瘤區域的局部免疫;Brocks等[17]在皮膚癌模型中發現,從表皮到真皮的MIF濃度梯度利于抗原提呈細胞向真皮層聚集,對于皮膚組織募集抗原提呈細胞從而抑制腫瘤生成至關重要。
然而Balogh等[18]對乳腺癌的研究發現,MIF表達的喪失反而使得更多活化的DC聚集到原發腫瘤中,導致瘤內IFN-γ+的CD8+/CD4+T細胞豐度增加,強化免疫監視。Hsieh等[19]則發現在皮膚炎性反應中MIF可通過CD74和CXCR2特異性地觸發NKT細胞的趨化性從而增強炎性反應,同時,對MIF表達水平的抑制則會大大減少IFN-γ+NKT細胞的皮膚浸潤,減弱免疫活動。可見在不同的疾病模型中MIF的功能存在明顯差異,取決于不同疾病具體生理環境下的MIF是否可以增強免疫提呈及免疫殺傷。
3.2 腫瘤相關巨噬細胞 TAMs作為TME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具有高度可塑性,是腫瘤內免疫逃避、新血管生成、細胞外基質重塑和腫瘤細胞增殖失調的重要決定因素,對腫瘤的生長起到重要調節作用[20-21]。
TAMs分為具有促炎抗腫瘤功能的M1經典激活表型和促進腫瘤生長和侵襲的M2替代激活表型;TME中的單核細胞轉變為TAM并經過M2極化后可抑制T細胞的抗腫瘤作用,產生促瘤作用,因此,M2極化TAMs被認為是腫瘤啟動子而M1極化TAMs被認為是腫瘤抑制因子[22-23]。Yaddanapudi等[22]指出MIF在TAMs募集和極化中具有重要作用,其研究表明在小鼠黑色素瘤模型中MIF的小分子拮抗劑4-碘-6-苯基嘧啶(4-iodo-6-phenylpyrimidine,4-IPP)可減弱TAMs的替代激活(M2),削弱其免疫抑制和促血管生成作用,說明MIF在小鼠黑色素瘤模型中起到了促瘤作用。但Castro等[1]在對耐藥型膠質母細胞瘤進行抗血管生成治療時發現MIF的耗竭會導致腫瘤邊緣TAMs的增加以及M2極化的增強,從而促進腫瘤細胞增殖和侵襲性生長,提示MIF可能存在一定的抑瘤作用,且主要表現在抑制瘤體侵襲與轉移方面。
3.3 調節性T細胞 Treg細胞可抑制機體對腫瘤的免疫應答,誘導腫瘤特異性局部免疫抑制和耐受,極大地促進腫瘤的生長和轉移;而有研究顯示MIF的表達與腫瘤相關Treg細胞濃度呈顯著正相關[24]。
有研究對結腸癌小鼠的脾臟和腫瘤細胞進行流式細胞分析發現MIF基因敲除(MIF-/-)小鼠的腫瘤相關CD4+Tregs水平顯著低于野生型(MIF+/+)小鼠。研究表明MIF是通過上調IL-2的表達來增加Treg的產生從而促進腫瘤生長。而已知IL-2確實可擴增CD4+FoxP3+Treg細胞,介導免疫抑制和耐受[24-25]。
研究顯示Treg細胞可抑制T細胞的活化,進而抑制腫瘤免疫,該過程與細胞毒T淋巴細胞相關抗原4(cytotoxic T lymphocyte antigen 4,CTLA-4)密切相關,而CTLA-4在FoxP3+Treg細胞表面呈持續性高表達。研究發現針對CTLA-4的單克隆抗體伊匹單抗(ipilimumab)可明顯增強黑色素瘤患者體內抗腫瘤免疫反應并提高生存率[26],由此可推測MIF可能通過MIF/IL-2/FoxP3+Treg/CTLA-4通路發揮腫瘤相關免疫抑制作用。
3.4 髓源性抑制性細胞 MDSCs是具有免疫抑制性的、未成熟的髓樣細胞,可有效抑制自體T細胞增殖和IFN-γ的水平[27-28]。促進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和PGE2的釋放是MDSCs抑制T細胞功能的重要機制;而MIF對于MDSCs維持在免疫抑制表型至關重要,中和MIF或抑制MIF的表達會導致免疫抑制型MDSC向免疫刺激性樹突細胞(DC)樣表型的功能性逆轉[27-30]。
Mao等[30]指出MIF是調節環氧合酶-2(cyclooxygenase-2,COX-2)表達的重要因素,而MDSCs需要借助COX-2來發揮其對同源T細胞的抑制作用。研究還證明外源性重組前列腺素E2(prostaglandin E2,PGE2)可維持MDSC表面標志物的表達,抑制了MDSCs功能表型向DC轉化。由此猜測MIF調節MDSC功能的路徑之一是通過COX-2上調PGE2的表達從而維持MDSC的免疫抑制表型,MDSCs再通過引發更多ROS與PGE2的釋放發揮T細胞抑制功能,促進腫瘤細胞免疫逃逸。
3.5 內皮細胞 腫瘤的生長離不開新生血管,而內皮細胞(endothelial cell,EC)的增殖受多個細胞因子調控,其中包括MIF[31-32]。MIF可通過CD74的介導同時上調血管內皮生長因子(VEGF)和白介素8(IL-8)的分泌,且這種誘導呈劑量依賴性;而IL-8在各種腫瘤微血管形成中都起著重要作用[11,33]。
有研究指出EC會分泌高水平的MIF,它與腫瘤內微血管密度(intratumoral microvessel density,IMD)呈正相關,這對于血管內皮細胞的增殖極為重要;當MIF水平受限瘤體的微血管生成隨之受到抑制,這也是MIF抑制療法產生抗腫瘤作用的機制之一[32]。
缺氧可最終導致腫瘤進展已得到證明[34],其中缺氧促進瘤體新生血管生成的機制也與MIF密切相關。腫瘤組織在缺氧環境下會大量釋放缺氧誘導因子(hypoxia-inducible factor,HIF),HIF則能夠上調VEFG從而促進新生血管形成[35-36],在該過程中MIF起了重要作用。一項近期研究顯示缺氧可通過HIF-1α和HIF-2α多重誘導人微血管細胞-1(HMEC-1)中的MIF表達和分泌[31],結合MIF對IL-8及VEGF的上調作用,HIF作用于MIF/VEGF、MIF/IL-8/VEGF軸促進新血管生成可能是缺氧環境產生促腫瘤作用的機制之一。
3.6 成纖維細胞 腫瘤狀態下激活的成纖維細胞被稱作腫瘤相關成纖維細胞(cancer-associated fibroblasts,CAFs),是腫瘤微環境的主要組成之一,可對實體瘤的生長、侵襲起到重要促進作用。TGF-β作為CAFs的最主要調控因子可以誘導成纖維細胞的激活,從而使得腫瘤微環境中富集CAFs,促進腫瘤細胞的增殖和遷移[37-38]。
Xue等[39]在房顫相關研究中發現MIF可以通過上調TGF-β的表達促進心肌成纖維細胞增殖,參與心肌結構重建。Leung等[40]則在IgA腎病模型中發現MIF可以時間和劑量依賴形式上調腎組織的TGF-beta1水平,而抗MIF治療會阻斷這種促進作用。但是Heinrichs等[41]在慢性肝損傷模型中發現MIF可以通過CD74/AMPK(AMP-activated protein kinase)信號通路的介導減少肝臟組織的纖維化。而目前尚缺乏腫瘤狀態下MIF對TGF-β及CAFs影響的相關研究,因此,關于MIF對實體瘤纖維化產生影響的途徑研究亟待開展。
4 總結與展望
MIF作為腫瘤微環境的重要成員和調節者之一正受到廣泛關注和研究,關于它對腫瘤細胞的作用存在分歧。眾多研究指向MIF可影響腫瘤微環境中的免疫細胞構成、上調VEGF水平、削弱局部免疫反應、促進新生血管產生,從而發揮促瘤作用;但隨著研究的深入也有學者提出某些腫瘤模型中MIF可能存在抑瘤作用,與VEGF相似,既有促血管生成的作用也有抗侵襲效果。
究其原因:(1)因為腫瘤微環境中其他細胞及細胞因子會影響MIF對免疫細胞的作用,而不同腫瘤、不同階段意味著不同的腫瘤微環境;(2)MIF與腫瘤進展之間可能存在量效關系,極限濃度的MIF對腫瘤產生的總體影響可能相反;(3)腫瘤細胞來源的MIF和免疫細胞/基質細胞來源的MIF可能經歷不同的翻譯后修飾,使得它對腫瘤細胞或其微環境產生不同的作用。
綜上所述,MIF對TME的作用復雜多變,假如能明確哪類TME下MIF表現為免疫抑制功能,在治療擁有該特征TME的惡性腫瘤時有選擇地利用MIF拮抗劑就能夠對TME進行定向調控,從而產生重要治療意義和廣闊的臨床應用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