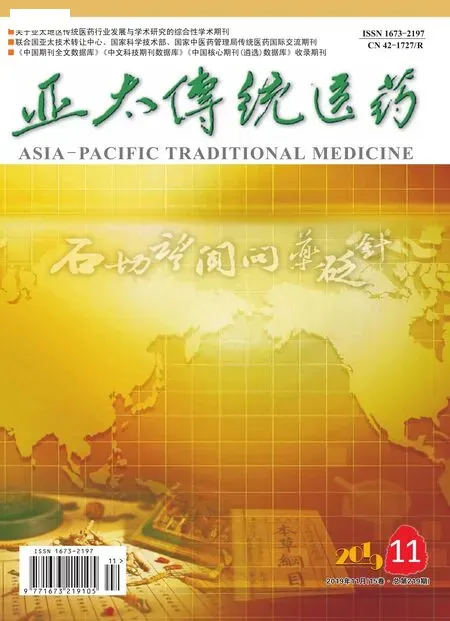基于血脈理論辨治慢快綜合征
陶燕楠,楊 潔,楊傳華*
(1.山東中醫藥大學 中醫學院,山東 濟南 250014;2.山東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 心內科,山東 濟南 250011)
慢快綜合征是病態竇房結綜合征的一個亞型,是指緩慢型心律失常與快速型心律失常交替出現的一種病癥。動態心電圖表現為陣發性心房顫動、陣發性心房撲動或房速發作前為竇性心動過緩、竇性停搏或竇房傳導阻滯,通常認為前者是后者的繼發癥。本病的危險性在于,無論是過長時間的心臟停搏或者過快的心動過速,都會造成心排血量在短時間內急劇下降,從而造成嚴重腦缺血、意識喪失或者暈厥,存在嚴重的阿斯綜合征的發作風險。西藥中抗心律失常藥物有一定的負性肌力、負性傳導以及負性頻率作用,除可應用于有明確適應證患者安裝心臟起搏器后的治療之外,目前西醫并沒有較好的治療措施[1,2]。但是中醫藥辨證論證慢快綜合征在臨床上卻取得了良好的療效[1],凸顯了中醫藥辨治的獨特優勢。
慢快綜合征病位在心,體現在脈,臨床可見遲脈、結代脈、極脈和急脈,屬中醫“脈遲證”“心悸”“厥證”等范疇。《素問·五臟別論》記載:“腦、髓、骨、脈、膽、女子胞,此六者,地氣之所生也,皆藏于陰而象于地,故藏而不瀉,名曰奇恒之腑。”中醫認為“脈”不單單是一種形態結構,而是獨立于其他臟腑的器官。《瀕湖脈學》有云:“脈乃血脈,氣血之先,血之隧道,氣息應焉。”血脈是一個涵蓋氣血經絡的整體系統,是運行氣血的通道。《黃帝內經》中“血脈”一詞共出現40次之多,其中對“血脈”的含義、關系、生理、病理及相關血脈病變進行了詳細論述,為后世理解和應用“血脈理論”提供了有力的依據。近年來,隨著“血脈理論”的不斷發展,中醫對于慢快綜合征的辨治有了新的思路。
1 “血脈理論”指導下對慢快綜合征的認識
1.1 “血脈理論”的內涵
《內經》言:“夫脈者,血之府也。”《靈樞·決氣》:“壅遏營氣,令無所避,是謂脈。”《內經》中已明確指出,血脈是氣血運行的通道。《靈樞·癰疽》曰:“血脈營衛,周流不休。”《靈樞·平人絕谷》言:“血脈和利,精神乃居。”《靈樞·天年第五十四》曰:“血脈和調,肌肉解利,皮膚致密……故能長久。”血脈貴在和利,血和脈相互協調,循環于周身,共同維系機體的康健。《素問·六節臟象論》曰:“心者生之本……其充在血脈。”《素問·痿論》曰:“心主身之血脈。”《素問·平人氣象論》曰:“心藏血脈之氣。”這些論述充分說明血脈是一個涵蓋氣血經絡的整體系統,為心所主,心氣推動血液在脈中運行,正所謂“血者濡也”“脈者瀆也”“心主血脈”,心、血、脈共同構成循環于周身的血脈系統。
1.2 慢快綜合征的病因病機
現代醫學認為,本病多發于老年人,當竇房結存在纖維化、脂肪浸潤硬化與退行性改變、淀粉樣變性、竇房結缺血、感染或者竇房結周圍神經及心房肌病變等基礎病變時,竇房結的起搏和傳導功能受到影響,產生了嚴重竇緩、竇性停搏、竇房阻滯等緩慢型心律失常。而對于快速型房性心律失常的發生原因,有些學者認為可能是肺靜脈和腔靜脈內肌袖異常的電活動驅動和觸發心房所引起[3],但具體原因目前尚未有明確結論。
中醫認為,本病病機復雜,但概括起來不外乎本虛與標實兩方面,虛乃氣血陰陽虛衰,實為痰濕、瘀血。《素問·痹論》指出:“脈痹不已,復感于邪,內舍于心。心痹者,脈不通,煩則心下鼓。”《瀕湖脈學》有云:“遲而無力定虛寒,代脈都因元氣虛,結脈皆因氣血凝。”據少量文獻報道,慢快綜合征作為病態竇房結綜合征的一個亞型,大多數學者認為,二者在病因病機上極其相似,可以概而論之。張大煒[4]認為本病在緩解期和發作期病機不同,由此將本病病因病機分而論之。李紹波等[5]研究認為,本病快速型心律失常期的病因病機為氣血陰陽皆虛,炙甘草湯可降低心臟的自律性,從而起到抗心律失常的作用。
《內經》云:“人之所有者,血與氣耳。”基于“血脈理論”的內涵指導,心、血、脈三者不可分割而論,言脈者,必不離心;言心者,必不離血。筆者導師楊傳華[6]認為,“脈”作為奇恒之腑,其榮衰隨人之“生、長、壯、老、已”的規律而發生變化,取決于腎精及腎氣的盛衰,因此,本病主要責之于心腎兩虛、血脈瘀阻。腎為先天之本,腎氣充沛,腎精充足,心腎相交,水火既濟,方可維持各臟腑的正常生理機能。心主脈,心氣推動和調控心臟的搏動和脈的舒縮,令脈道通利,血流通暢。氣主煦之,血主濡之。氣為臟腑組織的生理功能,“百病生于氣”,心氣充沛,心臟得以有規律的搏動,脈道得以有規律的舒縮。若心氣不足,鼓動無力,或陰虛血少,脈無以充,則心搏遲緩無力,氣血運行不利,脈道舒縮功能受限,血行滯緩,或痰濕、瘀血阻滯經脈,則脈或緩慢,或結代;病久陽損及陰,氣陰兩虛,陰虛生熱,或血脈瘀阻,瘀久化熱,則出現疾脈或促脈,陰陽虛極將脫則可見脫脈。
2 基于“血脈理論”辨治慢快綜合征
本病因脈律慢快不一而定其名,其病因病機在緩解期與發作期存在明顯不同,故須分而論之。
2.1 緩解期的治療
2.1.1 溫通心陽,活血復脈 氣主煦之,血主濡之。心陽虛衰,血脈失于溫運,則見胸悶胸痛、心悸氣短、頭暈乏力等癥,舌質紫暗或有瘀斑,脈緩而澀,是為心陽不振,血脈瘀阻證。臨證可選桂枝甘草湯合血府逐瘀湯,桂枝甘草湯出自《傷寒論》,僅由桂枝和甘草兩味藥組成,是仲景先師用以溫養心陽的基礎方。若無寒象,屬心氣虛;若兼見四肢發涼怕冷,但無全身畏寒者,屬心陽虛。偏于心氣虛者可加黨參、黃芪;偏于心陽虛者可加附子。
2.1.2 益氣養陰,活血復脈 心氣陰兩虛,血脈瘀阻,臨床可見心悸、乏力、氣短、口舌干燥,舌質暗紅,脈澀。針對這些證候的代表方劑為生脈散合丹參飲。生脈散首見于《醫學起源》,由人參、麥冬、五味子構成,方中人參味甘微苦,性微溫,入心、脾、肺經,可大補元氣,生津,安神益智,既可益氣又可養陰,臨證若兼見熱象,脈細數者,則用甘平之太子參代替,以益氣生津而兼清熱;麥冬味甘,性微寒,入心、肺經,可養陰生津;五味子味酸、甘,性溫,歸肺、心、腎、脾經,功能益氣滋腎、生津、安神,味酸能斂,故又可止咳、止汗、止瀉、澀精;丹參飲首見于清代陳修園的《時方歌括》,由丹參、檀香、砂仁構成,是化瘀行氣止痛之良方。兩方合用,共奏益氣養陰、活血化瘀之功。楊傳華老師臨證亦善用此法辨治慢快綜合征,療效顯著。
2.1.3 溫補心腎,活血復脈 腎陽為諸陽之本,腎陽虛衰,則心陽亦不足,或心陽久虛不復,亦可累及腎陽,正所謂“五臟之傷,窮必及腎”。然“五臟之傷,以腎為重”,故腎陽虛衰證病情較重。心腎陽虛的主要癥狀有畏寒肢冷、耳鳴耳聾、心悸胸悶、智力減退、精神疲憊、小便清長或夜尿頻多,舌淡少苔,脈多見沉遲而弱。臨證可用桂枝附子湯合生脈散加黃芪、丹參治療。桂枝附子湯出自《傷寒雜病論》,由桂枝、附子、生姜、大棗、甘草組成,合生脈散有溫陽益氣之功,丹參活血化瘀,暢通心脈,共奏溫陽益氣、活血散寒之功。現代藥理研究表明,丹參能增加冠脈微循環、改善血黏度,有利于改善竇房結、房室及室內傳導,具有提高心率的作用[7]。
2.2 發作期的治療
2.2.1 活血清熱,育陰復脈 心腎陽虛日久,心失滋養,水火不相濟,造成氣陰兩虛,陰血不足,氣血運行不利而致血瘀,瘀久則化熱,熱擾心神,迫血旺行,故見脈來疾數,口干咽燥、手足心熱、舌苔薄黃,均為陰虛化熱之象。本證屬虛實夾雜,臨證時可選用血府逐瘀湯合生脈散加龍骨牡蠣化裁運用。血府逐瘀湯出自王清任的《醫林改錯》,藥物組成有桃仁、紅花、當歸、生地黃、牛膝、川芎、桔梗、赤芍、枳殼、甘草、柴胡,全方以桃仁、紅花為君藥,輔以理氣、理血藥,功以活血化瘀、行氣止痛為主,此時生脈散中人參選用太子參代替,既可益氣養陰又可清熱,加以龍骨牡蠣鎮靜安神、定志復脈,共奏活血清熱、育陰復脈之功。研究表明,生脈散加龍骨牡蠣對氣陰兩虛型大鼠心悸心神不寧證有一定的療效[8]。
2.2.2 回陽救逆,固脫復脈 《內經》有云:“陰者藏精而起亟也,陽者衛外而為固也。”陰陽互為根本,相互依存。若陰陽互損日久,臟腑虛極,血脈鼓動無力,氣機升降無由,則可出現陰陽決離、氣血逆亂的離經之脈,證見心悸,氣不足吸,神疲蜷臥,意識障礙,雙目上視,四肢逆冷。臨證唯有從陰引陽,從陽引陰,方可固脫復脈,選方可用鎮陰煎(熟地、牛膝、甘草、澤瀉、肉桂、附子)。《景岳全書》云:“陰虛于下,格陽于上,則真陽失守……六脈細微,手足厥冷……速宜此法,使孤陽有歸,則血自安也。”故張景岳以此方回陽復脈,可資借鑒。
3 結語
綜上所述,慢快綜合征病因病機主要是氣血陰陽虛損,血脈瘀阻,臨床需分期分型辨治。“血脈理論”作為整個心腦血管疾病的辨證論證理論基礎,其內涵值得每個中醫學者細細鉆研。從“血脈理論”認識慢快綜合征有助于“血脈理論”的不斷發展,更有助于明確慢快綜合征的病因病機,從而準確辨證論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