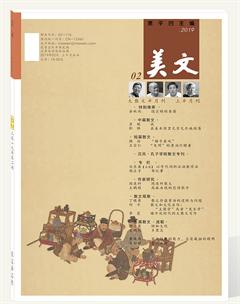媒介化時代的大散文寫作
無論在何種意義上說,今天這個時代都是一個被高度媒介化的時代。社會被媒介化了、文化被媒介化了、生活被媒介化了,人本身也被媒介化了。媒介從一種工具論意義上的信息傳播載體,正在成為本體論意義上的信息本身。本文認為,媒介化時代最重要的表征就是個體主體性的全面復活,每個人不僅僅是信息的接受者,更是信息的創造者和傳播者。在這樣一個時代情景中,人們似乎應該重新認識二十五年前《美文》創刊時,賈平凹主編所提出的“大散文”概念了。
一
二十五年前,賈平凹提出“大散文”概念時(賈平凹最早提出“大散文”是在《美文》創刊號的“發刊詞”中,《美文》創刊的時間是1992年9月),中國尚未接入互聯網(中國接入互聯網時間是1994年),更無博客、微博、微信、facebook、Twitter、抖音之類的玩意兒,更談不上移動互聯和自媒體。中國作家的寫作整體上還處于手書時代,所有的作品尚需通過報刊和書籍來發表。因此,賈平凹的“大散文”概念之于傳統散文而言,僅指文風的刷新(“鼓呼掃除浮艷之風,鼓呼棄除陳言舊套”)、內容的拓展(“鼓呼散文的現實感、史詩感、真情感”)和作者身份的擴容(“任何作家,老作家、中年作家、青年作家、專業作家、業余作家、未來作家、詩人、小說家、批評家、理論家,以及并未列入過作家隊伍,但文章寫得很好的科學家、哲學家、學者、藝術家等等”),而在當時看來并不重要的散文傳播媒介的變革,以及由此帶來的個體主體性的全面覺醒,還不可能提到議事日程中來,盡管當時創辦的《美文》本身就是在添加一種新的散文傳播媒介。
應該說,賈平凹提出“大散文”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對20世紀90年代成為“散文的時代”(李震《散文的時代》,載于《文學自由談》1993年第2期)發揮了重要作用。但20世紀90年代的媒介生態與文學格局決定了當時的散文尚處于文學創作、生產、傳播與消費的傳統流程之中。因此,大散文概念的提出在當時只能是對既有的散文局面的一種拓展和翻新,而在今天看來,卻是對真正大散文時代到來的一種預言和預演。
筆者認為,真正的大散文時代到來的機緣,是媒介化帶來的個體主體性覺醒與散文文體特征的契合。
一方面,以移動互聯網和博客、微博、微信等為標志的自媒體的大面積出現,使寫作與發表成為公眾的一種日常生活和自主權力,進而使每個寫作者個體的主體性得以實現。媒介化時代被稱為“眾聲喧嘩”的時代,人人都有寫作權、發言權、發表權;另一方面,散文在各種文體中本來就是一種大眾化的自由文體。讀過小學的人都寫過散文,每個讀書人都是從寫作文開始的。按照大散文的說法,學生作文當然屬于散文的版圖(盡管不一定是美文),再加上散文的寫作本來就是用來書寫日常生活和平常心態的。因此可以說,人人都是散文作家。
如此,在一個人人都有寫作權、發言權、發表權的時代,一種人人都可以動用的文體會創造何種景觀就可想而知了。真正的大散文時代由此到來了。
今天的“大散文”之大,大到不僅溢出了幾本有限的散文期刊、報紙副刊,而且充滿了博客、微博、微信和千百萬計的各類朋友圈、網絡論壇、網絡社區。“大散文”之大也不僅僅是指數量之大,還應該指類型之廣博、內容之豐富、作者群和讀者群之空前龐大,更應該指散文的寫作已經成為普通公眾的一種日常生活方式。
二
面對媒介化時代大散文概念的變異與散文寫作的公眾化、日常化趨勢,散文理論批評界和專業散文作家應該何為,正在成為一個需要深入討論的問題。
在討論這一問題之前,必須首先確立一個共識,那就是:媒介化時代公眾化的大散文寫作是中國散文發展的全新歷史進程和重要資源。這種資源是公眾智力的一種聚合,盡管魚龍混雜、良莠不齊,但無法否認,其中包含了大量可以推動散文發展的語言智慧和生活內容,也包含了大量精彩的散文篇什和審美元素。這些都是需要專業散文作家去關注、借鑒和學習的。
同時,還必須明確一種意識,那就是在散文寫作公眾化的時代,看似人人都會寫散文,散文寫作日常化、生活化,寫散文似乎越來越容易,但對于專業作家來說,散文寫作越來越難了。常識告訴人們,最容易的往往是最難的。而且在總體上,少數專業作家要超越公眾智慧,也是不可能的。在現實中,一篇散文要在浩若煙海的公眾寫作中脫穎而出,表現出與眾不同的專業性,比在專業作家獨領風騷的年代更加不易。
公眾寫作與專業寫作,公眾寫作者與專業作家,盡管在散文領域很難找到明確的分界線,但專業作家的寫作之所以能夠獲得更多公眾的關注,而被稱為專業寫作,理由恐怕不是專業作家的寫作每一篇作品都高于公眾寫作的任何一篇作品,而是專業作家對自己的寫作有更高的要求。
三
專業散文作家應該比公眾寫作者有更加自覺的文體意識。公眾寫作多是隨感隨性隨情景而發的。網絡環境和“微”語境中的寫作者往往并不認為自己是在寫散文,而是對某些感知、情緒、沖動和所思所想的自然表達和宣泄。專業作家則不然。當一個作家在寫一篇散文時,一定不會不知道自己是在寫散文。盡管他會力求物我兩忘,但他一定是在千方百計地要寫出一篇好散文來。這個時刻,決定一個作家能夠寫出一篇好散文的,除了他的專業素養、寫作經驗外,最重要的便是他比公眾更自覺的文體意識。散文文體意識的自覺會表現為一個作家對散文文體特性的深度認知和理解,對散文語言方式的自覺把握,以及由此自然生成的寫作的自律性。
所有文類都是按照某種審美品質和審美方式生成的,即使在公眾寫作中也是如此。所不同的是,在公眾寫作中,審美的意識畢竟被淡化了,泛化了。對此,專業作家的寫作應該自覺凝聚審美意識,凸顯審美品質,寫出具有審美獨異性的美文來。只有如此,專業作家的散文寫作才能夠在公眾寫作中具有顯示度。
審美意識其實也是一種公共意識,每個人都在一定程度上具備一些審美意識,但對文學而言,審美不僅要追求品質,更要追求獨異性。即使在同一審美品質,或同一美學類型中,真正優秀的作品在審美上必須是獨異的。同是書寫性靈的散文作家,林語堂主要是在思想中見出性靈的,張愛玲主要是在日常生活情趣中見出性靈的,孫犁、賈平凹則多是從自然山水中見出性靈的。
公眾寫作的時代是一個蕪雜、煩躁、喧囂和表面化的時代。每一個人似乎都在繁忙中奔走,在繁忙中寫作,在繁忙中完成自己的人生。忙,在漢字中屬于形聲字,從“忄”,從“亡”。“忄”即“心”,指“神志”。“亡”即“死亡”,指“喪失”“消失”等。因此,忙的意思就是“心死了”,也就是心靈停止感悟了。如此說來,繁忙的人是不具備心靈體驗的。而作為一個散文作家,如果沒有了心靈體驗和感悟,還談何寫作,談何散文?在這個意義上說,公眾寫作時代,專業散文作家最難能可貴的,是棄絕嘈雜,寧心靜氣,自覺進入心靈的深度體驗,小則在日常生活中寫出個人獨異的審美品質來,大則去感知時代和民族的脈動,寫出一個時代或一個民族獨異的審美品質來。
在所有的文體中,散文是離作家真實的日常生活最近的一種文體。一個專業的、優秀的散文作家必須自覺地去感悟生活、研究生活,感悟生活中的每一個細節,研究生活的來龍去脈。所幸的是,今天這個公眾寫作的時代,是一個生活發生巨變的時代。物質的極度膨脹,媒介的無孔不入,各種新型生活元素的出現和國際化進程的加快,都在劇烈地沖擊著人們的傳統生活秩序,都在為散文展示出空前龐大的審美空間和表現空間。這也是公眾化大散文寫作眾聲喧嘩的一個內在原因。
就在賈平凹提出大散文概念的時候,中國散文界出現了所謂文化散文的熱潮。時至今日,散文作家和公眾寫作者中,用散文談文化者,不僅絡繹不絕,而且越來越多。而文化,這個當代最熱的熱詞,到底在何種意義上可以作為散文書寫的對象,則很少有人問津。在經常看到的一些所謂文化散文中,似乎作家們樂于以文化研究專家自居,或以文物鑒定專家,或以考古學家等等職業文化研究專家的身份投入寫作。這一定是一個誤區。作家就是作家,與文化學者、文物鑒定專家、考古學家有著本質區別,而且也遠不具備這些專家的專業知識和專業素養,如果自擬為專家,用散文去做一些偽研究、偽鑒定、偽考古,不僅會誤導讀者,而且也會壞了專業行情和自己的名聲。那么,是不是一個散文作家就不可以書寫文化呢?當然不是。文化當然是散文書寫的一個巨大而且重要的領域。問題是作家不是文化研究專家。作家對文化的書寫只會是在品味、感知和穎悟層面上的,或者是在修辭層面上的,而非理性層面上的。即使是在理性層面上,也是在哲理,而非學理意義上的。作家應該是在用自己的心靈去感知文化、用自己的語言和敘事去呈現某種文化,而不是在研究文化。即使作家的寫作中涉及某些具體的文化信息,譬如歷史年份、歷史人物、名勝風物、文物古跡等等,那也只是作家的感知對象,作者可以通過自己真切的感知,悟到某種文化之上的情致和韻味,而非得出某種學術結論。用一個比方來形容這種區別,如果說文化是一塊金子的話,那么文化研究專家所完成的是關于這塊金子的物理學、材料學分析,而作家所完成的則是對這塊金子的造型、色彩和光芒的感知和描述;文化研究專家抵達的是實體,而作家抵達的則是這種實體所引發的精神反應。同時,還必須認識到,一個作家的語言方式、感知方式、作品形態,本身就是在呈現某種文化。而這種文化絕不是作家研究出來的,反倒是文化研究專家的研究對象。在這些意義上說,當今的專業散文作家應該靜心用自己的心靈去感知文化、體悟文化,并用自己的語言去呈現文化,用自己的作品去表達某種文化精神,而不是去做偽研究、偽堅定、偽考古。
四
今年是《美文》創刊,暨“大散文”概念提出25周年。當此之際,作為《美文》的讀者和作者,自然會有諸多感慨和感想。如欲歸納之,則當是,當年《美文》主編賈平凹以“大散文”的說法,本來就助長了散文這種人人可寫,卻又很難寫好的文體之自由本性。如今,這種無拘無束的大散文,又遇到了這個人人有寫作權、人人有發言權、人人有發表權的媒介化時代,散文便越發成為一種公眾化的文體。而公眾化并不是讓專業散文寫作變得更加容易,而是變得更難了。于是便提出專業散文作家要加強文體自覺、凝聚審美獨異性、注重深度體驗、研究日常生活、感悟并呈現文化精神等諸種建議。如果這些建議還有一定合理性的話,如果中國的專業散文作家果然能從上述方面發力的話,那么媒介化時代的大散文,整體上有望書寫出一部當代中國人的心靈史、一部當代中國人的日常生活史、一部精神層面上的活的中國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