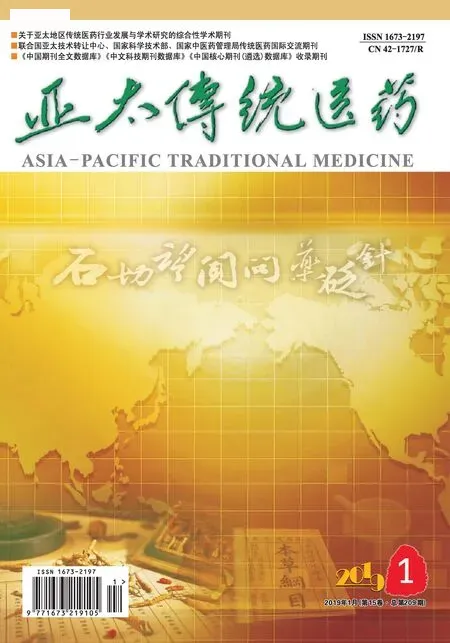黃古葉教授運用五苓散治療泌乳癥臨床經驗
,, , ,,
(1.廣西中醫藥大學,廣西 南寧530001;2.廣西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廣西 南寧 530023)
泌乳癥多見于高催乳素血證或粉刺性乳癰。高泌乳素血證[1]典型表現以高泌乳素為特征,是一種以溢乳、月經紊亂、不育、頭痛等為臨床特征的疾病。西醫常首選麥角胺類進行治療,雖有一定的療效,但副作用較大,停藥后容易復發。粉刺性乳癰[2]是一種以乳腺導管擴張且漿細胞浸潤為病變基礎的慢性非細菌性乳腺炎癥性疾病。此病的特點是好發于非哺乳期或非妊娠期婦女,常有乳頭凹陷或者溢乳。初起時腫塊多位于乳暈部,化膿破潰后膿中夾有脂質樣物質。易反復發作,形成瘺管,經久難愈,患者全身炎癥反應較輕。在西醫治療上,主要以手術為主,很難根治,易反復發作,病程長。
據報道,中醫治療泌乳癥療效確切,但傳統的臟腑、氣血、陰陽、三焦等辨證較復雜,標準不一,不易掌握,療效不顯著。胡希恕先生所著《經方傳真》有言:“執一法,不如守一方。”這充分說明方證辨證的重要性。
黃古葉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從事中醫臨床工作二十五載,熟讀經典,倡導“中醫傳承,經典先行”。以經典為基礎,倡導方證對應,根據“方證對應”的理論,善于運用經方治療臨床各種疾病,指導臨床實踐,現將黃師運用五苓散治療泌乳癥的經驗介紹如下,為中醫臨床治療泌乳癥提供參考。
1 病案舉隅
患者李某珍,女,39歲,已婚,發病時未在妊娠期及哺乳期,于2017年2月28日初診。現病史:患者雙側乳房脹滿1月。自訴1月前無明顯誘因出現雙側乳房脹滿,無疼痛,可擠出清稀透明樣液體,無鮮血流出,無紅腫,無腰酸乏力,無自汗出,納寐可,二便調。遂到廣西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就診,查性激素六項未見異常,未予處理。其后到當地醫院就診,再次查性激素六項:FSH:6.33mIU/mL,LH:6.55mIU/mL,PRL:6.55mIU/mL,PRL:137.11μIU/mL,EST:0.29ng/mL,E2:37.1pg/mL,PROG:0.27ng/mL,均正常。乳腺彩超未見異常。為求中醫治療,患者遂至我院肝病二區門診就診,刻下:雙側乳房脹滿,無疼痛,可擠出清稀透明樣液體,口干欲飲,晨起口苦,無腰酸乏力,無自汗出,納寐可,二便調。查體:有神,形體肥胖,雙側乳房軟,乳頭正常,未見破潰,未捫及包塊,無觸痛,擠壓可見乳頭滲出清稀透明樣液體,未見膿血。舌質淡紅,舌體胖大,苔白潤,脈沉細。既往史:無特殊。月經史:初潮14歲,28~30天一行,經期5~7天 。中醫診斷:泌乳癥;中醫辨證:蓄水證。黃古葉教授予五苓散方加減,處方:澤瀉10g,豬苓10g,白術10g,茯苓20g,桂枝12g,柴胡12g,川芎12g。制成免煎顆粒,14劑,1劑/d,每次開水沖150mL,分早晚兩次溫服。
患者連服14副,上述癥狀均除。隨訪兩月,患者述乳房脹滿等癥狀已消失,雙側乳房未見異常分泌物。
按:泌乳癥中醫并無記載,根據其臨床表現,可歸屬于“乳泣”“閉經”“粉刺性乳癰”等病證[2,3],可表現為未在哺乳期而乳房分泌出乳汁樣液體,雙側乳房脹痛。黃古葉教授認為此病多屬于“真水不足,客水為患”,患者多出現口渴,小便不利,伴或不伴煩躁。舌質淡紅或淡白,舌體胖大,邊有齒痕,苔薄白或薄白潤,脈沉細,屬于五苓散證。王晶[4]著《五苓散條文辨析》認為“五苓散證,水邪為患”,水邪為患,變動不居,可停留到機體任何部位[2]。太陽蓄水,膀胱氣化不利,水不下輸,津不上布,客水為患,變動不居,可停留到機體任何部位,蓄于上可致“吐涎沫而癲眩”“臍下有悸”;蓄于中則見“心下痞”“水入則吐”;蓄于下則見“小便不利”。黃教授認為乳房為足厥陰肝經所主,太陽蓄水蓄于上,困遏肝經,肝失之調達疏泄之職,則上為乳汁外泄,乳房脹。
在治則治法上,黃教授根據“方證相應”的思想,認為泌乳癥多屬于五苓散證,治當“溫陽化氣,利水滲濕”為法,基本方選五苓散,隨證加減。
2 討論
五苓散出自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是治療蓄水證的經典名方。根據《傷寒論》,五苓散方證可總結如下:口渴,小便不利,伴或不伴煩躁;舌質淡紅或淡白,舌體胖大,邊有齒痕,苔薄白或薄白潤,脈沉細。
本病案中,結合病史、體征及其舌脈象:舌質淡紅,舌體胖大,苔白潤,脈沉細,辨病屬泌乳癥,辨證當屬“蓄水證”。除雙側乳房脹滿外,患者兼有口干欲飲,晨起口苦,考慮合并少陽證。方選五苓散加柴胡、川芎。五苓散是治療太陽蓄水證的名方,其病機是三焦氣化不利,取“苓者,令也,能行肺,利三焦,以至于膀胱”之意,即“五苓散者,通行津液,克伐水邪,以行治節之令也”。
方中澤瀉為君藥,《神農本草經》云:“澤瀉味甘寒,主風寒濕痹,乳難消水,能行水上。”《素問·逆調論》云:“腎者,水臟,主津液。”可見腎具有主持和調節人體水液代謝的功能。膀胱氣化實際上隸屬于腎臟氣化之功。本方取其甘淡,直達腎與膀胱,利水滲濕。臣以豬苓、茯苓之淡滲,增強其利水滲濕之力。根據《神農本草經》,豬苓味甘平,解毒蠱;茯苓味甘平,主口焦舌干,利小便。兩藥合用,淡滲之功甚佳;白術味苦溫,主治濕痹,有健脾益氣、燥濕利水之效,故佐以白術、茯苓健脾以運化水濕;桂枝味辛溫,有溫通絡之功,本方取其溫陽化氣以運化水濕;柴胡性味苦平,主心腹,去腸中結氣,飲食積聚,寒熱邪氣,推陳致新,具有和解表里、疏肝利濕的功效。黃煌[5]在《中醫十大類方》中提到“柴胡證”,柴胡證由兩部分組成:①胸脅苦滿;②往來寒熱或休作有時。“胸脅苦滿”是柴胡證的必見指征,女性乳房脹痛、結塊也包括在內,中醫傳統所說的胸脅苦滿主要指自覺癥狀。柴胡帶包括胸脅部、肩頸部等,以軀體側面為主。本案患者雙側乳房脹滿,屬于柴胡帶范疇,故本方加用柴胡疏肝利濕。《本草匯言》記載:“川芎為血中氣藥,上行頭目,中開郁結,下調經水。”雖入血分,又能去一切風,調一切氣,有行氣開郁之效。全方淡滲利水、健脾運濕與下調經水相結合,共奏化氣利水之功。
3 結語
黃古葉教授遵從經典,踐行“方證相應”思想,平時十分善于運用經方治療各種疾病。“方證”是指用方的依據,即經方應用的證據,可包括證候群、體質、體征等。林億在《金匱要略論序》中也明確提出:“嘗以對方證對者,施之與人,其效如神。”方證的基礎是人,辨體與辨病同時進行,注重整體,關注當前。方證較之證型更為直接,易于掌握。黃教授運用五苓散治療泌乳癥充分體現了“方證相應”“有是證,用是方”的思想。
黃教授認為,經方用藥優勢顯著,其優勢有三:①經方藥物組成較少,有利于理解經方的結構,觀察臨床療效;②經方使用的藥物大多為常用藥,以植物藥居多,還有處方藥味少、價格比較經濟的優點;③經方治病的基本原則是方證相應,如《傷寒論》16條“觀其脈證,知犯何逆,隨證治之”及317條“病皆與方相應者,乃服之”。
綜上,根據“方證相應”思想,黃教授運用經方之五苓散治療泌乳癥,療效確切,為中醫臨床治療泌乳癥提供了重要參考;同時也為進一步了解五苓散方證,為中醫經典及方證與泌乳癥的相關研究積累了更多循證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