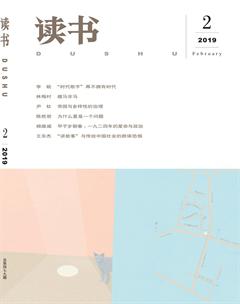作為社會記憶的夏文明
陳民鎮(zhèn)
由于尚未發(fā)現像甲骨文那樣系統(tǒng)性、自證性的文字材料,雖然地域上相當于夏墟、時間上相當于夏代的考古遺存已有較豐富的發(fā)現,但這些遺存是否與夏朝有關,仍有部分國內外學者質疑。與此相應,不少公眾對文獻中的夏代史事心存疑慮,公眾對考古學者與歷史學者的信任亦遭遇一定的沖擊。
有人說,夏朝只是神話,出自后人虛構;有人說,夏朝屬于信史,有關夏朝的史事基本可信。李曼在他的新書Soial Memory and StateFormation in Early China(《問鼎:早期中國的社會記憶與國家起源》)中則從社會記憶的角度對夏文明進行了重新解讀。
該書的核心內容此前已作為《重返夏墟:社會記憶與經典的發(fā)生》一文在《考古學報》二〇一七年第三期發(fā)表,引發(fā)較大反響。而新出的英文著作,則以更詳盡的論述呈現了從公元前三千紀晚期到兩千紀中期、早期中國的壯麗圖景。翔實的考古材料、前沿的理論視角、宏大的全球視野成為該書的基本旋律。
該書最引人注意的莫過于引入了“社會記憶”的范疇,以及以“高地社會”和“低地社會”來區(qū)分歷史地理單元。我們目前所知的夏朝信息,都出自周人追述,屬于周人社會記憶的表達。從西周的豳公盈、清華簡《厚父》到其后的《左傳》諸書,乃至戰(zhàn)國時代諸子的言說,對夏朝以及大禹事跡均多有稱述。周人的這種追述是否像陳夢家、楊寬、艾蘭(Sarah Allan)、陳淳等學者所說屬于神話的轉化,抑或確有其史實之素地呢?質疑夏朝的學者并無直接的證據否定夏朝,承認夏朝的學者也沒有一錘定音的材料說服質疑者,夏朝有無的問題似乎陷入了僵局。王國維根據《史記》中殷商世系為甲骨卜辭所證實,推論“由殷周世系之確實,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確實,此又當然之事也”(《古史新證》),在許多人看來顯然并不“當然”。
近來另一本關于夏史的專著——孫慶偉的《鼐宅禹跡——夏代信史的考古學重建》無疑是主張夏史為信史的。該書認為,考古學作為一門學科,不可能把自身的研究基礎建立在那些可遇不可求的遺跡遺物之上;在探索夏文化的過程中,刻意追求文字一類的證據,實際上是對考古學研究方法的不了解和不信任。
孫著就夏文化展開了系統(tǒng)性的考論,但由于在研究方法上并沒有完全超越前人,故仍未能打消一些讀者的疑慮。《問鼎》一書則擺脫了文獻的束縛,轉而從考古學出發(fā)梳理從良渚文化到商周的文化嬗替軌跡,從中發(fā)現了文化脈絡中的連續(xù)性以及斷裂之處。周人所追述的夏朝主要呈現出以下幾個層面:圣王紓解水患,奠定早期王權;冶金發(fā)端,青銅禮器成為王權的象征;以晉南、伊洛為中心的中原王朝的政治空問格局;禹跡天下觀。這幾個層面,都可以在龍山時代以及二里頭時期的考古發(fā)現中得到呼應。尤其是以晉南、伊洛為中心的政治空間格局,作為傳說中夏朝的核心區(qū)域,在龍山時代和二里頭時期盛極一時,卻在殷墟時期衰落。殷商王朝相繼放棄早商在關中、晉南、洛陽盆地、淮河流域以及長江中游設立的據點,晉南盆地幾乎成為一個無人區(qū),洛陽盆地也不再有大型聚落。這似乎反映了一種文化的斷裂現象。正是這種斷裂,暗示了另一種記憶連續(xù)性的可能。由于商人的勢力范圍存在其局限性,位處殷商勢力邊緣地帶的黃土高原、晉南、伊洛和關中,政治與文化更為多元,并無可能完全接受商人所創(chuàng)造的歷史神話。晉南、伊洛曾經的政治實驗以及由此確立的共同價值,卻有可能通過高地社會的族群傳承,并成為周人建國敘事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李曼看來,高地記憶群體與殷商王室史官一道,成為周人多元歷史知識的直接來源。周人首先一統(tǒng)關中盆地作為根據地,繼而占領晉南、伊洛的夏人故土,最后則征服東方的商王朝腹地,其后所推行的封建制度正是圍繞夏、商、周三代空間架構完成的。周武王選擇在洛陽一帶建立成周,以“宅茲中國”(何尊銘),便是基于“自洛、衲延于伊、衲,居陽無固,其有夏之居”(《逸周書·度邑解》)的社會記憶。這表明周人亟欲重拾商代以前的政治傳統(tǒng),通過回歸以洛陽為中心的政治秩序來營建周天下,以繼承王城崗一二里頭歷史傳統(tǒng)的政治理想。至于晉國所封之晉南“夏墟”,正是龍山時代的政治與宗教權力中心所在,“夏墟”的歷史原型很可能來自一千年前的陶寺及晉南大型龍山聚落群。伊洛與晉南有關夏朝的社會記憶,與兩地的考古發(fā)現高度契合,并非偶然。李曼強調,文獻與聚落考古特征的比較研究,顯示周人正是以這些歷史記憶為號召重建了晉南和洛陽社會,并借此恢復和鞏固了中原中心的政治秩序。
李旻同時也試圖抉發(fā)后人所“創(chuàng)造”的政治傳統(tǒng)。晉南的主要炊器是源自黃土高原河谷的鬲和斝,而伊洛的主要炊器則是源自淮河流域裴李崗傳統(tǒng)的鼎,兩地的陶器傳統(tǒng)差別顯著。李旻認為這種差異對夏文化的單一性形成挑戰(zhàn),關于夏朝的社會記憶可能是不同地點的幾段政治歷史拼合而成的結果。繼龍山社會崩潰而崛起的二里頭政權,反映了少康中興的史影,它并沒有聲稱建立一個新的王朝,而是在試圖繼承高地龍山遺產的同時,開啟了洛陽中心的中原政治秩序和以銅鼎為政治與宗教權威象征的文化傳統(tǒng)。
總之,周人對夏朝的敘說,正來自周代國家所共享的社會秩序和共同價值,并通過經典固化下來。《問鼎》一書旨在尋繹出這種社會秩序和共同價值,以及它們之于周人的重要意義。至于文獻中的夏史是否一定是史實,則不是該書關注的重點。李曼試圖在考古與文獻聚合之處觀察早期中國社會記憶的傳承,并尋找經典傳統(tǒng)發(fā)生的時代和動因,但他并未雜糅考古與文獻。他的研究是人類學與考古學的,而非歷史學與文獻學的。人類學與考古學的專長在于長時段的考察、理論的建構以及實物的驗證,卻不長于史實的分析與細節(jié)的追溯。如何發(fā)揮其所長,并取長補短,應成為學者所考慮的問題。羅泰(Lotharvon Falkenhausen)先生在《問鼎》一書的序言中指出,考古學研究已經可以可靠地通過物質遺存解讀歷史敘事,并為文本記錄提供重要啟示。該書正是這一旨趣的實踐,既做到了人類學與考古學本位的堅守,同時又為古史傳說的闡釋提供了新的視角,足以成為典范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