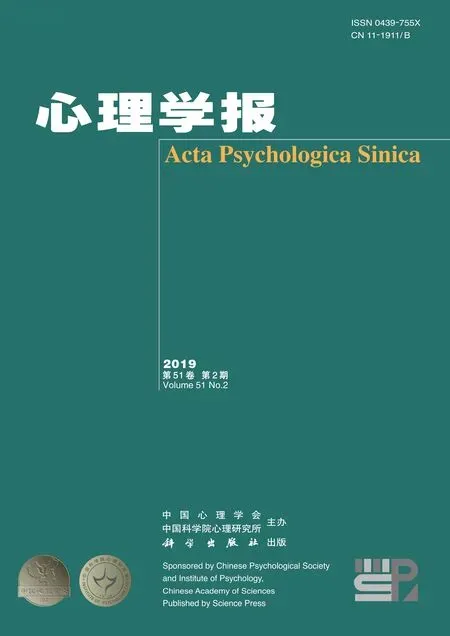辱虐管理與員工創造力:心理契約破壞和中庸思維的不同作用*
沈伊默 馬晨露 白新文 諸彥含 魯云林 張慶林 劉 軍
?
辱虐管理與員工創造力:心理契約破壞和中庸思維的不同作用
沈伊默馬晨露白新文諸彥含魯云林張慶林劉 軍
(西南大學心理學部, 重慶 400715) (中國人民大學商學院, 北京 100872) (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行為科學重點實驗室, 北京 100101) (西南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 重慶 400715) (江蘇第二師范學院經濟與法政學院, 南京 210029)
近年來, 辱虐管理與員工創造力的關系受到越來越多研究者的關注。在以往研究的基礎上, 本研究構建了一個有調節的中介作用模型, 以探討中國文化情境下辱虐管理影響員工創造力的中介心理機制及邊界條件。采用多階段?多來源的策略, 以93名主管和369名員工為對象, 通過多水平結構方程建模技術對三階段主管?員工配對調查所獲取的數據進行分析, 結果表明:主管的辱虐管理行為會通過心理契約破壞的中介作用, 對員工創造力產生間接的消極影響; 但該負向的間接關系的強度對高中庸思維者而言較弱。本研究有助于揭示辱虐管理影響員工創造力的心理機制及邊界條件, 研究結果對企業員工創造力及創新行為的管理實踐也有一定啟示。
辱虐管理; 心理契約破壞; 中庸思維; 創造力
1 問題提出
越來越多的組織已經意識到, 只有根據環境的變化, 開發出富有創造性的、獨特且實用的產品或服務, 才能讓組織在動態的復雜市場環境中贏得一席之地(Shalley, Gilson, & Blum, 2009; Zhou & Hoever, 2014)。領導作為組織環境的一個重要構成因素, 是員工創造性開展工作的重要決定因素之一。目前, 越來越多的研究者開始探討和檢驗領導者的辱虐管理(abusive supervision)與員工創造力之間的關系, 然而研究結果并不完全一致。例如, 有研究表明辱虐管理會直接降低員工的創造力(Liu, Liao, & Loi, 2012), 同時它可以通過內在動機和情緒衰竭的中介作用, 進而對創造力產生間接的消極影響(Han, Harms, & Bai, 2017; Zhang, Kwan, Zhang, & Wu, 2014)。然而也有研究表明辱虐管理不一定總會降低員工的創造力, 適度的辱虐管理甚至有利于提升員工創造力(Lee, Yun, & Srivastava, 2013)。研究者認為, 現有的相關研究并不足以解釋辱虐管理與創造力之間的復雜關系, 并呼吁在未來的研究中厘清辱虐管理對員工創造力的內在影響機制及邊界條件(Zhang et al., 2014)。
響應此號召, 我們在心理契約理論(Robinson & Morrison, 2000)和認知?情感加工系統理論(Metcalfe & Mischel, 1999)的基礎上提出辱虐管理會通過心理契約破壞(Psychological contract breach)的中介作用, 對員工創造力產生間接的消極影響; 同時該過程會受到中庸思維的調節。
1.1 辱虐管理、心理契約破壞與創造力的關系
辱虐管理是指下屬對上司不斷地表現出不包括肢體接觸的語言性或非語言性敵意行為的知覺, 如嘲弄奚落、公開大聲責罵、刻意冷落等(Tepper, 2000)。本研究認為辱虐管理會通過心理契約破壞的中介作用, 對員工的創造力產生間接的消極影響。心理契約是指在以承諾、信任和知覺為基礎的雇傭關系中, 個體對雇傭關系中雙方各自應承擔的責任或義務的一種信念(Morrison & Robinson, 1997)。當員工感知到組織未能履行心理契約中與員工貢獻相稱的一種或多種責任時, 心理契約破壞就產生了(Morrison & Robinson, 1997)。以往有研究者指出, 領導者在員工的心理契約的構建與維持過程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Tekleab & Taylor, 2003)。例如, 領導者在工作中對員工表現出較多的辱虐管理行為(如公開批評或貶損員工等)時, 員工會將其視為對自己的不尊重、蔑視與羞辱; 這與自己應該受到公正對待的期望或信念是相違背的, 它違反了雇傭關系中雙方“平等互惠”的交換原則及道德規范, 損害了領導在員工心目中的正面形象, 因此會導致較嚴重的心理契約破壞(丁桂鳳, 張澎濤, 2013; Parzefall & Salin, 2010)。
當員工感知到心理契約被破壞時, 為了維持個體與組織雙方交換關系的平衡, 員工會作出不利于組織的態度和行為, 例如在工作中表現出較低水平的創造力或創新行為(Khazanchi & Masterson, 2011)。研究者認為, 創新離不開溝通與交流, 在創新過程中個體不但要提出創造性的思想, 同時還要與同伴合作并交流相關的知識信息(Hempha?la? & Magnusson, 2012); 而且, 創新也意味著打破常規和改變現狀, 這無疑會遭到部分人的抵制, 因為創新會觸動到他們的利益。因此創新過程中需要員工敢冒風險, 懂得如何與他人溝通與合作, 甚至為了創新需要掌握一定的政治技能, 這都要求員工投入大量的時間和精力(Agarwal, 2016; Scott & Bruce, 1994)。而員工是否愿意投入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去從事創新性工作, 這取決于雇傭關系的質量(Janssen, 2000, 2004)。心理契約被看成是雇傭關系的晴雨表, 它對員工表現有著重要的影響, 因此常被用于解釋個體與組織的關系(Zhao, Wayne, Glibkowski, & Bravo, 2007)。實證研究表明, 當心理契約被破壞時, 基于平等互惠的交換原則(Blau, 1964), 個體的組織支持感和情感承諾會大大降低, 這會導致員工在創新過程中勇冒風險和積極投入(時間和精力等)的意愿大大減弱, 因此其采取新的、有創造力的方法或思路來解決工作中的難題的可能性較小(Khazanchi & Masterson, 2011; Kiazad, Seibert, & Kraimer, 2014; Ng, Feldman, & Lam, 2010)。由此我們提出:
假設1:辱虐管理會通過心理契約破壞的中介作用, 對創造力產生間接的消極影響。
1.2 中庸思維的調節作用
《中庸》曾開宗明義指出“不偏之謂中, 不易之謂庸; 中者天下之正道, 庸者天下之正理”, 就是要求人們為人處世時始終保持不偏不倚, 永遠執中協同, 這是必須堅持不能改變的法則。學者們認為, 中庸思維是根植于中國人內心的固有思維方式的深刻反映, 它被認為是一種調節矛盾以達到中和的生活哲理; 它時時刻刻都在作用于人們的言行, 是一套實用性很強的價值觀體系(楊中芳, 2010)。中國人這種整體性、辯證性的中庸思維模式是有異于西方的, 例如他們會把世界看成由復雜事情交織在一起的整體, 并力圖在這種復雜性之中去認識事物; 在對事物的分析時也不僅僅局限于事物本身, 而是包括它所處的背景與環境。吳佳輝和林以正(2005)在總結以往研究的基礎上, 將中庸思維定義為“由多個角度來思考同一件事情, 在詳細考慮不同看法之后, 選擇可以顧全自我與大局的行為方式” (p. 225); 并認為中庸思維總體上有三個方面的特點:(1)善于從多個角度來思考問題, 即多元性思考; (2)善于整合外在環境信息與自己的內在想法, 即整合性; (3)充分考慮自己行為可能帶來的后果, 以和諧方式作為行為準則, 即和諧性。因此, 中庸思維代表的是個體自我調節與約束自己的行為, 在行為之前會仔細審查行動對他人可能帶來的后果, 并選擇最佳的行動方案的思維方式(何軒, 2009)。
由于中庸思維注重個體的自我調節, 即通過自我反省、觀察形勢等反饋機制來修正自我行為, 我們借鑒認知?情感加工系統理論(Metcalfe & Mischel, 1999), 提出中庸思維可能會在辱虐管理、心理契約破壞和創造力的關系中起調節作用。該理論認為, 個體內存在“冷”和“熱”兩個平行但又相互作用的加工系統(cool/hot-system), 即基于認知的冷加工系統和基于情感的熱加工系統(Metcalfe & Mischel, 1999)。冷系統是由眾多信息節點相互聯系而構成的精細認知網絡, 能夠對外部刺激進行緩慢、系統的認知加工, 促使個體表現出理性的、策略性的行為反應, 是個體實現自我行為調節的基礎。與此不同, 熱系統是一個情感自動反應系統, 在外部刺激激活情感時, 自動、快速地引發個體做出趨近或規避的行為反應。兩個系統的交互作用決定了個體對外界刺激的行為反應。面臨外界刺激時, 基于情感的熱系統常常快速、情緒化地做出反射性反應; 個體自我調控的效果取決于認知加工系統能否有效抑制對刺激的沖動性反應。
作為顯著的負性刺激, 辱虐管理和心理契約破壞會激活員工的熱加工系統, 讓員工產生不良的負性情感體驗(Conway & Briner, 2002; Tepper, 2007); 而中庸思維作為一種認知思維方式和認知加工策略, 發揮冷加工系統的作用, 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調節辱虐管理、心理契約破壞和創造力這三者之間的關系。理由在于:
高中庸思維者善于多元思考, 因此在遭受到辱虐管理時會從多方面考察它產生的主要原因, 以及它給自己帶來的影響。與低中庸思維者相比較來看, 在處理具體事情時, 高中庸思維者往往會在一個更大的時間和空間框架中來審視形勢的變化。具體而言, 中庸思維會促使個體跳出“小我”意識, 把自己置于更大的一個集體(大我思考)或換到他人的角度來看待自己面臨的處境與問題(吳佳輝, 2006)。當遭受到辱虐管理時, 由于高中庸思維者善于多元思考, 他們會從動態的、更積極的角度來看待和評價組織的行為, 例如會看到領導(組織)在某些方面滿足其自身需求所作的積極努力。這種多元思考可作為一種注意力轉換的認知加工策略, 幫助員工由基于情感的熱加工系統轉向基于認知的冷加工系統(Sethi, Mischel, Aber, Shoda, & Rodriguez, 2000)。因此高中庸思維者在遭受辱虐管理時, 不會任由負面情緒和情感主導自己的行動, 而是會在認知重評行為后果后, 采取寬恕的姿態來面對(Ho & Fung, 2011), 因此產生心理契約破壞的可能性較小。相反, 低中庸思維者由于多元思考的能力比較弱, 因此在面對辱虐管理時往往會把注意力集中于辱虐管理行為的本身, 很少看到領導(組織)在某些方面滿足其自身需求所作的積極努力, 這導致其基于情感的熱加工系統無法有效地向基于認知的冷加工系統轉化, 因此在遭受辱虐管理時產生心理契約破壞的可能性較大。
即使遭受到較嚴重的心理契約破壞, 但和諧性和整合性的思維方式有助于高中庸思維者快速有效地由基于情感的熱加工系統轉向基于認知的冷加工系統, 從而實現自我行為的控制和調節。高中庸思維者會以維護和諧作為行為準則, 冷靜思考自己的行為是否會對組織或他人帶來不良的影響。和諧行為的選擇, 通過將行為后果在頭腦中成像, 整合內外信息, 通過比較、加工各種行為結果, 從而實現情感系統向認知系統的轉換(Metcalfe & Mischel, 1999)。在遭受心理契約破壞時, 我們猜想擁有和諧性和整合性的思維方式的高中庸思維者仍然可能會表現出較高的創造力。畢竟對大多數組織而言, 提高個體和組織的創造力, 不斷開發富有創意的商品及服務, 仍是其獲得核心競爭優勢的重要手段(Oldham & Cumming, 1996)。因此, 如果員工在工作中過于墨守陳規, 循規蹈矩, 不懂變通與創新, 這不僅會影響到員工本人的工作績效, 也會對與其有工作往來的團隊成員帶來不方便和麻煩, 造成人際關系的緊張; 而且, 自己在創新績效上的落后表現, 也會影響到整個團隊的績效, 這可能會激發主管的憤怒情緒, 使雙方關系愈發緊張(Li, Zhang, Law, & Yan, 2015)。此時即使遭受到較嚴重的心理契約破壞而使得為組織出謀劃策的創新意愿較低, 但為了維護與同事(或主管)之間關系的和諧, 高中庸思維者仍可能會積極改進自己的想法, 以便提出對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新穎的和切實可行的方案, 來避免人際關系的沖突(Yao, Yang, Dong, & Wang, 2010)。因此, 對高中庸思維者而言, 心理契約破壞和創造力之間的負向關系較弱。相比較而言, 在遭受心理契約破壞時, 低中庸思維者由于其在人際互動時并不太注重人際關系的和諧性, 因此不會通過提升自身的創新行為來避免人際關系的沖突。因此, 對低中庸思維者而言, 心理契約破壞與創造力之間的負向關系較強。由此提出假設2和3:
假設2:中庸思維可以調節辱虐管理與心理契約破壞之間的關系, 即個體的中庸思維越強烈, 辱虐管理與心理契約破壞之間的正向關系越弱。
假設3:中庸思維可以調節心理契約破壞與創造力之間的關系, 即個體的中庸思維越強烈, 心理契約破壞與創造力之間的負向關系越弱。
1.3 整合的模型
假設1~3所揭示的關系進一步表現為兩階段有調節的中介作用模式(Edwards & Lambert, 2007), 即當個體的中庸思維水平較弱時, 辱虐管理會較多地通過心理契約破壞的中介作用, 對員工創造力造成間接的消極影響; 而當個體的中庸思維水平較強時, 辱虐管理較少地通過心理契約破壞的中介作用, 對員工創造力產生間接的消極影響。據此, 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4:中庸思維調節了心理契約破壞在辱虐管理和員工創造力關系間的中介作用, 表現為被調節的中介作用模式, 即個體的中庸思維越強, 心理契約破壞在辱虐管理與創造力關系間的中介作用越弱; 反之當個體的中庸思維越弱, 心理契約破壞在辱虐管理與創造力關系間的中介作用越強。
本研究的理論框架如圖1所示。

圖1 理論框架
2 研究方法
2.1 樣本和調查過程
我們在上海、蘇州、重慶、南昌、廣州的9家企業(涉及通訊、制藥、房地產、教育培訓和市政建設)中進行問卷調查以收集數據。為避免共同方法偏差, 我們采用多階段?多來源的設計, 分三個階段收集了員工和直接主管配對的調查數據。調查時, 我們先與各公司人力資源管理部門進行溝通, 由人力資源部與各相關部門進行溝通協調, 并說明我們問卷調查的目的。我們先讓人力資源部確定被調查的員工和直接主管的名單, 并根據名單對配對問卷進行編號。我們在三個時間點收集數據。在與相關部門溝通后, 我們讓員工評定主管的辱虐管理行為(時間點1); 約1個星期以后(時間點2), 我們再讓員工報告心理契約破壞和中庸思維這2個變量的得分; 在大約兩個月后(時間點3), 我們讓主管對員工的創造力進行評價。在時間點1, 共有來自137個團體的572名員工參與我們的問卷調查, 其中有115個團體的員工返回了有效問卷共439份, 問卷回收率是77%; 在時間點2, 在這115個團體中共有109個團體的402名員工繼續參與我們的問卷調查, 其中有102個團體中的員工返回了有效問卷共377份, 問卷回收率是94%; 在時間點3, 我們再讓這102個部門(團體)的主管評價員工的創造力水平, 共有97個主管按時返回了調查問卷, 但最終只有93個團體的主管和員工的問卷能有效配對。由于以下原因, 我們刪除了部分相關數據:(1)主管和員工的問卷無法有效配對; (2)主要變量的數據缺失嚴重(如沒有報告或填寫); (3)主管和員工的數據雖能有效配對, 但主管評價員工的數目小于3。最終我們獲得369份有效配對問卷(93名主管和369名員工)。在369名下屬中, 男性占51.8%; 30歲以下的人占51.2%; 接受過本科及以上教育的人占27.7%; 59.5%的人在該公司工作不超過3年。
2.2 研究工具
辱虐管理:采用Tepper (2000)的量表來測量辱虐管理, 共15個條目。舉例條目為“我的主管常嘲笑我”和“我的主管常說我的想法和感覺很愚蠢”。該量表已由吳隆增、劉軍和劉剛(2009)在中國情境下使用, 并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本研究將采用R()、組內相關系數(ICC[1])和評判間信度(ICC[2])來衡量分數的一致性, 以判斷個體層面的分數是否能匯總成為群體層次的分數(Bliese, 2000)。統計結果顯示, 個體在辱虐管理上的得分具有較好的一致性(ICC[1]為0.17, ICC[2]為0.44,R()的平均數和中位數分別為0.95和0.97)。因此, 本研究有足夠的證據將其放置群體層面。在本研究中, 該量表的內部一致性系數為0.93。
心理契約破壞:采用Robinson和Morrison (2000)的量表來測量心理契約破壞, 共5個條目。舉例條目為“迄今為止, 本公司在招聘我時作出的所有承諾幾乎都實現了” (反向計分)。在本研究中該量表的內部一致性系數為0.96。
中庸思維:采用吳佳輝和林以正(2005)的量表來測量中庸思維。該量表由“多方思考”、“整合性”和“和諧性”這3個維度組成, 共13個條目。舉例條目為“我習慣從多方面的角度來思考同一件事情”、“我會試著在自己與他人的意見中, 找到一個平衡點”和“意見決定時, 我會試著以和諧的方式讓少數人接受多數人的意見”。本研究不在維度層面上展開細致研究, 所以將這3個維度上的得分合并取平均值。本研究中總量表的內部一致性系數為0.92。
創造力:沿用前人的做法(Wang, Tsai, & Tsai, 2014), 采用Oldham和Cumming (1996)編制的3個條目來測量員工的創造力, 共3個條目。舉例條目為“該員工經常會想出一些新穎的、實用的方法來改進績效”。本研究中該量表的內部一致性系數為0.88。
控制變量:有研究者指出, 在遭受不公平對待或人際虐待時, 不同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和工作任期的人, 其反應可能是不同的(Aquino & Douglas, 2003)。因此, 在本研究中, 我們控制了員工的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和工作年限。
本研究中所有量表均采用7點量表(1 = 完全反對; 7 = 完全同意)。所有量表均已在中國情境下使用過, 并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2.3 數據分析方法
數據分析的步驟如下:首先, 本研究采用驗證性因子分析來確認本研究中涉及的幾個變量的構念效度。其次, 本研究的數據呈現嵌套結構, 我們利用Mplus 7.0軟件(Muthén & Muthén, 2012)進行多水平結構方程建模(multilevel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MSEM), 以檢驗本文的研究假設; 特別是, 我們結合Edwards和Lambert (2007)的路徑分析技術來檢驗本文涉及的有調節的中介模型。同時, 我們還會通過蒙特卡羅再抽樣法(Monte Carlo resampling method), 來計算中介效應的置信區間, 以檢驗其顯著性程度。在本研究中, 所有的數據分析均納入了控制變量。
3 研究結果
3.1 驗證性因素分析
為了考察并確認各個變量的聚合效度(convergent validity)和區分效度(discriminant validity), 我們使用Lisrel 8.7軟件對369份員工?主管配對數據進行驗證性因子分析。結果表明, 4因子模型中各因子的因子負荷及t值均達到了0.05的顯著性水平, 且沒有不恰當解, 這說明本文涉及的幾個構念均具有較好的聚合效度。同時, 我們通過模型比較的方法來考察各個變量的區分效度。如表1所示, 4因子模型與另外5個模型相比, 對實際數據最為擬合(χ= 1480.66;= 588; χ/= 2.52; NNFI = 0.95; CFI = 0.96; RMSEA = 0.06), 說明本文所涉及的4個量表均具有良好的區分效度。

表1 驗證性因子分析結果
注:(1)= 369;= 93。(2) **< 0.01 (雙尾檢驗).
基準模型:辱虐管理、心理契約破壞、中庸思維、創造力;
三因子模型一:在基準模型的基礎上, 將辱虐管理和心理契約破壞合并為一個因子;
三因子模型二:在基準模型的基礎上, 將辱虐管理和中庸思維合并為一個因子;
三因子模型三:在基準模型的基礎上, 將辱虐管理和創造力合并為一個因子;
三因子模型四:在基準模型的基礎上, 將心理契約破壞和中庸思維合并為一個因子;
單因子模型:將辱虐管理、心理契約破壞、中庸思維、創造力合并為一個因子。
3.2 描述性統計結果
各變量的均值、標準差和相關系數如表2所示。心理契約破壞與員工創造力呈顯著負相關 (= ?0.13,< 0.05)。這些結果與我們的理論預期基本相符。
3.3 假設檢驗
3.3.1 心理契約破壞的中介效應檢驗
在假設1中我們假設辱虐管理通過心理契約破壞的中介作用, 對員工創造力產生間接的消極影響。由于本研究的數據呈嵌套結構, 因此我們分別以心理契約破壞、創造力為因變量, 以公司編號為自變量, 做單因素方差分析, 結果發現組間方差并不顯著(心理契約破壞:(8, 360) = 1.64,; 創造力:(8, 360) = 1.59,); 但當我們繼續以心理契約破壞、創造力為因變量, 以部門(主管)編號為自變量, 做單因素方差分析時, 結果顯示組間方差均極其顯著(心理契約破壞:(92, 276) = 2.78,< 0.01;創造力:(92, 276) = 3.59,< 0.01)。這表明這兩個變量來自部門(而非公司)的變異較大, 應進行兩水平分析以控制嵌套關系所導致的非隨機性的影響(Cohen, 1988)。兩水平結構方程建模結果表明, 辱虐管理與心理契約破壞(= 1.06,< 0.01)和員工創造力(= ?0.41,< 0.01)相關顯著; 心理契約破壞與員工創造力相關并不顯著(= ?0.04,)。這說明在不考慮中庸思維的調節作用的前提下, 心理契約破壞在辱虐管理和創造力的關系間的中介作用并不顯著(間接效應為?0.04; 95%置信區間為[?0.11, 0.03])。因此, 假設1并沒有得到數據的支持。需注意的是, 就統計本身而言, 這并不是分析被調節的中介效應的必要條件, 這是因為調節變量的潛在影響, 抵消了這種平均中介作用(劉東, 張震, 汪默, 2012)。

表2 均值、標準差及變量間的相關關系
注:(1)= 369;= 93。(2) *< 0.05 **< 0.01 (雙尾檢驗)。(3)各量表的信度系數標注在矩陣對角線括號內。(4)性別分為兩類:1 = 男; 2 = 女。年齡分為三類:1 = 20~29歲; 2 = 30~39歲; 3 = 40歲以上。受教育程度分為三類:1 = 高中及以下; 2 = 專科; 3 = 本科及以上。任職年限分為四類:1 = 1~3年; 2 = 4~6年; 3 = 7~9年; 4 = 10年以上。
3.3.2 中庸思維的調節效應檢驗
在假設2和3中我們假設中庸思維能調節辱虐管理與心理契約破壞、以及心理契約破壞與員工創造力之間的關系。由于我們的數據呈嵌套關系, 我們仍然利用Mplus 7.0軟件, 通過多水平結構方程建模技術來檢驗該假設。數據的分析結果如表3所示。從表3中可以看出, 在控制員工的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任職年限, 以及辱虐管理和中庸思維的主效應以后, 辱虐管理和中庸思維的交互項對心理契約破壞的影響不顯著(= ?0.14,); 但在控制性別等人口學變量以及心理契約破壞和中庸思維的主效應后, 心理契約破壞和中庸思維的交互項對員工創造力具有顯著的預測效果(= 0.18,< 0.01)。因此, 研究結果支持了假設3, 但是沒有支持假設2。

表3 中庸思維在辱虐管理、心理契約破壞和員工創造力關系間的調節效應分析
注:(1)= 369;= 93。(2) **< 0.01, *< 0.05。(3)括號中數據為標準誤。

圖2 中庸思維在心理契約破壞和員工創造力之間的調節作用
為了進一步確認中庸思維在心理契約破壞和員工創造力的關系間的調節效應的型態是否符合原先的預期, 我們參考Aiken和West (1991)的做法, 分別取中庸思維加減一個標準差的值代入回歸模型中, 并進行繪圖(見圖2)。從圖2中可以看出, 與低中庸思維相比, 在高中庸思維的情境下, 心理契約破壞和員工創造力之間的負向關聯性較弱, 這與原先的預期相符。簡單斜率分析(simple slope analysis)結果也表明, 在高中庸思維的條件下, 心理契約破壞和員工創造力之間的負向關聯性較弱(簡單斜率為0.09,); 相比較而言, 在低中庸思維的條件下, 心理契約破壞和員工創造力之間的負向關聯性較強(簡單斜率為?0.19,< 0.01)。其組間差異為0.28, 達到了顯著性水平(< 0.01)。這與原先的預期相符, 因此假設3得到支持。
3.3.3 有調節的中介效應檢驗
假設4中, 我們假設心理契約破壞在辱虐管理和員工創造力之間的中介作用會受到中庸思維的雙重調節。由于中庸思維能調節心理契約破壞與創造力之間的關系(假設3), 但不能調節辱虐管理與心理契約破壞之間的關系(假設2), 因此它只能構成第二階段有調節的中介效應模型(劉東等, 2012)。我們仍然利用Edwards和Lambert (2007)的路徑分析技術, 來檢驗中庸思維是否能調節以上間接關系。數據分析結果如表4所示。
從表4中可以看出, 中庸思維能調節心理契約破壞在辱虐管理和員工創造力之間的中介作用, 即當中庸思維水平較低時, 心理契約破壞在辱虐管理和員工創造力之間的中介作用十分顯著(間接效應為?0.12, 95%置信區間為[?0.22, ?0.03]); 但當中庸思維水平較高時, 該中介作用不再顯著(間接效應為0.07, 95%置信區間為[?0.04, 0.19])。其組間差異為?0.19, 達到了顯著性水平(< 0.05)。因此, 假設4基本得到數據支持。
4 討論
4.1 研究結果討論
創造力是企業可持續發展的主題。如何激發和維持員工的創造力, 已成為學界和企業界長期關注的話題。領導方式是影響員工創造力的重要情境變量, 本研究采用縱向研究設計, 運用多時間點、多來源數據, 借助多水平結構方程建模分析, 探討并檢驗了辱虐管理對創造力影響過程中心理契約破壞的中介作用, 以及中庸思維的調節作用。實證結果也總體上支持了我們的研究構想。總體而言, 本研究對于理論貢獻和管理實踐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
首先, 以往的研究在探討辱虐管理對員工創造力的影響時大多是基于社會學習理論(e.g., Liu, Liao, & Loi, 2012)和激活理論(e.g., Lee et al., 2013)等視角, 很少有研究從心理契約理論的角度來探討辱虐管理對員工創造力的影響過程及作用機制。本研究從心理契約理論的角度出發, 發現辱虐管理會通過心理契約破壞的中介作用, 對員工創造力產生間接的影響。雖然先前曾有研究者猜想辱虐管理可能會通過心理契約破壞的中介作用, 進而對員工工作態度和行為產生間接的影響(e.g., Parzefall & Salin, 2010; Restubog, Scott, & Zagenczyk, 2011), 然而目前鮮有研究為該假說提供相關的實證支持。本研究較早地提出辱虐管理可能會通過心理契約破壞的中介作用, 對員工創造力產生間接的消極影響, 并通過實證研究來檢驗, 這對以往研究是一個有益的補充, 它豐富了我們對辱虐管理的內在機理的認識。
其次, 本研究提出并檢驗了中庸思維作為一種邊界條件, 在辱虐管理?心理契約破壞?創造力的間接關系中的調節作用。中庸思維的調節作用為我們理解文化價值觀影響辱虐管理的影響效果的方式提供了線索。如前所述, 中庸之道強調人們在處理矛盾時要做到“執兩用中, 執中致和”, 以達到中正、中和、穩定、和諧的狀態。這使得高中庸思維者在思考問題時比較全面(Ji, Peng, & Nisbett, 2000), 在處理事情時也很少走極端(Lee, 2000), 在遇到不同意見甚至沖突時, 往往會尋求妥協(Cheung et al., 2003)。因此, 在遭受因主管的辱虐管理而產生的心理契約破壞時, 高中庸思維者會換位思考, 從動態的、更積極的角度來看待和評價組織的行為, 這有助于個體由基于情感的熱加工系統轉向基于認知的冷加工系統, 實現自我行為的控制和調節, 因而不會意氣用事, 而是會在組織需要的時候仍然會主動提出新穎性的、切實可行的想法與方案。雖然近年來國內對辱虐管理的研究逐漸增多, 但是目前大多數研究仍然根植于西方文化背景, 對中國本土文化情景下的辱虐管理研究還不太多。契合近來學者提出并檢驗中國文化情境下辱虐管理效應邊界的呼吁(丁桂鳳, 古茜茜, 朱瀅瑩, 劉建雄, 2012; 吳隆增, 劉軍, 劉剛, 2009), 本研究為辱虐管理?心理契約破壞?創造力的間接關系模型輸入了非常有價值的中國文化背景, 這也是本研究的最大理論貢獻所在。

表4 調節?中介模型分析
注:(1)= 369;= 93。(2)**< 0.01, *< 0.05。(3)括號中數據為標準誤。(4)表示辱虐管理到心理契約破壞的非標準化路徑;表示心理契約破壞到員工創造力的非標準化路徑;表示辱虐管理到員工創造力的非標準化路徑。(5)我們通過中庸思維的正負1個標準差(SD)來區分出高低組。
另外, 本研究對企業管理實踐也有一定的啟示作用:(1)本研究對領導者的日常管理具有一定的警醒作用。本研究結果提醒管理者應該要重視其辱虐管理行為的危害性, 并在管理實踐中采取有效措施以減少辱虐管理行為的發生。這是因為辱虐管理如果不加干預, 會讓員工體驗到心理契約的破壞, 進而在工作中會表現出較低的創造力。有鑒于此, 企業可針對主管展開相關的培訓, 提高其在工作中的個人修養, 學習如何人性化地管理下屬; 讓其真正重視辱虐管理行為的危害性, 并發自內心的去做出改變, 以期從源頭糾正主管的辱虐管理行為。(2)本研究對于管理者如何降低辱虐管理行為的負面效應也具有一定的參考意義。雖然辱虐管理行為在中國企業中普遍存在, 但本研究啟示管理者可從文化價值觀的塑造入手實施干預, 以實現員工行為的自我調節, 從而規避辱虐管理的負面效應。例如, 作為管理者, 可以為員工提供中庸文化的學習培訓, 培養員工的中庸思維方式, 修煉員工的“心性”, 讓員工懂得如何在工作中整體地、辯證性地看待主管的辱虐管理行為, 合理地調適工作中的負面情緒及認知, 以減少辱虐管理給員工創造力帶來的負面影響。
4.2 研究局限性及未來研究展望
本研究還存在一些不足之處:(1)本研究通過主管與員工的配對, 在三個不同的時間點收集數據, 這種研究設計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共同方法偏差; 但辱虐管理的測量具有敏感性, 會產生社會贊許效應, 因此在未來的研究中可以嘗試采用不同的方法(如運用深度訪談等質化研究的方式等)來收集上司的辱虐管理數據, 進一步探索辱虐管理對員工創造力的影響過程及作用機制。(2)本研究表明當個體的中庸思維水平較低時, 辱虐管理可以通過心理契約破壞的中介作用, 給員工創造力帶來消極的影響; 但Lee等人(2013)的研究表明辱虐管理與創造力之間呈倒U型曲線關系, 這說明辱虐管理不總是會降低員工的創造力, 在某些時候它可能有助于提升員工的創造力。因此, 我們呼吁研究者們在未來的研究中繼續探索辱虐管理影響員工創造力的潛在心理機制與邊界條件, 特別是要搞清楚辱虐管理是如何提高員工的創造力的。對于以上不足, 我們將在后續的研究中加以改進。
5 結論
本研究檢驗了心理契約破壞在辱虐管理和員工創造力之間的中介作用, 以及該間接關系間的調節作用。研究的具體發現如下: 主管的辱虐管理行為會通過心理契約破壞的中介作用, 對員工創造力產生間接的消極影響; 但該間接的影響過程會受到下屬中庸思維的調節。具體而言, 當下屬的中庸思維水平較低時, 心理契約破壞在辱虐管理和創造力關系間的中介作用較強; 當下屬的中庸思維水平較高時, 心理契約破壞在辱虐管理和創造力關系間的中介作用較弱。
Aiken, L. S., & West, S. G. (1991).. Newbury Park, CA: Sage Publications.
Agarwal, U. A. (2016). Examining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politics among Indian managers: Engagement as mediator and locus of control as moderator.(3), 415–437.
Aquino, K., & Douglas, S. (2003). Identity threat and antisocial behavior in organizations: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ggressive modeling, and hierarchical status.(1), 195–208.
Blau, P. M. (1964).. New York: John Wiley.
Bliese, P. D. (2000). Within-group agreement, non-independence, and reliability: Implications for data aggregation and analysis. In K. J. Klein & S. W. J. Kozlowski (Eds.),(pp. 349–381).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Cheung, T. S., Chan, H. M., Chan, K. M., King, A. Y. C., Chiu, C. Y., & Yang, C. F. (2003). On Zhongyong rationality: The Confucian doctrine of the mean as a missing link between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1), 107–127.
Cohen, J. (1988).(2 ed.). Hillsdale, NJ: Eribaum.
Conway, N., & Briner, R. B. (2002). A daily diary study of affective responses to psychological contract breach and exceeded promises.(3), 287–303.
Ding, G. F., Gu, X. X., Zhu, Y. Y., & Liu, J. X. (2012). The mechanism between superior's abusive and subordinate's performance behavior and intervention strategies.(9), 1347–1354.
[丁桂鳳, 古茜茜, 朱瀅瑩, 劉建雄. (2012). 上司不當督導與下屬績效行為的作用機制及其干預策略.(9), 1347–1354.]
Ding, G. F., & Zhang, P. T. (2013). Abusive supervision and normative commitment: The mediation effects of followership.(6), 796–800.
[丁桂鳳, 張澎濤. (2013). 領導不當督導與追隨者規范承諾: 追隨力的中介作用.(6), 796–800.]
Edwards, J. R., & Lambert, L. S. (2007). Methods for integrating moderation and mediation: A general analytical framework using moderated path analysis.(1), 1–22.
Han, G. H., Harms, P. D., & Bai, Y. (2017). Nightmare bosses: The impact of abusive supervision on employees’ sleep, emotions, and creativity.1), 21–31
He, X. (2009). Can interactional justice solve the silence problem?, (4), 128–134.
[何軒. (2009). 互動公平真的就能治療沉默病嗎? 以中庸思維作為調節變量的本土實證研究., (4), 128–134.]
Hempha?la?, J., & Magnusson, M. (2012). Networks for innovation-but what networks and what innovation.(1), 3–16.
Ho, M. Y., & Fung, H. H. (2011). A dynamic process model of forgiveness: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1), 77–84.
Janssen, O. (2000). Job demands, perceptions of effort-reward fairness and innovative work behaviour.(3), 287–302.
Janssen, O. (2004). How fairness perceptions make innovative behavior more or less stressful.(2), 201–215.
Ji, L. J., Peng, K., & Nisbett, R. E. (2000). Culture, control, and perception of relationships in the environment.(5), 943–955.
Khazanchi, S., & Masterson, S. S. (2011). Who and what is fair matters: A multi-foci social exchange model of creativity.(1), 86–106.
Kiazad, K., Seibert, S. E., & Kraimer, M. L. (2014). Psychological contract breach and employee innovation: A 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perspective.(3), 535–556.
Lee, S., Yun, S., & Srivastava, A. (2013). Evidence for a curvi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abusive supervision and creativity in South Korea.(5), 724–731.
Lee, Y. T. (2000). What is missing in Chinese-Western dialectical reasoning?(9), 1065–1067.
Li, Y. N., Zhang, M. J., Law, K. S., & Yan, M. N. (2015). Subordinate performance and abusive supervision: The role of envy and anger.(1), 16420–16420.
Liu, D., Liao, H., & Loi, R. (2012). The dark side of leadership: A three-level investigation of the cascading effect of abusive supervision on employee creativity.(5), 1187–1212.
Liu, D., Zhang, Z., & Wang, M. (2012). Mono-level and multilevel mediated moderation and moderated mediation: Theorization and test. In X. Chen, A. Tsui & L. Farh (Eds.),(2nd ed., pp. 545–579).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劉東, 張震, 汪默. (2012). 被調節的中介和被中介的調節: 理論構建與模型驗證. 見: 陳曉萍, 徐淑英, 樊景立(主編).(2nd; pp. 545–579.).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Metcalfe, J., & Mischel, W. (1999). A hot/cool-system analysis of delay of gratification: Dynamics of willpower.(1), 3–19.
Morrison, E. W., & Robinson, S. L. (1997). When employees feel betrayed: A model of how psychological contract violation develops.(1), 226–256.
Muthe?n, L. K., & Muthe?n, B. O. (2012).(7th ed.). Los Angeles, CA: Muthén & Muthén.
Ng, T. W. H., Feldman, D. C., & Lam, S. S. K. (2010). Psychological contract breaches,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and innovation-related behaviors: A latent growth modeling approach.(4), 744–751.
Oldham, G. R., & Cummings, A. (1996). Employee creativity: Personal and contextual factors at work.(3), 607–634.
Parzefall, M. R., & Salin, D. M. (2010). Perceptions of and reactions to workplace bullying: A social exchange perspective.(6), 761–780.
Restubog, S. L, Scott, K. L., & Zagenczyk, T. J. (2011). When distress hits home: The role of contextual factors and psychological distress in predicting employees’ responses to abusive supervision.(4), 713–729.
Robinson, S. L., & Morrison, E. W. (2000). The development of psychological contract breach and violation: A longitudinal study.(5), 525–546.
Scott, S. G., & Bruce, R. A. (1994). Determinants of innovative behavior: A path model of individual innovation in the workplace.(3), 580–607.
Sethi, A., Mischel, W., Aber, J. L., Shoda, Y., & Rodriguez, M. L. (2000). The role of strategic attention deployment in development of self-regulation: Predicting preschoolers' delay of gratification from mother-toddler interactions.(6), 767–777.
Shalley, C. E., Gilson, L. L., & Blum, T. C. (2009). Interactive effects of growth need strength, work context, and job complexity on self-reported creative performance.(3), 489–505.
Tekleab, A. G., & Taylor, M. S. (2003). Aren't there two parties in an employment relationship?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of organization-employee agreement on contract obligations and violations.(5), 585–608.
Tepper, B. J. (2000). Consequences of abusive supervision.(2), 178–190.
Tepper, B. J. (2007). Abusive supervision in work organizations: Review, synthesis, and research agenda.(3), 261–289.
Wang, C. J., Tsai, H. T., & Tsai, M. T. (2014). Linking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and employee creativity in the hospitality industry: The influences of creative role identity, creative self-efficacy, and job complexity., 79–89.
Wu, J. H. (2006). Zhongyong make my life better: The effect of Zhongyong thinking on life satisfaction., 163?176.
[吳佳輝. (2006).., 163–176.]
Wu, J. H., & Lin, Y. C. (2005). Development of a Zhong-Yong thinking style scale., 247–300.
[吳佳輝, 林以正. (2005). 中庸思維量表的編制.247–300.]
Wu, L. Z., Liu, J., & Liu, G. (2009). Abusive supervision and employee performance: Mechanisms of traditionality and trust.(6), 510–518.
[吳隆增, 劉軍, 劉剛. (2009). 辱虐管理與員工表現: 傳統性與信任的作用.510–518.]
Yang, Z. F. (2010). Multiplicity of Zhong Yong studies., 3–96.
[楊中芳. (2010). 中庸實踐思維體系探研的初步進展.1120–165.]
Yao, X., Yang, Q., Dong, N., & Wang, L. (2010). Moderating effect of Zhong Yong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behaviour.(1), 53–57.
Zhang, H., Kwan, H. K., Zhang, X., & Wu, L. Z. (2014). High core self-evaluators maintain creativity: A motivational model of abusive supervision.(4), 1151–1174.
Zhao, H., Wayne, S. J., Glibkowski, B. C., & Bravo, J. (2007). The impact of psychological contract breach on work-related outcomes: A meta-analysis.(3), 647–680.
Zhou, J., & Hoever, I. J. (2014). Research on workplace creativity: A review and redirection.(1), 333–359.
Linking abusive supervision with employee creativity: The roles of psychological contract breach and Zhongyong thinking style
SHEN Yimo; MA Chenlu; BAI Xinwen; ZHU Yanhan; LU Yunlin; ZHANG Qinglin; LIU Jun
(School of Psychology,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Business School,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CAS Key Laboratory of Behavioral Science,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School of Business and Law, Jiangsu Second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9, China)
Although creativity has been recognized as an important employee outcome related with work context, to date little research has examin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busive supervision and employee creativity, which has perhaps been hindered by the lack of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outlining the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is relationship. The current study examined the processes linking abusive supervision to employee creativity in the Chinese context by focusing on the mediating influence of psychological contract breach and the moderating influence of Zhongyong thinking style.
We collected data from 93 supervisors and 369 subordinates at three different time points. In the first survey, the subordinates were asked to provide information about abusive supervision and their demography. One week later, these subordinates were asked to answer some questions about psychological contract breach and Zhongyong thinking style. Approximately two months later, we asked these supervisors to rate their subordinates’ creativity. Multi-level structuring equation modeling technique and Monte Carlo resampling method were employed to examine the hypothesis about the moderating role of Zhongyong thinking style in the indirect relationship between abusive supervision and employee creativity through psychological contract breach.
These findings provided support for the hypothesis that the indirect relationship between abusive supervision and employee creativity through psychological contract breach is moderated by Zhongyong thinking style, such that the indirect relationship is weakened when Zhongyong thinking style is high, rather than low. These findings contribute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busive supervision and employee creativity in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imply that the negative influence of abusive supervision on employee outcomes could be decreased by guiding employees to cultivate Zhongyong thinking style because it can encourage self-regulation of behavior after experiencing abusive supervision.
abusive supervision; psychological contract breach; Zhongyong thinking style; creativity
10.3724/SP.J.1041.2019.00238
2016-12-30
* 國家杰出青年科學基金項目“組織行為”(71425003)、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面上項目(71872152; 71871214; 31671125)、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經費創新團隊項目(SWU1709123)和重點項目(SWU1709238)資助。
沈伊默, E-mail: shenym1980@126.com; 諸彥含, E-mail: zhuyh@swu.edu.cn
B849:C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