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書面漢語與中國語文現(xiàn)代化運(yùn)動(dòng):歷史、現(xiàn)實(shí)與反思
——為紀(jì)念現(xiàn)代漢語一百周年而作
刁晏斌
一、引言
學(xué)界一般認(rèn)為,1892年盧戇章《一目了然初階》的問世,標(biāo)志著切音字運(yùn)動(dòng)也就是中國語文現(xiàn)代化運(yùn)動(dòng)的開始。[1]關(guān)于中國語文現(xiàn)代化運(yùn)動(dòng)的目標(biāo)與訴求,周有光歸納為4個(gè)方面,即語言的共同化、文體的口語化、文字的簡便化和表音的字母化。[2]在這一百多年中,語文現(xiàn)代化取得的成果主要是普通話、現(xiàn)代白話文、規(guī)范漢字和漢語拼音。[3]
如果從1919年算起的話(這是多數(shù)人的意見),現(xiàn)代漢語已經(jīng)經(jīng)歷了整整一百年,而在百年間從形成到發(fā)展的整個(gè)過程中,現(xiàn)代漢語始終與一直持續(xù)不斷的語文現(xiàn)代化運(yùn)動(dòng)相生相伴。總體而言,百年現(xiàn)代漢語既是語文現(xiàn)代化運(yùn)動(dòng)的產(chǎn)物,同時(shí)也在很大程度上代表和反映了后者的實(shí)績與貢獻(xiàn),前者是果,后者是因。
長期以來,筆者從事“現(xiàn)代漢語史”的研究,主要以現(xiàn)代書面漢語為研究對(duì)象,所以本文主要立足于此,即現(xiàn)代白話文(也可以稱之為普通話書面語),來討論相關(guān)問題。
在周有光先生歸納的語文現(xiàn)代化4個(gè)大目標(biāo)中,與本文論題直接相關(guān)的是“文體的口語化”,也就是書面語的口語化,本文就此展開討論。
二、語文現(xiàn)代化與現(xiàn)代書面漢語的形成與發(fā)展
著眼于跟現(xiàn)代書面漢語形成之間的密切關(guān)聯(lián),我們把語文現(xiàn)代化運(yùn)動(dòng)中的言文一致即“文體的口語化”進(jìn)程分為三個(gè)階段。
(一)初步達(dá)成階段
“五四”白話文運(yùn)動(dòng)最終導(dǎo)致新型的漢民族共同語書面語初步形成,并使之開始取代文言成為社會(huì)文化生活中的主要書寫方式,由此也開啟了百年現(xiàn)代漢語的發(fā)展歷程。李如龍對(duì)此有以下一段敘述:
“五四”新文化運(yùn)動(dòng)為白話文鳴鑼開道,借助著宋元白話的藝術(shù)成就和普通話的群眾基礎(chǔ),經(jīng)歷了20年的反復(fù)拉鋸,白話終于取代文言,站住了腳跟。在宋元白話文的基礎(chǔ)上,經(jīng)過“國語運(yùn)動(dòng)”,一批新的語文學(xué)家提倡“我手寫我口”、編寫新語文課本在少年兒童中傳習(xí),吸收了現(xiàn)代普通話口語詞匯和語法,加進(jìn)少量歐化句式和文言成分,在一大批現(xiàn)代文學(xué)巨匠的共同努力之下,到了上世紀(jì)30年代,很快就建成了現(xiàn)代白話文的獨(dú)具特色的書面語系統(tǒng),應(yīng)該說,20世紀(jì)形成的現(xiàn)代漢語書面語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先前的書面語和口頭語的分離狀態(tài)。[4]
但是,此階段的白話文難免其“初期性”,在許多方面并不完備,而由此也招致了很多批評(píng)。周有光認(rèn)為,“五四”時(shí)期的白話文有時(shí)像小腳放大的“語錄體”[5];陳建民指出,“五四”是白話文的創(chuàng)新時(shí)期,無章可循,不講規(guī)范,各人按各人的語文功底,或夾雜近代白話和文言,或夾雜歐化句子,或使用方言俗語,隨意性很大,當(dāng)時(shí)就被人稱為“洋八股”“學(xué)生八股”,文縐縐,洋里洋氣,似通不通……它反映“五四”時(shí)期的漢語與當(dāng)代漢語確實(shí)存在著明顯的差異。[6]
就其“洋化”一點(diǎn),有人更是進(jìn)一步指出,白話文成了一種“披著歐洲外衣”,負(fù)荷了過多的西方新詞匯,甚至深受西方語言的句法和韻律影響的語言。它甚至可能是比傳統(tǒng)的文言更遠(yuǎn)離大眾的語言。[7]
人們對(duì)“五四白話文”的總體認(rèn)識(shí)與評(píng)價(jià),大致如俞香順?biāo)f:相對(duì)于文言來說,是“白”的、俗的,但是相對(duì)于大眾語言來說又是“文”的、雅的,因此懸浮于大眾語言與文言文之間。[8]
另外,即使這樣很不完善的白話文,也并未實(shí)現(xiàn)對(duì)所有使用領(lǐng)域的全覆蓋。“五四運(yùn)動(dòng)”雖然確立了白話文的地位,但是多半還限于狹義的文學(xué)的領(lǐng)域,至于報(bào)章雜志、政府公文、學(xué)術(shù)論文等實(shí)用的領(lǐng)域,仍然是充斥著文言、歐化影響的“三合一”文體,“白而不話”,離百姓真正的口語還有相當(dāng)大的距離。[9]甚至在學(xué)校教育中,那時(shí)候(引者按:指1926年)作文都是文言文,沒有寫白話文的。[10]
(二)初步改造階段
正因?yàn)槌醪叫纬傻默F(xiàn)代漢語書面語有如此的不足,所以人們一直呼吁對(duì)其加以改造甚至去除,其中比較集中且影響極大的事件有二,一是上世紀(jì)30年代的“大眾語運(yùn)動(dòng)”;二是上世紀(jì)三四十年代的“民族形式”論爭。
我們先說“大眾語運(yùn)動(dòng)”。
針對(duì)“五四”時(shí)期白話文過于歐化以及半文半白的情況,1934年6月,上海文化界由陳望道、胡愈之等人發(fā)起了“大眾語運(yùn)動(dòng)”,提出清算文腔白話和歐化白話,提倡“大眾說得出,聽得懂,寫得順手,看得明白”的大眾語,這是白話文運(yùn)動(dòng)在30年代的進(jìn)一步發(fā)展。[11]大眾語的目標(biāo)直指“五四白話文”之后漢語書面語如何建設(shè)、發(fā)展和規(guī)范,參與討論的名人和刊物眾多,涉及面較廣,影響十分巨大,成為當(dāng)時(shí)思想文化領(lǐng)域的一件大事。[12]有人認(rèn)為,“大眾語運(yùn)動(dòng)”可謂是中國語言規(guī)劃史上的一次劃時(shí)代的突破,它開始關(guān)注下層的民眾,并且第一次把語言規(guī)劃的焦點(diǎn)放大到整個(gè)國民身上。“大眾語運(yùn)動(dòng)”是“五四”時(shí)期的白話文運(yùn)動(dòng)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合乎邏輯的發(fā)展,它徹底擊退了文言文的復(fù)興逆流,促進(jìn)了白話文的通俗化和大眾化,把中國現(xiàn)代的語文改革和語文規(guī)范工作推進(jìn)到一個(gè)新階段。[13]
“大眾語運(yùn)動(dòng)”主要在文學(xué)界開展,雖然取得不少理論成果,獲得相當(dāng)高的評(píng)價(jià),但主要是在“方向”與“路線”上的提倡與呼吁,在文學(xué)以外的其他領(lǐng)域影響比較有限,而在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上的實(shí)績也并不突出,并未創(chuàng)造出一種嶄新的“大眾語文”,所以有人稱其為“無果而終”,并認(rèn)為其“學(xué)術(shù)影響較為有限”[14]。但是,它在理論上還是為后來的文藝大眾化做了前期準(zhǔn)備。[15]
次說“民族形式”論爭。
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史上,“民族形式”論爭是一個(gè)重要事件,有人認(rèn)為它是延安時(shí)期黨的宣傳部門有計(jì)劃、有領(lǐng)導(dǎo)地開展的一場(chǎng)全國性的文藝運(yùn)動(dòng),[16]它的指導(dǎo)方針和最終達(dá)成的認(rèn)識(shí),就是毛澤東1940年1月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明確指出的,革命文化“應(yīng)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農(nóng)勞苦民眾服務(wù),并逐漸成為他們的文化。”“為達(dá)此目的,文字必須在一定條件下加以改革,言語必須接近民眾,須知民眾就是革命文化的無限豐富的源泉。”[17]
從語文現(xiàn)代化的角度看,這無疑也是一次重要的語言規(guī)劃活動(dòng)及實(shí)踐,總體而言屬于對(duì)此前業(yè)已形成并在實(shí)際使用中的書面語的改造,并由此對(duì)現(xiàn)代漢語的發(fā)展及后來的走向產(chǎn)生深遠(yuǎn)的影響。在這一論爭中,民間語言被一些左翼理論家提到了決定性高度,有人認(rèn)為民間語言就是民族形式真正的中心源泉。[18]正是在這一理論思想的指導(dǎo)下,許多作家,尤其是解放區(qū)的作家,采用大眾所喜聞樂見的表達(dá)形式,如將板話等民間語言形式吸收進(jìn)小說,追求語言文字的通俗性,用常用詞、常見詞以及較為簡單的合乎語法規(guī)范的句式,力避受西方現(xiàn)代主義文學(xué)影響的陌生化和歐化句式。[19]由此,有人認(rèn)為完成了從“現(xiàn)代白話”到“革命白話”的轉(zhuǎn)換。[20]
文藝以外的其他領(lǐng)域大致也是如此,循著通俗化與大眾化的方向,甚至形成了“標(biāo)準(zhǔn)化的革命工作語言”以及“延安風(fēng)格”,隨著新中國的建立,它們最終被推向全國。[21]另外,這不僅是立足于當(dāng)下,同時(shí)還在為我黨奪取全國政權(quán)以后文化及語文政策的推廣做準(zhǔn)備。陳毅指出:“這種大規(guī)模的計(jì)劃(筆者按:指建立‘革命文化’,包括語言形式的民族化),不僅是抗戰(zhàn)文化推行的眼前需要,而且已經(jīng)是建國的文化改革的偉大任務(wù)之開始。”[注]詳見陳毅《關(guān)于文化運(yùn)動(dòng)的意見——在海安文化座談會(huì)上的發(fā)言》。轉(zhuǎn)引自石鳳珍《從“舊形式”到“民族形式”——文藝“民族形式”運(yùn)動(dòng)發(fā)起過程探略》(載《西南民族大學(xué)學(xué)報(bào)(人文社科版)》2006年第3期)
總體而言,“民族形式”論爭所達(dá)成的認(rèn)識(shí)、觀念及其實(shí)踐,雖然取得了豐碩成果,但主要是在延安以及解放區(qū)范圍內(nèi),尚未推向全國,也未能完成對(duì)當(dāng)時(shí)書面漢語的全面改造。
(三)徹底改造階段
對(duì)1949年以前“舊語文”的徹底改造,始于新中國成立后的1950年代。關(guān)于建國前的書面語及其使用情況,周有光以報(bào)刊文章為例指出,以《大公報(bào)》為代表,都是“半文半白”而“文多于白”,被稱為“新聞體”。這種文體,只適合上層知識(shí)分子,不適合文化較低的廣大群眾,即使看了可以懂,讀起來是聽不懂的。[22]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新中國成立后面臨的國際、國內(nèi)形勢(shì),很快推動(dòng)中共中央把文字改革提上工作日程。因?yàn)橐环矫妫@是國民經(jīng)濟(jì)恢復(fù)發(fā)展和新中國掃盲運(yùn)動(dòng)的需要;另一方面,它也被當(dāng)作新中國對(duì)舊有文化改造的組成部分。[23]
1955年,有關(guān)部門組織召開了“現(xiàn)代漢語規(guī)范問題學(xué)術(shù)會(huì)議”和“全國文字改革會(huì)議”,這是中國語言規(guī)劃史上兩次非常重要的會(huì)議,它標(biāo)志著我國的語言規(guī)劃進(jìn)入完全由政府主導(dǎo)、社會(huì)各界和人民大眾廣泛參與的歷史新時(shí)期,開始了有目標(biāo)、有組織、有領(lǐng)導(dǎo)、有計(jì)劃的大規(guī)模社會(huì)語言規(guī)劃活動(dòng),[24]其在書面語改造方面的基本目標(biāo),就如劉少奇所說:“我們的邏輯,我們的造句文法,我們的選詞用字都必須使人人能懂。”[25]
經(jīng)過從中央到地方,從學(xué)術(shù)界到普通民眾的共同努力,現(xiàn)代書面漢語到1955 年已“基本形成”[26]。學(xué)界對(duì)此已有很多歸納總結(jié),比如陳章太指出:在以前文體改革的基礎(chǔ)上,徹底完成文體改革,白話文完全替代文言文。具體任務(wù)有5項(xiàng):書面語口語化,新聞、公文、布告等用白話文寫作;漢字排版、書寫橫排、橫寫;采用新式標(biāo)點(diǎn)符號(hào);采用阿拉伯?dāng)?shù)字;進(jìn)行文風(fēng)改革。[27]王定芳認(rèn)為,新中國成立后,無論是書報(bào)雜志,還是政府公文,用的都是口語化的白話文,白話文得到全面實(shí)行,終于實(shí)現(xiàn)了“言文一致”的書面語改革。在此基礎(chǔ)上提出了現(xiàn)代漢語規(guī)范化的方向和原則,引導(dǎo)白話文更加純潔健康地發(fā)展。白話文的全面實(shí)行和現(xiàn)代漢語的逐步標(biāo)準(zhǔn)化、規(guī)范化,是書面語改革的重大收獲。與百年前相比,書面語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漢語言文字現(xiàn)代化的諸項(xiàng)內(nèi)容中,書面語改革、書面語現(xiàn)代化是最徹底最成功的。[28]
(四)小結(jié)及余論
中國語文現(xiàn)代化在中國現(xiàn)代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新中國成立以前,它是新文化運(yùn)動(dòng)的一個(gè)組成部分;新中國成立以后,它成了國家的一項(xiàng)重要國策,是社會(huì)主義建設(shè)的重要一環(huán)。[29]現(xiàn)代漢語書面語從“五四”時(shí)期基本形成,到建國后最終定型,既是中國語文現(xiàn)代化運(yùn)動(dòng)的結(jié)果,同時(shí)也反映了它的努力與追求,二者之間是密不可分的。如果稍加總結(jié),基于對(duì)本階段漢語書面語現(xiàn)狀及其發(fā)展的了解,結(jié)合語文現(xiàn)代化運(yùn)動(dòng)的具體事實(shí),我們對(duì)其性質(zhì)與目標(biāo)有以下兩點(diǎn)認(rèn)識(shí)。
其一是革命化,它是語文現(xiàn)代化的重要推力,并且在相當(dāng)程度上決定了其服務(wù)對(duì)象與理想目標(biāo)。卞覺非指出,我國在追求現(xiàn)代化的目標(biāo)中,提倡白話文和推行新文字始終被看成是革命的組成部分。[30]建國之前,相關(guān)主張及實(shí)踐是政治斗爭以及身份識(shí)別與認(rèn)同的工具,周薦曾以雅、俗詞語的使用為例,對(duì)此作過很好的說明:“詞語雅俗間的角力,在20世紀(jì)上半葉國共兩黨的決戰(zhàn)中顯得尤其突出。國共兩大陣營的眾多領(lǐng)袖人物都是運(yùn)用自己的母語――漢語的高手,但他們所用詞語的雅俗卻有著截然的不同。這種現(xiàn)象的出現(xiàn)很難從他們各自的教養(yǎng)上找到原因,因?yàn)閮纱箨嚑I領(lǐng)袖階級(jí)的人物中有相當(dāng)一批曾受過良好的教育,有的甚至同出一門(如同出身黃埔);而只能從他們?yōu)橹?wù)、獻(xiàn)身的階級(jí),從他們所建立的政權(quán)的基礎(chǔ)上尋找原因。”[31]107-108
建國之后,語文現(xiàn)代化的政治色彩與性質(zhì)得到進(jìn)一步突顯。此時(shí),語言對(duì)于鞏固剛剛建立的政權(quán)當(dāng)然是至關(guān)重要的,語言為國家政權(quán)服務(wù)的政治目的體現(xiàn)尤為明顯,而語言規(guī)劃的突出特征就是其政治性。[32]此外,在政治立場(chǎng)及觀念下,新中國也要在文化等領(lǐng)域與舊中國切割,而語言是其中的一個(gè)重要方面:舊中國半文半白的書面語面貌需要改變,甚至于連民族共同語的名稱也要改為“普通話”而不再保留“國語”的舊名。
關(guān)于建國后改“國語”為“普通話”的原因,一般的解釋是:“為了體現(xiàn)各民族的平等與相互尊重,為了避免少數(shù)民族誤以為國家只推行漢語而歧視少數(shù)民族語言。”[33]然而,在我們看來,除此之外還另有原因,這就是為了與“國民黨及其以前的時(shí)代”作有效的區(qū)隔。
中國共產(chǎn)黨機(jī)關(guān)報(bào)《人民日?qǐng)?bào)》1951年6月6日發(fā)表的社論《正確地使用祖國的語言,為語言的純潔和健康而斗爭!》,對(duì)中國的語言規(guī)劃以及現(xiàn)代漢語的發(fā)展影響深遠(yuǎn),該文的一段話可以作為我們以上觀點(diǎn)的一個(gè)明證:
應(yīng)當(dāng)指出:正確地運(yùn)用語言來表現(xiàn)思想,在今天,在共產(chǎn)黨所領(lǐng)導(dǎo)的各項(xiàng)工作中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在國民黨及其以前的時(shí)代,那些官僚政客們使用文字的范圍和作用有限,所以他們文理不通,作出又長又臭的文章來,對(duì)于國計(jì)民生的影響也有限。而在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dǎo)下的中國就完全不同了。黨的組織和政府機(jī)關(guān)的每一個(gè)文件,每一個(gè)報(bào)告,每一種報(bào)紙,每一種出版物,都是為了向群眾宣傳真理、指示任務(wù)和方法而存在的。它們?cè)谌罕娭杏绊憳O大,因此必須使任何文件、報(bào)告、報(bào)紙和出版物都能用正確的語言來表現(xiàn)思想,使思想為群眾所正確地掌握,才能產(chǎn)生正確的物質(zhì)的力量。
這樣,兩個(gè)不同的名稱自然就具有了兩種不同的政治內(nèi)涵。[34]
其二是通俗化,它反映了語文現(xiàn)代化的目標(biāo)定位,同時(shí)也決定了現(xiàn)代書面漢語的基本精神與面貌。這一點(diǎn),“五四”新文化運(yùn)動(dòng)的先行者們就不斷提出,可以說,通俗化以及與之密切相關(guān)的大眾化,成了貫穿整個(gè)中國語文現(xiàn)代化運(yùn)動(dòng)的一條主線,即如韓立群所說:“貫穿始終的以通俗化為目標(biāo)的觀念,其基本傾向是強(qiáng)調(diào)語言形式的‘口頭告白性質(zhì)’。從三十年代‘大眾語’運(yùn)動(dòng)到抗戰(zhàn)時(shí)期的‘口語化’運(yùn)動(dòng),這種傾向愈來愈明顯,并且逐步由理論付諸實(shí)踐。”[35]王均也認(rèn)為,20世紀(jì)30年代開始提倡的普通話有三個(gè)特點(diǎn),其中第二個(gè)是大眾的,也就是“俗語”,不是雅語。[36]
關(guān)于這種通俗化的語言策略,趙樹理曾有明確的表述。在談到自己處理作品語言的經(jīng)驗(yàn)時(shí),他說:“‘然而’聽不慣,咱就寫成‘可是’;‘所以’生一點(diǎn),咱就寫成‘因此’;不給他們換成順當(dāng)?shù)淖盅郏麄兙筒辉敢饪础W盅蹆喝绱耍渥右彩峭瑯拥牡览怼渥娱L了人家聽起來捏不到一塊兒,何妨簡短些多說幾句;‘雞叫’本來很習(xí)慣何必寫成雞在叫狗在咬呢?”[37]
在中國語文現(xiàn)代化的進(jìn)程中,革命化的目標(biāo)與通俗化的追求其實(shí)是互為因果、互為表里的,以下一段話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diǎn):
毛澤東在井岡山革命根據(jù)地時(shí)期就強(qiáng)調(diào),宣傳黨的方針政策要力求通俗易懂,倡導(dǎo)大眾化、通俗化的文風(fēng),讓艱深晦澀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深入人心,和勞苦大眾溶為一體。加之當(dāng)時(shí)蘇維埃政權(quán)所在地的瑞金地處贛南,經(jīng)濟(jì)非常落后,交通不便,文化教育事業(yè)基本上是一片空白,群眾的受教育程度極低。當(dāng)時(shí)的最大任務(wù)是解決占人口 80%以上的工農(nóng)群眾的受教育問題,文學(xué)作品的藝術(shù)成就和總體水平要求不是很高,主要目的在于宣傳鼓動(dòng)群眾參加革命。在這樣的形勢(shì)下,蘇區(qū)革命文學(xué)的特點(diǎn)逐步地走向通俗化。[38]
建國以后的語文現(xiàn)代化運(yùn)動(dòng),無疑仍是貫徹這一路線與方向,不斷鞏固強(qiáng)化、拓展加深、推廣普及,最終實(shí)現(xiàn)文體的口語化,達(dá)成言文一致的目標(biāo)。
三、現(xiàn)代書面漢語的特點(diǎn)及其表現(xiàn)
中國語文現(xiàn)代化進(jìn)程中的革命化目標(biāo)與通俗化追求及其實(shí)現(xiàn),最終鑄成了現(xiàn)代書面漢語最基本、最重要的特點(diǎn),并且在建國后直至當(dāng)下的書面語及其使用中都有充分的表現(xiàn)。本小節(jié)中,我們就此展開討論。
(一)口語化:現(xiàn)代書面漢語的最重要特點(diǎn)
如前所述,“文體口語化”是語文現(xiàn)代化的四項(xiàng)任務(wù)之一,并且實(shí)際上也是它的不懈追求之一。由此,我們就可以歸納出現(xiàn)代書面漢語的重要特點(diǎn):口語化。這個(gè)“口語化”與上邊我們所說的“通俗化”也是高度一致的。很多學(xué)者均論及這一特點(diǎn),比如有人指出,中國大陸承繼了“五四”和解放區(qū)的傳統(tǒng),說白話,寫白話,文風(fēng)樸實(shí)、易懂,言文一致,說出來的話大家聽得清,寫出來的文章大家看得懂。……我國的報(bào)紙、雜志、影視媒體、國家文書、法律法規(guī)、商業(yè)契約等都普遍使用明白易懂的口語化的文體。[30]
毫無疑問,“口語化”的“口語”指的是“通俗易懂”的大眾的口語,所以,同樣的意思,人們也經(jīng)常表述為“大眾化”或“通俗化”。比如,周殿生著眼于海峽兩岸民族共同語的對(duì)比指出,臺(tái)灣“國語”在很大程度上繼承和沿襲了“五四”以后白話文的某些特點(diǎn),即使是口語也不乏斯文;而大陸的普通話則更多地表現(xiàn)為大白話和大眾化,因此更為普通化[39];于年湖、王少梅從“具有口語色彩的詞越來越多地在公文中使用”及“縮略語在公文中的大量使用”等方面說明了本應(yīng)最具書面語特征的公文語言在當(dāng)下的“通俗化傾向”。[40]
說到特點(diǎn),一定要從比較中得出,所以人們?cè)谡劦浆F(xiàn)代書面漢語“口語化”這一特點(diǎn)時(shí),經(jīng)常立足于海峽兩岸民族共同語的對(duì)比。韓敬體指出,解放后,大陸語文教育提倡語體文,倡導(dǎo)言文一致,作品語言趨向口語化,不少文言詞被語體詞或短語所取代,書面語中傳承的帶文言色彩的詞語大為減少,書信用語也語體化了。[41]
現(xiàn)代書面漢語“口語化”這一特點(diǎn)也可以通過一些學(xué)者對(duì)臺(tái)港澳語用狀況的描述對(duì)比顯現(xiàn)。澳門學(xué)者黃翊這樣寫道:“在港澳寫作人和閱讀人心目中,幾乎形成一個(gè)共識(shí)或風(fēng)氣:半文半白的作品或兼用文言詞語的作品常被認(rèn)為具有古雅的風(fēng)格,表明此類文章的作者是念過書、有文化的人。”[42]毫無疑問,這樣的共識(shí)或風(fēng)氣在中國大陸或內(nèi)地,基本已經(jīng)不存在了,以下一段話對(duì)這此說得非常清楚:
“理論上,口語、書面語分屬不同系統(tǒng),但經(jīng)由晚清以降的白話文運(yùn)動(dòng),以及新中國成立以后的普通話推廣運(yùn)動(dòng),今日中國人的‘說話’與‘作文’之間,差別不是很大。尤其是中國大陸的文人學(xué)者,更多受陳獨(dú)秀、胡適、魯迅、周作人等‘五四’新文化人的影響,希望拆除我們/他們、文言/白話的藩籬,而拒絕劉師培、蔡元培兼及文言的主張,故所撰文章普遍比較直白、淺俗、酣暢。反觀臺(tái)灣及香港的文化人,似乎更愿意在二者之間保留必要的縫隙。這一差異,說話時(shí)隱約感覺到,寫文章或正式典禮上致辭,就更顯豁了。”[43]
筆者多年從事海峽兩岸民族共同語的對(duì)比研究,后來由此進(jìn)一步擴(kuò)展到兩岸四地以至于全球華語的范圍。通過對(duì)比,對(duì)現(xiàn)代漢語(普通話)書面語的上述特點(diǎn)有了越來越清晰的認(rèn)識(shí)。我們?cè)?jīng)用“兩個(gè)距離”的差異來總結(jié)與歸納海峽兩岸的語言差異及其造成原因:一是與早期國語的距離,大陸遠(yuǎn)大于臺(tái)灣;二是書面語與口語的距離,臺(tái)灣遠(yuǎn)大于大陸。[44]至于以上兩個(gè)距離差異的產(chǎn)生原因,就普通話一方說,正是語文現(xiàn)代化運(yùn)動(dòng)所追求的目標(biāo)及其結(jié)果。
(二)“口語化”特點(diǎn)的具體表現(xiàn)
現(xiàn)代書面漢語的上述特點(diǎn)在詞匯方面表現(xiàn)得最為充分,所以我們就以此為例進(jìn)行說明[注]在語法等其他方面也有很多表現(xiàn)值得總結(jié),限于篇幅,本文暫且不提。。著眼于普通話與非普通話的對(duì)比,我們概括為一“多”一“少”。
一“多”,是方俗詞語多。
方俗詞語多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建國以后新產(chǎn)生很多此類詞語,且往往有一定甚至很高的使用頻率;二是很多舊有的此類詞語擴(kuò)大使用范圍,或者提高了使用頻率。
關(guān)于前一方面,有人指出,20世紀(jì)尤其是50年代以來,祖國大陸和臺(tái)灣社會(huì)漸趨穩(wěn)定,漢語在兩岸各自贏得了一個(gè)重要的發(fā)展時(shí)期。在大陸,此一時(shí)期最為引人矚目的現(xiàn)象之一是伴隨著俗文化的增長,俗詞語加速度地大量產(chǎn)生出來,例如“一風(fēng)吹、鐵算盤、抬轎子、生荒地、家長里短、大手大腳、三三兩兩、一了百了”等。[31]110我們隨意翻檢熊忠武主編的編年體《當(dāng)代中國流行語辭典》(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屬于此類的詞語數(shù)量不少,比如1951年的“大鍋飯、工人老大哥、寬大無邊、美國大鼻子、美國鬼子、訴苦”;1955年的“大包工、混入黨內(nèi)、黑題目、紅月亮、九個(gè)指頭和一個(gè)指頭、兩本帳、兩條腿走路、潑冷水、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chǎn)、上馬、照妖鏡、坐衛(wèi)星”。
關(guān)于后一方面,表現(xiàn)也非常充分,其中最具典型性的是一組“萬能動(dòng)詞”的高頻使用。筆者曾經(jīng)對(duì)屬于此類的“搞、干、弄”等進(jìn)行過較為細(xì)致的討論,[45]特別是使用量最大的“搞”,我們還專門進(jìn)行過兩岸四地的對(duì)比研究,[46]包括對(duì)其使用范圍及頻率等的調(diào)查與分析,一個(gè)明顯的事實(shí)是,所得數(shù)據(jù)遠(yuǎn)高于同期的臺(tái)港澳地區(qū)。
與“搞”異曲同工的還有一個(gè)“抓”,《現(xiàn)代漢語詞典》的釋義是“加強(qiáng)力量做(某事)、管(某方面)”,這個(gè)動(dòng)詞的使用頻率也非常高,可以與之共現(xiàn)、充當(dāng)其賓語或?qū)ο蟮脑~語也相當(dāng)多,而隨著賓語或?qū)ο蟮牟煌渌硎镜恼Z義關(guān)系也有所不同,比如“抓革命、抓農(nóng)業(yè)、抓階級(jí)斗爭、抓科研、抓計(jì)劃生育”等。此外,此詞也用于一些固定或比較固定的組合形式,如“齊抓共管、真抓實(shí)干、抓大放小、嚴(yán)抓嚴(yán)管、嚴(yán)抓不放、抓出成效、抓嚴(yán)抓實(shí)抓細(xì)”等。《人民日?qǐng)?bào)》華東版1998年11月30日曾刊登一篇文章,說某縣一位領(lǐng)導(dǎo)干部在一次報(bào)告中強(qiáng)調(diào)了25個(gè)“抓”,內(nèi)容是“抓思想教育、抓認(rèn)識(shí)深化、抓重點(diǎn)部位、抓工作機(jī)制、抓薄弱環(huán)節(jié)、抓計(jì)劃制定、抓工作突破、抓典型示范、一把手親自抓、各級(jí)領(lǐng)導(dǎo)都要抓、分管領(lǐng)導(dǎo)具體抓、工青婦部門一齊抓、抓管理、抓鞏固、抓深化、抓評(píng)比、抓監(jiān)督、抓后進(jìn)、抓整改……”。[47]
對(duì)此,曾經(jīng)有臺(tái)灣學(xué)者感到大惑不解,因而這樣說道:“如‘抓’、‘搞’這兩個(gè)語意粗鄙的動(dòng)詞,使用范圍相當(dāng)廣泛,從抽象的權(quán)柄,勞動(dòng),到具體實(shí)物,都可一貫使用。”[48]
一“少”,是指“古雅”詞語少,主要是文言詞語用得少。
這一點(diǎn),從海峽兩岸語言運(yùn)用對(duì)比這一視角來看,也非常明顯,學(xué)者們也早就注意到了。李志江指出,相比較而言,大陸的普通話更為崇尚口語,許多書面語詞在大陸已漸罕用,甚至不用,退而成為古語詞;臺(tái)灣的“國語”更為強(qiáng)調(diào)傳承,許多書面語詞在臺(tái)灣一直使用,甚至在口語中也十分活躍。[49]金振邦著眼于兩岸應(yīng)用文體的差異指出,港臺(tái)應(yīng)用文中還保留著相當(dāng)數(shù)量繁瑣陳舊的術(shù)語,如大陸已不用的送禮帖中的“代障、代料、桃儀、喬儀、程儀、鵝金、鏡屏、奠儀、祭儀、祭幛、祭筵”等;還有喪葬禮帖專用的“壽終正寢、壽終內(nèi)寢、初終、成殮、享壽、成服、開吊、反服、斬衰、斯年、孤子、哀子、孤哀子、棘人”等;還有訃聞中的用語,如“罪孽深重,不自殞滅,禍延顯祖考”,“泣血稽顙、抆淚稽首”等。[50]萬星也開列了一些臺(tái)灣仍在使用,而大陸已經(jīng)或基本不用的喪葬用語,如“哲人其萎、生勞死哀、懿復(fù)長昭、德范堪欽、福壽全歸、懿范長存、挽環(huán)、星沉宿海、哀挽、遺澤千古、德被群倫、為聯(lián)敬挽之、千秋永別、永垂范澤、同泣啟、同泣叩”等。[51]
臺(tái)灣之外,港澳以及其他華語社區(qū)大致也是如此。新加坡的周清海先生曾講過一段他的親身經(jīng)歷:“很多年以前,我曾主持印度外交官語言考試,發(fā)現(xiàn)他們讀得懂《人民日?qǐng)?bào)》的評(píng)論文章,而對(duì)我們《聯(lián)合早報(bào)》的社論,閱讀的困難卻比較大,就是因?yàn)椤堵?lián)合早報(bào)》保留了許多文言的現(xiàn)象。”[52]施春宏則比較了泰式華文與普通話書面語在這方面的差異:相對(duì)于普通話,泰式華文詞語的“歷史”色彩較濃,這首先表現(xiàn)在其字義或詞義顯得比普通話要“古舊”一些,即文言色彩明顯。……泰式華文詞語“歷史”色彩較濃的更為顯著的標(biāo)志是,一些在普通話詞匯系統(tǒng)中被看作歷史詞或準(zhǔn)歷史詞(即在特定表達(dá)中偶有使用)的詞語,在泰式華文中的使用仍比較普遍。文中舉了“庶民、冠蓋、矢言、墟日、京畿、苦主”等的用例,最終結(jié)論是:“從普通話的視角來看,泰式華文的‘文白夾雜’現(xiàn)象比較顯著。”[53]
以上的一“多”一“少”能說明什么?或者說我們應(yīng)當(dāng)怎樣認(rèn)識(shí)這一現(xiàn)象?以下從“語體”的角度來進(jìn)行初步的分析。
馮勝利建立了一個(gè)丁字形二元對(duì)立的語體模式,其結(jié)構(gòu)圖示如下:[54]6

馮勝利認(rèn)為,就書面語來說,包含俗常、正式與莊典三種文體。與此大致可以類比,崔希亮區(qū)分了現(xiàn)代漢語書面語的三重境界,其一是正確的書面語,其二是明白的書面語,其三是典雅的書面語,認(rèn)為這是現(xiàn)代漢語書面語的三個(gè)層次。[55]
詞匯使用與語體之間的關(guān)系非常密切:詞匯是有語體屬性的,語體不同用詞不同,不同的詞用于不同的語體。[56]由上述一“多”一“少”可以看出,現(xiàn)代書面漢語中多的是俗常因素,而少的則是莊典因素。馮勝利也就兩岸三地的對(duì)比指出:“大陸正式語體逐步成熟的同時(shí),港臺(tái)的特殊文化和環(huán)境則保持著莊典語體的發(fā)展。”[54]13
結(jié)合以上圖示及表述,我們大致可以對(duì)現(xiàn)代書面漢語作一個(gè)語體方面的描述:總的來說是壓“高”就“低”,即通過減少古代詞語(此外也包括古代句式等)數(shù)量及使用頻率的方式,來達(dá)成和實(shí)現(xiàn)正式書面語的通俗化與口語化。換句話說,現(xiàn)代正式體的書面漢語離莊典語體遠(yuǎn)而離俗常語體近。
文學(xué)是語言的藝術(shù),所以文學(xué)界對(duì)現(xiàn)代書面漢語的上述特點(diǎn)及其表現(xiàn)極為關(guān)注,并多有評(píng)論。有人指出:“(新的文學(xué)語言)應(yīng)能適應(yīng)服務(wù)于以‘工農(nóng)兵’為主體的‘大眾’這一目標(biāo)。這種大眾的初等或初等以下文化程度決定了新的文學(xué)語言的一條重要標(biāo)準(zhǔn):非文人化或非知識(shí)分子化,為工農(nóng)兵大眾所喜聞樂見。為達(dá)到這一標(biāo)準(zhǔn),就需要對(duì)以前的文學(xué)語言傳統(tǒng)來一次新的整合:語言俗化,也就是語言的大眾化或通俗化。”[57]有人甚至認(rèn)為,新文化運(yùn)動(dòng)百年是一個(gè)舍雅求俗、棄精取粗的全過程:“在一百年當(dāng)中,中國文學(xué)作為語言現(xiàn)象,是一個(gè)不斷俗化、不斷把文學(xué)語言降低為現(xiàn)實(shí)語言的流程。”[58]
四、對(duì)幾個(gè)相關(guān)問題的認(rèn)識(shí)與反思
經(jīng)過幾代人一百多年的努力,中國語文現(xiàn)代化運(yùn)動(dòng)無疑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就其具體表現(xiàn)及結(jié)果來看,恐怕也并未止于至善,而由此就引發(fā)了我們的一些思考與反思,主要有以下幾點(diǎn)。
(一)一元與多元
所謂一元,就是堅(jiān)持單一的目標(biāo)、滿足單一的需求,而多元?jiǎng)t是在此基礎(chǔ)上考慮更多的因素,滿足更多人對(duì)語言文字的更多訴求。總體而言,我們認(rèn)為語文現(xiàn)代漢語運(yùn)動(dòng)中言文一致的追求及目標(biāo)過于單一,主要表現(xiàn)是并未真正以整個(gè)社會(huì)各個(gè)層次與階層的全體民眾為服務(wù)對(duì)象。具體而言,即如以下一段文字所說:
在19世紀(jì)末興起的張揚(yáng)人的理性本質(zhì)之啟蒙主義大方向下,有識(shí)之士們極力要使語言文字服務(wù)于人的求知活動(dòng)。而且在“開民智”思想的指導(dǎo)下,他們更注重語言文字改革為下層民眾的求知活動(dòng)服務(wù)。他們認(rèn)為,改革者的心目中更應(yīng)當(dāng)有“千中九百九十九之農(nóng)工百業(yè)毫未學(xué)問之人”[注]引者按,此語出自王照《普通字義辯》,見其所著《官話合聲字母》。,文化建設(shè)的重點(diǎn)應(yīng)是“教凡民”。……他們的語言文字改革,主要致力于“造就下流社會(huì)之利器”[注]引者注,此語出自沈鳳樓在半日學(xué)堂開學(xué)典禮上的演說,轉(zhuǎn)引自倪海曙《清末漢語拼音運(yùn)動(dòng)編年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27頁。,為此而力求文字易認(rèn)易識(shí),語言通俗易曉,書面語與口頭語相一致,利于“普通”民眾學(xué)習(xí)“普通”知識(shí),便于社會(huì)各個(gè)階級(jí)、階層之間的信息、感情的溝通和交流。[59]
正因?yàn)槿绱耍杂腥苏J(rèn)為,語文現(xiàn)代化運(yùn)動(dòng)“自始至終貫穿著‘五四’運(yùn)動(dòng)所提倡的‘平民化與大眾化’的精髓”[60]。
建國之后,語文現(xiàn)代化目標(biāo)人群亦即服務(wù)對(duì)象就更加明確了:新中國成立后,實(shí)現(xiàn)了人民當(dāng)家作主,但是80%的人不識(shí)字的現(xiàn)實(shí),限制了人民民主權(quán)利的運(yùn)用。要使文盲半文盲迅速地掌握使用文字,不能不正視傳統(tǒng)繁體字的難認(rèn)、難記、難寫不易掌握的問題。為了使廣大勞動(dòng)人民比較容易地掌握文字工具來學(xué)習(xí)文化技術(shù),更充分地運(yùn)用民主權(quán)利,而大力推行文字改革,這是中國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dǎo)新中國文字改革的初衷和出發(fā)點(diǎn)。[23]
縱觀一百多年的語文現(xiàn)代化運(yùn)動(dòng),確實(shí)是幾乎只著眼于“千中九百九十九之農(nóng)工百業(yè)毫未學(xué)問之人”,并且在“教凡民”“開民智”“造就下流社會(huì)之利器”這種單一目的之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開創(chuàng)了我國語言文字及其使用的新局面。但是,站在今天的立場(chǎng),立足于對(duì)現(xiàn)代書面漢語的審視,我們不禁要反思“一元與多元”的問題。
一般社會(huì)中,如果作最粗略的劃分,與上述單一目標(biāo)人群相對(duì)的是“識(shí)文斷字”的知識(shí)分子,而在這場(chǎng)深入持久的語文改革運(yùn)動(dòng)中,知識(shí)分子的利益與訴求顯然被有意地忽略了。早在1957年,就有語言學(xué)家指出:“文字該不該改革,不決定于五百萬知識(shí)分子對(duì)漢字的感情,而決定于六萬萬人的利益”,“文字改革本來不是為著現(xiàn)在已認(rèn)識(shí)方塊字的知識(shí)分子,而是為著現(xiàn)在還不認(rèn)識(shí)字和將來要認(rèn)識(shí)字的千百萬勞動(dòng)人民和我們的子孫萬代。”[注]詳見《1957年文字改革辯論選輯》(新知識(shí)出版社,1958年版)第198頁。轉(zhuǎn)引自王愛云《中國共產(chǎn)黨與新中國文字改革(1949— 1958)》(載《黨史研究與教學(xué)》2009年第6期)。這里說的是文字,但其具體所指顯然并不止此,而是包括語言文字的方方面面。
文學(xué)界與思想界對(duì)這個(gè)問題的認(rèn)識(shí)可能更深入一些,有人指出:“‘言文一致問題’不僅是一個(gè)知識(shí)命題,也是一個(gè)權(quán)力命題,表面上是書面語和口語之間的關(guān)系,實(shí)際對(duì)應(yīng)的恰是知識(shí)分子和工農(nóng)大眾,深層涌動(dòng)著民粹主義思潮,或曰大眾崇拜。且看建國后歷次運(yùn)動(dòng),被整治清肅者無不是教授和知識(shí)分子,知識(shí)分子與民眾結(jié)合,是惟一正當(dāng)?shù)某雎罚m可對(duì)應(yīng)‘言文一致’運(yùn)動(dòng),換句話說,被語言革命所吞沒者,正是早期語言革命的倡導(dǎo)者,知識(shí)分子在這場(chǎng)革命運(yùn)動(dòng)中,不僅要廢除漢字,甚至還要消滅自我。”[61]
上述“吞沒”與“消滅”的具體表現(xiàn),就是現(xiàn)代書面漢語“雅”與“俗”因素的此消彼長,由此最終形成其“口語化”的突出特點(diǎn)。
以下我們將要討論的兩個(gè)問題也與上述“單一性”有密切關(guān)系。
(二)“工具論”與“經(jīng)濟(jì)論”
在語文現(xiàn)代化的實(shí)踐及其研究中,“工具”是一個(gè)高頻詞,在具體的研究成果中,很多都有相關(guān)的表述。例如,有人認(rèn)為,由“文學(xué)工具革命”催生了真正意義上的漢民族共同語,結(jié)束了兩千年來我國文言分離的歷史,確立了白話文學(xué)的正宗地位,白話最終成為漢民族文學(xué)和教育的有效工具。這不僅是我國語文現(xiàn)代化的一項(xiàng)偉大成果,就是放在數(shù)千年中華文明發(fā)展進(jìn)程中來看,也是一個(gè)劃時(shí)代的貢獻(xiàn)[62]。還有人指出:“中國語文為什么要現(xiàn)代化?一句話:就是要讓中國人有簡便易學(xué)、省力、高效率的語言文字工具,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國民素質(zhì)和促進(jìn)現(xiàn)代化建設(shè)。”[63]
縱觀一百多年的中國語文現(xiàn)代化運(yùn)動(dòng),我們完全有理由把它表述為“語文工具的革命”。但是,由于上述目標(biāo)人群的單一性,以往所強(qiáng)調(diào)的工具,也具有明顯的單一性。卞覺非認(rèn)為,過去的文字改革工作在當(dāng)時(shí)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把注意力集中在漢字簡化方面,是有進(jìn)步意義的,因?yàn)楫?dāng)時(shí)的突出問題是要解決漢字難學(xué)、難寫的問題。這顯然是從漢字的工具屬性著眼的緣故。但不容忽視的是它卻忽視了漢字的其他屬性。事實(shí)上,文字至少有三個(gè)屬性值得注意:一是書寫工具;二是文化屬性,它是文化的載體;三是它的社會(huì)屬性。第一點(diǎn)人們過去考慮得比較多,第二、第三點(diǎn)卻重視不夠。[64]這里說的是文字,無疑也是包括語言在內(nèi)的。而由于上述第二、三兩點(diǎn)重視不夠,就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以下事實(shí):語言文字決不僅僅只是人們常說的工具、符號(hào),它的發(fā)達(dá)根系深扎于所生長的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同時(shí)它的每一根根須都與中華民族文化的筋脈相聯(lián)系。[65]很顯然,單一的、簡單的工具論是無法涵蓋語言文字全部功能的,而在客觀上,對(duì)語言文字狹隘的工具論理解也阻礙了人們?nèi)フ_認(rèn)識(shí)它與民族文化傳統(tǒng)以及個(gè)人內(nèi)在心理和思維之間的連帶關(guān)系。所以,有人認(rèn)為,從切音字母到合聲簡字再到國語概念的提出,雖然呈現(xiàn)了認(rèn)識(shí)上的遞進(jìn),但“簡易文字”和“統(tǒng)一語言”的要求都沒能最終落實(shí)到主體精神的層面。[66]
在“工具論”的理論與認(rèn)識(shí)下,“經(jīng)濟(jì)論”自然產(chǎn)生,以下一段話非常有代表性:
語文現(xiàn)代化的指導(dǎo)思想是語言文字經(jīng)濟(jì)學(xué)。一般意義的經(jīng)濟(jì)學(xué),研究在經(jīng)濟(jì)領(lǐng)域如何實(shí)現(xiàn)投入最小化,效益最大化;把這個(gè)思想移植到語言文字領(lǐng)域,就是要研究人們?cè)谡莆铡⑹褂谜Z言文字方面,如何以最小的投入,獲取最大的效益——這就是語言文字經(jīng)濟(jì)學(xué),或者叫做經(jīng)濟(jì)學(xué)思想指導(dǎo)下的語言文字學(xué)。用這個(gè)指導(dǎo)思想來看語言文字為什么要現(xiàn)代化,為什么能夠現(xiàn)代化,展開一點(diǎn)說就是:第一,因?yàn)檎Z言文字是工具的一種。車輛、輪船、飛機(jī)是人類的運(yùn)輸工具,語言文字是人類交流、思維的工具。運(yùn)輸工具要方便、省力、高效率,交流、思維的工具同樣要方便、省力、高效率。第二,人的壽命是一個(gè)常量,學(xué)習(xí)并掌握語言文字工具所需要的時(shí)間是一個(gè)變量。人的一生,掌握語言文字工具的時(shí)間縮短了,應(yīng)用語言文字工具去獲取信息、發(fā)送信息、思考問題的時(shí)間就增加了,為社會(huì)服務(wù)、創(chuàng)造價(jià)值的時(shí)間就延長了。[63]
以我們今天的認(rèn)識(shí)來看,語言文字固然是交流與思維的工具,因此使用中的經(jīng)濟(jì)性應(yīng)當(dāng)是一個(gè)重要的考量因素,但這不應(yīng)當(dāng)也不可能成為語言文字及其現(xiàn)代化的全部內(nèi)容,因?yàn)椋罢Z言還具有社會(huì)交際功能,其發(fā)展是離不開它的使用者和社會(huì)大環(huán)境的,語言規(guī)劃的目的就是優(yōu)化它的交際功能,從而取得社會(huì)文化效益乃至政治、經(jīng)濟(jì)效益。”[13]另外,一種語言始終伴隨著民族性和當(dāng)代性,在某種意義上,它是民族文化最為深層的歷史積淀,裏挾著極為深厚的文化底蘊(yùn),[67]11而這顯然就不是單一的“工具性”及“經(jīng)濟(jì)性”所能包含的。
有人在語文現(xiàn)代化研究中提出一個(gè)“語文感”的概念,具體包括語感與文化感,前者的對(duì)象是語言的形式,后者的對(duì)象則是語言的內(nèi)容。語言的內(nèi)容包含意義上的真假、道德上的善惡、文藝上的美丑等。從語文感討論語文現(xiàn)代化的問題才能夠全面[68]。按這一提法與思路,以往的語文現(xiàn)代化似乎只注重語感而忽略了文化感。
(三)白話與文言
這方面值得反思之處是,長期以來,我們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把白話與文言對(duì)立起來了,甚至看作非此即彼不可并存的兩種客觀存在?
“言文一致”是語文現(xiàn)代化運(yùn)動(dòng)的重要口號(hào),“言”指白話,而“文”則主要指?jìng)鹘y(tǒng)的書面漢語,即文言,“五四”以后還包括那種歐化的、半文半白的所謂“新文言”。按一般的道理,言文一致可以有三種達(dá)成路徑:一是以“言”統(tǒng)“文”,二是以“文”統(tǒng)“言”,三是“言”“文”融合,很顯然,我們的語文現(xiàn)代化采取的是第一種策略。關(guān)于這一點(diǎn),呂叔湘說得非常清楚:“語文現(xiàn)代化,照我的理解,包含兩個(gè)方面。一個(gè)方面是書面漢語的現(xiàn)代化,就是拋棄文言文,改用白話文。這件事從五四時(shí)代開始,很快就取得勝利。現(xiàn)在寫文章都用白話,只有少數(shù)作者有時(shí)候夾用文言詞語稍微多了點(diǎn),但是還不到‘喧賓奪主’的程度。”[69]
“拋棄文言文,改用白話文”顯系“以言統(tǒng)文”的直白表達(dá)。在這一觀念下,呂文委婉地批評(píng)了“夾用文言詞語稍微多了點(diǎn)”現(xiàn)象,而有人對(duì)此則用“徹底清除”表達(dá)了更加堅(jiān)定決絕的立場(chǎng):
書語口語化的目標(biāo)已經(jīng)基本實(shí)現(xiàn),除了個(gè)別文史專家寫新文言、半文言,少數(shù)人推崇文言(例如高考閱卷中給文言作文打高分),想在全局上恢復(fù)文言文是絕對(duì)不可能了。但是,白話文中夾雜文言詞語的現(xiàn)象短時(shí)間內(nèi)不容易消除,主要原因一是漢字很容易使文言殘留,二是錢玄同、趙元任、葉圣陶、王力、呂叔湘、周有光等前輩的語文思想得不到有力的宣傳,大多數(shù)人還不知道什么叫做“典范的、純粹的白話文”。“語文現(xiàn)代化”一方面堅(jiān)決反對(duì)“搖頭晃腦背論語,子曰詩云讀五經(jīng)”,一方面要在書面語中徹底清除文言“化石”。[63]
有人甚至從“思想”的高度進(jìn)一步拉升對(duì)此的認(rèn)識(shí):
書面語言口語化,經(jīng)過“白話文運(yùn)動(dòng)”,經(jīng)過解放以來的白話文教學(xué)和實(shí)踐,可以說已經(jīng)全面取代了文言文。白話文給漢語書面語的使用創(chuàng)造的價(jià)值也是無法估量的。然而,有人并不珍惜這個(gè)成果,文白夾雜,甚至復(fù)古傾向不時(shí)出現(xiàn)。有的是因?yàn)檎`導(dǎo),有的是思想問題。現(xiàn)代化的目的就是方便大眾,但有的人不管大眾。[70]
上述把文言與白話完全對(duì)立起來的認(rèn)識(shí)有非常深刻的政治背景,其實(shí)也就是我們上文所說語文現(xiàn)代化運(yùn)動(dòng)政治性的具體表現(xiàn)。有人就此指出,民國文言白話之爭,究其實(shí)質(zhì),是一場(chǎng)對(duì)立階級(jí)之間的政治斗爭。民國以前,文言、白話由于受到雅俗觀念的制約,基本處于對(duì)抗?fàn)顟B(tài),不同語體成了不同階級(jí)政治身份的象征:文言是上層統(tǒng)治階級(jí)的語言,白話是下層百姓群眾的語言。[71]
受語文現(xiàn)代化運(yùn)動(dòng)“大眾化”目標(biāo)的約束和驅(qū)使,最終的選擇毫無疑問只能是取白話而去文言。然而,從漢語史的角度來看,文言曾經(jīng)是古代的“白話”(口語)或與之相去不遠(yuǎn),而白話則是由文言分化發(fā)展而來,因此二者根本無法一刀兩斷。關(guān)于這一點(diǎn),以下的認(rèn)識(shí)比較中肯:
“現(xiàn)代漢語地位的確立,其實(shí)是古代漢語系統(tǒng)內(nèi)部兩股話語權(quán)力博弈斗爭的結(jié)果,最終白話系統(tǒng)取代文言系統(tǒng)具備了話語權(quán)。正因?yàn)槎咧g相生相克、對(duì)立統(tǒng)一,所以不管多么‘現(xiàn)代’,文言與白話,與后來的現(xiàn)代漢語總是藕斷絲連。……不少人因?yàn)楝F(xiàn)代漢語的‘現(xiàn)代性’而忘記了它的‘古代性’和‘文言性’,這既不符合歷史事實(shí),同時(shí)還妨礙了現(xiàn)代漢語的健康發(fā)展。”[72]
就現(xiàn)代書面漢語的實(shí)際看,情況也確實(shí)如此。
呂叔湘說:“新的書面語又會(huì)從舊的書面語吸收有用的成分:在現(xiàn)代漢語書刊里,文言成分,特別是利用文言詞素造成的新詞,比《水滸傳》和《紅樓夢(mèng)》里多得多。”[73]
李如龍就當(dāng)下的語用情況進(jìn)一步指出:上古、中古的詞匯經(jīng)常為現(xiàn)代漢語所用,成語、諺語、典故、引用語就是古語沿用于今語的通道。“閣下、光臨、拜見”還要經(jīng)常用于外交場(chǎng)合,“有朋自遠(yuǎn)方來,不亦樂乎”“海內(nèi)存知己,天涯若比鄰”經(jīng)常被引用,“登頂、下潛、鐫刻、解讀、遺存、境況、景觀、滯納”都是從文言來的,一旦需要表達(dá),就端出來用。維權(quán)可以設(shè)“驛站”,航班可以設(shè)“經(jīng)停”,網(wǎng)絡(luò)可以加以“遮蔽”,種種“沿襲啟用、改裝翻新、重新創(chuàng)造”都會(huì)使現(xiàn)代書面語和文言詞的界限模糊起來。[4]
正是基于這樣的認(rèn)識(shí),有人認(rèn)為,如果說得更徹底一些,只要還有漢語,只要漢語不死,我們的書面語就無法徹底根絕“文言成分”,口語中也難以完全杜絕作為“語言活化石”的“文言字眼”,除非漢語壽終正寢而為某種外語所徹底取代。即使是假如漢語真的滅亡了,漢語的“底層遺存”也會(huì)活在那種新的語言之中,從而在細(xì)微之處潛移默化地改變著那種語言。[26]
五、余論:語文現(xiàn)代化與現(xiàn)代漢語——永遠(yuǎn)在路上
1995年12月,江蘇省語言學(xué)會(huì)學(xué)術(shù)委員會(huì)邀請(qǐng)南京的部分語文工作者在南京大學(xué)以“語文現(xiàn)代化問題”為題進(jìn)行座談,[64]一些參加者談到自己對(duì)語文現(xiàn)代化運(yùn)動(dòng)的看法,其中以下幾個(gè)觀點(diǎn)令人印象深刻,在我們看來,既體現(xiàn)了對(duì)以往的反思,同時(shí)也表達(dá)了對(duì)未來的期許:
新文化運(yùn)動(dòng)以后的白話文忘記了漢語有詩一般的語言的美,漢語適合表達(dá)意境美、音樂美。
語文現(xiàn)代化的基礎(chǔ)是語文觀的現(xiàn)代化。在研究規(guī)范時(shí),必須考慮如何把“文人氣”與“從眾從俗”結(jié)合起來,不能只是“一廂情愿”。
我們今天提出語文現(xiàn)代化,是基于當(dāng)代中國建設(shè)現(xiàn)代化社會(huì)而考慮的,即“中國當(dāng)代語文的現(xiàn)代化”,目標(biāo)是適應(yīng)現(xiàn)代的社會(huì)生活。現(xiàn)代社會(huì)生活的特點(diǎn)之一是文化生活的分層化。
所謂語文現(xiàn)代化實(shí)際上是要解決如何使我們的漢語文更好地為社會(huì)服務(wù)的問題,這是我們提出語文現(xiàn)代化的一個(gè)基本出發(fā)點(diǎn)。要實(shí)現(xiàn)這一目標(biāo),基本的思考之一就是語文生活的多元化。
時(shí)下,“與時(shí)俱進(jìn)”早已由口號(hào)演變?yōu)樯钊肴诵牡挠^念,而這一觀念在中國語文現(xiàn)代化運(yùn)動(dòng)及相關(guān)研究中,似乎更多的是表現(xiàn)在工作內(nèi)容的增加,如有人在上述周有光所提四項(xiàng)任務(wù)的基礎(chǔ)上,又增加了信息處理的電腦化以及術(shù)語的國際化和標(biāo)準(zhǔn)化。[74]至于某一具體任務(wù)是否應(yīng)根據(jù)民眾以及社會(huì)文化等的發(fā)展變化而隨時(shí)調(diào)整,似乎并未引起更多的關(guān)注。比如,就言文一致來說,無論社會(huì)全體民眾的文化水平與受教育程度,還是社會(huì)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的發(fā)展水平與需求,都今非昔比,那么,在現(xiàn)實(shí)的條件下,我們的工作目標(biāo)是不是依然還要以“人人能懂”為唯一目標(biāo)?社會(huì)群體自身及其現(xiàn)實(shí)追求的多元化,當(dāng)下個(gè)人以及社會(huì)對(duì)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重新認(rèn)識(shí)與回歸取向,是否需要在語文現(xiàn)代化的指導(dǎo)方針及具體工作中體現(xiàn)出來?有人曾就此用很恰當(dāng)?shù)谋扔魑竦乇磉_(dá)了自己的意見:“面對(duì)即來的威脅與死亡,人們不會(huì)考慮如何養(yǎng)生。這是可以理解的,但今天,應(yīng)該是到了我們需要冷靜思考漢語書面語的過去、現(xiàn)在和將來的時(shí)候了。”[54]9在我們看來,對(duì)漢語書面語的冷靜思考也就是對(duì)中國語文現(xiàn)代化相關(guān)理論、思想與實(shí)踐的冷靜思考。我們的問題是,在多數(shù)人已經(jīng)達(dá)到或越過“溫飽”階段的今天,“養(yǎng)生”是否也應(yīng)該提上日程?
最后,回歸本文的主題:百年現(xiàn)代書面漢語是中國語文現(xiàn)代化的直接產(chǎn)物,二者互為鏡像。借由前者,我們可以反觀后者,明其得失,而這是當(dāng)前語文現(xiàn)代化及其研究應(yīng)有的一個(gè)立場(chǎng)與角度;立足后者,我們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與理解百年現(xiàn)代漢語書面語的發(fā)展變遷事實(shí)及其產(chǎn)生原因,同樣也可以明其得失。客觀地說,我們?cè)谶@兩個(gè)方面結(jié)合得都還不夠,由此也就留下了未來進(jìn)一步研究的空間,并且這樣的研究還要不斷地隨著社會(huì)的發(fā)展而發(fā)展,而這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永遠(yuǎn)在路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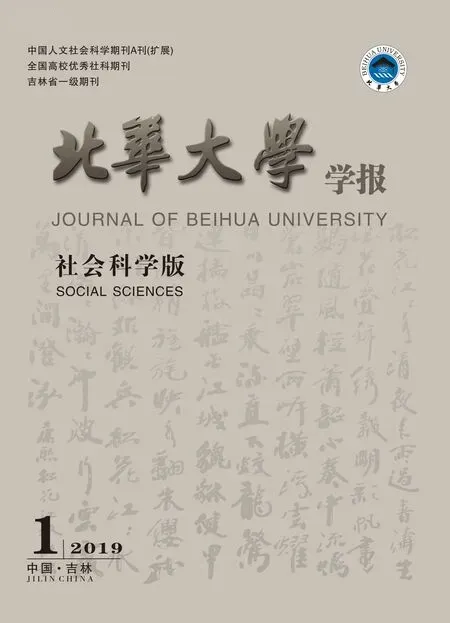 北華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9年1期
北華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9年1期
- 北華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的其它文章
- 《紫釵記》的送別空間書寫與情感抒發(fā)
- 《全明詞》作者小傳訂補(bǔ)
- 田錫交游考
- 涉華問題上日本政府與媒體的互動(dòng)性研究
- 西方民粹化民主的理論之根
- 多琳·馬西城市政治學(xué)中城市地理空間的三重維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