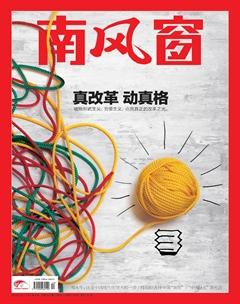多少黑名單,曾互道晚安
張熙

時下,勾搭文化已成為青年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各式各樣的約會軟件也使得年輕人的交往模式和情感表達發生了深刻而微妙的變化。人與人的相識在移動通訊和社交媒體的幫助下相當方便快捷,人們的交往范圍因突破了時間空間及社會網絡的限制而更加自由廣泛,個性化的交友需求也得到了極大程度地滿足。然而,“心悅君兮君不知”的無奈或許已然一去不復返,但“相與之情謂之厚”的臻美卻似乎未能總是如愿。
畢竟,約會軟件能帶來緣分,卻未必能留得下真情;能帶得來相遇,卻未必能守得住陪伴。網絡空間的瞬息萬變,虛擬世界的撲朔迷離,更是為約會軟件的使用和體驗增添了諸多不確定因素。用戶資料是否真實,人際聯結是否穩定,情感基礎是否牢靠等問題,也讓人們在使用約會軟件呼朋喚友、尋情覓愛的同時,感到些許焦慮、無力甚至是恐慌。我們不禁困惑,約會軟件上為何往往摯愛難尋?
首先,用戶匹配的隨機聯結往往使得社交關系脆弱而易逝。或許他們之間有著共同的興趣或類似的經歷,但這些所謂的對應和匹配,當失去了生活、學習或工作這些經驗性的共同基礎時,難免飄飄然。盡管約會軟件大大縮短了人們交往的時間和經濟成本,但殊不知這些成本之間也蘊藏著日積月累的情誼與磕絆磨合的默契。“記得當時年紀小,你愛談天我愛笑”,這份似水流年的追憶在轉瞬即逝的社交平臺上蕩然無存;“從前的日色變得慢,一生只夠愛一個人”,這種與子偕臧的守候在左拉右劃的約會軟件上亦不敢奢求。到頭來,真是初遇時只怕相見恨晚,轉身時唯恐避之不及—曾幾何時,多少黑名單,曾互道晚安。
其次,線上遠程的交流方式難免帶來一種自我投射的幻覺。人們難免會想,眼前的你,到底是真正的你,還是我心中的人?然而,無論你我,現實的接觸不應被遠程的通訊所遮蔽,切身的相處也無法被憑空的想象所取代。否則,人們難免會把自己對于良人佳婿的主觀想象投射在這含情脈脈的電波之間,不由得會把自己眼前的鄰家女孩置換成那夢中的天外飛仙,更有甚者就在此在與他者之間,就在實在與虛幻之間,兩個人的你來我往慢慢蛻化成一個人的日思夜想,彼此間的你儂我儂逐漸蜷縮成自顧自的黃粱一夢—就只怕,哪怕遇到對的人,最后卻愛上自己。
此外,消費時代的技術媒介容易讓彼此因自我物化而犧牲。感情的價值和意義之一,體現在能使彼此成為更好的自己;那些自我期許帶來的砥礪與進步,本來可以讓彼此通過各自努力和互相促進而共同進步。然而,在約會軟件和社交平臺上,不管是修圖軟件,還是套路戲碼,這些“正能量”會在無形中變質為一種自我偽裝和互相欺騙。一方面,人們生怕對方有絲毫不滿,進而用各種手段讓自己看起來近乎完美,但不知不覺中失去了一份對待自我應有的本分和坦誠。另一方面,這種過猶不及的自我造作,也會轉嫁成對對方不切合實際的期待。無法接受不完美的自己,更對他人揀四挑三。到頭來,欲求湮沒了真情,妄想磨平了癡心。
誠然,約伴好找,摯愛難尋。這不僅是約會軟件的后遺癥或勾搭文化的副產品,更迫使我們進一步思考,在網絡時代下的消費社會,人與人的聯結到底該如何實現,深層次的情感交流又究竟何以可能。一百年前,當社會學大師齊美爾提出“社會何以可能”的追問時,他所面對的是一個逐漸分化,呈現異質并不再熟悉的現代社會。一百年后,當我們談論約會軟件上的那點事時,我們所面對的則是一個虛擬、復雜乃至奇幻的網絡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