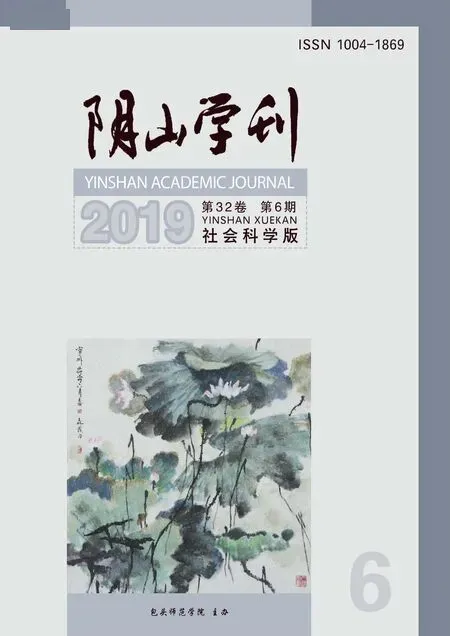知性大氣 清新脫俗
——《生活在別處》解讀*
張 偉
(包頭師范學院 學報編輯部,內蒙古 包頭 014030)
一
《生活在別處》應該在七八年前出版,作者對出書,非常慎重,可以說是太過謹慎了。左挑右選,反復打磨,一拖再拖,現在才與讀者見面,成為一朵遲放的鮮花。吳建榮是個完美主義者,對自己的文字,近乎嚴苛。《現代版梭羅和他的瓦爾登湖》里寫到:“我想也許就是因為太喜歡了,所以才難以完成,而正是因為沒有完成,才最喜歡,因為還有想象的空間。世間的事大抵如此。”[1]269說的是維克多的房子,無意中也說出了《生活在別處》的命運。最后這句,很魯迅。
我在這里特別想表達一個意思:寫作者對文字的敬畏之心。
本來,在這方面,我們有著優良的傳統,古人敬惜字紙,讀書有儀式感,要焚香沐浴。再往前追溯,漢字的誕生,就是一件很神圣的事情,“天雨粟,鬼夜哭。”我們應該有一種文字的潔癖(周作人就是這樣評價魯迅的),高揚文字上的清潔精神。
而這一點,恰恰是今天的文化生態出了問題的地方。出版門檻低,特別是進入自媒體時代,誰都可以隨時隨地發表,文字垃圾,泛濫成災。
全民寫作,我們有過深刻的教訓。20世紀50年代的大躍進,刮起一股民歌風,農民都站出來了,摩拳擦掌,出口成詩。70年代,小靳莊賽詩會,搞得如火如荼。半個多世紀過去了,留下什么了?除了笑料,別無什物。
我們不缺寫書的人,卻缺讀書的人。詩歌界有一句諷刺性的話,說寫詩的人比讀詩的人都多。其實,散文的情況也差不多,散文門檻更低,所謂“易寫難工”,寫散文的人更多,像蝗災之年的蝗蟲一樣,沸反盈天。要厚積薄發,要多讀少寫,甚至不寫。寫也可以,自娛自樂,不要輕易拿出來發表。寫的過程是吸收消化的過程,是整理思想的過程。但,一篇文章,一旦發表,就不再是個人的事情,而成為社會文化的一部分。要愛護文化生態,不要成為視覺污染的制造者。
多讀,吳建榮就是一個典范。
她的讀書隨筆,特別值得文學評論工作者學習。不同于評論文章,她以感覺還原感覺,是描述,不是闡釋,或者說,是在描述中闡釋,描述她理解、接受的過程,構成與作家的對話關系,真正有一種“理解之同情”在里面。不像有些評論職業寫手,拿陳腐的理論生硬地去肢解作品,像套用數學公式解題一樣,機械操作,把鮮活的作品拿來,削足適履地給僵死的教條做注腳。
積我多年的閱讀經驗,經得住讀第二遍的東西不多。包括一些名家之作,讀第一遍時覺得很好,讀完放在案頭,想抽空再看一遍。讀第二遍時,覺得不過爾爾。《生活在別處》里的大部分作品,以前在報刊上發表時,我都讀過,現在結集成書,從頭到尾又系統地讀一遍,仍然很耐讀,很有嚼頭。
從第二輯讀書隨筆看得出來,吳建榮的閱讀面很寬。“不薄今人愛古人,”“轉益多師是吾師。”她選擇書很高端,很有品位,“尋找與自己心靈契合的文字”。她讀書、讀人、讀自己,既入乎其內,又能出乎其外,不是讀死書,而是把書讀活。只有這樣,把自己帶進去,用魯迅的話說,“把自己燒進去”,才能抵達讀書的高境界。特別是文學閱讀,“象喜亦喜,象憂亦憂”,方不辜負作者的良苦用心。《圖書館紀事》的開頭就交代,自己沉浸、游泳在書海里,忘懷了世俗的一切,以至于顧此失彼,東方亮了西方不亮,在生活中有很多損失,她仍然樂此不疲,樂而忘返。
吳建榮散文所擁有的特質,恰恰是現在許多作者所缺失的。而且,這些質素,又是不容易學到的。單說讀書吧,兩個問題,一是閱讀量,二是閱讀的質量。閱讀量不夠,該讀的書沒讀,這一點不必多言。閱讀的質量,也是個大問題。我在《讀書當讀經典》里談到,人與人之間的區別,不僅在于讀不讀書,還在于讀什么書。你讀的都是膚淺的東西,你也就深刻不到哪兒去;你讀的都是庸俗的東西,你也就高雅不到哪兒去。[2]112你只對武俠癡迷,或只對玄幻、穿越之類的癡迷,偏食,營養不均衡,趣味偏狹,文學素養難得提高。開卷未必有益。現在我要進一步表達的是,大家讀了同樣的書,收獲也會各不相同。經常有人搖頭晃腦地說,我讀了這個,讀了那個,可是,收獲幾何呢?就好比山珍海味沒少吃,但你腸胃功能不行,吸收消化不了,好東西都白吃了。吳建榮的讀書隨筆,見證了她的閱讀品質。李建軍說:“一個人的文學修養集中體現在他的文學趣味上。趣味意味著選擇和判斷。一個有著雅正趣味的讀者,會選擇和欣賞那些真正的大師和第一流的杰作,而排斥那些虛假的“大師”和不入流的劣作。”[3]203她在高端閱讀中,培養起自己雅正的文學趣味。
她對作家的特色、風格,概括很準確,把握得很好。讀了第二輯,要跟著吳建榮學讀書。也許有人會不以為然:你可以說我不會寫,怎么能說我不會讀?我要說,不會寫是因為不會讀。
二
吳建榮的散文,知性,大氣,沒有花花草草,沒有鶯鶯燕燕,沒有小女人的忸怩作態,一掃小女人散文的脂粉氣,不事粉黛,天然真純。文字之于散文,不僅是工具,而具有本體論的意義,與作者的思想水平的高低,對生活的感悟程度深刻與否,息息相關,一而二,二而一。大劑量的閱讀,深致而獨特的思考,給予她豐富的滋養,使她的散文真力彌滿,既有深廣、坦蕩的包容性,也有剝繭抽絲、可觸可摸可感的細節性。
吳建榮的散文,清新脫俗,舉重若輕。她的脫略繩墨,一掃起承轉合之類的八股氣,《母親的粥》體現充分,堪稱佳妙。《母親的粥》沒有那些很老套的軌范,一上來就呈現一個家庭生活中再平常不過的場面,一件極普通的小事:母親把粥熬糊了。通過對話和心理描寫,寥寥幾筆,就把每個人的情態鮮明地刻畫出來。母親的沮喪、等待安慰、對父親的遷怒,父親的包含著善意解嘲的揶揄,“我”的怪怨及稍后的安慰,純任白描,形神畢現。對親情,作者沒有做提純的、“真空化”的處理,而是讓筆下的每個人在正常的空氣中呼吸、生活。作者善于體察并悉心理解母親的一片苦心,“她永遠能把所有的問題都怪怨到我爸身上,但是對我們總是滿含愧疚。”熬臘八粥,“說得好像很隨意,但是其實是很有章法的。”作者文思跳躍,由淡淡的糊味,一下子跳回到童年,沒有冗詞贅語,不做任何交代,省略銜接過渡,母愛親情就在這淡淡的糊味中彌漫開來。五官感覺中,嗅覺、味覺都關乎味道,占比2/5,我們中國人尤其看重味道,“味”也就成了中國美學的重要范疇。淡淡的糊味,那是母親的味道、童年的味道、幸福的味道,那是每個人的味蕾不可更易的味覺記憶。只有心思細敏的人,才能寫出這種生活的幽微;反過來,寫作,有益于細致地品咂生活。這是一種雙向生成的關系。沒有枯燥的說教,沒有庸常的議論,卻在積蓄中順理成章地讓感情引爆、升華。結穴處又回到眼前的粥上來,首尾圓合。
《我的高考記憶》敘寫作者高中時的一段心理創傷。老師對“差生”的輕慢和挖苦,類似“你家祖墳冒青煙”這樣的侮辱性詞句,深深地傷害了幼小的心靈。明明是應屆生,出于升學率統計的考慮,老師硬逼著升學無望的“我”填成往屆生,無異于雪上加霜。(富有戲劇性的是,“我”補習時因高考勝券在握又被指令填成應屆生,讓另一位應屆生受到“我”當初同樣的傷害。)作品議論開篇,開場之后的第一節仍未進入實質性的敘述,我揣度,這未必是吊胃口,未必是蓄勢的寫作策略運用,實在是心有余悸,不敢、不肯去觸碰那早已結了痂的傷疤,仿佛一碰就血流不止似的。是的,雖事隔多年,那心結還是一個解不開的死結。文中密集出現的詞匯,諸如,“自卑”“羞恥”“恥笑”“怨恨”“心痛”“輕視”“忽視”“蔑視”“不屑”“對峙”等,在在表征著萬箭穿心的傷痛。由于傷害太重了,作者繁復地、多層次地加以揭示。老師偶爾的夸贊,“我”也無動于衷,哀莫大于心死。同桌的鼓勵,“你一定能考上”,本是一句平常的話,對“我”而言,卻像注入了一針強心劑,是匱乏中的補償。
該文當初在雜志上發表時,標題為《我記得你,已沒有恨意》。時間,是最偉大的心理醫生,那顆被刺痛的心,在悠悠歲月中漸趨療愈。包括寫作此文,以筆傾訴,也是一次紓解,是一個療程的自我治療。完成著和解,與老師的和解,與自己的和解,與這個到處充斥著殘酷競爭的世界的和解,走向釋然、坦然。其實,老師也是很敬業、很有責任心的。降線后“我”可以上大專了,她騎著自行車趕到“我”補習的學校來通知“我”,那情景,著實讓人感動。她苦口婆心地做工作,讓“我”回到母校,回到她的班上補習,也讓讀者看到了為人師者的一顆拳拳之心。結尾寫到,后來“我”和同學一起去家里看望老師,她像換了一個人似的,“溫和而隨意”,“也許是她老了,也許是我們長大了。”其實都不是,是關系變了,已經從那種緊張的師生關系中解脫出來了。這篇散文,好就好在,把這些復雜的、糾結的感情表達得很準確,很到位。
緊隨《我的高考記憶》排在第一輯第二篇位置上的是《那些不時移動的小黑點》。也許并沒有什么特別的用意,從高考到上大學,按時序的自然排列而已。我卻愿意把這兩篇對比著來讀。前者的文字是冷硬的,色彩是枯淡的。而后者是溫軟的,華美的,靈動的。作者按感情波段而驅遣文字,語言背后是人文情懷的有無、多寡。《我的高考記憶》已如上述,《那些不時移動的小黑點》里主要出現兩個人。女生們喜歡年輕的英語老師,不僅源于那種懵懵懂懂的來自異性的吸引,更“因為從小到大,離經叛道地教我們罵人的老師,他是第一個;而真正能體會到我們的感覺并讓我們學著自由表達的,他也是第一個。”“他從不像別的老師一樣視我們為無物,更不會用一些規章教條來限制我們。”這種人性化的教育,使學生獲得充分的自尊感,才是最寶貴的,才是讓作者念念不忘的。為了抄近路,學生們踩踏草坪。同樣滿蘊著人文情懷的老校長,不僅沒有批評她們,幾天以后,還在她們踩踏的地方鋪出一條小路。難怪作者感受到,“東北師大的時光永遠帶著暖意,就連冬天那積雪覆蓋的寒冷都是陽光普照的暖。”讀《那些不時移動的小黑點》,我想到徐志摩,想到他的《再別康橋》,一文一詩,那是非常接近的一種情愫,虔誠的、宗教般圣潔的感情,面對神圣的知識殿堂,景仰、依戀,戀愛一樣的感覺,投去深情的一瞥。化而為文字,是抒情的,唯美的,漾溢著詩性的,如甘冽的山泉汩汩而來。除了男教師、老校長,校園里的樹,可謂第三主角了,作者滿含深情地投注那么多的筆墨。在她的筆下,樹不只是植物,而是有靈性的存在,人之于樹,是一種審美態度,構成審美的主體間性,即與花草樹木平等地對話與交流,這與徐志摩甘做康河里的一株水草,建立起緊密的、顯明的互文關系。“風吹過,那些翩然起舞的葉子,隨風搖擺的枝條,就像感染了年輕學子的張揚。”相互濡染、熏陶,已然分不清何者為我、何者為物。在作者眼里,白了頭發的老教授,也是校園里的一道風景。學問漸漸成了刻在臉上的皺紋,長在鬢邊的白發。看,皺紋也因了學養而成為審美對象,增生出審美價值。作品起首點題,從老師課上提問的“小黑點”寫起,卻按下不表,蕩開一筆,任思緒隨風飄揚,散散漫漫,洋洋灑灑,摹景狀物,寫意抒情,瀟灑夠了,才又回到那個小黑點上。最后一節,不忘照應上文,再次點出兩個人、一棵樹。結構上大開大合,開合自如,撒得開又收得攏,不拘謹,不束縛,表現出嫻熟的駕馭力。
《為那不舍的紀念》是《鹿鳴》的“命題作文”,寫平房生活,瑣碎、日常,拉拉雜雜,卻很吸引讀者,何也?養牛為賺錢,毫無疑問。靠勤勞致富,也是天經地義。但這顯然不是作品的重心所在。辛辛苦苦,只落了個不賠不賺,家人泰然處之,并沒有為此而傷懷。三聚氰胺事件傷及養牛戶,換了別的作者,可能會就此大做文章,這也不是吳建榮的關注點。寫出普通人的小日子,寫出熱騰騰的煙火氣,寫出善良的一家人其樂融融,才是旨歸。絮絮叨叨中,人對人、人對土地、人對家園、人對植物、人對動物、動物對人,那綿密交織著的感情,樸素得像土豆,深厚得像大地,親切得像正在吮吸著母乳的小驢駒,頻頻觸動讀者的淚點。媽要在城里的家給孩子們做飯,又“不放心爸,怕爸吃不好,怕爸給她的那些牛們、驢們吃不好”,同甘共苦,相濡以沫,感人至深。注意,是“她的那些牛們、驢們”,媽對所豢養的家畜們的親如子女的愛意,躍然紙上。“我”看見操勞的爸“躺在牛槽上睡著了”,“我的淚瞬時就流下來。”我讀到這里時,眼睛同樣濕潤了。研討會上,一位女青年學者說到此處,也哽咽的不能自已。我們都有這樣一位父親,父親的經歷各不相同,父親的情懷都是一樣的。鄰里之間,打招呼,拉家常,一反鋼筋水泥的冰冷。“媽總感嘆,地真是好東西,只要撒一點種子就要什么有什么。”這是對土地的感恩。“走時,爸盯著讓我把院子的角角落落都拍了個遍。”這是對家園的不舍。媽做著農活,“還不時地自言自語,后來才聽清是和莊稼說話。”學者們振振有詞,動輒甩出“天人合一”的大概念來借以嚇人,而只有有過耕作經歷的人,才體會得到其深意。“爸從小就喜歡放牛”,養牛是他的夙愿,賺錢倒在其次。從老家買回的牛,有人出雙倍的價錢要買,他不賣,便是明證。不得不把牛賣掉時,爸媽考量的不是價錢,而是“選定養牛養得好的人”。兒子與狗嬉戲玩耍,充滿了村趣和野趣。動物對人的那份感情,更打動人心。牛離去時,“不情愿地哞叫,哀哀的,好遠還能聽見。”狗對舊主人的忠誠,“走出去老遠,我還能聽見它嗚咽著,跳來跳去,抖得鐵鏈子嘩嘩響。”中國是個古老的農業國,我們的基因里埋下了農耕文明的種子,無論你現在身處何方,過農家生活的情結根深蒂固。
散文這種文體,要求作者以裸裎的靈魂面對讀者,與讀者推心置腹,任何的虛假,都是散文的大敵,都將置散文于死地。你想躲躲閃閃,你想閃爍其詞、瞞天過海,你這樣做的時候,就已經暴露了你的虛偽,你的不真誠。楊朔的被拋棄,不僅因為模式化,他抒發的那份感情就是建立在浮夸的、虛假的理念之上的。所以,散文對創作主體的人格要求是高的,我把散文命名為“全人格文體”。它要求作者擁有一顆真誠的、可以讓讀者觸摸到的“散文心”,坦誠、開敞,不同于小說的虛構,不同于詩歌的想象,而是一種散文的“實在”。
和小說不同,小說家鬼精鬼精的,比鬼都精,把自己隱藏的很深,躲在敘述人后頭不出來,你在小說里根本看不見他。這樣說,當然是調侃了。其實是小說這種文體的創作規律使然。1875年底,到1876年初,法國作家喬治桑與福樓拜在來往書信中展開了一場有關寫作原則的爭論。福樓拜說:“說到我對藝術的理想,我以為就不該暴露自己,藝術家不該在他的作品里露面,就像上帝不該在自然里面露面一樣。”這句話,可以看做是小說家的宣言。恩格斯也講過,“作者的見解愈隱蔽愈好。”
詩人呢,如果說小說的敘述人不能和作者劃等號,詩中的抒情主人公也未必是作者本人。有時是為“神”代言,不止一位詩人描述過,仿佛神靈附體,下筆若有神助。有時是“大我”的喉舌,這個“大我”,可以是民族、祖國、階級,往小了說,也可以是鄉親、同仁等。退一步說,即便是“小我”,抒情主人公也可以和詩人的現實人格拉開距離。特別是泥沙俱下、迷失于途的當今詩壇,擅“鬼嚼”的詩人混跡其間,詩行里,不僅找不到詩人的影子,連個人影子都找不到,鬼影幢幢。畫鬼容易畫人難,因為誰也沒見過鬼長的啥樣,不僅能哄鬼,也能哄人。所以,有的詩人鬼畫符,在說哄人的鬼話,欺世盜名。(自然也是調侃。)
三
散文之妙,正在于文無定法,不拘格套,破除章法,瀟灑、隨性地去書寫。《圖書館紀事》在幾節思辨性的文字之后,又轉而去敘述在圖書館里的所見所聞,一個老人,一個女人,一個家庭,有特寫鏡頭,有群像雕塑,形形色色的人,盡收筆下。無論寫什么,都楚楚可見,三言五語就勾勒得形神兼備。看似枝蔓橫生,旁逸斜出,卻是一線相牽,不僅像老舍《茶館》那樣場景恒定,更系于對人生的思考,對意義的探尋,對精神的觀照。
吳建榮的散文,看似很隨意,沒有刻意經營的痕跡,其實,是極練似不練。前人在這方面總結的很多。“大音希聲,大象無形,大巧若拙”,信筆寫來,“常行于所當行,止于所不得不止。”“最高的技巧是無技巧。”她的詞匯量并不大,很少見到有生僻的詞出現在她的作品里,積極修辭她也很少使用,比喻稍多一點,其他的修辭格,她用得很少。她的構段,也是短小的段落居多,斬截、跳脫、精悍、明快,絕不拖泥帶水,婆婆媽媽。從風格上說,她追求的是清水芙蓉之美。她的語感、語態都很好。她也特別看重這一點,甚至有點任性。取書名為“生活在別處”,不為別的,“只是從一開始就喜歡這幾個字”。就是一種感覺,一種直覺,說不出個所以然來的第六感。這是職業的任性、專業的任性,是應該得到理解、尊重和包容的任性。直覺背后有覺解,任性背后有理性。細想來,還是經得住分析的。“別處”,換一個大眾化的說法,就是“詩和遠方”,而又不像后者那么直白、淺俗,語義的模糊性,為讀者釋義留下空間,更耐尋味。人類初民時期創作的神話,在神祗和英雄身上任奇思妙想馳騁,那就是他們的“別處”。“此處”與“別處”,可以是現實與理想,可以是物質與精神,可以是空間意義上的,也可以是心理意義上的,想象的余地很大。作者不安于現狀,昂揚進取的精神自在其中。
類似的任性的話,我從別的作家那里也聽到過。鐵凝說,我就喜歡“阿里郎”這幾個字,莫名地喜歡。徐則臣說,我沒去過耶路撒冷,對這座城市所知甚少。我就是對這幾個字感興趣,說不清道不明地感興趣,一定要寫一篇叫《耶路撒冷》的小說,于是就寫了。作家終其一生都在致力于培養自己的語感,好作家要有好語感,要找這種感覺。
請看這幾句話:“我常常在圖書館忘記了時間,甚至怨憤為什么人要吃飯,為什么人要睡覺,為什么要去上課,如果能天天待在圖書館里該多好。”換成一個蹩腳的寫作者,“廢寢忘食”四個字就全解決了,可能還會為簡練而沾沾自喜,然而,這一縮減,就變得索然無味了。吳建榮的“三問”,似乎無理,恰恰契合于古人所推崇的“無理而趣”,這樣寫,味道就出來了,文學性氤氳其間。總有學生問我,多用成語好不好?我回答說“因人而異”。成語是濃縮的精華,凝練而表現力強;成語背后常常有一個典故,意蘊豐厚,文化含量高。應鼓勵小學生乃至初中生多用。成語因為是“公共語言”,世世代代相沿襲,被廣泛地重復使用,像“公共象征”一樣,“陌生感”蕩然無存,讀者熟視無睹,感覺遲鈍、淺淡、麻木,因而其沖擊力也就多有折損。所以,一個成熟的作家,是應該慎用成語的,甚至要警惕成語的混入。吳建榮深諳此道,我們來看這句:“幾百年前的筆跡,依然靈動新鮮,栩栩,如生。”用上這個習見的成語,讀者不感無覺,苛刻一點說,是敗筆。而中間加一逗號,攔腰斷開,就有了意思。她對虛詞的使用,也很講究,如:“安靜卻激越,單純而浩渺,平和又深邃。”第一句是硬轉,第二句是聯合,第三句是微轉,準確而不可移易。她的文字,隨性,俏皮,靈動,跳脫。讀張愛玲,寫張愛玲,不時抖摟出一些細細碎碎的張氏句子來。
《成長》的結尾:“有些慚愧,有些驕傲。”文字之儉省,令人嘖嘖。媽媽先睡了,沒能陪著兒子寫作業,為自己感到慚愧;兒子靠自己調整,成績提上去了,為兒子感到驕傲。如果啰里啰嗦地寫這么一大堆,反而索然。精精神神的8個字,以少勝多,“無畫處皆成妙境”。“慚愧”之后加句號,也許更好。就這些不起眼兒的地方,很值得寫作者學習。
現代漢語以雙音節的詞為主,通常兩個字只是一個詞,所以,二字句,在別人的作品里很少見到,吳建榮卻不同流俗,多有使用。就像一個愛惜身材的美女,絕不允許有哪怕是一丁點贅肉上身。
“學習好的站成一波,學習不好的湊成一堆。”(《我的高考記憶》)動詞、量詞的運用,平中見奇。似不經意,不事雕琢,天然出之,卻極富表現力。“站”,多有精神。“湊”,顯得萎靡,不振作。“一波”、“一堆”,這非典型性量詞,前者透著力量,如果以圖示意,那箭頭一定是向上的,指示著力的方向。后者則讓人聯想到庸常的、廉價的東西,棄之如敝屣。
偶爾閃現的陌生化的字句,也是那么自然、熨帖。寫女人懼老、拒老,“美容、健身、像小姑娘一樣嫩嫩地說話”,這“嫩嫩地”,訴諸于人的視覺?觸覺?味覺?似乎都有,我也說不清,反正不是聽覺,她偏偏用來描繪聽覺,陌生、新鮮,美感頓增。
“我們覺得自己很忙,覺得這種匆匆奔走的學習很大學。”“很大學”,副詞與名詞的超常搭配,讓人想起那個著名的句子,“這里的天空很希臘。”余光中先生也寫過《天空,非常希臘》。歐化,伴隨白話文而來,已逾百年,是是非非,爭論不休。我以為,在具體語境中才好做出褒貶。如這個長句:“他甚至教我們在戀愛分手時怎樣說出有尊嚴的話讓對方自慚形穢,被人冒犯時,怎樣甩出去一個簡短的單詞,平復我們的怒氣諸如此類。”這個被后置的“諸如此類”,就是典型的歐化,很別致的句子,很自然地還原出英語課堂的情境氛圍,恰到好處,得其所哉。
四
《圖書館紀事》是近作,標志著她的新的高度。發散性的思維,密集的意象或事象,加大了作品的張力。有的段落,像繞口令,仔細體會,卻頗有意味,很耐琢磨,哲理瑩然。這不是單純的語言的問題,是思想深度的外顯,說明作者的思想越來越成熟了。請看這幾個段落——
有的人需要很多書,要讀很多書才能弄明白一個道理,也可能讀很多書也不能過好一生,有的人不用讀書就什么都明白了。有的人覺得自己沒讀書也過得挺好。
一個人比一本書大,但一本書也可能比一個人大得多;一個人比一本書復雜,但一個復雜的人可能永遠弄不懂一本簡單的書,也可能一個簡單的人終于用一生讀懂了一本復雜深奧的書。[1]278
這些句子,還真有點培根論學問的味道。抽象思辨,提煉概括,基于對書的熱愛,對書這種人類文化載體的熟稔和體認,更是辯證思維的結晶。剔除冗余,壓縮凝聚,以雋語出之,基于作者嫻熟、練達、千錘百煉、游刃有余的文字表達。
語言學理論有所謂“辯證詞”,這篇散文里,有許多“辯證句”。如,“就像書給人類帶來了什么一樣,沒有人知道。但似乎所有人都知道。”“我讀的越多,知道的就越少。”“我的生活因此(泡圖書館—引者注)變得單一而豐富,我哪里都沒去,可是我去過很多地方,我沒交一個男朋友,可是我體驗過多少偉大的愛情。”短短的后記里,又出現了幾處這樣的句子,“有時候覺得好像清晰如昨卻又恍然前世。”“火冷去了,但仍保持著燃燒的姿勢。”“記錄我穿過歲月時曾經泛起的笑靨,或者哀愁。”狄更斯《雙城記》的開頭,那一段正反對舉的排比句,自問世以來一直被津津樂道:“這是最好的時候,這是最壞的時候;這是智慧的年代,這是愚蠢的年代;這是信仰的時期,這是懷疑的時期;這是光明的季節,這是黑暗的季節;這是希望之春,這是失望之冬;人們前面有著種種事物,人們前面一無所有;人們正在直奔天堂,人們正在直下地獄。”這絕不是玩弄修辭技巧,而是復雜的世態在智慧的頭顱、成熟的思想中的顯影。再看這兩段,更其高妙——
人的一生比一本書長得多,而也可能一本書比人的好幾代都長得多。寫書的人死了,他的書留下來了。人如果想讓自己留下來,最好把自己變成一本書——由自己或別人寫出來。把自己變成書的人雖然死了,可是仍然活著。他們從書里伸出手來,碰觸這世界。他們也會站在書里看這世界。很多人都會認識他,從他那里學自己沒學到的東西,看自己沒看到的世界。他把自己的思想留在書里,別人也從書里再得到這些思想。人類就這樣一代一代傳承下來。
它是一個世界,擁有一切卻還能擁有更多;它充滿了秘密,卻敞開著這秘密;它有自己的四季變化,陰晴冷暖,感知一切卻保留一切;它無知無覺卻全知全覺,它是纖弱敏感的內心,又是浩大萬能的宇宙;它在有限的時空里擁有無限的時間和空間,它是人類創造的,卻是超出人類的一個永恒的存在……[1]279
吳建榮寫作的路徑很寬展,她有幾副筆墨,寫什么都寫得好,隨物賦形,移步換景。這一點也是難能可貴的。劉紹棠早慧,少年天才,可是后來被讀者遺忘甚至是遺棄了,現在見不到關于劉紹棠的評論了,很少有人提起他。為什么?形成套路了,重復自己。一個人超越別人難,超越自己更難。因為腦袋還是那顆腦袋,現在醫學發達,可以換腎、換其他器官,腦袋不能揪下來換了,你的知識結構、思維方式,一旦形成,就很難改變,固化了,形成定勢了。我們說洗心革面,脫胎換骨,但“洗腦”,就含貶義了。
《謎一樣的敖倫蘇木》,也許不是很重要的一篇,卻是最能顯示吳建榮創作潛力的一篇。平心而論,她對敖倫蘇木、蒙元歷史文化,并沒有太多的了解,而能發思古之幽情,鋪展出那么一大篇文字,好像成吉思汗的鐵騎雄風,賦予她的筆端以靈感,縱橫捭闔,激發出“巨大恢宏的想象”。這篇散文,文思飛揚,馳騁無疆,破空而來,絕塵而去。同類題材的作品多粘滯于史料,無法超拔出來,她占有資料不夠,索性避其短而揚其長,一任思緒蔓延開來,將頑石點化為精靈。
《我那樹一樣的少年》是散文詩的筆法。“我看見你像一陣風,穿過懶散的街道,驚起迷蒙的樹,把閑人們的目光拉長。”詩的語言,詩的節奏。不知有意還是無意,前四節還押尾韻,“長”“望”“上”“光”,很響亮的ang韻。我想,應該是無意的,母愛的深情鼓蕩胸懷,自然而然地流淌而出。這份感情,泛濫開來,已經漫溢到了“桌角的臺燈”“深夜的星光”,不是刻意地尋覓意象,而是紛至沓來的意象簇擁著撞向筆端。作者落墨于兒子中考那天,這是成長中的一個重要節點,一個個細節,一個個片段,以密集的鏡頭呈現,閃回著,跳蕩著。“你”,第二人稱更便于傾訴,這也是自然地呼喚,而非商販經營似的掂斤播兩;“兒啊,每一天,你在媽媽的視線里,每一天,你在媽媽的心頭上。”熱烈的抒情,不加斂抑,淋漓盡致地表達出來。
《土豆》,一般俗套的寫法,會從對爺爺的概括敘述開始,她卻從爺爺的呵斥聲寫起。一番鋪陳之后,又在爺爺的親切的罵聲中落筆,呼應了開頭。沒有直接說出對爺爺的思念,帶皮吃土豆的細節,卻讓這份感情隱含在字句里了。
歷來推崇“孝”,卻未見有多少孝子。人親人,往下親,才是我們的國情。寫親子關系的作品可謂夥矣!也俗濫成災。《寫在母親節》有異于同類題材之處,在于它更真實,更有層次感,特別是更精悍。人取我棄,作者沒有膩膩糊糊地堆砌一般人眼里的亮點,印證所謂“孩子總是自己的好”的俗念,而是寫兒子的小小的叛逆,寫兒子的羞于表達對媽媽的愛,寫那些看上去乖謬的、不和諧的瑣屑,卻那么真實,給讀者留下深刻烙印,而又絲毫無損于母子親情。作者沒有笨拙地去交待兒子的年齡段,那體現不同年齡心理的行為特征,清晰而明了。省卻了冗長的敘述,疊加密致的細節,不斷強化,短小的篇幅里蘊藏著并釋放出巨大的容量。現在沒人提“典型化”了,似乎成了陳舊、老套的同義語,殊不知,藝術加工和提煉,永遠都不會過時。“簡練是才能的姊妹。”(契訶夫語)過濾掉那些可有可無的雜質,精準采擷動情點,這是一種能力,了不起的能力。“句有可削,足見其疏;字不得減,乃知其密。”(劉勰語)“刪繁就簡三秋樹,領異標新二月花。”(鄭板橋題書齋聯)前人精警的總結,發人深思。創作用形象思維,這已成為盡人皆知的常識。而抽象,也是必須的。這里所說的抽象,當然不是邏輯推理,不是說教味道的東西,正如繪畫里有蒙德里安、康定斯基那樣的抽象的形象,文學創作,也要走出形而下的低徊,讓思辨挑起文字,讓文字飛揚起來。《老是一件很陰險的事》,表達的意趣與朱自清的《匆匆》接近,但比《匆匆》老到、厚實。在作品的抽象度上,即對材料的篩選,取精用弘,做得很完美。
寫“老外”的幾篇,因為是非虛構,所以不能稱小說。但其小說的筆法,小說的意味,讓我們有理由相信,她寫小說,也一定是高手。布萊恩、伯妮、愛麗,一個個性格那么鮮活,仿佛就在讀者的身邊走動著,隨時可以與之攀談。敘述那么圓熟,毛茸茸的細節,舉手可掬。布萊恩生活在社會的邊緣,有些落魄,有點無厘頭,又有幾分可愛。恕我直言,有些小說作者,使盡渾身解數,也做不到這樣的立體、圓融。
這部作品集,散文選的少了,隨筆選的多了。看得出來,吳建榮偏愛自己的隨筆。其實,她的散文更好。隨筆對讀者的要求比較高,從思辨力上,從知識量上,都有門檻。讀書隨筆,如果讀者沒讀過這本書,他就很難與你產生共鳴。讀過了,但達不到你的認識水平、認知高度,也無法同頻共振,甚而至于覺得你是在做過度闡釋。所以,隨筆知音難覓,有時候是費力不討好的。而散文中的人和事,讀者更容易感同身受。希望吳建榮多寫一些散文,下一個集子多收一些散文。總體而言,吳建榮散文的水準,高于她的隨筆。換言之,她敘述、描寫的功力,在議論之上。她對所敘寫的人、事、物,都能做到體貼入微,并能精準地呈現,還讓人覺得云淡風輕,不費力氣。她的隨筆,就高低有參差了,有的靈感噴涌,妙語連珠,有的則流于一般化。
個別地方,文字上的、知識性的,訛誤、疏漏,還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