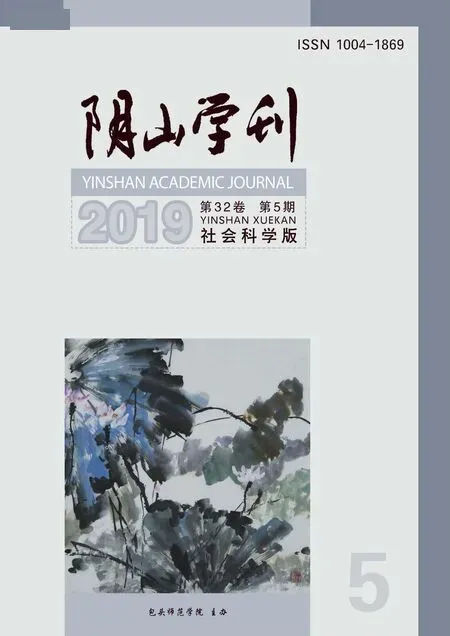身 體 的 突 圍
——《查特萊夫人的情人》中女性身體觀念的變遷 *
邱 明 婷
(廣西大學 文學院,廣西 南寧 530004)
長期以來,身體在人類的心理認知和文化定別上一直處于被貶斥的地位。而與此同時,在性別視域下,遭否定的身體又往往與女性有著密切的關聯。從某種程度上來說,父權制社會中的女性一度所處的附屬地位、壓制境況與受身心二元論貶抑的身體的遭遇極為相似,可以說“女人就是身體,承受著與身體一樣的歷史”[1]81。自20世紀以來,女性及其身體不但仍未擺脫父權制的壓制,還在現代工業文明影響下遭受到客體化、工具化的威脅。然而隨著現代和后現代哲學思潮的涌現,女性身體觀也在建構、顛覆與重建等活動的交替中發生著遷移變化,日益呈現出一種多元的發展態勢。勞倫斯在其作《查特萊夫人的情人》中多有關于女性身體形象的敘述;然而這些女性身體形象往往不全是靜態單一的,而是豐富、變化著的,從中既顯現出工業文明與男權制社會下女性身體所遭受的不同層面上的困境,也折射出女性身體觀念的發展、變遷狀況。
一、身體的歷史與困頓處境
追溯歷史,身體的處境往往處于困頓之中。早在古希臘羅馬時期,自身體與靈魂劃分界限后,身體就不但與靈魂逐漸對立,而且還被歸于靈魂之下,受到貶斥。盡管在亞里士多德的思想批判下,身體因作為靈魂依存的形式和質料而具有了一定的重要性,但深究其觀點卻可以發現,身體在亞里士多德的等級結構排列中依舊位列靈魂之下。時至中世紀,思想家們對于身體的思考本質上仍延續了古典時期的肉身低賤而靈魂崇高的觀念,即使一部分中世紀思想家試圖取消這種二元對立關系而賦予二者以統一性,但由于身體在實際構成中只是作為靈魂的最低層次,其存在的直接目的僅是為服務于靈魂的運作,因而身體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仍像工具之于主體活動那般被動。隨之而來的人文主義思潮雖然高揚了人的主體性和身體的欲求,但這并不意味著身體的處境有所好轉,這只不過意味著身體不再一味地遭受信仰的束縛而得以有喘息的機會。而18世紀掀起的啟蒙思想運動則使得理性取代了上帝和邏各斯而成為了人們重新確證自身的方式。然而在各思想家強調理性概念的同時,關于身體的言說卻逐漸走向了沉默。身體在理性思潮中逐漸成為缺席的狀態,最多不過只是“以感覺的名義偶爾地探出頭顱”[1]110。
身體與性別有著緊密的聯系。在父權社會下,男女兩性關系往往與傳統的身心二元論相呼應:女性一再被界定在身體范疇中,而男性則與具有理性和智慧的思想相等同。古希臘哲學家曾就男女兩性的差異比較得出女性天生不如男性的結論,而這一結論也深刻影響了后世相關觀念的形成,以至于17世紀以來的哲學家們在談及女性時不但將女性與男性相對立,且視女性為被動的客體。可以說,在對身體的認識與理解發生轉向之前,在西方傳統思想與父權制的二元對立觀中,身體“與自我相分離,由女性所承載”[2]50;女性身體由此或受貶低,或遭壓制,甚至一度陷入了失語的境遇,背負著歷史的種種偏見踽踽而行。
二、女性身體的異化
女性身體的歷史是不斷受壓制的歷史,直至現代工業文明興起,身體仍未能走出這一困頓的境遇,反而還遭受到“異化”的威脅,更深一步地被支配、規訓。這里的“異化”主要意指在工業文明與父權社會的雙重作用下,女性活生生的身體被物化為某種可生產、可利用的有效工具,既需要有實用價值,又需要能符合男性需求。勞倫斯在其作《查特萊夫人的情人》中所塑造的幾個女性人物形象都面臨著身體遭受異化的困境,透過她們可以看到,女性身體在被異化后呈現出的不同狀態:或無力自救,或走向馴服,抑或被剝奪話語。
1.康妮:無力掙脫的工具性存在
在工業文明對工具理性的高揚中,身體逐漸成了可計算、可規定和可生產的機器式存在。而身體的這種新的定位一旦與女性相結合,女性則將再次遭受其自然身體與具有社會價值的工具性身體的痛苦二分。主人公康妮原本充滿活力,在嫁給克利福德后,二人最初度過了一段甜蜜美滿的生活。然而不久,克利福德因作戰負傷而落下了終生殘疾。起初,康妮全身心地支持、照料著丈夫,使克利福德得以激發寫作的熱情并從中感受到了其生命存在的意義。但克利福德本性卻是冷漠無情的。正如康妮所感受到的那樣,克利福德“身上根本就沒有可觸及的東西;他只是一個對人類交往的否定罷了”[3]16。受工業文明所引發的工具理性思維的影響,克利福德認為女性身體只是一種可以“提供效用和創造價值的工具”[3]69,周圍的人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就是可以為他所據有、操控的物品,他無需加以關照,即使是作為妻子的康妮也不例外。由于癱瘓,克利福德失去了生育能力,但為了傳續他所看重的那份古老的家族地產,他不惜提議讓康妮借種生子,要求康妮將性事只當作身體的一次機械式行為。而康妮內心對于愛與性的生命情感體驗到底如何,在克利福德看來那都是無關緊要的,因為他認定“肉身是個多余的累贅”,并且“女人是無法享受精神生活的最高樂趣的”[3]292。在小說中,克利福德與康妮就生育孩子的問題進行過三次討論,每一次,克利福德都依仗其權威向康妮表明他的立場和要求而無視康妮個人的思想情感。在克利福德一味的算計和寄生下,康妮的身體“已經開始松懈,一種近乎衰萎的松垮消瘦,沒真正生活就已經老了”[3]85。然而面對這副日趨病態的身體,康妮自身卻陷入了不知如何進行自我解救的迷茫狀態。無疑,康妮的身體在克利福德的控制下逐漸能量透支,變為一個受動的工具性存在,只能在單調的生活中陷于空虛和孤獨的泥沼。
2.博爾頓太太:被馴服的對象
女性身體的異化還表現為客體化、工具化的身體形象被內化于女性意識之中,女性內在地接受了社會與文化權力對其身體進行的規整與調配而成為被馴服的對象。博爾頓太太本是教區的一名護士,在看護礦工的那幾年里她本人總是顯得自信滿滿,指揮自如,那些受護理的礦工們“常常使她覺得自己是那么高貴,她超人般地實施著管理”[3]99。然而這種境況在她被聘請到拉格比做克利福德的私人護理后卻完全改變了——“她那種指揮別人的自信神態不見了,變得神經兮兮。在克利福德面前,她是靦腆的,幾乎是害怕的,寡言少語”[3]98。拉格比周圍所縈繞的工業文明氣息與克利福德所代表的男性權威力量對博爾頓太太生存的設限,不但使她曾經保持的自信力與信念感淡化了,更是讓她“把自己當成動作的客體而非動作的發動者”[4]62,逐漸自覺地接受了現處的客體化境況。小說末尾部分中,當克利福德得知康妮向他提出離婚請求的消息而倍感情緒失落時,博爾頓太太的身體竟成了他心安理得地獲取的撫慰情緒的對象——“他常常握著她的手,把頭偎在她懷里……‘吻我吧!’于是她輕輕吻他身體,哪兒都吻,半嘲弄地輕吻”[3]368。可以說,在博爾頓太太這里,身體之所以陷入窘迫的處境不僅僅是由于外界的操縱,更是由于其內在地接受了男性的意愿與工具性的思維,將他者的身份意識自覺地加以認同,從而失去了自主的感受力與行動力。
3.伯莎·庫茨:受驅除的怪物
不同于康妮與博爾頓太太,梅勒斯的妻子伯莎·庫茨本人在小說中一直處于缺席的狀態,只是在其他故事人物的敘述、對話或書信之中才被提及。在這里,身體可以說被徹底地奪去了自我真實的體驗而被抽象化、他者化,并被男性以物的性質、作用來加以評判。
伯莎在其他人物的敘述中大都被描繪為一個粗俗蠻橫的悍婦。梅勒斯因為對肉欲的需要而娶了伯莎,婚后,二人最初都沉湎于肉欲的歡愉之中;然而由于性格矛盾、價值分歧等問題,梅勒斯開始與伯莎展開了身體間的對抗——他們相互扭打,又相互拒絕發生性關系以懲罰對方的肉體,直到伯莎生下了孩子為止。但梅勒斯只是將伯莎當作其發泄肉欲和情緒的工具,當他厭煩了伯莎及其身體時,他便采取了一種置之不理的態度,隨后趁著戰爭爆發,決然拋下伯莎和孩子而參了軍。在康妮與梅勒斯的一次對話中,康妮用其女性所特有的情感體驗對伯莎表示了同情,認為伯莎的一些狂亂行為實際上是在以另一種方式希望得到丈夫的關注,因而她從某種程度上對伯莎的遭遇表示了同情。而梅勒斯是否對伯莎傾注過真正的愛,在故事中似乎沒有確證,但梅勒斯對伯莎身體的憎恨感卻是顯得十分明顯。他曾憤怒地指出“她是個喪門星,披著一張人皮!……”[3]351-352從某種程度上說,伯莎的身體在梅勒斯的審視下不但被貶斥為人生發展的障礙物,更是被異化為一個已與人性情感抽離的怪物。而伯莎,在與梅勒斯分離的數年后,曾企圖用其肉身喚起梅勒斯對她的回心轉意,然而她卻發現丈夫早已移情他人。伯莎試圖再次進行抗爭,但是這一行動只能被他者所描述與定性,其結果不但只能歸于無效,反而更加深了伯莎形象的惡化。在工具理性思維與男權思維的沖擊下,伯莎的下場只能是被當作怪異無用之物而丟棄、驅逐。可見,勞倫斯所塑造的伯莎這一女性形象,既缺失了自身的主體性,卻又無法言說與表述自我,暗含了女性身體最為困乏而又凄涼可悲的局面。
三、女性身體的突圍之徑
然而身體畢竟不是一種純粹的物質性存在或靜態的符號,它內在地含有對于生命的體驗以及與思想意識的互動性,并且也蘊藏著與外在世界建立關聯的可能性。這種潛在的質性無疑為女性身體的突圍創造了機會。
“主體間性”是20世紀西方哲學突顯出來的一個重要概念,本質上可意指人作為主體在對象化的活動方式中與另一主體之間的關聯性。現象學家梅洛-龐蒂將主體間性思想化用到了他的身體研究,提出了“身體—主體”的觀點。梅洛-龐蒂認為,身體并不是像傳統理論所認為的那樣,是某種被動的工具或一般的客觀對象,相反,身體本身“具有一種意向性的功能,它能夠在自己的周圍籌劃出一定的生存空間或環境”[5]74。也即身體本身就是一個能動自如的知覺主體,即“身體—主體”。此外,自我的“身體—主體”與他人的“身體—主體”以及世界之間也不是二元對立的,而是各自具有自主性的同時又始終處于一種交流互動的關聯之中,可以彼此開放、擁抱理解、和諧共存。可以說,梅洛-龐蒂的“身體—主體”觀點既使身體在理論層面上成為了本體概念,也為身體擺脫被對象化和工具化的束縛提供了可能。
盡管尚未有資料表明勞倫斯接受了主體間性思想理論的影響,但從勞倫斯對于兩性關系的態度以及他在《查特萊夫人的情人》中對于身體、人際關系等等的書寫中可以看到主體間性的潛在蘊涵,在一定程度上也暗含了勞倫斯對于主體間性觀念的親和。
1.身體—主體的建立
身體的主體間性關系的建立離不開身體主體性的生發,身體主體性的發現可以說是對于身體的一種重新體認。梅洛-龐蒂曾經指出,身體首先不應是對象世界的組成部分,而是本身就是一個能夠自主籌劃自身所需的生存空間和環境的主體。從這個觀點出發可以認識到,對于女性來說,身體不再是那個被時時貶抑、客體化的工具或物品,通過肯定和激發其內在所蘊涵的主體性,女性身體本身具有了一種掙脫困境的可能性。
小說中,康妮正是通過逐步樹立起身體的主體性而迎來了其身體解圍的新希望。如前所述,康妮曾經遭受過身體被異化的煎熬,身體的異化不但使康妮喪失了其主體性,還令其陷入到巨大的痛苦感和孤獨感之中。然而與梅勒斯的初次相遇卻使康妮突然意識到身體本身所能透出的生命存在意義:“是一種閃光,是熱度,是個體生命的白色火焰,以可以觸摸的輪廓顯現出自己:肉體!”[3]79。可以說,這種對身體與生命意義的領悟像是一股新鮮涌出的清泉流貫了康妮干涸的生命。文中描述了康妮在告別梅勒斯后返回家中的臥室做了一件她很久以來都沒做過的事情,那就是在鏡子前凝視著自己的身體。通過對自己身體的凝視,康妮發現了她生命力的嚴重缺失,同時激發起了她對現狀的深深不滿,使她在內心中逐漸升騰起一種反叛情緒。而這無一不體現出了身體主體性的覺醒。
博爾頓太太對身體的認識發生轉變主要體現在其對康妮的反抗行動、自主選擇逐漸產生了認同感。博爾頓太太在與康妮的幾次接觸中開始察覺到,康妮在逃離男主人克利福德的束縛的過程之中,不僅不再顯得憔悴、力不從心,反而變得充滿活力與自信。康妮的身體與精神狀況的變化讓博爾頓太太意識到,康妮的行為事實上是存有著一定合理性的,因為它恰恰確證、促發了女性自我的尊嚴感、能力感與意義感,因而她最終是贊同康妮的出走的。同時,博爾頓太太也對她的主人克利福德的行為予以了反觀。她意識到,克利福德實際上更接近于一個無用之物,因為他既缺乏具有蓬勃生命力的身體,他身上的虛偽、自私與冷酷也讓他不可能具備超越性的精神。可以說,博爾頓太太對她的兩位主人的親近感的變化以及她自身認識度的提升體現出了其身體主體意識的蘇醒。
然而主體性的建立雖然表明身體有了向其生命本質回歸的可能性,但同時也意味著身體存在有偏入以自我為中心的傾向,建構起保衛自身而疏離他者的外殼,使自身成為圍困自我的惡因。在小說中,康妮的姐姐希爾達即為如此。希爾達在小說中被刻畫為一個始終保持有強烈自我主體意識的人物。希爾達一直清楚地認識到自己的身體不應當附屬或聽任于任何人,尤其是男性,對此她還曾明確表示:“我不想當任何男人的小甜甜,也不想當泄欲器”[3]316。因而希爾達時常表現出對自身的主體性和獨立性的護衛而對周圍男性的漠視或對抗,她與克利福德的論理、與丈夫的不合和與梅勒斯的爭執等等即為她的這一強烈主體意識的表現。希爾達守護著她的那方凈土,為自己的身體搭建起一個個堅不可破的堡壘,雖然這看似成為了自己身體的主管人,但從另一層面來看又未嘗不是在以隔離他人和圍困自己來作為代價呢?因而從某種程度上來說,身體主體性的建立確實是對身體本身的尊重與重視,但真正要使身體得以突圍仍需更進一步地向主體間性邁進。
2.兩性主體間性關系的建立
在身體的主體間性關系中,自我的身體—主體與他人的身體—主體既要存有各自的主體性,同時也始終處于一種交流互動的關聯狀態之中;而正是基于此,他者與我才得以彼此開放,從而達到相互理解、相互關情。勞倫斯在《查特萊夫人的情人》中主要借康妮與梅勒斯二人之間的交往表達了其對于兩性及身體關系的認識,而這一認識也與主體間性思想有著一定的契合。
兩性主體間性關系成立的可能性在西方女性主義學者中得到過一定的闡釋。法國女性主義者露西·依利格瑞批判地接受了現象學家梅洛-龐蒂的“身體—主體”觀點,從而建立了自己的身體理論,即提倡一種具有互為主體性的、和諧的而又理想的兩性關系的“二人同行”說。在“二人同行”說中,依利格瑞主張女性要獲得其主體性必須要真正擁有其身體以及自我的意識和對他人的意識,并且還要在相互的意識中與男性共同分享主體性;而只有男性與女性互相存在于對方的意識之中,平等的身體關系和兩性關系才有建立的可能。英國新女性主義學者的主張也蘊含了兩性的主體間關系的思想,她們認為,男女之間不是一方對另一方的壓抑或超越,而是要在相互尊重對方的身體的基礎上,彼此補充、相互包容,從而構成一個和諧的共同體。勞倫斯與女性主義學者的主張在一定程度上是契合的,他在對兩性關系的思考與書寫過程中也明顯蘊含了主體交互的思想。從他借小說《戀愛中的女人》中的人物伯金之口所提出的關于兩性雙方關系的“雙星平衡”觀可以看到,勞倫斯既不贊同女性臣服于男性的觀點,亦不認同女性至上的主張,而是希望男性與女性可以保持各自的獨特性與主體性,進而共同走向主體間平等和諧的交往。在他的《查特萊夫人的情人》中,康妮與梅勒斯就充分體現了兩性間相互包容與相互關情的聯系。
康妮與梅勒斯之間的交往盡管在最初只是為了相互獲得情欲上的滿足,但隨著兩人關系的走近,他們分別察覺到了自身生命的孤獨狀態與不完整,開始萌生出想要完善自身的想法。同時,他們也希望自身能夠為對方所尊重與信任,而不是僅僅被當成滿足情欲的工具。在彼此敞開心扉的過程中,他們逐漸發現了對方生命與自身生命的相適與互補,進而相互欣賞,彼此包容。在小說中有這樣一段關于康妮與梅勒斯的對話:
“不,”她說,“我喜歡你的身體。”
“真的?”他答道,哈哈大笑。“啊,那么你我扯平了,因為我也喜歡你的身體。”[3]211
在這里,康妮與梅勒斯所要表達的不再是對于肉欲的渴求,他們彼此間也并未視對方身體如一個可以隨意處置、壓制或者超越的對象。在他們各自看來,他或她就是一個健康的、獨立存在的人,可以相互珍愛,從而實現肉身與精神兩個層面上的相互親和。
梅勒斯曾對康妮坦言過:“我想從女人身上得到自己的快樂和滿足,我卻從沒有得到過,因為如果女人不是同時也從我這兒得到她們的快樂和滿足,我是絕不可能得到我的快樂和滿足的。這種事從未發生過。這需要兩個人都進入角色”[3]258。可以看到,梅勒斯是追求著人與人特別是男性與女性之間的靈肉的和諧同一的,而這種兩性間的靈肉合一只有當雙方彼此尊重對方的主體性并與對方達成相互理解、相互關切的關系時才能夠真正得以實現。而康妮與梅勒斯正是在他們的一次次交往中逐步走向了主體間相互關情的狀態,進而實現了靈與肉的和諧統一。結尾處敘寫到康妮懷上了梅勒斯的孩子,兩人均表現出了對于他們愛情結晶的共同期盼與守護,這也體現出了勞倫斯對身體在兩性彼此尊重、和諧共處的關系中獲得新生的期待與肯定。
四、結 語
《查特萊夫人的情人》中對于女性身體的敘述透露出女性身體觀念的變遷。可以看到,在勞倫斯的筆下,女性身體從最初被視為不能自由言說與行動的工具性存在中逐漸得到喚醒,開始意識到生命活力、身體獨立等對于個體生命的重要性,進而構建起了自身的主體意識。而與此同時,身體既是自主完整的但又是與他者息息相關的。女性既要認識自己、擁有自己的身體,同時也應與男性相互交流、構成關聯,在不同維度的交織作用下達成兩性情感、精神的自由和諧與友愛尊重。勞倫斯用文學的詩意書寫了現代社會中女性身體的遭遇,并充分展現了一個作家對于人本身、生命本身的深刻關注與不斷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