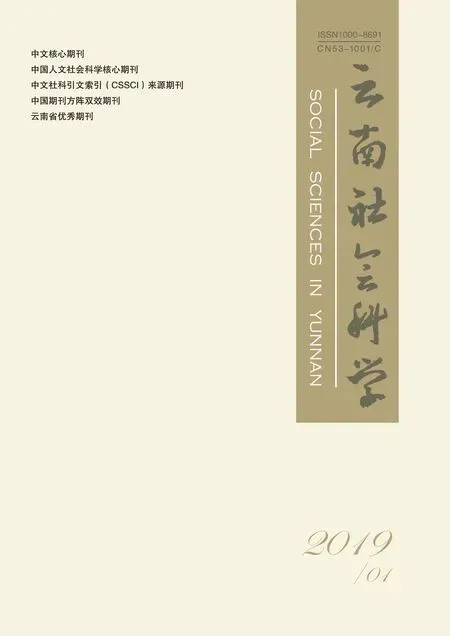“市民社會”抑或“富民社會”
——明清“市民社會”說再探討
林文勛 張錦鵬
一、問題的提出
在明清社會研究中,明清“市民社會”論是頗具沖擊力的一家之說。持此觀點的學者認為,在明清時期中國社會已經出現了一些異質特征——經濟轉型、市民階層興起、思想啟蒙運動、公共領域活動以及大眾意識興起等諸多方面,并試圖用這異質特征來界定明清的時代性質,并以此為據,提出了“市民社會”之說。他們的觀點主要體現于三方面:一是明清資本主義性質因素興起。明清商品經濟發展出現多種類型的富戶,這些富戶即為“市民”,明清市民階層初步形成并在反專制、反封建的斗爭中嶄露頭角。[注]①這一觀點的代表人物是傅衣凌、侯外廬等主張明清資本主義萌芽觀的一些學者。參見: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經濟試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明清社會經濟變遷論》(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以上兩部著作及傅衣凌相關成果均收錄于2007年中華書局出版的《傅衣凌著作集》叢書中。侯外廬從思想史視角也討論了相關觀點(相關著述見下)。二是啟蒙思想出現,這是明清走向市民社會的思想動向和社會意識形態。[注]②這一觀點的代表人物是侯外廬、艾爾曼、溝口雄三等。相關成果見:侯外廬:《中國早期啟蒙思想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8月。[美]艾爾曼:《從理學到樸學——中華帝國晚期的思想與社會變化面面觀》,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年。[日]溝口雄三:《中國前近代思想的演變》,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中國的公與私·公私》,北京:三聯書店,2011年。三是“公共領域”的發展。明清士紳、商人在許多公共領域發揮作用,形成具有自治特征的團體生活,甚至發揮出批評政府的功能。[注]③這一觀點代表人物是羅威廉、蘭京、卜正民等。相關研究可見:Rowe,W.Hankow: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89.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The public sphere in modern China”,Modern China 16.3,pp.309-329.1990.Rankin,M.Elite,Activism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Zhejiang Province,1865-1911.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The origins of a Chinese public sphere:local elites and community affairs in the late-imperial period”,Etudes Chinoises 9.2,pp.13-60.1990.這種觀點與明清停滯論[注]④許多學者從不同的角度提出了明清社會停滯論,如伊懋可的“高水平均衡陷阱”說、黃宗智的“過密化”理論、費正清“沖擊-反應”模式乃至內藤湖南的“唐宋變革論”也意在論證明清中國的停滯衰落。形成鮮明對立,認為明清中國已經出現了一股新生的力量,或能打破中國傳統社會的桎梏,走向新的變革時代。
筆者認為,明清社會既不是有新生力量涌動的“市民社會”,也并非缺乏發展動力的停滯社會,而是“富民社會”。所謂“富民社會”,是從“民”的演變歷史軌跡來考察的、對中國傳統社會性質而提出的一種“假說”。中唐以來,中國社會發生巨大變化,這一變化主要表現為“富民”作為一個重要的財富力量成長起來,成為社會的中間層、穩定層、動力層;這一社會中堅力量推動著社會前進,使唐宋及以后的中國傳統社會具有與以前的漢唐社會不同的歷史特征。“富民社會”具有的流動性、市場化、平民化特征,體現為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大一統國家政權穩定均質運行。宋元明清這四個朝代,都具有“富民社會”的特點,都具有同質性,應將其作為一個整體性社會階段來看待。
二、明清富戶不是“市民”而是“富民”
20世紀50年代史界前輩傅衣凌先生認為,明清江南社會出現了大量農業型、產業型、商業型富戶,這些主要“依靠工商業”積累財富的“富戶”,“更加促進了工商業的發達”,“并在工商業中出現有大批的中小工商業者,這般中小工商業者廣泛地散布于江南的鄉村城鎮中,形成為廣大的市民階層”,“動搖了自然經濟,也改變了整個的社會階級的比重”[注]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經濟試探》,收錄于《傅衣凌著作集》,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263頁。。
筆者認為,“江南富戶”并非“市民”,而是“富民”階層。將傅先生的《明代江南市民經濟試探》(下文簡稱《試探》)一文“富戶”的史料與唐宋時代史料所見“富民”進行對比,就可以發現明清“富戶”與唐宋時代“富民”有諸多相似。《試探》一文指出:明朝“以田稅之多寡者較之,惟浙西多富民巨室”[注]《明太祖實錄》卷49,洪武三年二月庚午條,上海:上海書店,1984年,第965頁。。明初徙天下富戶以實京師或其他地區,僅洪武二十四年(1391)遷徙富戶14300余戶,永樂元年(1403)遷徙富戶3000余人。[注]傅衣凌:《明清江南市民經濟試探》,第234頁。唐宋時期類似的“富民”史料亦不少見:“惟州縣之間,隨其大小,皆有富民。”[注](宋)蘇轍:《欒城集》(下)卷8《雜說九首·詩病五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555頁。“鄉村上三等戶及城郭有物業戶”,“是從來兼并之家”。[注](清)徐松等輯:《宋會要輯稿》食貨4,劉琳、刁忠民等點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6053頁。若就個案來看,《試探》一文列舉明清有“以力穡致富,甲于縣中”[注](明)歸有光:《震川先生集》卷25《行狀·魏誠甫行狀》,周本淳點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592頁。的魏氏、有“累貲至千金”[注](明)繆昌期:《從野堂存稿》卷5《仰峰王君傳》,《續修四庫全書》第1373冊,第472-473頁。的王守璽、有“起機房織手”“至百萬”[注](明)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卷28《果報·守土吏狎妓》,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713頁。的蘇州潘氏、有“以巨貲為番商”[注](明)姚士麟:《見只編》卷上,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50頁。的童華、有以一張織機起家“后四祖繼業,各富至數萬金”[注](明)張瀚:《松窗夢語》卷6《異聞記》,盛冬鈴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19頁。的張氏等。而唐宋時代個案亦多,有“至富敵至貴”[注](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卷495《雜錄三·鄒鳳熾》,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第4063頁。的王元寶、有“家有綾機五百張”[注](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卷243《治生·何遠明》,第1875頁。的定州何明遠、有“用機械起家”財富累積至幾十萬的“富民張三八翁”[注](宋)洪邁:《夷堅志補》卷7《直塘風雹》,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1609頁。、有被“貲至十千萬,邢人呼為‘布張家’”[注](宋)洪邁:《夷堅志·乙志》卷7《布張家》,第242頁。的張氏、有“積資至巨萬”[注](宋)陳亮:《陳亮集》卷30《何夫人杜氏墓志銘》,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436頁。的東陽何氏等。可見,明清“富戶”與唐宋“富民”不僅在史料的文本表述上有很多相似之處,在他們起家致富的方式以及財富多寡等方面,也并無明顯的差異。明清“富戶”應與宋元“富民”看作為同一類群體或同一社會階層。
當然,這種“選精”式個案比較并沒有太多的意義,科學研究更需要的是從整體視角進行比較研究。傅衣凌先生從“江南富戶”經營活動,看到了明清契約關系發展在生產關系上呈現出的“若干的新因素”;從江南城鎮下層市民反封建運動,“隱約地反映出新的市民意識的要求”。在他看來,這些包含著新因素、新意識的明代江南“市民經濟”,具有資本主義萌芽特點。[注]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經濟試探》,第263頁。但是,持明清資本主義萌芽論的學者,卻無法解釋一個問題,即明清時期所謂資本主義萌芽的種種“新因素”幾乎都能在唐宋甚至漢唐時代找到其蹤影,對此傅衣凌先生用“中國歷史的早熟性”來解釋它,[注]傅衣凌:《明清社會經濟變遷論》,收錄于《傅衣凌著作集》,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5、6頁。雖可解釋其“萌芽”而不“成長”之原因,但卻不能對已經出現新因素的漢唐不被納入“萌芽”期做出合理解釋。
毋庸置疑,明清商品經濟的深化發展使得中國社會生產關系的發展出現了一些新的動向,但是這些新動向主要是富民階層追求經濟利益的結果,離開了富民,很難對這些問題做出合理解釋。唐宋時代可以見到諸如王元寶之類的大商人者,但是這樣的人數寥寥,尚未形成規模,而明清時期商人和手工業者的經濟實力大大加強。宋代有蜀商、南商、北商等地方性商人群體,而明清時期已經形成了諸如徽商、晉商、閩商等大商幫,其興起地域更多、市場活動更廣。但是他們的經營活動總體上來看仍然是傳統型的,只能歸結為對宋元商業的擴張型發展。吳承明先生的研究頗具說服力:明代“國內市場顯著地擴大了,這表現在商運路線的增辟和新的商業城鎮的興起。但明代商路的增辟主要是在南北貿易方面,尤其是大運河的利用;這包括有政治因素,不完全是商品經濟發展的結果……長距離販運貿易有了發展,并且已逐步由奢侈品以及特產品貿易專項以民生用品的貿易為主……但是,終明之世,長距離販運貿易在整個市場交易中仍很有限,而其中工農業產品的交換并不占主要地位;農村產品,大半還是單向流出,得不到補償和交換……徽商、陜商等大商幫的出現,說明國內市場有相當的積累貨幣資本能力。但這種積累主要是經營鹽及茶布等商品而來,多少是假借封建政權的力量形成的。”[注]吳承明:《論明代國內市場和商人資本》,原載《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集刊》1983年第五集,后收錄于吳承明《中國的現代化:市場與社會》,北京:三聯出版社,2001年,第111-165頁。唐宋租佃制和雇工制有不少新變化,租佃關系的市場化和契約關系的明晰化是私有制下富民追求經濟利益的結果,而明清時期“田底權”和“田面權”的分離,則使土地產權多元化,也使產權的實現方式更加合理化,這是一種保障土地經營主體多方收益權的制度安排,反映了在商品經濟下富民與其他階層的民眾通過利益共享而達到經濟收益最大化的理性選擇。宋代的佃農已經擁有了較大自由租佃權,但是地主和佃農不平等關系依然存在,官方多次頒布不得“強抑人戶租佃”[注](清)徐松等輯:《宋會要輯稿》職官58之24,第4627頁。的法令。明清時期,佃農的人身依附關系進一步松弛,但是多數佃農并沒有擺脫傳統的主仆關系。有關徽州文書研究顯示:要求脫離佃仆身份的佃仆與極力維持“主仆之分”的主家糾紛,一直延續到清代后期,仍然是徽州訴訟中最嚴重的問題。[注][日]中島樂章:《明代鄉村糾紛與秩序:以徽州文書為中心》,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58頁。
可以說,明清時期種種“新因素”,實質上是唐宋富民階層崛起以來在經濟領域內出現的種種現象,這些現象產生于商品經濟的發展,隨著商品經濟發展深化,也必然表現得更加典型和更加突出,但是其發生機理和現象本質并未出現質的變化。只有從“富民”階層成長和“富民社會”這一框架下來分析和理解這些明清出現的新動向,才能找到合理的解釋。
三、明清士紳由“富民”轉化而來
羅威廉認為“士紳”和“工商業者”是“市民社會”的主體力量。[注][美]羅威廉:《晚清帝國的“市民社會”問題》,載鄧正來:《國家與社會:中國市民社會研究》附錄一,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235-253頁。傅衣凌先生也認為一部分下層士民,如生員、監生、儒童之類,參與了反封建斗爭,他們是市民階層的組成部分。[注]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經濟試探》,第318頁。
何謂“士紳”?明末清初的顏光衷說:“鄉紳,國之望也。家居而為善,可以感郡縣,可以風州里,可以培后進,其為功化,比士人百倍。”[注](清)顏光衷:《官鑒》,見(清)陳弘謀輯:《從政遺規》卷下,金華:國民出版社,1940年,第122頁。清代《欽頒州縣事宜·待士紳》也說:“紳為一邑之望,士為四民之首。”[注](清)田文境、李衛:《欽頒州縣事宜·待士紳》,同治重刊版,第22頁。日本史學界有關士紳的定義可歸納為三種:一是包括現任官、退任官、卸任官以及未初仕的秀才、舉人、候補官僚和有官銜者;二是僅指在野的官僚;三是認為士紳由地方名家大族、大地主、大商人和高利貸者、有官職功名者組成。[注]郝秉健:《日本史學界的明清“士紳”論》,《清史研究》2004年第4期。張仲禮將“紳士”定義為“通過功名、學品、學銜和官職”而獲得身份地位者。[注][美]張仲禮:《中國紳士:關于其在十九世紀中國社會中作用的研究》,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1年,第1頁。徐茂明認為:“所謂‘士紳’,主要是指在野的并享有一定政治和經濟特權的知識群體,它包括科舉功名之士和退居鄉里的官員。”[注]徐茂明:《明清以來鄉紳、紳士與士紳諸概念辨析》,《蘇州大學學報(哲社版)》2003年第1期。這些界定說明學界對士紳的概念和內涵的認識是有較大差異的。筆者認為,中國傳統社會后期(宋元明清)社會群體可分為官、紳、民三個階層:在職的官員屬于官僚層;民屬于無特權層;士紳則居于這兩個階層中間,是官僚與民眾之間的一個特殊階層,既與權力有一定關系又不完全屬于權力階層。士紳具有較為突出的在野性和地方性的特點。士紳并非“市民”,是明清時期從“富民”階層轉化而來的一個階層,它本質上屬于“富民”,士紳階層即為“富民”階層。
富民向士紳轉化的動力機制是財富保持和社會地位獲得,其轉化關鍵通道是科舉制度。轉化步驟有三:(1)通過接受教育實現知識獲得,形成文化資本;(2)通過科舉考試追求功名,實現特權獲得,形成政治資本;(3)通過參與地方社會活動,實現威望獲得,形成社會資本。據此,富民將其財富資本有效地轉化為文化資本、政治資本和社會資本,推動了富民階層的成長,也在這個過程中實現了富民士紳化。
具體而言,財富是富民在社會上立足和發揮作用的基礎,但在商品經濟競爭性、流動性規律的作用下,貧富分化和流變十分頻繁,“千年田換八百主”,擁有財富者要保持家業的長久興旺,必然傾向于追求更為穩定的職業和更高的社會地位。進入官僚階層顯然是當時最理想的選擇,宋代一位官員曾說:“今天子三年一選士,雖山野貧賤之家所生子弟,茍有文學,必賜科名,身享富貴,家門光寵,戶無徭役,休蔭子弟,豈不為盛事?”[注](宋)陳襄:《古靈先生文集》卷20《仙居勸學文》,《全宋文》(第50冊)卷1083《陳襄七》,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年,第103頁。由此在社會中形成“中上之戶,稍有衣食,即讀書應舉或入學校”[注](宋)張守:《毗陵集》卷7《論措置兵民利害劄子》,《全宋文》(第173冊)卷3786《張守八》,第320頁。的風尚。宋代以后蒙學、鄉學等鄉村教育的發展,則是廣大庶民特別是富裕之家為追求社會地位改變而戮力推動的結果。
從明代進士家庭成分統計表來看,永樂九年(1411)至成化五年(1469)之間,社會流動率在60%-86%之間,弘治十八年(1505)以后在38%-55%之間。有明一代基本保持50%左右的上升率。[注][美]何炳棣:《科舉和社會流動的地域差異》,王振忠譯,《歷史地理》第11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明代后期到清代,科舉制度形成的社會流動逐漸減弱,但是仍然具有流動意義。錢穆認為中國社會特殊性有三,其中之一是“士常出于農民之秀者,后世之所謂耕讀傳家,統治階級不斷自農村中來”[注]錢穆:《政學私言》,《錢穆先生全集》,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142頁。,所言就是富民在科舉制度的激勵下支持弟子讀書,通過考試選拔機制使家庭中的成員進入官僚集團,從而穩定家業和提升家庭社會地位現實。在此過程中,富民實現了向“士”轉化的過程。
科舉制度被認為是具有“平等精神”的人才選拔制度,事實上這是對富民階層更為有利的制度。在缺乏公共教育制度的古代社會,延聘塾師或是將子弟送入私塾,以及不斷參加各級考試的考試費和旅行費,都需要長期支出不菲費用。故雖有異質才俊者出身貧寒,但大多數中舉者都是家庭殷實者。另外,富人實現縱向社會流動還有一個特殊的便利,就是他們可以通過捐納買官,如清代可通過捐例監生和例貢生跳過“童試”,官方還專門為特殊商人(鹽商)設立單獨考試名額。[注][美]張仲禮:《中國紳士:關于其在十九世紀中國社會中作用的研究》,第202頁。
當然,通過科舉成為官僚集團中的一員這一通道仍然是狹窄的。即便是北宋以后科舉取士名額不斷增加,國家官僚制度能夠容納的人數的有限性與富民群體規模擴大、考試大軍人數逐年增長的矛盾仍不斷加劇,科舉入仕之途始終處于千軍萬馬過獨木橋之態,能夠通過鄉試、省試、殿試三級考試,最終進入國家官僚體系的人為數寥寥。即便經過千辛萬苦實現了科舉登第,士人的仕宦命運也頗為艱難。隨著讀書應試人員規模擴大和科舉取士名額增多,官僚職位有限,獲得選人資格者雖能得到一個官職頭銜,但是需要經過多年的“選海”和“待闕”并在多位舉薦官推薦之下方得“破白”改官。在這樣的制度設計之下,大量無權無勢的士人流向地方社會。[注]王瑞來:《士人流向與社會轉型》,《上海師范大學學報》2014年第3期。與此同時,一些通過科舉獲得功名在官僚體系任職者,在其致仕之后也回流到地方社會,此即在官為“士”、在野為“紳”。需要強調的是,明清時期在鄉村社會里十分活躍并呈現出地方代言人特色的,當屬那些獲得官方正式認可的學銜和官職、但是并沒有資格實際任職的群體,例如明清時期通過“童試”獲得生員頭銜者,以及那些通過捐納、舉薦、賜爵等方式獲得官職或者某種功名(如監生、例貢生)者。這些人被張仲禮稱之為“下層紳士”,所享有的官方特權十分有限,在社會聲望方面也大大低于“正途”獲得功名者,卻構成了這一階層龐大的數量規模。[注][美]張仲禮:《中國紳士:關于其在十九世紀中國社會中作用的研究》,第1-75頁。
由此可見,富民階層士紳化的過程,也就是富民階層在追求更高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的過程中發生分化而走向地方化、民間化的過程。正是由于明清時期農產品商品化趨勢進一步加強、手工業和商業結合得更加緊密、商品經濟得到更為廣泛和更加深化發展這一社會經濟背景下,財富與知識、政治權力進一步集中的程度不斷加深,士紳階層也因此應運而生。可以認為,士紳實質上是富民階層的一部分,富民才是士紳的基礎。富民士紳化并非簡單的社會現象,而是富民發展壯大后的一種必然趨勢。
四、明清社會是“市民社會”嗎?
“市民”并非一個空間意義上的概念,而是社會意義上的概念,是10世紀以來西歐城市復興運動中發展起來的新興社會力量,他們在經濟上追求自由化,以發展工商業為主;在政治上批判專制主義,尋求政治的民主;在價值觀念上,追求人的解放和思想的自由。市民社會是市民階層為主體、追求個人自由和法治社會而產生的一種新社會形態。黑格爾認為市民社會的基本特點是個體自由和個人權利的獲得。霍布斯指出市民社會的基礎是國家提供社會秩序保障。馬克思強調了市民社會是商品經濟下締結的社會關系的總體呈現。葛蘭西認為在社會意識形態上掌握權力才是市民社會的基礎。哈貝馬斯進一步將市民在“公共領域”的參與度和話語權作為理解市民社會的維度。從十四五世紀到十八九世紀,西歐社會經歷了城市復興運動、思想啟蒙運動、工業革命、資產階級革命等一系列重大社會變革,推翻了封建君主制度,建立了以資本主義制度為其制度基礎的市民社會。從黑格爾到哈貝馬斯對市民社會的種種表述,正是上述歷史過程的理性觀照。一些中外學者將明清社會看作是“市民社會”,似有西方經驗套用中國問題研究之嫌。
(一)明清“反封建”斗爭是富民階層與國家的矛盾而非市民階層的資本主義運動
前文已述,一些學者強調明清時期新興的“市民階層”作為一種社會力量所發起反封建斗爭。應該看到,富民與國家始終處于既依存又對立的關系,富民與國家的博弈長期存在。如在北宋時期國家按戶等攤派差役,主要依靠富民提供公共服務,有不少富民不堪差役之苦采取“析居”等方式逃避之法。又如南宋時期地方官員依靠富民賑災救濟,但是一些富民卻采用不予理會或公然反抗的方式抵制。[注]參見張錦鵬:《北宋社會階層變動與免役法制度創新》,《西南大學學報》2007年第3期;《財富改變關系:宋代富民階層成長機理研究》,《云南社會科學》2016年第6期。明清時期的確出現了不少與富民、士紳組織或參與的社會沖突,典型的事例如蘇州機戶抗稅運動、蘇松地區的搶米風潮等等。[注]相關事件可參閱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經濟試探》,第287-335頁。不過,這些群體事件所表達的訴求,僅僅是罷稅和抗議物價這類經濟訴求,或者是對貪官污吏的懲罰,沒有明確的政治指向和權力要求。一旦官府為平息勢態取消不合理科索或懲罰當事官吏,反抗者的訴求得到回應,斗爭隨即平息。但是,經濟領域的種種不合理現象和制度依然普遍存在,廣大工商業者相同的命運依然在不同的時間和地點繼續上演。這表明,這些財富實力有進一步增長的工商業者,他們關心的只是自己的命運而非群體的命運。同樣,在各種反抗斗爭中起領導作用的“下層士民”,是士紳化的富民,也是追求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的個體性表達,他們與國家的矛盾,即是富民與國家的矛盾而非其他性質的矛盾。這種矛盾自富民階層產生起就一直存在,并伴隨著富民階層的成長過程而呈現出多樣性。
(二)明清時期思想領域的新思維是“保富論”的繼承發展而非啟蒙思想出現
明清時期是否出現啟蒙思想的問題,也是討論明清是否是“市民社會”的一個焦點。王夫之、黃宗羲、顧炎武、戴震、章學誠、龔自珍等人的思想,常被看作是中國早期的啟蒙思想。[注]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第5卷《中國早期啟蒙思想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但21世紀以來已有不同的評價。葉世昌分析了王夫之早期的保商思想和晚期的抑商思想,認為抑商思想是王夫之的主流思想;對黃宗羲的工商皆本論也從其特定涵義去理解,進而否定其“啟蒙”性。[注]葉世昌:《中國古代沒有代表“市民階級”的啟蒙思想》,《上海財經大學學報》2005年第4期。筆者認為,明清時期在思想領域的確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也產生了一些新的觀點,但是從根本上說,這些新的思想和新的觀點都是唐宋以來思想觀點的進一步豐富和發展,在根本上沒有脫離傳統思想的范疇,所以很多思想家在闡述自己思想的時候表現出矛盾性和兩面性。
討論思想領域內的變化,值得關注的是宋代以來“保富論”的新思潮的興起與發展。所謂“保富論”就是公開宣揚富民的重要性,并主張對富人予以保護。宋代“惟州縣之間,隨其大小,皆有富民。”如何看待富民和貧富不均問題,蘇轍認為:“此理勢之所必至,所謂: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注](宋)蘇轍:《欒城集》(下)卷8《雜說九首·詩病五事》,第1555頁。司馬光認為:“夫民之所以有貧富者,由其材性愚智不同。”[注](宋)司馬光:《司馬光集》卷41《章奏二六·乞罷條例司常平使疏》,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920頁。明代邱浚也認為:“天生眾民,有貧有富。”[注](明)丘浚:《大學衍義補》(上)卷25《市糴之令》,北京:京華出版社,1999年,第242頁。王夫之認為“兼并”“積習已久……而弱者亦且安之矣”[注](明)王夫之:《讀史通鑒》卷5《哀帝》,《船山全書》第10冊,長沙:岳麓書社出版社,2011年,第193頁。,這種情形“非豪民之能鉗束貧民而強奪之”[注](明)王夫之:《宋論》卷12《光宗》,《船山全書》第11冊,第277頁。。這說明,宋以來人們對存在富民階層這一現象已達成共識,認為這是社會發展的客觀必然性,各階層都應該接受貧富分化這一事實。從富民與國家的關系來看,由宋元至明清,很多思想家都極力強調富民對國家的重要意義。如葉適指出:“富人者,州縣之本,上下之所賴也。”“富人為天子養小民,又供上用,雖厚取贏以自封殖,計其勤勞亦略相當矣。”[注](宋)葉適:《水心別集》卷2《民事下》,《葉適集》(下),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第657頁。丘浚說:“富家巨室,小民之所賴,國家所以藏富于民者也。”[注](明)丘浚:《大學衍義補》(上)卷13《蕃民之生》,北京:京華出版社,1999年,第123頁。王夫之亦言:“大賈富民者,國之司命也。”[注](明)王夫之:《黃書》大正第6,《船山全書》第12冊,第530頁。“國無富人,民不足以殖。”[注](明)王夫之:《讀通鑒論》卷2《漢高帝》,《船山全書》第10冊,第89頁。清末的魏源也提出:“富民一方之元氣,公家有大征發,大徒役皆依賴焉,大兵,大饑饉,皆仰給焉。”[注]魏源:《古微堂內外集》卷3《治篇》,近代中國史料叢刊本第43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第164頁。顧炎武針對江南地區重賦的問題對朝廷提出嚴厲批評,正如今人鄭天挺所評論:“蘇、松、常、鎮、嘉、湖、杭七府賦重,這是事實,但是官僚吵嚷賦重,是代表誰說話呢?他們不是代表一般農民,而是反映富戶的愿望。”[注]鄭天挺:《讀〈明史·食貨志〉札記》,《及時學人談叢》,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83頁。至于東林黨人反對礦監監稅使、體恤富民的思想,是城市經濟發達以及商人和富民力量增強的反映。與一些學者將東林學派的主張看作“市民意識”觀點不同,亦有學者認為,明代后期陽明學派、東林派、朱子學派所共有的理念,就是藉“禮”實現宗族、鄉村秩序的確立。[注][日]小島毅:《中國におけゐ禮の言說》,第七章至末章,東京大學出版會,1996年。筆者認為,這些觀點揭示了明清思想領域的主流與本質。
由此可見,明清時期這些思想認識與宋代“保富論”一脈相承,是宋代“保富論”的繼續和發展,要說它們之間有什么不同,那就是明清時代的思想家呼吁保護富民的言論更多了,討論如何處理富民與國家關系問題更為深入和多視角了。如黃宗羲所提出的“工商皆本”論,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把農業為本工商為末的思想顛倒過來;又如,顧炎武認為追求個人利益是實現國家富裕的結果,[注](清)顧炎武:《日知錄集釋》(全校本)卷13《名教》曰:“司馬遷作《史記·貨殖列傳》謂:‘自廊廟朝廷巖穴之士,無不歸于富厚。’等而下之,至‘吏土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于賂遺。’而仲長敖〈核性賦〉謂:‘倮蟲三百,人為最劣。爪牙毛皮,不足自衛,唯賴詐偽,迭相嚼嚙。等而下之,至于臺隸僮豎,唯盜唯竊。’乃以今觀之,則無官不賂遺,而人人皆吏士之為矣;無守不盜竊,而人人皆僮豎之為矣。自其束發讀書之時,所以勸之者,不過所謂‘千鐘粟’‘黃金屋’,而一旦服官,即求其所大欲。君臣上下懷利以相接,遂成風流,不可復制。”黃汝成集釋、欒保群等點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767頁。與曼德維爾《蜜蜂的寓言》所分析“個人惡行能導致社會繁榮”[注][荷蘭]伯納德·曼德維爾:《蜜蜂的寓言》,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的觀點異曲同工。這說明,明清時期的思想家在對經濟現象的本質性認識較之前的思想家更進一步。
(三)明清民間組織并非為批評政府的“公共領域”而是“國家話語”的地方代言人
關于明清出現“公共領域”這一問題,如蘭京和羅威廉通過對浙江和漢口的個案研究,強調清代城市體系里有一個由商人、士紳所主導的公共領域,發揮了城市自治功能和對政府的批評功能。如羅威廉指出,“19世紀中國城市中,不僅形成了城市階級,也出現了城市社團”,形成了一個以行會為中心的,實質層面上的市政管理機構”,“這說明,政治功能的逐步普及化是以經濟力量的‘私域化’平行展開的。”[注][美]羅威廉:《漢口:一個中國城市的商業和社會(1796-1889)》,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415-421頁。不可否認,明清時期商業行會、商人會館、善堂善會、地方宗族等成長很快,并且在社會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不過,這些中間組織并非明清時代的產物,如明清時期十分興盛的商業行會、會館,其前身即為宋代的行會,這是宋朝官府為了便于對商人征稅斂費而成立的行業中間組織。明清時期商業行會、會館雖已褪去官方色彩,但也并非是國家的異己力量。王日根對明清會館進行全國性和整體性考察發現:至明清時期,在商業會館、士紳會館和移民會館中,“士紳、士商或紳商發揮了重要作用,商人的士人化、士人的商人化是明清市場經濟發育的直接產物,也注定了這一時期從商人員盡管眾多,卻并無明確的政治地位,自我獨立意識亦不顯著,從而使明清社會在總體上尚未脫離傳統社會軌道。”[注]王日根:《中國會館史》,上海:中國出版集團東方出版中心,2007年,第442頁。究其史實,商人會館多以商務和教育為其首要目標,以信息融通、互助協作的方式拓展商務,是“富民階層”追求財富為其目標而抱團求利的產物。會館也承擔了支持商人弟子或同鄉黨族科場考試“俱樂部”的教育功能,表明會館在“富民階層”士紳化中所發揮的平臺作用不可忽視。王日根進而認為會館在社會整合方面所起到的作用是有限的,“他們在會館竭力謀求本會館成員間的感情聯絡、信息交流與穩定發展,實際上也維持了基層社會的穩定,彌補了封建管理體制管理社會的不足之處”,因此“會館的發展是明清中央集權加強與基層社會自我管理機制不斷建立與完善的結果”。[注]王日根:《中國會館史》,第443頁。李約瑟也曾經說過:“中國的商會也是社會上的一部分團結力量,只是它并不像歐洲的商會那樣具有政治上的重要作用。”[注][英]李約瑟:《四海之內:東方和西方的對話》,勞隴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7年,第49頁。
至于明清華南宗族的發展,亦有一些學者認為“是明代以后國家政治變化和經濟發展的一種表現,是國家禮儀改變并向地方社會滲透過程在時間和空間上的擴展。這個趨向,顯示在國家與地方認同上整體觀念的改變。宗族的實踐,是宋明理學家利用文字的表達,推廣他們的世界觀,在地方上建立起與國家正統拉上關系的社會秩序的過程。”[注]科大衛、劉志偉:《宗族與地方社會的國家認同——明清華南地區宗族發展的意識形態基礎》,《歷史研究》2003年第3期。而由地方士紳所興辦和領導的明清民間慈善機構,主要起到的是國家制度和傳統秩序的維護作用,而非獨立運行的、甚至與政府對抗的異己力量。[注]梁其姿:《施善與教化:明清的慈善組織》,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08頁。這些富民階層利用組織和運營民間慈善機構來傳播儒家價值,推行儒家秩序,以紓解明清時期因經濟發展和各種社會矛盾所造成的社會焦慮,“沒有任何一個階段的善堂對既存社會秩序及政權提出挑戰,它們的主要功能是鞏固既存秩序”[注]梁其姿:《施善與教化:明清的慈善組織》,第322頁。。
總體來看,學界有關明清“市民社會”的分析和論證,對學界充分認識明清社會的變化有很大的啟發。但是認為明清是“市民社會”的說法并不能令人信服。筆者認為,這是以西方坐標來標示中國社會,是用西方話語來解釋中國問題,并不能從本質上認識和理解中國社會。
五、明清社會依然是“富民社會”
綜上所述,明清社會從根本上來說還是一個富民社會。明代陳邦瞻在編撰《宋史紀事本末》時指出:“宇宙風氣,其變之大者三:鴻荒一變而為唐、虞,以至于周,七國為極;再變而為漢,以至于唐,五季為極;宋其三變,而吾未睹其極也。”[注](明)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附錄1《宋史紀事本末敘》,北京:中華書局,第1191頁。按照他的說法,宋代形成的新的社會,到明代還在繼續發展,并未達到它的頂點。近代思想家嚴復也說:“中國之所以成為今日現象者,為善為惡,姑不具論,而為宋人之所造成,什八九可斷言也。”[注](清)嚴復:《嚴幾道與熊純如書札節鈔》,《學衡》第13期,上海:中華書局出版社,1922年,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影印本。在嚴復看來,由宋而起的一些重要因素長期地規定著社會發展走勢,從宋代到他所處的近代都是一個完整的歷史階段。日本學者中島樂章亦指出近年有關研究呈現一種趨勢:“在以往的中國史研究中,對于宋至清這一傳統中國的后期,有明確區分為‘宋元史’與‘明清史’的傾向。但最近越來越多的研究,無論是政治制度史、社會經濟史,相比元、明間的中斷性,反而更重視起來連續性。”[注]中島樂章舉出砂明德的《江南史的水脈》、檀上寬《明初帝國體制論》都是這傾向的成果,他自己亦持有相同的觀,參見其著作《明代鄉村糾紛與秩序:以徽州文書為中心》。這些認識與我們對歷史發展演進的階段性判斷是一致的,宋元明清是一個完整的歷史時期,明清社會仍然是“富民社會”。理由有三:
其一,“富民”階層依然是推動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動力層。富民階層是商品經濟發展的產物,商品經濟發展又進一步促進了富民階層壯大。在追求自身財富的過程中,富民階層作為社會的動力層,推動了社會生產力進一步發展。李伯重對江南經濟發展的研究表明,明清時期中國經濟并未陷入“馬爾薩斯陷阱”,經濟仍然呈現出繼續發展的特性。推動明清江南經濟發展的最主要力量是分工和專業化的發展,即“斯密型動力”。[注]李伯重:《英國模式、江南道路與資本主義萌芽》,《歷史研究》2001年第1期。按費維凱的分析,“斯密型成長”模式經濟總量、勞動生產率都能夠提高,但是技術變化不大。[注]Albert.Feuerwerker.“PresidentialAddress:Questions about China's Early Modern EconomicHistory that I Wish I Could Answer”,Journal of AsianStudies (Ann Arbor),Vol.5,No.4.為什么這一時期技術創新動力不足,而以集約化勞動方式或以專業化方式提高生產率成為人們追求的目標?關鍵因素在于這一時期生產力發展的背后推動力量,主要靠的是富民階層。“土地是財富之母,勞動是財富之父”,這是富民階層藉以成長為財富力量的源泉。與技術創新風險大、周期長、需要特殊才能相比,最大化利用土地和最合理利用勞動力成為有財富實力或投資能力的富民,是成本最低、風險最低、收益最明顯的選擇。從產權角度來看,富民階層在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過程中,推動了農業經濟中的租佃關系和雇傭關系深化發展,促進了產權實現形式多元化和資源配置方式合理化。這就是繼宋代農業發展達到了相當的水準之后,明清時期繼續保持了穩步增長原因所在。在工商領域中,富民階層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的結果,則是擴大了市場容量,促進了產品商品轉化率和商品市場擴散度。僅以與富民生產經營活動關系最為密切的糧食貿易而言,郭松義估測乾隆時期商品糧長距離運輸4350—5450萬石,另有跨省的中距離糧食運輸約300萬石。[注]郭松義:《清代糧食市場和商品糧數量的估測》,《中國經濟史研究》1994年第4期。龍登高估計乾隆時期米糧長距離貿易為4600—4800萬石,可能達到5000萬石。[注]龍登高:《中國傳統市場發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77頁。以國內市場中的大宗商品結構來看,清代市場上最大量值的工業品已經從明以前的鹽向棉布轉換,吳承明先生精辟地指出:“這是一個進步。因為鹽的產量,僅決定于人口數量;布,則與社會經濟的發展密切關系。”[注]吳承明:《論清代前期我國國內市場》,《歷史研究》1983年第1期。這些發展變化,無不以富民階層追求個體經濟利益的動力直接勾連。這便是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強調的:每個個體追求各自的經濟利益,最終導致的是國民財富的增長。[注][英]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年。
其二,富民依然是國家統治所依賴的中間層。自富民成為中國傳統社會的一個重要階層,富民就是國家統治者所依賴的對象。中唐“兩稅法”的改革將國家稅賦征收依據由人丁轉向資產,兩宋按民戶資產高低來征取役錢和差役的趨勢進一步擴大。[注]參見葛金芳《兩宋攤丁入畝數辨析》,《中國經濟史研究》1988年第3期。《兩宋攤丁入畝趨勢輔論》,《暨南大學學報》1991年第3期;柳平生、葛金芳《南宋攤丁入畝考析》,《思想戰線》2018年第2期。明清時代通過“一條鞭法”和“攤丁入畝”的改革,以財富豐少決定承擔賦役多寡在制度上更明晰化和在差派上更便利化,其目的同樣是達到國家租金最大化。明初推行依靠富民的糧長制,任用富民擔任糧長并給予具有皇權特色的儀式性獎勵,其目的在于“以良民治良民”。[注]《明太祖實錄》卷68,洪武四年九月丁丑,第1279頁。朱元璋在晚年頒布《教民榜文》:“今出令昭示天下:民間戶婚、田土、斗毆、相爭,一切小事,須要經由本里老人、里甲斷絕。若系奸盜詐偽、人命重事,方許赴官陳告。”[注]一凡藏書館文獻編委會:《古代鄉約及鄉治法律文獻十種》(第1冊),明太祖欽定《教民榜文》,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89頁。能擔當此責的耆老,不僅是年高者,“其合設耆老,須于本鄉年高有德、眾所推服人內選充”[注]何廣:《律解辯疑》卷4《戶律·禁革主保里長》條,《中國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編第1冊,北京:科學出版社,1994年,第299頁。,實則由有財富、有文化、有威望的年長的富民來擔當此任,這也是國家充分利用富民在地方的社會影響力來實施社會控制、降低官府行政成本之舉。不少實證研究表明,明代中后期仍然有相當多的地域性民間糾紛是通過鄉紳等名望人士“排難解憂”,或豪民等“武斷鄉里”“私受詞狀”。[注][日]中島樂章:《明代鄉村糾紛與秩序:以徽州文書為中心》第283頁。岸本美緒也指出清初期無論是“國家審判”還是“民間調停”對當時地方社會的人們來說,都是休戚相關,十分盛行的。[注][日]岸本美緒:《〈歷年記〉所見清初地方社會生活》,初出《史學雜志》95編6號,1986年。后收入岸本美緒《明清交替與江南社會——17世紀中國的秩序問題》,東京:東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有學者指出:明代地方社會“這是以南宋至元代不斷增強的士人和當地有勢力者、有名望人士通過精英主義完成‘自下而上’社會秩序形成為基盤,通過國家控制,重新構建‘自上而下’的鄉村統治體制”[注][日]中島樂章:《明代鄉村糾紛與秩序:以徽州文書為中心》,第284頁。。清代統治者借助保甲制度實施基層控制,保長、甲長仍然是由地方富民、富戶擔任。士紳階層由富民轉化而來,因其具文化優勢和特權榮耀,更容易形成地方性影響力,統治階層深刻地認識到士紳階層在鄉村社會的重要性,主動利用他們為自己的統治服務。晚清時期面對白蓮教反叛等社會秩序失控情勢,朝廷在各地倡導興辦團練,其團練負責人,亦從士紳中選拔。應該看到,武裝力量的地方化和非國家化,客觀上會對國家安全和政權穩定造成很大的政治風險,不過清朝團練“地方組建武裝的形式還是趨于沿著實際存在的政治和社會體制的軸線具體化”[注][美]孔飛力:《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第11頁。。這表明,主持團練的士紳仍然是以國家意志為社會擔當。毋庸置疑,在國家統治者極力利用富民來進行社會秩序控制的實踐中,重構和強化了富民作為社會中間層所發揮的作用。
其三,富民依然是維護社會穩定的穩定層。一些學者將明清社會稱之為士紳社會,充分肯定士紳在介于國家行政機構和個人或家庭領域之間的“公共領域”所發揮的積極作用。明清的國家制度設計上確實體現了“皇權不下縣”,以縉紳地主、鄉紳為主體的地方精英對鄉村社會形成了實際控制權。需要強調的是,士紳所發揮的作用并非代替國家進行鄉村自治,而是主動配合國家進行社會治理。眾所周知,鄉約、社學是明中葉以后廣泛發展起來的基層教化組織,是鄉紳施展其社會影響力的舞臺。清代鄉約的主要職能是定期宣講圣諭(康熙《圣諭十六條》、雍正《圣諭廣訓》等),社學宗旨是“教子弟以正其身心為首務”,“凡學徒入塾,須先讀《小學》、《孝經》,以端其本”[注](清)丁日昌:《撫吳公牘》卷9《札蘇藩司飭屬設立社學》,《丁日昌集》(上)卷4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91、492頁。。它們都是主動配合國家治理需要,以傳播和強化統治者意志為其宗旨。明末同善會以代表儒學正統的孟、荀、揚雄、王通、韓愈等“賢人”為崇拜對象,到了清中期,道教的文昌帝君代替了“五賢”而成為同善會的神祗。[注]梁其姿:《施善與教化:明清的慈善組織》,第159頁。梁其姿分析這一變化原因是辦會組織者從名流大儒向地方一般士人轉變,行善目的從積善避災向追求功名轉變。從明代儒學道義轉向清代追求科舉功名這一變遷路徑來看,善會組織中本質性的東西并沒有改變,行善的目的在于通過積德積善來提高自我修養,進而踏上功名之路,而這一切是以遵循國家正統和儒家文化價值為其前提的,是士紳主動向國家意志靠攏的體現。善堂善會的組織者多為中低級士紳,而以高級士紳為主體的學術界、思想界,亦盛行同樣的價值理念。在其他地方性公共活動中,這些被稱為地方精英的士紳們,也是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己任,以國家倡導的儒家價值約束自己、規范他人,積極地以貫徹國家制度地方化實踐為其榮耀,從而形成了事實的鄉村自治或地方化運動。政府雖然不在場,但是國家的影子無處不在,國家意志時時刻刻規范著影響著人們的社會生活。這正是明清富民階層在地方社會中主動維護國家秩序的結果。
六、余 論
不可否認,明清社會從表象上出現了一些令人矚目的新變化和新事物,然而若從社會特質視角去探究,我們發現,這些新變化和新事物都發端于唐宋社會變革之際,且與富民階層息息相關。自晚唐以降,一個新的社會階層——“富民”階層崛起,并在宋元明清這一長時段中發揮著社會的動力層、中間層、穩定層的作用,使這一時期成為與上古三代的“部族社會”、漢唐時代的“豪族社會”完全不同的“富民社會”。
就本文考察的明清社會而言,這一時期的富民、富戶并非市民,他們與西歐資產階級革命前夜的市民階層存在著本質的區別。“富民”階層在追求個體經濟利益最大化的同時,也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發展走向多元化,提供了社會經濟發展的物質動力;朝廷利用富民的財富力量增強了國家的社會保障力和地方治理力。他們是推動社會沿著原有軌道繼續向前的強大驅動力,而非變革傳統制度的新興資本主義力量。明清時期在各種“中間領域”或“公共領域”中盛行的價值理念,也始終與國家意志和儒家價值保持一致,主動與政府同構社會秩序,這與西方市民社會中國家與個人之間具有獨立主體意義的“公共領域”有著根本不同。因此,明清社會不是“市民社會”,而是與宋元一脈相承的“富民社會”。唯有把宋元明清作為一個完整的歷史階段,突破斷代研究的局限性,做跨時段通貫性研究,才能找到解構中國傳統社會變遷的鑰匙。
明清時期“富民”階層的士紳化,既增強了“富民”階層的社會話語權和社會影響力,也為“富民社會”的衰落和走向終結埋下了伏筆。擁有文化知識成為“富民”階層的利器,既可通過科舉渠道獲得政治特權,也可通過文化資本獲得地方權力,無所不在的明清士紳地方控制就是主要以其政治特權和文化資本而獲得的。縱觀歷史的發展,任何一個階層,一旦取得政治特權并形成一定的壟斷之后,必然走向反面,士紳階層也是如此。當通過“士”與“官”成功對接,富民就脫離了“民”,成為“官”的支持者而非“民”的代言人。當富民為科舉入仕為目標按照國家價值導向學習知識,他們所形成的文化權力在進行基層控制時,必然成為國家秩序的維護者而非個體價值的倡導者,這個階層就越來越遠離了“民”的特色和活力了。由此可見,“富民社會”向“士紳社會”轉化時,其間不可避免地會發生自掘墳墓的邏輯,那就是“士紳社會”是“富民社會”的最高階段也是最后階段。“富民社會”的發展前景應是近代的“市民社會”,中國社會演進之路終將被近代化的曙光照亮而邁向新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