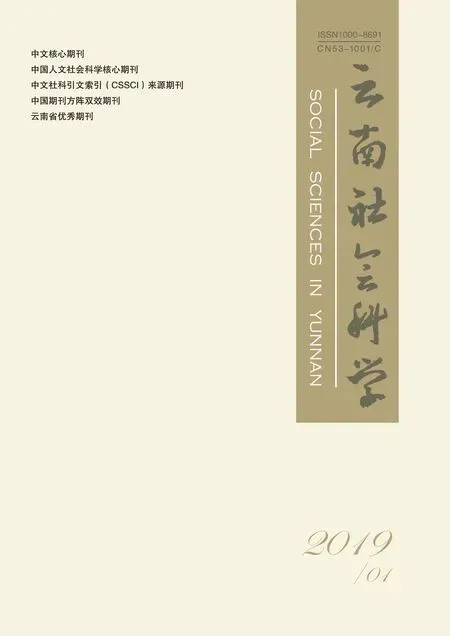中國國家縱橫治理結構的原型與轉型
——基于家戶制的視角
任 路
國家治理現代化是整個現代化進程中的關鍵問題,但是每個國家在治理現代化的進程中所選擇的道路卻是不同的。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談治國理政時一再強調:“一個國家選擇什么樣的治理體系,是由這個國家的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決定的,是由這個國家的人民決定的。中國今天的國家治理體系,是在中國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上長期發展、漸進改進、內生性演化的結果。”[注]①習近平:《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人民日報》2014年2月18日。為此,需要對中國國家治理體系進行歷史性的回溯,近年來,一些學者提出“郡縣國家”引起了有關傳統國家治理體系的廣泛討論[注]②相關討論集中在曹錦清、劉炳輝發表的系列論文,如曹錦清、劉炳輝:《郡縣國家:中國國家治理體系的傳統及其當代挑戰》,《東南學術》2016年第6期;曹錦清等:《筆談:郡縣制傳統與當代中國治理》,《華東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5期;劉炳輝、熊萬勝:《超級郡縣國家:中國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演變與內在機制》,《東南學術》2018年第3期。,不過,“郡縣國家”主要側重于“制度”本身,如中央集權郡縣制、文官制度、行政區劃和鄉土社會自治等,對于傳統國家治理體系所賴以存續的社會土壤并未有過多的闡述,這恰恰是傳統國家治理體系之所以長時間延續的關鍵所在。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國家治理結構實際上是內生于一定的社會土壤之上。中國是典型的小農社會,在“一家一戶”的小農社會基礎之上的國家治理結構是什么形態?本文從家戶制的視角出發,提出中國國家治理體系是以“家”為單位的國家橫向治理與以“戶”為單位的國家縱向治理的結合,這種縱橫的治理結構最早可以追溯至早期國家形成時期,其后一直延續下來,并在整個現代國家建設進程中長期發展、漸進改進和內生演化,以至于當前乃至將來一段時間中國的治理結構仍然表現為國家縱向治理與基層社會橫向治理結合的特征。
一、家戶傳統與國家治理結構原型
縱觀世界歷史,國家之間的競爭不僅僅是經濟實力的比拼,而且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較量。近代以來,中國在與西方現代國家競爭中屢屢失敗,傳統國家治理似乎走到了歷史的終點,主政者試圖自強、求富、變法、革命等來學習西方治國之道,然而中國現代國家構建并非坦途,而是一路坎坷,促使人們回過頭來重新審視傳統的國家治理,找到國家治理的起點和原型。起點決定路徑,原型制約轉型。所謂起點和原型是指:“那些能夠對現代社會產生長遠影響的本源型傳統,構成現代社會發展的基礎性制度,是現代社會的歷史起點和給定條件。”[注]徐勇:《中國家戶制傳統與農村發展道路——以俄國、印度的村社傳統為參照》,《中國社會科學》2013年第8期。中國作為一個早熟國家,秦漢以后就建立起以郡縣制為基礎的發達官僚組織體系,形成國家自上而下的縱向治理體系。但是受制于農業帝國有限的生產剩余,傳統國家在大多數時候里并不足以支撐深入基層社會的龐大官僚體系,以至于越靠近基層社會國家官僚就越少。統治者除了稅賦徭役治安之外,實行“以民治民”的策略,并不主動干預鄉村社會,以至于“人但聞嗇夫,不知有郡縣”,基層社會是“民事民治”的橫向治理,由此形成國家的縱橫治理結構。雖然歷經王朝更替,但是這一結構得以延續,成為中國國家治理結構的起點和原型。
當然,中國國家縱橫治理結構之所以能夠綿延不絕,除了郡縣和文官制度所構成的超穩定結構外,還有其深厚的社會基礎,即家戶制傳統。在歷史上,“家”與“戶”是兩個不同性質的社會單元,從“戶”的基礎上形成國家縱向的行政管理體系,從“家”的基礎上形成國家橫向的社會自治體系,并成功地在傳統國家治理結構中合為一體,將國家縱向的行政管理建基于橫向的基層社會自治,形成一種具有內在韌性的國家治理結構。
一是自戰國后期到秦朝,廢井田、開阡陌,以前的宗法農民由于國家授田,逐步成為國家的“編戶”。“編戶”的結果是形成以居住地為標準將家庭和及其個體劃分為責任單元,其上輔以作為基層建制的鄉里制或保甲制,延伸到郡縣的建制體系,“戶”遂成為整個國家治理的基本單元,是國家組織、社會治安、賦稅征收、壯丁分配和臨時差役的單位。傳統國家依托于“戶”這一單位,雖然“皇權不下縣”,但是其行政影響力可以延伸到縣級以下。由此建立起國家自上而下縱向治理關系。這一治理關系由郡縣制和賦稅作為紐帶,表現為“行政權力支配社會”。
二是中國的“戶”是建立在“家”的基礎之上。“古代中國以小農經濟為基礎,一個個相互獨立的家戶構成了社會的基本組織要素。”[注]徐勇:《非均衡的中國政治:城市與鄉村比較》,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年,第72頁。并且“家”是比“戶”更為久遠的血緣組織。歷史越往前追溯,“家”的作用就越明顯。對于有著悠久文明的中國,同樣有著悠久的“家”傳統,進而將國家治理化簡為“齊家治國平天下”,將“家”作為整個國家治理的基礎。于是在“集家成國”的邏輯下,國家治理以“家”為基點形成三個層次的基層社會治理結構,最基本層次的是“家治”,即以家庭為單位形成的治理。“‘家’是整個社會與政治的基本組成單元,家庭內部的老人權威和長幼有序的秩序,即‘男女有別、長幼有序’和‘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的制度規范是內生的,并內化于家庭成員的精神之中,具有強大的自治力量。”[注]徐勇:《中國家戶制傳統與農村發展道路——以俄國、印度的村社傳統為參照》。中間層次的是族治,即擴大的家,宗族范圍內的自我治理。巴林頓·摩爾在論述傳統中國時認為:“中國農民往往在家庭或宗族中按照自己的方式維護秩序,農民除了要求官府防止強盜保護谷物以外,對官僚機構并無他求。同時,官府和上層階級對農民的基本生活方式起不到什么作用,中國農民主要生活在自己的小家庭或者大家庭內部。”[注][美]巴林頓·摩爾:《民主與專制的社會起源》,拓夫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87年,第163-165頁。最外層次的是村治,即家之外村落空間內自身力量形成的治理。非血緣關系的農戶并沒有宗族那樣的先賦性的共同要素,而是后天所面對的公共問題形成的,比如共同安全、水利合作、生產互助等。顯然,這些問題已經超出的家庭與宗族的能力范圍,農民不得不在血緣單位之外建立新的地緣上的橫向聯系,以便能夠解決共同問題,滿足共同的需求,從而形成跨越血緣家庭或家族之上的村落自我治理。
與中國傳統社會的超穩定結構一樣,基于家戶制度的國家縱橫治理結構雖然歷經政權的更替和王朝的循環,但是始終以不同的表現形式存續下來,并在不同階段呈現不同的形態。王朝初立則重編戶籍,強化國家稅賦治安責任,待政權穩固則逐步減輕國家干預,倡導鄉紳自治,以達到“以民制民”的目的,到后期則由于戶政荒廢,難抑地方勢力,遂出現政權崩潰,國家又進入下一個王朝政治循環之中。整體上,傳統國家治理依賴于“家”與“戶”兩個單元的合力,同時“家”與“戶”之間也存在著內在的張力,在合力與張力的基礎上,歷史上曾經出現過不同程度的均衡或失衡狀態。歸納起來有三種典型的形態:
一是弱家強戶模式。以秦為代表,早在秦國,商君變法之初便頒布“分異令”,“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注]《史記·商君列傳》。概言之,由國家對家庭家族進行強制拆分,家里有兩個男丁而不分家,賦稅則要加倍。父母兄弟不能居住在一起,必須分家分居。其目的是建立歸屬于國家管轄的無數小農,并以一套完善鄉官制和嚴密的秦律將小農組織到中央集權的國家體系當中,由此建立國家與農民的直接聯系,并將稅賦徭役等直接加諸于農民,形成強大的國家動員和資源汲取能力。然而,弱家強戶的結果是國家與農民之間缺少中間緩沖地帶,孤立分散的小農失去了家族、村落共同體等血緣或地緣性保護,直接面對國家的稅賦徭役,往往因為征斂無度導致家庭解體,出現大量的破產小農,脫離本已弱化的血緣或地緣而成為流民,如此國家的編戶策略逐步走向崩潰,整個國家治理體系慢慢陷入衰敗的境地。由此表現為一種國家縱向治理占據絕對主導地位,而國家橫向治理虛弱的狀況。
二是強家弱戶模式。以魏晉南北朝為代表,隨著統一的中央集權的松弛,門閥士族等勢力控制著基層社會,國家雖然有編戶之名,卻沒有編戶之實,大量的小農依附于地方豪強巨族,淪為大族的莊戶或者部曲,地方豪強借助于特權聚攏族眾,隱匿戶口,強化人身依附關系,成為所謂的“塢主”,并在基層社會形成相對獨立的塢堡和莊園等。以往那種國家與小農的直接聯系被隔斷,稅賦徭役等也必須借助塢主等力量才能夠完成,以至于成為國家不得不承認的既成事實,北魏初期的宗主督護制便是一例。《魏書·李沖傳》記載:“舊無三長,惟立宗主督護,所以民多隱冒,五十、三十家方為一戶。”在這種情形之下,國家編戶齊民實際上已經名存實亡,依附宗主之下的農民往往有數百家、上千家,乃至萬家,均為私家人口,并未登籍,不是國家人口,對于國家稅賦征收和徭役調發來說極為不利。由此呈現的是以地方勢力自我管理為特點國家橫向治理發達,而以行政權力為載體的國家縱向治理相對羸弱。
三是強家強戶模式。以唐宋為代表,隋唐開始士族逐漸衰落,基于均田制基礎上的編戶再一次形成小農與國家的直接聯系,國家的賦稅徭役兵役等與田制結合起來,農民逐漸擺脫豪強大族控制,轉變為“國家農民”,使政府控制的小農人數大大增多,從而增強了國家縱向治理。延至宋代,均田制雖已崩潰,不抑兼并,土地自由買賣,地主經濟興起,但是與以前“宗主”相比,農民與地主的人身依附關系大為減弱,地主不足以形成與中央對抗的地方勢力,國家權力能夠延伸到編戶,之后的保甲制更進一步強化了國家控制。更為重要的是宋代開始興起的宗族,經過士大夫的積極倡導,逐漸形成敬宗收族之風,達到管攝人心和收攏族眾的目的,國家依靠血緣關系能夠更加順暢地組織基層社會,維持基層社會秩序,并建立了一系列與國家縱向治理相融合的宗族制度,如祭祖、族規、族訓、族長、族產等,此后逐步發展完善,一直延續到明清,成為中國基層社會自我管理的重要機制。即便皇權不下縣,也能夠天下治。
二、抑家強戶與國家縱橫治理結構的轉型
進入現代國家建設后,基于“家”與“戶”的傳統國家治理結構遭遇巨大的挑戰。對于國家治理來說,新政治對舊政治的改造首先是從作為傳統國家治理基礎的家戶制開始的。在傳統中國,家庭與整個國家治理相聯系,家庭構成了國家治理的社會基礎。當傳統中國步入現代世界體系之后,全面的民族危機導致全面的反思,在知識界醞釀著一股強烈的反傳統情緒,其中尤以對家庭的批判最為激烈,認為中國之所以落后是因為家庭的原因。新舊之間、傳統與現代之間的矛盾在家庭議題上得到充分體現。吉登斯在論述現代性過程中也認為:“家庭是傳統和現代性之間斗爭的場所。”[注]鄭曦原、李方惠:《通向未來之路:與吉登斯對話》,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47頁。于是,先知先覺的知識分子中提出了一大批家庭革命的論說,甚至有所謂毀家論,比如:“欲開社會革命之幕者,必自破家始”。[注]漢一:《毀家論》,《天義報》1907年第4卷,張枬、王忍之編: 《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2卷下冊),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0年,第932頁。之后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繼續批判傳統社會家長制、宗族制等,主張與傳統文化做一個徹底割裂。上述對于家庭及其背后傳統文化的批判集中在知識分子群體當中,類似于思想的啟蒙,并沒有擴展到整個社會群體,社會影響有限。不過,思想界已然開始重新審視家庭傳統及其在國家治理中作用,尤其是負面效應。后續的改革者或革命者試圖改造和超越血緣性的家庭或者宗族,在廣泛的意義上建立公民與國家的關系,逐步打破以“家”為基礎的國家橫向治理結構。很明顯,改造或者超越的第一步是從宗族這一“擴大的家”展開的,進而延展到村落,它們是整個國家與小農的中間層,猶如堅硬的外殼,保護家庭不受國家權力的驚擾,而國家權力向下延伸的過程中首先要面對的便是這一力量。
一是國家力量對宗族勢力的替代。J.羅斯·埃什爾曼在談到中國家庭的時候認為:“‘家庭’網絡表現了許多我們所知道的政府部門的職能,征稅,執法、教育,福利等。那么似乎可以相信,當一個革命政權建立之時,族會被嚴厲地批評。”[注][美]J.羅斯·埃什爾曼:《家庭導論》,潘允康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第210頁。基于此,在新政治建立的過程中,國家不斷地擴展著自己的職能,并向鄉村社會延伸權力,原來依靠宗族進行自我管理的方式逐漸被取代。辛亥革命以后,國民黨在鄉村建立了由人民選舉產生的新政權。這些政權并不能完全取代宗族,但有時被看作一種必須認真對待的勢力。隨著時間的推移,到30年代,宗族甚至在以往強盛的地區都似乎消弱了。[注][美]W.古德:《家庭》,魏章玲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6年,第168頁。當然,國家在基層社會對于宗族功能的替代需要隨著國家治理能力的提升逐步完成,但是不可否認的趨勢是宗族越來越成為國家的對立面。
二是邊緣人物對鄉紳階層的替代。20世紀以來,在宗族消弱的同時,原先在村落中充當自治力量的鄉紳階層也消失了。與鄉紳產生相伴的科舉制廢除后,鄉紳再生產機制中斷,城市工商業的發展讓原來居村的鄉紳離開土地,進入城鎮,鄉紳與村落的聯系中斷。正如杜贊奇所論述的一樣,“原來傳統士紳所承擔的保護型經紀逐漸從鄉村政權中隱退,豪強、惡霸、痞子一類邊緣人物開始占據底層權力的中心。充任公職演變成了為了追求實利,甚至不惜犧牲村莊的利益。”[注][美]杜贊奇:《文化、權力與國家》,王福明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49頁。原本存在于鄉村社會的宗族、士紳等橫向治理逐漸萎縮,于是出現了近代以來鄉村社會危機,由于宗族、士紳的退出,鄉村社會秩序混亂和公益事業廢弛,現代國家縱向治理又不能夠提供足夠的公共服務,反而更多地從鄉村汲取稅賦等資源,隨之而來的基層政權的不斷內卷化等,進一步加劇了鄉村社會的衰敗。
三是新政治組織對舊政治網絡的替代。為了挽救鄉村危機,中國共產黨嘗試著通過鄉村革命的方式重建基層社會,以農民的土地問題作為革命的核心。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通過土地改革運動,沒收地主土地歸為農民,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以此實現了對基層社會的廣泛動員與全面整合,并翻轉了整個鄉村社會的權力結構。“傳統士紳主導的宗族自治的效力,在20世紀上半期已經逐步趨向消解,但對此進行徹底改造則是1949年之后,到1959年的時候,中國的宗族已被非親屬關系的社團組織——公社制度所代替。”[注][美]W.古德:《家庭》,第168頁。并且,國家將社會控制的組織建構擴展到以自然村為基礎的村內,形成一個以黨組織為核心的農村政治組織網絡。[注]徐勇:《政黨下鄉:現代國家對鄉土的整合》,《學術月刊》2007年第8期。于是,一種基于政治原則組織起來,隸屬于行政權力的黨政群團組織代替了原來的士紳與宗族等,承擔起基層社會的公共事務。
在國家橫向治理逐漸萎縮的同時,以“戶”為基點的行政權力通過“抑家強戶”直接對家庭進行第一次系統性的改造。首先是對家庭經營的改造。黃宗智認為:“新中國成立之后,國家政權試圖通過其“社會主義改造”計劃控制和掌握每家每戶的經濟決策權。為了達成這一目標,新政權主要采取了土地改革、糧食三定(國家對糧食實行定產、定購、定銷)以及生產集體化等三個主要步驟。經過這些運動,舊的以分散、自立的小農農村經濟為基礎的政治經濟體制被巨大的、以集體化和計劃經濟為基礎的黨政國家體制所取代。”[注][美]黃宗智:《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第167頁。實際上,作為生產、分配和消費單位的家庭被“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公社所取代,社員身份代替家庭身份,土地與其他生產資料歸集體所有,由生產隊集中安排勞動、評工記工分來分配,甚至連消費也由公社安排,如公社食堂等,進一步消弱了作為社會組織單元的家庭經濟功能。
其次是家庭觀念的改造。一直以來,小農最看重的是自己的小家庭,以至于生命的價值與意義全在于家庭之中。隨著國家行政權力對家庭經營的改造,家庭觀念也必須作出相應的調整。正如張樂天所言:“農民是偏好傳統小家庭農業經營方式的,而公社制度是以承認集體利益為前提的,這要求農民根據集體利益和發展集體經濟的需要來調節自己的行為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注]張樂天:《告別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95頁。為此,不得不將教育農民作為中國關鍵問題提出來,并借助于定期的社會運動和思想改造活動,壓制農民內心深處的家庭觀念。“集體化的浪潮推動個人為超越家庭的集體而做出犧牲。無論個人主義在共產黨統治下的前景如何,它已經使得個人放棄對家庭的忠誠。”[注][美]閻云翔:《私人生活的變革——一個中國村莊里的愛情、家庭與親密關系:1949~1999》,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第253頁。
最后是家長權威的改造。以父權、夫權為代表的家長權威也被作為新政權的對立面,打倒封建家長和實現婦女解放,在家里鬧革命,以前內生的家長權威,及其附屬的家規家訓等在破舊立新的過程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公社體制內的干部權威與階級規則等。
家庭與國家的張力最終以國家對家庭的改造收尾,家庭從傳統國家治理的核心地帶轉變為現代國家治理的邊緣地帶,與之相比,作為國家治理基本單位的“戶”得到強化,成為國家權力滲透鄉村社會的關鍵所在。對于鄉村來說,“戶”成為公社體制中生產隊之下的基本單位,是公社生產分配的基本單元,是公社社員的最小集合體,是國家行政權力延伸的最末梢。
三、回歸家戶與國家縱橫治理結構重塑
通過公社時期國家對于“家”與“戶”的改造,國家權力全面滲透鄉村社會,身處鄉村的每個人都能夠感受到國家權力的存在。公社體制中的每個人從家庭關系中脫離出來,成為公社的“社員”,形成一種統一的身份建構,并依靠社員的身份與其他人建立關系,并擴展到整個社會關系網絡。不過,與家庭這種依靠內在血緣力量凝聚的社會組織形式相比,人民公社主要是國家組織而成的,屬于家戶之間形成的橫向組織,需要外部性力量鞏固其權威和秩序。羅斯·埃什爾曼在論述中國家庭時認為:“中國的共產主義在消弱傳統家庭的某些方面的時,并沒有使家庭這一經濟社會單位從根本上毀滅掉……全部中國家庭都作為一個生產單位參加了公社,他們是農業和小型工業可以依賴的穩定的基礎。盡管國家把家庭作為一個人民生活的重要單位,家庭還是一個經濟單位。”[注][美]J.羅斯·埃什爾曼:《家庭導論》,第220頁。
事實上,公社體制在建立及發展過程中始終面臨著家戶制傳統的影響。通過對公社體制的細致考察,張樂天認為:“人民公社試圖以共產主義的名義消解傳統的家庭,結果導致了普遍的災難。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就是新制度與舊傳統相妥協的產物,它在自己的制度框架內承認了家庭制度的合法性,恢復了許多傳統家庭的職能。”[注]張樂天:《告別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第282頁。他更進一步提供證據,即“整個生產體系不得不承認生產隊作為基本的生產和分配單位的地位,生產隊往往是過去的自然村落,進而延續了村落格局。這就使得建立在小農家庭基礎上的人民公社從一開始就蘊含著‘一種瓦解公社的力量’”[注]張樂天:《告別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第282頁。。
正如對家戶的改造過程一樣,家戶也用同樣的方式瓦解著公社體制。隨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農業生產中具體的工作是由家庭來組織經營與管理,“農民的家戶觀念得到確認和釋放,農民為家庭的利益而奔波,為家庭的面子而抗爭,為家庭的尊嚴而努力”[注]張樂天:《告別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第377頁。。回歸“家戶”的過程一如改造“家戶”迅速,后者依靠國家的行政權力,而前者依靠的是基層社會的力量。
當然,回歸“家戶”并不是回到傳統家庭,而是在基層社會治理中重新發現家戶制傳統,畢竟,家庭功能的恢復并不等于傳統的家庭化社會組織模式的恢復,基層社會中雖然具體的功能是由家庭來組織的,但整個家庭與傳統家庭相比卻日益受制于國家權力,由此在新的基礎上建立新的以“家”和“戶”為基點的國家縱橫治理結構。[注]任路:《“家”與“戶”:中國國家縱橫治理結構的社會基礎——基于“深度中國調查”材料的認識》,《政治學研究》2018年第4期。
新的起點源于村民自治的產生。1980年,廣西宜州合寨大隊正式分田到戶,各家各戶獲得了土地的生產經營權,生產生活明顯改善了,但是村里賭博多、盜竊多、砍伐樹林多、唱痞山歌多、放浪蕩牛馬多、搞封建迷信多。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公社體制逐步解體,一大批的生產隊長“躺倒不干”,公社和生產大隊也管不過來,基層社會出現了“權力真空”。于是,合寨大隊下面的果作和果地屯,在韋煥能、蒙光新等人的帶領下,將村民組織起來,每家派個代表推選出“村民委員會”,在村落范圍內建立自下而上的村民參與機制,不僅恢復了農村的社會秩序,而且興辦了單家獨戶難以完成的各種公共建設與公益事業,實現了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和自我監督。在地方主政者的推動和高層領導的關注下,村民委員會作為基層群眾自治組織的地位逐步得到確立,被視為農村政治體制改革的先聲。[注]任路:《田野政治學:村治研究與中國政治學的重建——以中國村民自治為重點表述對象》,《云南社會科學》2017年第3期。到1983年,全國大部分農村地區普遍建立了村民委員會,1987年《村委會組織法》試行,1998年修訂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以下簡稱《村委會組織法》)頒布施行,群眾自治成為國家基本政治制度之一,并且在各地的村民自治實踐中,村民大會、村民代表會議等組織體系日益完善,村規民約、村民自治章程等制度規范逐步健全,村務公開和民主監督等機制不斷創新,由村民自下而上參與的基層群眾自治奠定了國家橫向治理的基本框架。
與此同時,撤社建鄉之后,國家基層政權延伸到鄉鎮一級,《村委會組織法》明確村委會協助鄉鎮政府開展工作,并在村級建立黨的組織,國家行政權力通過鄉鎮、村、組傳遞到農戶,保證了國家政策的貫徹落實,將家戶納入到整個國家行政體系之中。村民自治成為國家行政權力整合鄉村社會的重要機制,形成當前基層社會治理的“鄉政村治”的基本格局。實際上,“鄉政村治”是向家戶制傳統的復歸,是以“家”為基礎的自治權力和以“戶”為基點的行政權力的縱橫治理結構的再造。居于家戶與國家之間的村干部承擔著雙重角色,既是基層群眾組織的當家人,又是基層政府的代理人,處于國家縱向治理與橫向治理的連接點上。
四、結論與進一步的討論
從家戶制傳統出發提出國家縱橫治理結構及其內在演化,就其形式上來說是對傳統國家治理形態的追溯,回到歷史的深處去追問小農社會之上的國家治理,就其實質而言則是要回答現代國家建設過程中如何去選擇國家治理體系的問題,以及尋找未來國家治理結構的發展路徑。
與傳統的國家縱橫治理結構不同,隨著經濟社會基礎的變化,尤其是在現代國家建設深入推進的過程中,為了動員和組織現代化建設,國家權力必須全面滲透和整合鄉村社會,汲取更多人力、資源等支撐國家建設,必然強化國家行政權力。自清末民國以來的現代國家建設,士紳退出鄉村社會,宗族作用逐漸弱化,傳統國家橫向治理呈現萎縮,國家縱向治理則成為國家治理結構的主體,由于缺少監督和制衡,國家縱向治理帶來的是基層政權內卷化,加劇了鄉村社會的衰敗,國家治理并沒有出現預料的結果,反而背道而馳,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重新組織基層社會,才結束了基層政權的內卷化,第一次將國家行政權力一竿子到底,實現對鄉村社會的全面滲透與高度整合,與之相伴的是對家戶的徹底改造以及橫向治理的消失,但是即便如此,在人民公社時期,公社體制不得不依靠外在的行政力量來維持,實際上不得不向家戶制妥協,在一定程度上承認家戶的合理性。直到分田到戶之后,家戶基礎上的村民自治興起,國家行政權力上移,形成“鄉政村治”格局,國家縱橫治理結構得以復歸。
在國家縱橫治理結構再造的過程中,始終存在著自治權力與行政權力的內在張力,是不是現代國家建設所強調的單向國家治理結構與家戶制下國家縱橫治理結構兩種路徑之間沖突。其實自治與行政并沒有本質上的沖突,關鍵是彼此的銜接,在傳統國家治理中,官府權力與士紳權力、宗族權力之間也會有矛盾,但是整體來說,大多數時候彼此都恪守權力邊界,士紳與宗族捍衛自治,避免國家權力干預,國家權力也奉行簡約治理,尋求與士紳和宗族的合作,形成相對穩定的國家治理結構。如今的國家治理當然也可以實現穩定的縱橫治理結構,而且有條件來達到這個目標,與以前相比,現代國家建設從民族國家、民主國家以及民生國家轉變,鄉村社會從資源汲取向資源賦予轉變,尤其是新農村建設以來,大量的公共資金投入農村,大量的公共事務產生于農村,這些資金的使用和公共事務的處理都離不開村民的參與,離不開基層社會的自治。因此,未來國家縱橫治理結構的理想模式依然是“政府治理與基層自治相互銜接與良性互動”,從國家縱橫治理結構的內生演化進程來看,縱向治理和橫向治理缺一不可,關鍵是實現兩者的銜接與互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