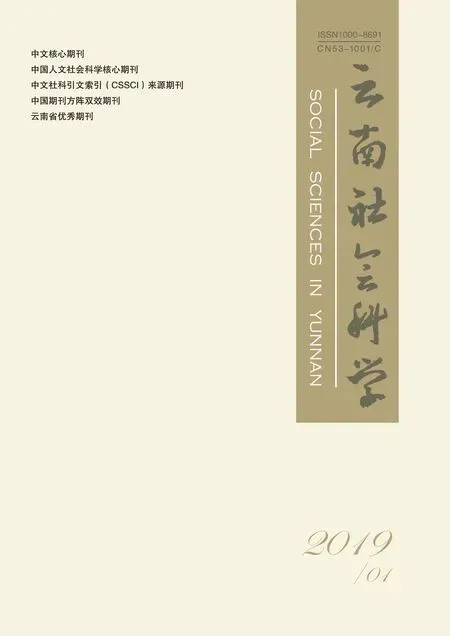重塑階級邏輯:當代生命政治的范式轉換及其建構性意義
李愛龍
在福柯和阿甘本那里,生命政治都是作為一個消極概念出現的,它表征的是這樣一種社會現實,即個體生命成為權力運作的直接對象,而其昭示出來的解放道路卻是向柏拉圖主義的回歸,即通過某種神秘化的精神修煉實現個體的生命救贖。無疑,福柯和阿甘本的生命政治是資本邏輯蹂躪下的浪漫主義式的嘆息,它直接取消了革命話語的歷史正當性。但是,意大利自治主義者奈格里卻從根本上變革了生命政治的解讀范式,他將生命政治從社會治理領域轉移到物質生產領域,從而翻轉了生命政治的主流研究范式,賦予生命政治革命潛能。在生命政治的視域下,奈格里首先提出了“勞動的技術構成”,并指出,“確立勞動的技術構成,能夠為我們提供一個基礎,不僅能夠讓我們認識到當下資本主義的剝削和管控形式,同時也可以為我們提供從資本中得到解放的工具”。[注]①邁克爾·哈特、安東尼奧·奈格里:《大同世界》,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99頁。由此可見,他不僅把生命政治當作理解當代資本主義的鑰匙,而且還試圖挖掘出其中潛在的解放意義。
然而,研究者們并未足夠重視奈格里的生命政治的范式轉型,將之片面理解為人本主義的烏托邦幻想。大衛·哈維指出奈格里的生命政治批判有余而行動不足,缺少實證性的客觀維度,極易把人引向神秘主義的方向。“我個人希望,作品中少一點斯賓諾莎,多一點馬克思,少一點關聯性(relationalities)和非物質性(雖然論述得非常美麗詩意);多一點對表征、客觀性(對象化)和物化的物質方面的論述。關聯性和非物質性夠多了!來點具體的提議、現實的政治組織和真正的行動可好?”[注]②大衛·哈維:《解釋世界還是改造世界——評哈特、奈格里的〈大同世界〉》,《上海文化》2016年第2期。相對奈格里徒具空洞姿態的激進性,齊澤克則主張“回到列寧”,“既反對經濟決定論,同時又反對純政治的態度”。[注]③許紀霖:《帝國、都市與現代性》,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88頁。有鑒于此,本文的目的就在于正面闡釋奈格里的剝削理論及其所蘊涵著的對于重塑階級邏輯的建構性意義,彰顯其反抗資本邏輯的革命本性。
一、生命政治與生命權力的二元對抗
尋找革命主體,重塑階級邏輯,成為全球化視域下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普遍關注的核心話題。在這一致思取向之中,尤以意大利自治主義者奈格里的“諸眾”最為激進。但是,批評者就“諸眾”的政治能力提出質疑,認為“諸眾”缺乏“人民”所具有的組織性和統一性,難以展開自覺的政治行動,其行動的解放旨趣也難以得到保障。其實,這種質疑是西方思想傳統的一大偏見,這一偏見在阿倫特那里表現得最為明顯。在她看來,“按照古代思想,‘政治經濟學’本身就是個語詞的矛盾,因為任何‘經濟的’事情,即與個人生命和種族延續有關的一切,按定義都是非政治的家庭事務”。[注]阿倫特:《人的境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頁。換句話說,勞動者只關注自然必然性的生存問題,難以形成自覺的政治訴求,從根本上缺失政治行動的能力。筆者認為,奈格里的“諸眾”作為革命主體,深層地植根于其生命權力與生命政治之二元對抗的理論邏輯之中。
生命政治濫觴于福柯,并在阿甘本那里得到充分的發展,進而成為當代激進政治話語的一大顯學。然而,在福柯-阿甘本的思想圖景之中,生命權力和生命政治是同一的。所謂政治就是一種權力運行機制,二者共同揭示的是資產階級的自由民主制是如何淪為集權專制的。但是,在奈格里的思想圖景之中,生命政治與生命權力是截然相反的,二者處于一種對抗關系之中。可以說,奈格里實現了某種形式的“術語革命”,賦予了生命政治與生命權力全新的規定性。“生命權力作為一個最高主權權威高高凌駕于社會之上,強行推行自己的規定與秩序。而生命政治生產則內在于社會之中并通過勞動的合作性的形式創生著各種社會關系和社會形式。”[注]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Multitude.New York:The Penguin Press,2004,pp.94-95.那么,生命政治和生命權力相互之間的對抗關系表現為何種模式呢?在這種對抗關系之中,哪一方具備邏輯上的先在性呢?為了更好地回答這個問題,不得不將理論視角轉移到奈格里對馬克思《大綱》“機器論片斷”的激進政治解讀上來。可以說,這構成了奈格里生命政治的主要理論支援背景。
相較于一般馬克思主義者著眼于馬克思的《資本論》,奈格里更為看重的是馬克思的《大綱》。在奈格里看來,馬克思的《資本論》宣告的是資本邏輯的絕對統治地位,“把經濟的社會形態的發展理解為一種自然史的過程。不管個人在主觀上怎樣超脫各種關系,他在社會意義上總是這些關系的產物”。[注]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頁。在這樣的思想前提之下,無產階級的革命主體性得不到足夠的重視,解放事業只能寄希望于資本邏輯的自我崩潰。而關鍵的問題在于,如果缺失了無產階級的革命主體性,資本邏輯的崩潰是否會自動帶來解放。
在奈格里看來,《大綱》尤其是“機器論片斷”具有更為激進的政治闡釋空間,因而是超越資本邏輯之絕對統治地位的一個理論抓手。在“機器論片斷”中,馬克思指出了一個顯而易見的“經濟事實”,那就是,機器體系的應用顛倒了生產過程中勞動者與勞動工具之間的關系。在機器體系應用之前,勞動工具是勞動者的延長器官,勞動者在生產過程中居于中心地位。但是,機器體系的應用全面消解了勞動者的支配地位,使其日益成為勞動工具的附屬物和看管者。“機器則代替工人而具有技能和力量,它本身就是能工巧匠,它通過在自身中發生作用的力學規律而具有自己的靈魂。”[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1頁。由此,勞動者的活勞動日益貶值,相反,固定資本以及相對剩余價值的創造日益構成資本增值的主要方面。質言之,社會一般智力而不是活勞動的能動性成為創造剩余價值的源泉。正如阿爾都塞所指出的那樣,“勞動力技能的再生產(作為大趨勢)傾向于越來越少地(通過生產內部的學徒期)‘當場’獲得,而是越來越多地在生產之外,通過資本主義的教育制度以及其他場合和機構來完成”。[注]陳越:《哲學與政治:阿爾都塞讀本》,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24頁。
對于這一“經濟事實”,如果依照福柯-阿甘本的生命政治話語范式來解讀的話,其結論必然是,資本權力已經布展到了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在這一認知型的引導下,人類性的解放事業必將在嚴密的權力之網中日益變得萎縮,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個體性的精神修煉,其實質上是柏拉圖主義式的哲學對政治的僭越。奈格里當然不認同這種美學救贖,他所著眼的是一種現實的政治籌劃。這樣的話,他就不得不從馬克思的有關階級斗爭的論述出發,對這一“經濟事實”做出不同于客體邏輯的主體性解讀。馬克思曾指出,“自從工人階級逐漸增長的反抗迫使國家強制縮短勞動時間,并且首先為真正的工廠強行規定正常工作日以來”,[注]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471頁。機器體系的構建以及相對剩余價值的創造就成為資本增值的重心。從中可以看到,機器體系以及相對剩余價值是為了應對工人的反抗,即勞動階級的反抗催生了資本權力的新機制,權力只是對反抗的管控。這就構造了一種資本與勞動二元主體的對抗性結構,“如果一方面資本是主體,那么在另一方面,勞動一定也是主體”。[注]安東尼奧·奈格里:《〈大綱〉:超越馬克思的馬克思》,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161頁。
在這個意義上,與其說“資本論”從客體邏輯的層面上揭示出資本權力鐵一般的運行規律,倒不如說,“勞動論”從主體邏輯的層面上揭示出資本權力的深層緣由,其表征的是勞動主體創構性的歷史作用。由此,奈格里創造性地闡釋了馬克思的作為社會關系的資本概念。西方馬克思主義之所以遠離工人階級的實際斗爭而墮入意識形態批判,就在于他們不是從相互關系的角度來理解資本,僅僅將資本看作是自我封閉和自我形塑的絕對客體。在奈格里看來,資本與勞動雙方處于對抗性關系之中,正是它們的對抗才促使二者處于相互規定之中,形成一個“建構-解構”的雙螺旋結構。“這一被資本支配的客體化過程,開始揭示出一個新的工人階級主體性水平。”[注]安東尼奧·奈格里:《〈大綱〉:超越馬克思的馬克思》,第162頁。這樣的話,奈格里就避免陷入一種還原論的思維窠臼,即片面拒斥客觀性的主觀主義傾向。這才是奈格里所強調的政治化解讀的真實涵義。
奈格里對“機器論片斷”的政治化解讀成為其生命政治思想的理論地坪,或者說,資本與勞動的二元對抗關系不過是權力與反抗相互關系的一個縮影或一次應用。在奈格里看來,反抗先于權力,“權力只能施加在自由主體身上”。[注]邁克爾·哈特、安東尼奧·奈格里:《大同世界》,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15頁。在福柯那里,主體自由構成了權力自身的運行機制,它使得權力不再是一種非法性的暴力,而成為一種合理化的治理技藝。與之相反,在奈格里這里,主體自由不再是權力的合理性外衣,而是權力機制得以生成的深層源動力,是不妥協的反抗形塑了權力,在二者的對抗性關系中反抗占據著支配性地位,它迫使權力不斷地解構反抗的新態勢。“分析是立足于對被壓迫者和被剝削者斗爭的分析,認識到這是每一種制度性關系和每一個社會組織圖式的根源所在。”[注]邁克爾·哈特、安東尼奧·奈格里:《大同世界》,第15頁。
如此一來,以生命政治與生命權力的二元對抗關系為認知框架,奈格里在機器體系中看到的不是革命主體性的退卻,而是一種以“諸眾”為中心的全新革命情勢。在奈格里那里,生命政治并非是一種權力機制,而是一種面對權力機制所形成的反抗性的協同行動。“帝國采用‘生命權力(biopower)’方式統治,勞動者以‘生命政治生產’對抗。”[注]張早林:《從“諸眾”到“共有者”——哈特與奈格里激進政治主體的邏輯轉換及當代意義》,《南京社會科學》2015年第7期。機器體系作為資本權力的布展形式,消解了勞動者在物質生產過程中的支配性地位。但與此同時,活勞動的外化實現了一次存在論意義上的轉移,即由產品的物質形式轉移到了產品的非物質形式或生命形式,從物質勞動轉向了非物質勞動或生命政治勞動。產品的物質形式具有易逝性,是不可通約的,很容易被完全圈定為私有財產;而產品的非物質性則具有共有性,是可以被共享的,不能完全被資本所獨占,總是存在著某種剩余。因此,它打破了工廠與社會、勞動時間與非勞動時間、生產主體與生產客體之間的界限,內涵著一種新型的社會聯合。
生命政治勞動可以說表征著“諸眾”的存在方式,即“諸眾”的聯合是在非物質生產過程之中自發地形成的,而不像“人民”那樣需要一個外在的組織或領導。由此,傳統的產業工人從滿足自然需要的必然性和孤立性之中解放出來,成為自主的社會工人。奈格里斷言,“馬克思所視為未來的正是我們的時代”,[注]邁克爾·哈特、安東尼奧·奈格里:《帝國——全球化的政治秩序》,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50頁。在其中,整個勞動的現象學和全世界的生產景象將被重新定義。非物質生產日益取代物質生產,在生產過程中占據支配地位。這并不僅僅是一個生產范式的轉換,而是從根本上表征著一種勞動者的全新存在方式,預示著突破資本權力以及變革人類文明的全新可能性。
二、生命政治批判空間的構建
奈格里的生命政治思想所要構建的就是一種不同于“資本論”的且作為“資本論”內在源動力的“勞動論”。這種“勞動論”確證了“諸眾”作為革命主體的合法性。由此,奈格里才能構建生命政治的批判空間。在筆者看來,這種批判空間實際上就是對傳統馬克思主義的經典概念進行生命政治闡釋,在資本全球化時代賦予其新內涵。在筆者看來,在構建生命政治批判空間的過程中,剝削、共產主義以及危機這三個概念最具腳手架的意義,它們分別回答了重塑階級邏輯的可能性、現實性以及必要性。
剝削,在馬克思主義話語中處于核心地位,它被用于揭示資本主義社會的非正義性。但是,人們對剝削的研究一般聚焦于對剝削性質的界定,即剝削是一個可被精確計算的事實性概念,還是一個存在論意義上的道德性概念。這種研究路徑不自覺地分享了如下思想前提,即剝削表征的是資本權力的絕對統治,勞動者的主體性在剝削體系中日益萎縮。依據奈格里的生命政治思想,這種研究路徑勢必要被翻轉的。因此,重新闡釋生命政治剝削,構成了奈格里生命政治批判空間的重要基礎。
奈格里指出,“確立勞動的技術構成,能夠為我們提供一個基礎,不僅能夠讓我們認識到當下資本主義的剝削和管控形式,同時也可以為我們提供從資本中得到解放的工具。”[注]邁克爾·哈特、安東尼奧·奈格里:《大同世界》,第99頁。很顯然,奈格里的“勞動的技術構成”是與馬克思的“資本的技術構成”相對應的,是生命政治與生命權力二元對抗關系的具體再現。如果說資本構成自身的邏輯在于從自身外部榨取剩余價值,那么勞動構成自身的邏輯就在于維持自身價值穩定。在奈格里看來,所謂“勞動的技術構成”聚焦于勞動產品的使用價值以及勞動者自身的主體性因素,其核心要義在于“誰在生產、生產了什么以及如何生產的問題”。[注]邁克爾·哈特、安東尼奧·奈格里:《大同世界》,第99頁。
在生命政治生產的時代境遇下,“勞動的技術構成”呈現出三大趨勢——“非物質生產的霸權或主導地位”“工作的女性化”“移民與社會和種族混合過程的新模式”。這三大趨勢共同表征的是非物質勞動的協作具有自主性,“合作是非物質性生產勞動的內在的一部分,勞動本身生產出社會合作,而且就是對社會本身的生產”。[注]許紀霖:《帝國、都市與現代性》,第62頁。換句話說,非物質生產活動不再以物質生產資料為中心,而是以勞動者的智力、情感等主體性因素為核心,協作內涵在勞動過程之中。由此,資本對勞動的剝削就帶有了生命政治色彩,資本不再直接干涉勞動過程,而是直接剝奪非物質勞動的成果(以勞動者的情感、智識等來表現自身的“人造共同性”),“當下的資本主義積累更多地在勞動過程之外實現,如剝削就以剝奪共同性的形式得以實現”。[注]邁克爾·哈特、安東尼奧·奈格里:《大同世界》,第102頁。在奈格里看來,這種直接剝奪共同性的剝削,具有兩方面的特質。一方面,它是對馬克思異化概念的回溯,它使得勞動者在勞動過程中體驗不到自身的生命活動和主體性。另一方面,它是對資本主義地租的回溯,因為利潤產生于資本對生產協作的直接參與,而地租則是對勞動成果的直接私有化。
共產主義,是馬克思對未來社會的一種設想。遺憾的是,馬克思并未對其實現方式和表現形式做出明確的界定,只是在原則高度上指出要在批判舊世界中發現新世界。這就給后來的理論家敞開了闡釋空間,其中影響最為深遠的就是立足于資本邏輯的客體化的闡釋路徑。這種闡釋路徑的核心觀念在于,將共產主義內嵌于資本的必然邏輯環節之中,認為共產主義會在資本邏輯的自我崩潰中自行到來。但是,在奈格里看來,這種闡釋路徑根本上是對資本邏輯的認同,是對共產主義理想的放逐,將共產主義當作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它不僅“完全遮蔽了始終伴隨資本主義危機趨勢的革命主體性模式及其深層轉型后具備的全球性和對抗性特征”,而且無視“資本主義的發展史完全從屬于工人階級的自主性和自我決定”這一社會現實。[注]宋曉杰:《共產主義:革命主體性話語與替代性政治想象——奈格里對共產主義思想的重構》,《廣西社會科學》2013年第4期。因此,這種客體邏輯意義上的共產主義勢必要被解構和顛覆。
奈格里指出,共產主義不是資本邏輯的必然產物,其在根本上依賴于勞動者的革命主體性,勞動者的革命主體性才能保證共產主義的解放走向。據此,奈格里認為,社會主義并不必然過渡到共產主義,其實質上是資本邏輯的新形式,“國有資產理論、計劃理論、剝削關系中的不平等,都是從資本的不斷革命中產生的”。[注]安東尼奧·奈格里:《〈大綱〉:超越馬克思的馬克思》,第200頁。奈格里區分了私有、公有和共有。在他看來,資本主義的私有和社會主義的公有都表征著一種排他性的產權制度,也就是說,財產并不是共有共享的,而是被劃歸到某一利益集團內部。而共產主義的共有則是一種財產的共同占有模式,它并不以某種合理性標準將財產劃歸給一部分人。因此,共產主義是對資本主義的絕對顛覆,“是對價值規律、對價值本身,對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變異體的摧毀”。[注]安東尼奧·奈格里:《〈大綱〉:超越馬克思的馬克思》,第113頁。共產主義彰顯的是一種不斷革命的對抗邏輯,它是勞動者不斷謀求奇異性的政治實踐以及自由的不斷生成。由此,共產主義并不僅僅意味著客體意義上資本主義及其變異體的滅亡,更為本質的是它表征著一種人類文明的新形態以及人類存在的新境界,而唯有勞動者的革命主體性方能代表這種新形態和新境界的前進方向。
在傳統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危機內在聯結著革命。但是,歷史實踐證明,危機并不一定導致革命及其成功,相反,危機卻成了資本主義價值累積自我修復的內在環節。如何重新建立危機與革命之間的內在關聯,成為馬克思主義時代化的重大課題。在傳統馬克思主義視域中,物質生產占據著支配性地位,因此,社會基本矛盾只能是生產資料私有制與社會化大生產之間的矛盾。在奈格里看來,這是一個客體化的矛盾,其引發的危機必將是客體化的危機。這種客體化危機促使資本主義改變生產組織形式,應用機器體系,切斷勞動者與生產資料之間的直接關聯,從而使生產的支配形式過渡到生命政治生產,也使剝削發生了歷史性轉變。奈格里就此指出,雖然客體化的危機沒有葬送資本主義,但是其催生出的生命政治生產卻隱匿著對資本主義更具破壞力的主體性危機(生命政治危機)。
在非物質勞動的條件下,社會基本矛盾轉變為生命政治生產的共同性與資本對共同性的私有化之間的矛盾,其引發的危機是主體性的危機。首先,由于共同性作為一種人類共有和共享的主體性因素,布滿于整個社會生活空間,無處不在且無時不有,因此,這種主體性危機將是全局性的。其次,由于生命政治作為生命權力管控機制的內在源動力,資本對共同性的私有化嚴重降低了生命政治生產的效率,阻礙了生命政治生產的可持續性,因此,生命權力必將成為無源之水。最后,生命政治生產打破了工廠與社會、勞動時間與非勞動時間的界限,使工人走出工廠而成為社會工人,由此,革命主體將不再僅僅是工人階級,而是更具普遍性的“諸眾”。質言之,物質勞動向非物質勞動的轉變從根本上昭示著資本主義社會危機的新形式以及掙脫資本權力的新道路。
綜上,奈格里通過對剝削、共產主義以及危機的生命政治闡釋,以之為腳手架,搭建起了生命政治批判空間。第一,對剝削的關注是奈格里自治主義馬克思主義的一大特色。在他看來,不僅在過去,而且在當下,剝削都是揭示社會生活中隱匿著的奴役與支配進而確立斗爭之不可消除性的概念工具。唯有確立起當代社會中的剝削新范式,重塑階級邏輯才有可能。第二,共產主義表征著人類社會的理想,而對共產主義的理解直接決定著當下采取何種政治策略。奈格里看到,客體主義的闡釋路徑不會導向解放,反而會鈍化對資本邏輯的批判。因此,唯有對共產主義的主體性闡釋,方能保障運動的解放旨趣,使重塑階級邏輯具備現實性。第三,危機往往被視為革命契機,在奈格里看來,客體化的危機成了資本邏輯自我修復的內在機制。因此,唯有對危機的主體性闡釋,才能重新建立起危機與解放之間的內在關聯。
三、重塑危機和解放的內在關聯
毋庸置疑,本文開篇所談及的國內外研究者對奈格里所提出的批評意見不是無的放矢,而是植根于馬克思主義學理之中的,而無需諱言奈格里的理論演進中存在著明顯的學理不足。然而,筆者以為,考慮到當今資本主義社會所發生的巨大變化,考慮到其推翻資本權力的理論旨趣,奈格里的理論探索有其建構性意義——它立足于當代資本主義實踐,建構自主的、抵抗的政治主體,重塑階級邏輯。正是通過對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剝削新形式的關注,才使得奈格里將危機的新形式和解放的新道路聯結起來。
如上所述,危機理論是傳統馬克思主義解放敘事中至關重要的一個環節。由社會基本矛盾所引發的經濟危機往往是激起無產階級革命的直接原因。這是科學社會主義區別于空想社會主義的一個根本點,即革命不是一種偶然的恐怖活動,而是植根于社會歷史運動規律之中的。因此,傳統馬克思主義在危機與解放之間建立一種直接性的關系。但是,歷史表明,經濟危機并不能夠引發革命。相反,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矛盾的外在展現,是其生理過程的一個必經階段,它對于改善資本主義積累機制具有一定的作用。立足于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轉變,奈格里洞見到傳統危機理論的不足,將這種危機界定為“客觀性的經濟危機”,并指出,“資本就是通過崩潰,或者說通過危機所導致的創造性破壞而得以運作的”。[注]邁克爾·哈特、安東尼奧·奈格里:《大同世界》,第106頁。那么,奈格里是如何在當代資本主義條件下重塑危機與解放之間的內在關聯的呢?
這就必須回到奈格里生命政治的話語范式。根據這一話語范式,奈格里在兩個方面重新闡釋了危機與解放之間的內在關聯。首先,危機的爆發導源于勞動者的主體性,而不是資本積累鏈條的斷裂。傳統的危機理論僅僅注重勞動對資本的實質性從屬,而忽視了其中內在隱含著的權力機制,“權力只能運用于自由的主體之上”。在非物質勞動的條件下,資本權力對勞動的剝削,實際上是對勞動者以創造性和主體性來表現自身的人造共同性的褫奪。而正是由于人造共同性無時不有且無處不在的特質,資本權力所引發的自由主體的反抗必然滲透進社會交往網絡的每一個環節,其所帶來的危機必將是全面而深刻的。
其次,由于人造共同性的非稀缺性,那些不能被資本完全私有化的剩余共同性本身就構成了反抗資本權力的強有力陣地。傳統危機理論囿于物質生產的狹隘眼界,僅僅看到資本對全部剩余產品的獨占,從而片面夸大資本權力的絕對性。而在非物質勞動的條件下,資本已然難以實現對共同性的完全獨占,那些剩余共同性包含著革命和解放的潛能,是將情感性的對抗轉化成策略性的反叛的堅實基礎。正因此,資本對勞動的每一次剝奪,不是意味著資本的勝利,而是意味著資本為自己樹立起了堅定的反叛者。“雖然客觀性的經濟危機對資本主義積累來說有一定作用,但是主觀性和政治性的危機對資本卻是一種實在的威脅。”[注]邁克爾·哈特、安東尼奧·奈格里:《大同世界》,第106頁。
由此,筆者發現,傳統“客觀性的經濟危機”或許還能成為資本積累的生理過程,是其有機體內部的良性癌細胞,是其發展過程中的“歷險”,那么,非物質勞動條件下的“主觀性的和政治性的危機”則成為埋葬資本的墳墓,成為激起“諸眾”(即革命主體)革命和解放潛能的歷史契機。
既然危機已經從客體性質轉變為主體性質,那么,與之相關聯的解放道路是否也發生著相應的轉變呢?答案是肯定的。奈格里的邏輯是,與危機相伴生的革命必然需要革命的承擔者即革命主體,而在當今資本主義社會中,“我們不應該將諸眾理解為一種存在,而應該理解為一種制造”。[注]邁克爾·哈特、安東尼奧·奈格里:《大同世界》,第125頁。換句話說,革命主體并非是現成的存在者,而是需要被建構的。這種建構方式就是“出走”,通過“出走”以來獲得人造共同性。“果真如此的話,也許摧毀權力結構的起義事件就足夠了,壓迫枷鎖下的完美人類社會就會自動繁榮地生長出來。”[注]邁克爾·哈特、安東尼奧·奈格里:《大同世界》,第254頁。由是觀之,只要作為革命主體的諸眾是現成在手的,那么,革命及其所帶來的解放就是水到渠成的。因此,非物質勞動語境下的階級斗爭采取“出走”的形式,革命的關鍵就在于,通過“出走”而制造諸眾。
奈格里在《大同世界》中對“出走”作了一番界定:“我們所謂的出走,是通過實現勞動力潛在自主性的方式從與資本的關系中退出的過程。因此,出走不是拒絕生命政治勞動力的生產力,而是拒絕資本對生產能力日益強加的制約因素”。[注]邁克爾·哈特、安東尼奧·奈格里:《大同世界》,第112頁。從這一界定中,我們必須把握三個要點。
首先,“出走”的真實意義就是“實現勞動力潛在自主性”,也就是將勞動力的潛在自主性具體化,從根本上終結資本對非物質勞動的管控。我們可以進一步追問,如何實現勞動力潛在自主性?在非物質勞動條件下,勞動者所從事的勞動在形式上已經實現了自主協作,資本在生產協作中已經不發揮實質性的作用。但奈格里指出,實際上,資本權力布展于整個社會,以至于其權力觸角遍及家庭、企業乃至整個國家。整個社會關系變成一種腐化的單向度的秩序體制。在這種腐化的社會關系中,資本終將剝奪勞動者的自主性。由此,所謂“出走”就是逃離腐化的社會關系,賦予形式化的自主協作以實質性意義。
其次,“出走”既不是回歸生產力不發展的落后狀態,也不是無中生有地創造未來,只有以共同性為基礎,能夠創造和利用共同性的“出走”才是可能的。共同性,尤其是以語言、文字、符號為典型代表的人造共同性,是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蓄水池,是人類文明進步的階梯和支撐點,深層次地表征著客觀的社會歷史進程。因此,“出走”就是對共同性的占有。與黑奴赤裸裸地走向別處的逃亡不同,“出走”是這樣一種抵抗策略,即停留在原有處所,改造社會關系和生產模式。奈格里強調,在從資本制約關系中退出的同時,生命政治勞動力必須找到能夠實現其潛在自主性的全新的社會關系和生命形式。這就從另一個側面凸顯出奈格里并非僅僅關注主體性維度,而罔顧社會歷史發展的客觀維度。
第三,作為一種主體自我建構的方式,“出走”的目標是一種在社會關系之中展現自主性、創造和分享共同性的社會主體。這就有力地回應了后現代主義純粹個體的致思路向。后現代主義思潮的口號就是消解包括形而上學在內的一切宏大敘事,力圖將個體從其封閉之中解救出來,但其拯救的方式無非是具有神秘意味的個體自我修煉,就像福柯那樣訴諸一種“生存美學”,以此來創建一種唯一的、風格化的、不可還原(不可換算)的審美主體。在奈格里看來,反抗并沒有被資本權力消解,而是被培育起來,被布展到社會網絡的每一個環節,被轉型到社會生活的每一時刻,因而只有處于關系網絡中的社會主體才能肩負起反抗資本權力的使命。因此,后現代主義只是渲染了資本權力的絕對權威,把問題引向了神秘主義方向,實際上是放棄了對資本的反抗。
綜上可知,奈格里生命政治范式轉換的建構性意義并沒有因其學理上的不足而被遮蔽起來,相反,卻因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新特點以及現實需要對理論探索的新要求而被昭顯出來。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條件下,奈格里重新建立起危機與解放之間的內在關聯,從而重塑了階級斗爭邏輯。這一理論探索不僅重新發現馬克思主義理論中久被忽視的階級話語范式,對于片面強調資本權力進而退化為意識形態批判的西方馬克思主義來說,無疑是一種解毒劑,而且在新的時代語境中,以馬克思主義為理論工具,思考人類社會共同面臨的新問題,從而為馬克思主義以及人類社會的未來發展提供了一種可能性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