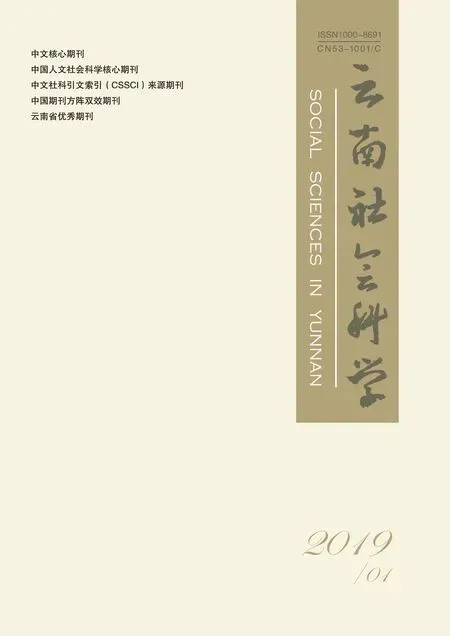文化鏡像中的后現代人類學與中國人類學的認知論革命
袁年興 彭旖旎
人類渴望了解自身及其存在意義,這是人類之所以成為“人類”的本性。人類學作為一門“關于人類本性的話語”[注]①權威工具書《不列顛百科全書》對人類學的定義是“人類學,是關于人類本性的話語”。人類學家馬林諾斯基也指出:“人類學是研究人類及其在各種發展程度中的文化(Culture)的科學,包括人類的軀體,種族的差異,文明(Civilization),社會構造,以及對于環境之心靈的反應等問題之研究。”參見林惠祥:《文化人類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第4頁。的學科,在長達一個多世紀的歷史中構建起了一種自我認知的文化鏡像。我是誰?誰又是我們?在這種終極追問中,早期人類學確立了一種把西方文化作為鏡像中心的現代認知論基礎。在與“原始文化”的對照過程,人類學這種尋找自我的過程始終依賴于一種自圓其說的想象過程,最終也不可避免地導致了早期人類學家迷失在文化的幻覺與真實的鴻溝之中。可以說,人類對于自身的認知程度遠遠不及于對其所周遭的物質世界,而前者恰恰反映了人類學發展過程中西方世界的傲慢、偏見和迷茫。
20世紀60年代興起的后現代主義為人類學的認知論革命提供了一種契機,這突出表現在“誰說話”及“怎么說”的方法論層面。后現代人類學試圖通過“自我”與“他者”之間的對話,構建一種“自我”與“他者”的相互生成過程,從而試圖緩解主體迷失的不足。只是,從最初的“文化之鏡”到后現代的“鏡中之我”,盡管當代人類學無論是學科價值、研究對象還是理論基石,都相異與其誕生之初的原初形態,但是人類學家并沒有逃離與“他者”在雙重想象中的僵化狀態。長期以來,后現代人類學的認知論問題被學界的方法論視角遮蔽,對以西方世界為中心的“文化鏡像”所造成的心理困境并引起足夠的重視。
對于處于世界話語體系邊緣地帶的中國人類學而言,在早期應對西方人類學的文化鏡像困境中,就充分體現了中國人類學家的超高智慧和人文素養,只是這種相對溫和的“文化相對主義”還是停留在自我言明的文化之鏡中。進入21世紀以后,中國人類學家表現出了把人類作為一種整體性存在的認知趨勢,不僅為中國人類學從世界話語體系的“邊緣地帶”發現“中心”的認知論危機提供了可能性,而且也在“世界人類學”的高度開啟了人類學的一種新境界。也正是這種認知論的徹底革命,使得人類學的“中心”和“邊緣”的不同發展軌道日益清晰。人類學如何在中國話語體系的推動下,重新確立了為人類命運共同體謀福祉的學科本質,這是一個耐人尋味且需要得到進一步彰顯的研究議題。
一、方法論的革命:后現代人類學的文化鏡像
從學科起源上來講,人類學屬于一門以研究“異文化”為起點的學科,其中的“道德”問題已取得了學界的共識。在早期對“原始文明”的描述中,西方人類學家顯然刻意支持了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認知論偏見,導致了人類學生產的知識不是維護人之價值和尊嚴的思想歸宿,相反卻成為西方世界發動戰爭、四處掠奪以及進行殖民統治的知識基礎和精神支柱。20世紀60年代興起的后現代主義無疑是人類思想的一次重大變革。后現代主義的興起,最早引發了格爾茲(Geertz)對人類學文化譜系的質疑。格爾茲試圖解構西方文化在文化對照中的中心地位,主張通過深度描述“土著人的觀點”來理解他者的獨特意義系統和結構形態。在格爾茨看來,與“原始”不同,“地方”一詞是研究對象對于他們自己的通稱,特別是在“地方權利”的背景下這個詞富有了政治內涵。正是這種對文化主體的重新定位,20世紀70年代的人類學界把“純”人類學立為首選,把應用或實踐人類學“打入危險、可疑和‘不道德’的另類”[注]Marietta L.Baba and Carole E.Hil.What.s in the Name of-Applied Anthropology. An Encounter with Global Practic.NAPA Bulletin,2006:25.。
到20世紀80年代,后現代主義傾向在人類學中進一步明朗化。其中,堅持“寫文化”和“文化批判”的人類學在地方性知識的基礎上,完全顛覆了傳統民族志通常所采用客位與主位的辨證關系,借助各種話語或符號在行動和參與中發現、認識及表達自我。在如何表述的焦慮狀態中,后現代人類學力圖表明,即使是地區性的知識系統,也是一種自我鏡像的呈現,只能通過多元的闡釋達到跨文化的溝通和對自身意義的深刻認識。當然,后現代思潮對人類學影響不僅僅停留在民族志的書寫問題,“而是針對其整個方法論和認識論所做出的全面回應”[注]瞿明安:《西方后現代主義人類學評述》,《民族研究》 2009年第1期。。經過民族志科學性的解構之后,“純”人類學的話語地位明顯削弱,越來越多的人類學者在學術研究和現實應用間尋求一條中間道路,試圖彌補文化之鏡的迷失和不安。
對于后現代人類學家而言,對他者的異文化的關懷,意味著人類學在更多時候表現的是一種不道德儀式的表演。這種不道德的儀式表演暗藏了一種什么樣的意義或企圖?儀式的表演顯然體現了一種優越感,表面上是闡明一種文化的普遍性,其本質是把他者的一切視為西方社會的過去。這種津津樂道的、感覺良好的文化霸權主義,在薩伊德(E.W.Said)看來,具有布萊克所指的“心魂鍛造的鐐銬”的色彩。為此,薩伊德倡導一種“人文主義”,即“歷史地、理性地運用心智,臻于反思性理解和使真實的情況昭然若揭之境”[注][美]愛德華·W.薩伊德:《東方學》,王宇根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年,《序言》第9頁。。在這種儀式表演中,傳統人類學對“他者”的言說來構建西方社會自己的歷史,在與“原始文化”的自戀式想象關系中被建立一種“鏡像之我”,其本質是“以某種形象出現的小他者倒錯式的意象”[注]張一兵:《不可能的存在之真——拉康哲學映像》,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年,第126頁。,屬于一種“虛假的自我”。
后現代主義對傳統人類學的解構也進一步促進人類學家對自身的反省,受后現代主義影響的人類學者采取反“權威的”視角,將地方文化看做日常生活實踐,重點關注全球霸權在地方的表現形式以及地方對于全球化的反應。正如薩伊德的東方主義滲透著一種主客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這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使地方文化與西方文化呈現出了一種“雜糅”的特質。對此,在霍米·巴巴(Bhabha,Homi.K)指出:“殖民者的主體構成也不可能是單方面的,而是脫離不了作為‘他者’的被殖民者;殖民主體的形成徘徊于‘自戀’與‘侵略’的身份之間,而威脅正來自于作為參照的‘他者’的缺失。”[注]Homi K.Bhabha,Signs Taken For Wonders questions of ambivalence and authority under a tree outside Delhi,May 1817.Critical Inquiry,1985,12 (1) ,pp.144-165.在霍米·巴巴看來,文化“雜糅”的本質在于顛覆了殖民主義話語的合法性,“它們以驚人的種族、性別、文化、甚至氣候上的差異的力量擾亂了它(殖民話語)的權威表現,它以混亂和分裂的雜交文本出現于殖民話語之中”[注]Homi K.Bhabha,Signs Taken For Wonders questions of ambivalence and authority under a tree outside Delhi,pp.144-165.。
其實,早在20世紀60年代,印度人類學家斯利尼瓦斯引入了“梵化”這個概念表達了類似于“雜糅”的話語功能。“梵化”這一概念涉及較低等級階層對高等階層和生活方式的采納,并且十分強調梵文經典中的觀念和價值觀。斯利尼瓦斯所指出,英國的殖民統治在推動廣泛的社會變遷后,隨之而來的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矛盾,即當婆羅門越來越“西化”的時候,另外的種姓則變得越來越向“梵化”發展。[注]M.N.Srinivas,Social Change in Mordern Idi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6,p.145.斯利尼瓦斯發現,與西方接觸后的環境并沒有削弱舊的傳統文化,比如種姓制度,反而加強了它們。隨著現代化將印度教從親屬關系和農村社區的束縛中分離出來,它變得越來越集中于寺廟、教派、小的朝拜團體和朝圣。如此一來,在種姓、語言和宗教團體基礎上形成的自愿協會變得更加重要,因為它可以彌補傳統社會和環境上的缺失——只是,當時這種與西方人類學并不太融洽的觀點并沒有引起足夠的反響。
上述對地方文化的獨特視角表明,人類學者一方面積極參與討論文化全球化背景后的霸權主義以及由此導致的文化多樣性發展問題,另一方面以后現代思潮為批判工具,尋找新興學科定位的同時,關注日常生活背后的文化權力關系。在后現代主義對傳統人文科學的批判中,人類學家們似乎看到了“鏡像中的自我”的羞恥——借用薩特對“羞恥”這樣一種很有意思的“意識”現象來解釋,人類學家的“羞恥根本上是承認他人是我和我本身之間不可缺少的中介:我對我自己感到羞恥,因為我向他人顯現;而且通過他人顯現本身,我都能像對一個對象(客體)做判斷那樣對我本身做判斷,因為我正是作為對象(客體)對他人顯現的。”[注][法]薩特:《存在與虛無》,陳宣良譯,北京:三聯書店,1997年,第29頁。后現代人類學通過對自我認知論的革命顯然奠定了“自我實踐”的特質,“它的意義是:自我是由反省意識所領悟的一個客體,也是被它所構成的一個客體。”[注][法]薩特:《薩特哲學論文集》,潘培慶、湯永寬、魏金聲等譯,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8年,第47頁。這種“羞恥”意識引發的“自我”(Ego)內在反思,無疑使人類學更像有關研究人性的學科。
二、鏡像的結構化:后現代人類學的認知論問題
事實上,奧威的“那喀索斯”和黑格爾的“自我意識辯證法”表明,完全通過“他者”反射自我的存在意義在原則上是不可能的。在傳統人類學的文化鏡像之中,西方中心主義的想象特質過于依賴于與“異文化”共同構成的“自我統一”的幻想之中,其本質為一種文化自戀和文化霸權。在后現代主義的沖擊下,后現代人類學家一方面賦予自身一種忘我感,另一方面又致力于追求完美性和統一性中的一份子的體驗。后現代人類這種解構-粘合(并非重構)的做法,在認知論的視角中,其實是想向自己存在的不足讓步,最終還是越來越把人類學家引向想象的層面,以便通過傳統與現代、原始與文明的對話而穩定下來——我們可以把這種民族志的結構視為“后結構主義”。人類學的結構主義傾向是“在每一種制度和習俗的下面去找到這種無意識的結構,來得到對其它制度和習俗能夠有效的解釋原理”[注][瑞士]皮亞杰:《結構主義》,倪連生、王琳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年,第77頁。,即“結構主義者相信系統知識是可能的;后結構主義則聲稱,所知的惟是這一知識的不可能”[注][美]喬納森·卡勒:《論解構》,陸楊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第13頁。。
正如霍克斯在評價列維-斯特勞斯的神話結構時所言:“如果說在神話中發現存在意義的話,那么這種意義不可能存在于組成神話的那些孤立的因素之中,而只能存在于這些要素被結合起來的方式之中。”[注][英]特倫斯·霍克斯:《結構主義和符號學》,瞿鐵鵬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6-57頁。后現代人類學徹底拋棄了這種“人類心智的產物”的結構圖式,轉向一種語言對象的交流結構。如在《后現代民族志:從關于神秘事物的記錄到神秘的記錄》一文中,斯蒂芬·泰勒指出:“民族志可能正是對話本身,或是關于共同環境的一系列并置的并列敘說,或者也可能僅是探尋共同主題的一系列獨立敘說,甚至是各種敘說或一個旋律和多個變奏曲的對位交織。”[注][美]理查德·G.福克斯主編:《重新把握人類學》,和少英譯,昆明:云南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13頁。在后現代人類學看來,“主體”屬于一種結構性的功能項,民族志的目的在于揭示人類學家與研究對象之間的秩序,系統分析這種關系的方式和結構,并從語言學、邏輯學或詩學的角度進行描述——這種主體的狀態其實蘊含著一個自相矛盾的論題——“我是他人”——這也顯然有別于“他人是我的歷史”的傳統人類學的立場。
無論是奧貝耶斯科爾的《馬渡莎的頭發:關于一起個人象征符號與宗教經驗的一項研究》,還是米歇爾·羅薩多的《知識與激情:伊龍哥特人的自我概念和社會生活》,包括法弗雷特·薩達的《致命的言語:博卡吉人的巫術》或文森特·克拉潘扎諾的《圖哈米·一個摩洛哥人的圖像》等,盡管后現代民族志試圖顛覆傳統人類學有關“文明”與“野蠻”的認知結構,然而“我”的一切是作為“他者”顯示出來的,而“他者”又是作為另外一個“我”呈現的。換言之,在后現代人類學的文本結構中,在這些竭力表達自我的人類學家背后,存在著另一個主體——研究對象,這種間接表達自我的方式其實證明了“我”如何成為“非我”,而成為“他人”。自我的統一性似乎隱藏了起來,而陷入了一種與他者對峙的僵化狀態。
在對人類學學科功能的本體問題的質疑上,后現代主義一個最為重要的本質特點就是“不確定性”。一般認為,在后現代人類學中,二元對立思維中的邏輯和修辭、理性和情感、客觀性和主觀性之間的區別已蕩然無存。然而,后現代主義者實際用不同方法操縱傳統人類相同的問題:他們選擇人類學家的在場,盡可能通過主體間的對話形式描述一種自我與他者之間的想象結構,從而導致產生了一種類似于文學上的“意識流”——一個由多元性、模糊性、間斷性、反叛、消解中心、移置等概念掩蓋主體存在不足的范疇。他者的“非我”狀態在于追蹤“自我衰落”的過程,而具有反思意識的自我則被囚禁在“自我的他性”的困境之中。
總體看來,人類學的理論基礎在于把人類視為一種線性演變的存在,認為可以通過科學試驗的方式,客觀地觀察、描述、研究人類社會。正是因為這一點,“從西方中心論到文化相對主義,從人類學家的價值中立到價值介入,從對大傳統的迷戀到對地方性知識的尊重,人類學所取得的每一個進步,都是認識論向前發展的體現”[注]周大鳴:《關于人類學學科定位的思考》,《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社版)》2012年第1期。。然而,正如弗雷德·布萊克(C.Fred Blake)指出,后現代人類學所推動的文化相對主義在人類學領域之外,已經(并將繼續)被扭曲——即用“文化”取代“種族”曾經的所指——“文化觀念引發了一種新的‘種族主義,當基于膚色的種族隔離最終被視為是缺乏科學根據后,那些基于差異將人們區分開來的人便轉向了‘文化’和‘文化遺存’以尋求歧視和排外的更為堅實的科學基礎”[注]C.Fr ed Blake:《美國文化人類學的當代理論趨勢》,《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8年第7期。。當后現代的認知觀念進入西方社會的大眾話語后,文化相對性便成為了種族歧視的新的根據。
三、鏡像邊緣的自我認識:中國人類學的本土化歷程
社會的整體性以及理性的普遍性一直以來是人類學研究中的一個基本假設,不同國家的人類學家也正是依賴于這些共同承認的假設,構建起了人類學的世界話語體系。在人類學的世界話語體系中,“西方中心主義”掌握了象征著真理和權威的知識話語權,中國人類學則長期處于一種“邊緣話語”的地帶——所謂“邊緣話語”,是“以主流話語、中心話語的反面被定義,邊緣的他者地位由主流話語建構”[注]丁建新、沈文靜:《邊緣話語分析:一些基本的理論問題》,《外語與外語教學》2013年第4期。。對于處于邊緣話語地帶的中國人類學而言,自西方人類學傳入中國以來,“本土化”作為學科發展的主旋律,主要是在“學科整體性”的語境中介紹和傳播西方人類學的文化體系,并運用于中國的具體實踐之中。在這近一個世紀的“本土化”訴求中,中國人類學的學科發展無疑深受邊緣化條件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充當了西方人類學的另一類“鏡像”——在中心的文化之境中,探索“自我”存在的空間和意義。
邊緣的文化鏡像實際上與“真實”無涉,在本質上屬于文化霸權的一種價值溢出。處于邊緣地帶的中國人類學在應對這種鏡像效應的過程中,充分體現了中國早期人類學家的超高智慧和深厚的人文素養。相對于西方人類學對“他者”的研究旨趣,中國人類學從其誕生開始就借用西方人類學的研究范式開展中國本土社會研究,大體路徑是從社會組織、生計方式、風俗禮儀等文化形態,或選擇其中的一個方面如人際關系、家庭關系、宗族、族群等來對展開民族志式的描述。無論是以少數民族文化史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南派”,還是秉承功能主義的“北派”,早期中國人類學在實現人類學中國化的過程中跨越了西方人類學“獵奇”的心態。正如1938年馬林諾斯基贊譽費孝通的《中國農民生活》是人類學實地調查和理論工作發展中的一個里程碑一樣,中國人類學的鄉土情結凝聚了“土生土長的人在本鄉人民中間進行工作的成果”[注]費孝通:《江村經濟:中國農民的生活》,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第13頁。。這實際與40余年后格爾茨提出的“地方性知識”存在著一種跨越時空的切合,即秉持著一種相對溫和的“文化相對主義”。在這種“文化相對主義”的支配下,大量來源于田野工作的第一手材料,使中國人類學具有開辟一條屬于自己的學科路徑的可能性。
經過近百年的發展,不可否認,當代中國的人類學始終沒有擺脫西方人類學一些關鍵性概念所提供的視角,如“文化”“文本”“民族志”“他者(異文化)”“地方性知識”等。沿著前人對西方人類學的消解和重構足跡,當代中國人類學借助西方人類學的各種話語或符號,積極參與鄉村文化建設研究、城市化進程中流動人口研究、邊疆地區民族問題研究、重大災害后重建研究等社會熱點問題。這種借助“他者”概念的自我發現、自我關照和自我表現,一方面使中國人類學長期處于世界話語體系的邊緣地帶,另一方面又有助于中國人類學家在邊緣地帶比較清晰地認識到了“中心”的各種文化危機。這種危機,正如王銘銘教授指出:“盡管20世紀社會人類學的理論經歷了功能主義、沖突理論、結構主義、過程理論、象征人類學、后結構、后現代主義等思想流派的演變,但其對于非西方的闡釋與理解,卻一直立基于‘我’/‘本文化”’與‘非我’/‘異文化’之間的相互觀照基礎之上。”[注]王銘銘:《他者的意義——論現代人類學的“后現代性”》,《廣西民族學院學報》2000年第2期。
在后現代人類學中,盡管人類學家試圖通過田野對象的“聲音”來建立文化表達的合法性,但是在福柯看來,權力和知識是相互依存、互為關照的,這個共生體的表象是知識,其本質其實就是權力,“所有的知識都是權力意志的體現,這就意味著我們不敢講出實在的真理和客觀的知識”[注]Selden Raman,A Reader's Guide to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Sussex:The Harvester Press Limited,1885,p.98.。“主體民族志”的提出顯然試圖超越后現代人類學家與“他者”在雙重想象中的僵化和對立狀態。在朱炳祥教授看來,主體民族志拒絕對傳統人類學“永恒的結構”和“普遍規律”的探尋,而是在民族志書主體與地方主體之間尋找彼此融合的概念視角,并由此以一種“裸呈”的方式呈現地方主體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注]朱炳祥:《反思與重構:論“主體民族志”》,《民族研究》2011年第3期。與后現代實驗民族志比較而言,“主體民族志”使人類學家與研究對象之間的秩序建立在彼此包容和相互理解的基礎上,體現了一種互為鏡像和互為主體的持續過程,有助于促進人類學的知識體系在多維視角客觀地反映一個時代的意義世界。如在《“三重敘事”的“主體民族志”微型實驗——一個白族人宗教信仰的“裸呈”及其解讀和反思》一文中,朱炳祥教授通過“裸呈”田野對象的神靈信仰,在“三重敘事”的語境中揭示了祖先作為精神主體在日常生活中的客觀存在及其文化意義。
在當代中國民族志的文本結構中,大多數學者傾向于傳統人類學“永恒的結構”“普遍規律”與后現代主義之間的密切合作。這種傾向一方面延續了人類學在研究“他者”制度體系和文化觀念等內容的科學性,強調客觀觀察和忠實描述;另一方面,又質疑人類學作為一種科學實踐的有限性,強調人類學家需要在與研究對象的對話中回歸到后者的意義世界之中,而不僅僅立足于“文化的書寫”。如清華大學張小軍教授主張一種“互為經驗的文化志”[注]張小軍、木合塔爾·阿皮孜:《走向“文化志”的人類學:傳統“民族志”概念反思》,《民族研究》2014年第4期。。“互為經驗的文化志”解構了人類學家作為知識生產的絕對主體地位,既強調地方文化固有的“信息編碼系統”,又強調人類學家與研究對象的文化共識。北京大學王銘銘教授則指出,包括中國人類學在內的當代人類學出現了“民族志新本體論”的回歸,強調在文化價值交流的敘事中“重新煥發民族志書寫”的傳統區域。[注]王銘銘:《當代民族志形態的形成:從知識論的轉向到新本體論的回歸》,《民族研究》2015年第3期。無論是“互為經驗的文化志”,“民族志新本體論”,這實際上主張人類學家應主動成為地方文化的鏡像,從而最終還原地方文化的客觀邏輯,而不是像傳統人類學一樣從“異文化”中尋找迷失的“自我”。
四、走向世界的“我們”:中國人類學的認知論革命
毋庸置疑,當代中國人類學一直立足于認知論的視角審視西方人類學的倫理缺陷以及中國人類學在“本土化”中的思維局限,并在不同程度克服了西方人類學“自我”與“他者”的二元對立思維及其衍生的文化危機,顯示了中國學者對中國社會變遷的敏感性和洞察力。特別是對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的研究,“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思路成為一條重要的理路,不同少數民族的傳統習俗、語言、信仰、經濟活動等作為一種相對獨立的意義世界得到了深度描述,這些成果共同構成了中國“地方性知識”的壯麗景觀。尤其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中,現代科學技術在中國社會中的文化意義及其運作邏輯越來越受到關注,現代性背景下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的生存危機引起了學界的警惕,中國鄉土人類學再次承擔起“地方性”的使命,主要是圍繞著當下某一社會焦點問題來展開調查與研究,探討民族文化的去向問題。
21世紀伊始,如何看待“地方性知識”在全球范圍內也發生了明顯的變化。2001年11月2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中聲明:“文化在不同的時代和不同的地方具有各種不同的表現形式。這種多樣性的具體表現是構成人類的各群體和各社會的特性所具有的獨特性和多樣化。”隨后,在2003年10月17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又頒布了《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保護“地方性知識”無疑獲得了合法性地位和正義的基礎。近幾年來,相關研究一個明顯的突破在于從“文化生態”的視角研究文化遺產的形態、樣式及其生存發展狀況。與傳統人類學“文化生態”的類比傾向及其構建色彩不同的是,中國人類學賦予了“文化生態”更多的意義內涵,如方李莉教授把“文化生態”視為一張“生命意義之網”[注]方李莉:《文化生態失衡問題的提出》,《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2001年第3期。,高丙中教授強調了“文化生態”的人本存在主義立場[注]高丙中:《關于文化生態失衡與文化生態建設的思考》,《云南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2012年第1期。,這種“文化生態”理論的新突破,無疑有助于在文化的真實領域領悟人類活動的意義訴求及其本質特征。
與文化人本存在主義的認知論相似,許憲隆、納日碧力戈等人提出了“民族共生”的理論見解,把民族文化多樣性的“意義之網”解讀為一種命運共同體,突出了人類存在意義的整體性以及文化實踐的動力來源。正如許憲隆指出:“‘共生互補’理念在促成文化生態學與民族關系研究的結合之后,不僅僅旨在研究文化與生態環境的相互關系,還把著眼點放置于更廣闊的研究空間,即不僅包括人與自然的共生互補關系,還包括個人與個人、集團與集團、民族與民族等人類世界中的共生互補關系。”[注]許憲隆、張成:《文化生態學語境下的共生互補觀——關于散雜居民族關系研究的新視野》,《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11年第5期。這顯然有助于克服后現代人類學的主體對立的方法論困境。在《族群的共生屬性及其邏輯結構》一書中,筆者也致力于探索族群作為“互為主體”存在的共生情景以及族群主體多層面的辯證位置,試圖揭示族群互惠共生的邏輯結構和倫理意義,從而構建一種超越二元論和分離主義的族群認知和行為范式——“共生即存在,共生使存在而存在,這是族群的本源屬性,也是人類存在的根本方式。”[注]袁年興:《族群的共生屬性及其邏輯結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第243頁。
人類學的核心問題在于“如何認識人類和人性”,而不應只探討“民族志如何書寫”的方法論問題。民族共生的理論視角不僅有助于我們推動中國人類學在原初領域的持續深入以及相關理論和研究范式的中國化,更有助于中國人類學在世界話語體系的邊緣地帶發現話語中心的文化危機,對人類的審視有更為深刻的視野和認識。不可否認,當下的民族共生論一直以“西方中心主義”作為對立面來闡述自己的主張,需要超越以“他者”為鏡像的不足,并采取一種更加寬廣的整體性視角看待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全球性問題,譬如資源枯竭、生態系統功能退化、貧窮和沖突等——這些問題又與當代人類問題與特定的文化過程有關,直接威脅著人類的幸福和未來發展。對此,高丙中教授指出:“自二戰結束以來,中國人也越來越清楚地看到全球化和世界性社會在我們面前的呈現。因為這個社會不是部落,不是傳統,也不只是現代民族國家的帝國,我們看到的跨國的和國際的現象是可以作為經驗來把握的。”[注]高丙中:《海外民族志與世界性社會》,《世界民族》2014年第1期。
正當中國鄉土人類學從傳統文化的闡釋轉向研究現代化、全球化及城鎮化背景下的地方文化危機時,當代西方應用人類學也存在著一種“全球化”的視野,只是這種全球化視角始終無法擺脫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思維邏輯中演繹著現代文明的語言游戲。在中國人類學的“全球化”視野下,高丙中、麻國慶等中國人類學家率領他們的團隊把目光投向了海外,直接以海外社會的實地調查為研究的依據,構建面向全球人類社會的研究平臺,這其中既包括西方發達國家,也包括發展中國家,“它標志著中國社會學人類學工作者開始從本國的需要出發,運用一種世界性的眼光來去對包括西方國家在內的海外世界進行實地性的考察。”[注]莊孔韶、蘭林友:《我國人類學研究的現狀與前瞻》,《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9年第3期。中國海外民族志雖然在文本書寫中依然存在著“自我”與“他者”的互相生成過程,但是把文化多樣性的視角納入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視角,突出“人”作為一種整體性的存在在文化實踐中的意義,這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文化相對主義主張的“自我”與“他者”互為文化鏡像可能導致的主體對立問題,也有助于克服后現代人類學的認知論困境。
大量海外民族志的陸續出版,既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重新凝視世界的新視角,也逐漸確立了“我們的世界”作為一個富有卓見的新認知在當代中國人類學的特殊地位。如趙萱通過對耶路撒冷土地爭奪的民族志材料的解讀,對于巴以之間“何故為敵”和“與誰為敵”等命題提出了全新理解[注]趙萱:《“圣地”秩序與世界想象——基于耶路撒冷橄欖山基督教社群的人類學反思》,《世界宗教文化》2018年第3期。;龔浩群通過研究泰國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的公共性轉換過程,揭示了由宗教建構起來的公共性邏輯在現代社會的轉化形式[注]龔浩群:《信徒與公民:泰國曲鄉的政治民族志》,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吳曉黎通過對印度喀拉拉邦社會政治的研究發現,印度種姓等級價值雖然已從公共領域退卻,但種姓歧視仍在個人的層面存在[注]吳曉黎:《社群、組織與大眾民主:印度喀拉拉邦社會政治的民族志》,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張金嶺通過描述法國里昂的“紅十字”社區結構成為一個地方社會“整體”的過程,揭示了法國社會互動中的價值觀念、家庭與社會福利、社團組織與社會發展、地方民主實踐、身份認同等內容[注]張金嶺:《公民與社會:法國地方社會的田野民族志》,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與當代西方人類學比較而言,中國海外民族志緩解了人類學學科研究中的特殊主義與比較方法、地方視角和全球視角之間的緊張關系,這種模式以“他者”的經驗意識為參照,注重“自我”對“他者”的對應以及彼此主體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造。
在現實層面,當代中國開啟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宏偉工程,“一帶一路”倡議也加強了中國與沿線國家人民的命運關聯——人類作為一種整體性的存在愈發清晰。對于當代中國人類學而言,把人類作為一種整體性存在的認知論基礎,為解構和重構人類學的世界話語體系奠定了基礎。無論是鄉土人類學,還是海外民族志,當代中國人類學在一定程度上規避了西方人類學的二元對立思維,這主要表現在一方面不斷糾正著西方話語體系的狹隘認知,另一方面致力于探索“他者”鏡像與“自我”內省的對比,從而使人類學的“文化之鏡”統一于對“人類”和“人性”的研究基石之上。可以預見,中國人類學的發展不僅能夠立足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意識,而且更會表現出一種有別于西方“全球意識”的立場和思考方式——以一種人類整體性的存在意義,重構人類學作為一門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福祉的學科本質。尤其是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話語背景下,當代中國人類學無疑開啟了世界人類學的新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