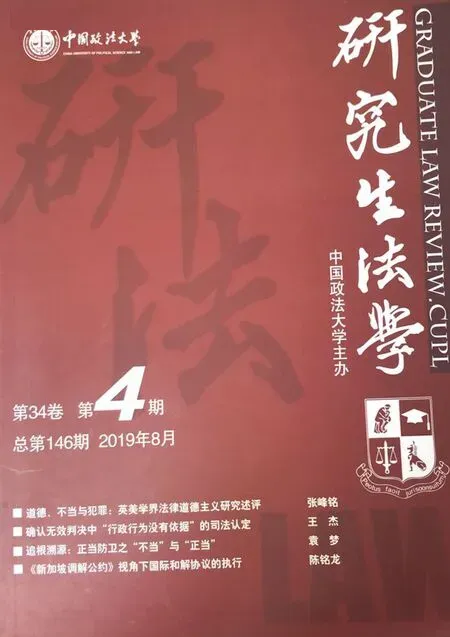《新加坡調(diào)解公約》視角下國際和解協(xié)議的執(zhí)行
陳銘龍
一、執(zhí)行國際和解協(xié)議的現(xiàn)實(shí)動(dòng)因
2018年12月20日,聯(lián)合國大會(huì)第73屆會(huì)議決議通過了《聯(lián)合國關(guān)于調(diào)解所產(chǎn)生的國際和解協(xié)議公約》(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Agreements Resulting from Mediation,該公約于2019年8月7日在新加坡開放簽署,故稱《新加坡調(diào)解公約》,下文簡稱《公約》),為國際商事調(diào)解的程序規(guī)范及其產(chǎn)生的國際和解協(xié)議在不同國家間的承認(rèn)與執(zhí)行提供了有效的法律依據(jù)。我國參與了《公約》的審議和起草,并于2019年8月7日成為《公約》的46個(gè)首批簽約國之一。為順應(yīng)國際商事爭議解決的發(fā)展趨勢,提升“一帶一路”建設(shè)過程中的國際商事爭議解決效率,我國應(yīng)當(dāng)準(zhǔn)確理解《公約》對執(zhí)行國際商事調(diào)解形成的國際和解協(xié)議的要求,并積極探討我國現(xiàn)行制度與《公約》如何銜接以及改進(jìn)、完善我國現(xiàn)行立法的方向。
國際商事爭議一般有四種解決方式——協(xié)商(negotiation)、調(diào)解(mediation)、仲裁(arbitration)以及訴訟(litigation)(1)參見劉曉紅、袁發(fā)強(qiáng)主編:《國際商事仲裁》,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0年版,第6~12頁。在國際商事爭議解決中尚有微型審理(minitrials)、簡易陪審團(tuán)(summary jury trial)、早期評議審理(early trial evaluation)等諸多英美法的ADR,本文主要關(guān)注文中所述的四種解決方式。,長期以來,調(diào)解(2)雖然《公約》在行文中并未明確使用“commercial mediation”,但從其序言第2條的“a method for settling commercial disputes”以及《公約》第1條第2款規(guī)定的適用范圍排除事項(xiàng)可知《公約》是在國際商事關(guān)系語境下使用“mediation”一詞,應(yīng)將其與國際公法上的“居間調(diào)停”和民事領(lǐng)域的“調(diào)解”區(qū)分開;同理,“仲裁”亦存在國際投資爭議仲裁、勞動(dòng)仲裁等通過仲裁程序處理但不體現(xiàn)國際商事關(guān)系的爭議解決活動(dòng),“協(xié)商”與“訴訟”的含義和類別則更為豐富多樣。為免贅述,本文中“調(diào)解”與“訴訟”“仲裁”“協(xié)商”皆系在國際商事爭議解決語境下使用,特此說明。被視為訴訟和仲裁中解決爭議的輔助手段。事實(shí)上,在國際商事爭議解決領(lǐng)域中,調(diào)解一直具有獨(dú)特的價(jià)值與優(yōu)勢。在經(jīng)濟(jì)全球化和產(chǎn)業(yè)精細(xì)化的宏觀背景下,許多國際商事交往具有長期性、穩(wěn)定性,在諸如汽車制造業(yè)、飛機(jī)制造業(yè)這類供應(yīng)鏈龐大復(fù)雜、遍布全球的行業(yè)中尤其如此。訴訟和仲裁總有勝方,但從維護(hù)當(dāng)事人商業(yè)信譽(yù)和降低潛在成本的角度考慮,錙銖必較的裁判可能使雙方當(dāng)事人都成為敗方。(3)參見何貴才:《涉外商事調(diào)解案例評析》,光明日報(bào)出版社2013年版,第45頁。在訴訟曠日持久、耗費(fèi)巨大,而仲裁日益呈現(xiàn)司法化(judicialization)(4)指近年來國際商事仲裁中越來越多地適用民事訴訟的規(guī)定,致使仲裁逐漸朝向訴訟模式演化,程序繁瑣、冗長,當(dāng)事人為與對方保持長期良性關(guān)系而選擇仲裁的初衷亦逐漸為激烈的對抗性取代。參見于湛旻:《國際商事仲裁司法化問題研究》,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18頁。趨勢的情形下,調(diào)解無疑能更好地回應(yīng)爭議當(dāng)事人友好解決爭議、維護(hù)長期良好關(guān)系的訴求,同時(shí)其也能在彌合跨文化沖突(5)參見楊玲:《國際商事仲裁程序研究》,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38~40頁。和處理多邊爭議(6)See S. I. Strong, Beyond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Th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Mediation, 45 Wash. U. J. L. & Pol'y. (2014), p.20.等訴訟和仲裁難以妥善處理的問題上展現(xiàn)更高的爭議解決效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所屬法系不一,民族文化背景差異不可忽視,具體法律制度更是千差萬別。在一些混合了不同法系特點(diǎn)的國家如約旦,一起案件的裁判周期長達(dá)3—4年,執(zhí)行周期也長達(dá)12—18個(gè)月,(7)參見廖永安、段明:“我國發(fā)展 ‘一帶一路’商事調(diào)解的機(jī)遇、挑戰(zhàn)與路徑選擇”,載《南華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8年第4期,第28頁。顯然不能滿足高頻率國際商事交易的需求。因此兼具靈活性、高效性和非嚴(yán)格規(guī)范性的調(diào)解是解決“一帶一路”國際商事爭議的良好進(jìn)路。
事實(shí)上,在20世紀(jì)中期之前,國際商事爭議當(dāng)事人更加傾向于通過調(diào)解解決爭議。20世紀(jì)中期之后,仲裁才逐漸取代調(diào)解成為更受當(dāng)事人偏好的爭議解決方式,(8)See S. I. Strong, Beyond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Th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Mediation, 45 Wash. U. J. L. & Pol'y. (2014), p. 12.時(shí)至今日,高達(dá)90%的國際商業(yè)合同中包含有仲裁條款。(9)See Otto Sandrock, The Choice Between Forum Selection, Mediation and Arbitration Clauses : European Perspectives, The America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Vol. 20. (2010), pp. 7-37, 轉(zhuǎn)引自王琦:“海南全面深化改革進(jìn)程中的國際商事糾紛調(diào)解機(jī)制研究”,載《海南大學(xué)學(xué)報(bào)(人文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9年第3期,第117頁。促成該種轉(zhuǎn)變的一個(gè)重要原因即是1958年《承認(rèn)及執(zhí)行外國仲裁裁決公約》(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Arbitral Awards,下文簡稱“《紐約公約》”)賦予了國際商事仲裁裁決在各締約國間自由流動(dòng)的能力,使其能得到締約國司法機(jī)關(guān)的強(qiáng)制執(zhí)行,從而得以切實(shí)地保護(hù)當(dāng)事人的權(quán)益。《公約》通過之前,調(diào)解形成的和解協(xié)議(10)實(shí)際上將《公約》中的“Settlement Agreements”直接譯為“和解協(xié)議”是有瑕疵的。首先這在字面上體現(xiàn)不出調(diào)解員的作用,而和解協(xié)議產(chǎn)生于調(diào)解恰是《公約》對認(rèn)定和解協(xié)議能否執(zhí)行的重要要件;其次“和解協(xié)議”容易與當(dāng)事人自行協(xié)商達(dá)成的和解協(xié)議或是仲裁、訴訟過程中產(chǎn)生的和解協(xié)議混淆,產(chǎn)生歧義。參見溫先濤:“《新加坡公約》與中國商事調(diào)解——與《紐約公約》《選擇法院協(xié)議公約》相比較”,載《中國法律評論》2019年第1期,第199頁。多是作為當(dāng)事人之間的契約處理的,(11)參見祁壯:“‘一帶一路’建設(shè)中的國際商事調(diào)解和解問題研究”,載《中州學(xué)刊》2017年第11期,第64頁。和解協(xié)議本身并不具備強(qiáng)制執(zhí)行力,這從根本上阻礙了調(diào)解在國際商事爭議解決中發(fā)揮應(yīng)有的作用。2014年S. I. Strong教授在密蘇里大學(xué)法學(xué)院爭議解決研究中心主持的一項(xiàng)調(diào)研表明:絕大部分受訪者是期望建立國際間承認(rèn)與執(zhí)行和解協(xié)議的統(tǒng)一機(jī)制以利其運(yùn)用調(diào)解解決國際商事爭議的。(12)See S. I. Strong, Use and Perception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Mediation and Conciliation: A Preliminary Report on Issues Relating to the Proposed UNCITRAL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Mediation and Conciliation, University of Missouri School of Law Legal Studies Research Paper Series Research Paper No. 2014-28. (2014), pp. 52~53. 該調(diào)研系為聯(lián)合國國際貿(mào)易法委員會(huì)第二工作組(爭議解決部)起草國際商事調(diào)解公約收集資料,該工作組負(fù)責(zé)《公約》的起草工作。《公約》最后只采用了“執(zhí)行”和解協(xié)議的表述,因?yàn)椤俺姓J(rèn)”多指認(rèn)定爭議解決結(jié)果具有可執(zhí)行性的過程但不最終決定能否執(zhí)行,對實(shí)操影響不大,能否執(zhí)行才是當(dāng)事人最為關(guān)切的。該觀點(diǎn)在聯(lián)合國國際貿(mào)易法委員會(huì)《第二工作組(仲裁和調(diào)解)第六十三屆會(huì)議(2015年9月7日至11日,維也納)工作報(bào)告》,聯(lián)合國文件A/CN.9/861,第71段中有記載。同年聯(lián)合國國際貿(mào)易法委員會(huì)(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下文簡稱“貿(mào)法會(huì)”)在倫敦金融城舉辦“構(gòu)建國際爭議解決未來的公約”論壇,征詢來自20多個(gè)國家的150余名使用者(跨國公司經(jīng)營者)、國際仲裁和國際調(diào)解領(lǐng)域的顧問、仲裁員、調(diào)解員及學(xué)者對調(diào)解的態(tài)度,結(jié)果顯示:
2/3的使用者認(rèn)為降低風(fēng)險(xiǎn)和降低成本是解決國際爭端的最重要因素;超過3/4的使用者投票表示應(yīng)盡早在爭議中使用調(diào)解;2/3的使用者對訴訟或仲裁前進(jìn)行調(diào)解的爭議解決條款有需求;約80%的使用者認(rèn)為仲裁機(jī)構(gòu)和法庭應(yīng)在第一次會(huì)議上探討其他爭議解決方法是否適合參與爭議解決的問題;85%的使用者和47%的顧問認(rèn)為需要制定一項(xiàng)聯(lián)合國國際貿(mào)易法委員會(huì)(UNCITRAL)公約,以承認(rèn)和執(zhí)行調(diào)解協(xié)議。(13)參見王淑敏、何悅涵:“海南自貿(mào)試驗(yàn)區(qū)國際商事調(diào)解機(jī)制:理論分析與制度建構(gòu)”,載《海南大學(xué)學(xué)報(bào)(人文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8年第5期,第27頁。
2017年,美國新澤西城市大學(xué)商學(xué)院爭議解決中心就國際商事爭議解決方式的選擇和動(dòng)因?qū)碜?4個(gè)國家的2500余名當(dāng)事人問詢調(diào)研。調(diào)研報(bào)告顯示在國際商事爭議解決中共計(jì)64%的受訪者選擇“不經(jīng)常”或“從不使用”調(diào)解;對于在選擇調(diào)解上采取保守態(tài)度的原因,57.14%的受訪者表示系因“對調(diào)解程序不熟悉”,位列第二的原因是占比28.09%的“缺乏國際上的執(zhí)行機(jī)制”;然而在被問及“是否考慮將調(diào)解條款納入合同”時(shí),僅有23%的受訪者表示“從不考慮”,在被問及“設(shè)若存在執(zhí)行和解協(xié)議的國際機(jī)制時(shí)是否選擇調(diào)解作為爭議解決機(jī)制”時(shí),80%的受訪者給出了肯定的答復(fù)。(14)See David S. Weiss & Michael R. Griffith, Report on International Mediation and Enforcement Mechanisms, Institute for Dispute Resolution (IDR) NJCU School of Business. (2017), pp. 11-18. 該報(bào)告系為聯(lián)合國國際貿(mào)易法委員會(huì)第二工作組(爭議解決部)第67次會(huì)議收集的資料。《公約》起草之初貿(mào)法會(huì)第二工作組的報(bào)告亦中提及:
更多地使用調(diào)解的一個(gè)障礙是,調(diào)解達(dá)成的和解協(xié)議比仲裁裁決執(zhí)行起來難度更大。一般而言,調(diào)解達(dá)成的和解協(xié)議作為當(dāng)事各方之間的合同已經(jīng)可以執(zhí)行,但依據(jù)合同法跨境執(zhí)行可能繁瑣且費(fèi)時(shí)。最后,此類合同不容易執(zhí)行可能影響商業(yè)當(dāng)事方進(jìn)行調(diào)解的積極性。(15)聯(lián)合國國際貿(mào)易法委員會(huì)《解決商事爭議——國際商事調(diào)解/調(diào)停所產(chǎn)生和解協(xié)議的可執(zhí)行性——秘書處的說明》,聯(lián)合國文件A/CN.9/WG.II/WP.187,第2段。
可見,實(shí)踐中國際商事爭議當(dāng)事人最為關(guān)心的并非是具體的爭議解決方式,而是該種方式產(chǎn)生的解決結(jié)果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切實(shí)的執(zhí)行力。《公約》的正式生效使調(diào)解形成的和解協(xié)議獲得國際上的執(zhí)行力,對爭議當(dāng)事人的權(quán)利保障大為增強(qiáng)。可以預(yù)見,隨著《公約》的生效,調(diào)解將迎來發(fā)展高峰,這也要求調(diào)解參與人在實(shí)踐中正確理解、適用《公約》的各項(xiàng)規(guī)定——尤其是關(guān)系到當(dāng)事人實(shí)體利益的和解協(xié)議的執(zhí)行條件。下文擬從正反兩方面探討《公約》規(guī)定的和解協(xié)議的執(zhí)行條件,界定“何種和解協(xié)議可按《公約》要求獲得執(zhí)行力”,并探討我國的現(xiàn)行立法如何與《公約》銜接。
二、可執(zhí)行的和解協(xié)議的適用范圍
(一) 和解協(xié)議應(yīng)當(dāng)具有國際性
據(jù)《公約》第1條第1款規(guī)定,可得執(zhí)行的和解協(xié)議應(yīng)當(dāng)具有國際性。事實(shí)上,《公約》制訂過程中對和解協(xié)議的國際性亦非從無爭議。從貿(mào)法會(huì)第二工作組的相關(guān)會(huì)議討論記錄來看,和解協(xié)議的國際性主要關(guān)注兩組區(qū)分:
1. “國際”調(diào)解與“國內(nèi)”調(diào)解
該組區(qū)分的出發(fā)點(diǎn)是考察調(diào)解過程本身體現(xiàn)的國際性。《公約》前期審議過程中,一種觀點(diǎn)認(rèn)為,為禮讓締約國國內(nèi)法,減少統(tǒng)一協(xié)調(diào)不同法域和解協(xié)議執(zhí)行制度的阻礙,“文書的范圍應(yīng)局限于有別于國內(nèi)過程的‘國際’調(diào)解過程所產(chǎn)生的和解協(xié)議”;(16)聯(lián)合國國際貿(mào)易法委員會(huì)《第二工作組(仲裁和調(diào)解)第六十三屆會(huì)議(2015年9月7日至11日,維也納)工作報(bào)告》,聯(lián)合國文件A/CN.9/861,第30段。另一種觀點(diǎn)認(rèn)為,調(diào)解的國際性并不重要,應(yīng)當(dāng)關(guān)注的是和解協(xié)議本身體現(xiàn)國際性,區(qū)分國內(nèi)調(diào)解和國外調(diào)解反而會(huì)使和解協(xié)議執(zhí)行制度的統(tǒng)一協(xié)調(diào)面臨更大困難。這兩種觀點(diǎn)的分歧在于國內(nèi)調(diào)解是否應(yīng)當(dāng)納入《公約》的適用范圍,前者注重調(diào)解過程的國際性,后者注重和解協(xié)議的國際性。然而,對“和解協(xié)議國際性”的認(rèn)定同樣存在一定爭議,對該事項(xiàng)有觀點(diǎn)認(rèn)為,時(shí)常會(huì)出現(xiàn)國內(nèi)公司達(dá)成具有涉外因素的和解協(xié)議的情形,例如一方公司的母公司、財(cái)產(chǎn)、實(shí)際控制人或持股股東與公司營業(yè)地不在同一國境內(nèi)等,因此建議《公約》將該類和解協(xié)議納入執(zhí)行范圍中,以適應(yīng)復(fù)雜公司架構(gòu)條件下的國際商事實(shí)踐慣例。(17)See Eunice Chua, Enforcement of International Mediated Settlement Agreements In Asia: A Path Towards Convergence, 15 A. I. A. J. (2019), pp. 5-6.
從《公約》最終的文本看,貿(mào)法會(huì)沒有特別注重國內(nèi)調(diào)解與國際調(diào)解的區(qū)分,而是更務(wù)實(shí)地從結(jié)果出發(fā),考察和解協(xié)議體現(xiàn)出的國際性;也沒有過度擴(kuò)大和解協(xié)議“國際性”的認(rèn)定依據(jù),因?yàn)椤耙獙?fù)雜公司架構(gòu)作出清晰準(zhǔn)確的認(rèn)定是有困難的”。(18)Eunice Chua, Enforcement of International Mediated Settlement Agreements In Asia: A Path Towards Convergence, 15 A. I. A. J. (2019), p. 6.基此,《公約》第1條第1款b項(xiàng)特別規(guī)定作為識(shí)別和解協(xié)議國際性聯(lián)結(jié)點(diǎn)的當(dāng)事人營業(yè)地所在國不能是“和解協(xié)議相當(dāng)一部分義務(wù)的履行地國”或者“與和解協(xié)議所涉事項(xiàng)關(guān)系最密切的國家”,得通過《公約》獲得執(zhí)行的和解協(xié)議只能由至少兩方“在不同國家設(shè)有營業(yè)地”的當(dāng)事人達(dá)成。由此也可見調(diào)解總是以高效解決爭議為首要導(dǎo)向,與訴訟“查明事實(shí)、準(zhǔn)確認(rèn)定、公正裁判”的要求有所區(qū)別。
2. “外國”和解協(xié)議與“國際”和解協(xié)議
調(diào)解和仲裁有諸多相似之處,例如二者都基于當(dāng)事人的意思自治發(fā)生、不必然受一方當(dāng)事人國內(nèi)法的管轄、在程序進(jìn)行上當(dāng)事人擁有高度的自決權(quán)等,因此貿(mào)法會(huì)在《公約》起草、制訂過程中亦時(shí)常對比、借鑒《紐約公約》的規(guī)定。《紐約公約》第1條規(guī)定:“被申請承認(rèn)及執(zhí)行地所在國認(rèn)為非內(nèi)國裁決者,也適用本公約。”有觀點(diǎn)認(rèn)為《公約》在認(rèn)定和解協(xié)議的國際性時(shí)不必拘泥于“國際”和“國內(nèi)”的區(qū)分,而應(yīng)當(dāng)師法《紐約公約》關(guān)于仲裁裁決國籍屬性的認(rèn)定標(biāo)準(zhǔn),從執(zhí)行地國的角度識(shí)別和解協(xié)議的國際性,(19)參見聯(lián)合國國際貿(mào)易法委員會(huì)《第二工作組(仲裁和調(diào)解)第六十三屆會(huì)議(2015年9月7日至11日,維也納)工作報(bào)告》,聯(lián)合國文件A/CN.9/861,第34~39段。主張和解協(xié)議作為“非內(nèi)國化”(denationalized)的爭議解決結(jié)果既可以是因?yàn)闃?biāo)的、當(dāng)事人、法律關(guān)系發(fā)生地等客觀聯(lián)結(jié)點(diǎn)具有涉外因素,也可以是因?yàn)閳?zhí)行地國主觀上不認(rèn)為該和解協(xié)議屬于國內(nèi)和解協(xié)議,例如該國國內(nèi)法規(guī)定調(diào)解員具有外國國籍屬于和解協(xié)議的涉外事由。按照該種觀點(diǎn),一些國內(nèi)調(diào)解機(jī)構(gòu)調(diào)解形成的和解協(xié)議也可被認(rèn)定為國際和解協(xié)議并按《公約》獲得執(zhí)行力。
借鑒仲裁裁決的“非內(nèi)國化”或可為和解協(xié)議的執(zhí)行帶來便利,但應(yīng)當(dāng)認(rèn)識(shí)到,從本質(zhì)上看,仲裁“非內(nèi)國化”趨勢的產(chǎn)生背景是當(dāng)事人意思自治與仲裁地法的矛盾。在現(xiàn)代仲裁中,當(dāng)事人選擇仲裁地點(diǎn)具有偶然性,選擇在一地仲裁并非當(dāng)然代表當(dāng)事人愿意受仲裁地法(lex arbitri)支配的意愿,國際商事仲裁可以不受仲裁地法的限制,仲裁裁決的法律效力也不必由仲裁地國的法律賦予。(20)參見趙秀文:《國際商事仲裁法》(第二版),中國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12年版,第152頁。然而在調(diào)解中,確認(rèn)調(diào)解機(jī)構(gòu)所在地或者和解協(xié)議作出地對和解協(xié)議的執(zhí)行卻沒有太大意義,因?yàn)楹徒鈪f(xié)議本身具有高度的意定性,即便在《公約》生效前,國際上也從無“調(diào)解及其和解協(xié)議必須依照調(diào)解地法作出”的立法例,因此強(qiáng)調(diào)和解協(xié)議的“非內(nèi)國”屬性意義不大;相反,因?yàn)檎{(diào)解比仲裁更為“飄忽不定”,對和解協(xié)議“非內(nèi)國”屬性的認(rèn)定應(yīng)當(dāng)進(jìn)一步限縮。貿(mào)法會(huì)第二工作組同樣認(rèn)為:“不能以類同于仲裁裁決的方式對待和解協(xié)議,因?yàn)椴槊骱徒鈪f(xié)議與某一調(diào)解地或法定調(diào)解地的關(guān)聯(lián)因素并非總是易事,況且仲裁裁決通常都有一個(gè)決定其‘外國’性質(zhì)的裁決下達(dá)地。”(21)聯(lián)合國國際貿(mào)易法委員會(huì)《第二工作組(仲裁和調(diào)解)第六十三屆會(huì)議(2015年9月7日至11日,維也納)工作報(bào)告》,聯(lián)合國文件A/CN.9/861,第15段。
從最終確定的《公約》文本考察,《公約》對和解協(xié)議國際性的認(rèn)定并未過度擴(kuò)大,而是集中在當(dāng)事人營業(yè)地這一聯(lián)結(jié)點(diǎn)上。此外,根據(jù)《公約》第2條第1款,當(dāng)事人有多個(gè)營業(yè)地的,應(yīng)以其與爭議有最密切聯(lián)系或當(dāng)事人共知的營業(yè)地為識(shí)別根據(jù),避免當(dāng)事人以此規(guī)避國內(nèi)法的管轄。
(二)和解協(xié)議應(yīng)當(dāng)體現(xiàn)商事性
貿(mào)法會(huì)的官方文本將“Settlement Agreement”譯為“和解協(xié)議”是容易產(chǎn)生歧義的,因?yàn)椤昂徒鈪f(xié)議”的字面含義極其廣泛,《公約》自身也為“和解協(xié)議”的界定設(shè)置了諸多規(guī)則。《公約》第2條規(guī)定:“本公約不適用于以下和解協(xié)議:(a) 為解決其中一方當(dāng)事人(消費(fèi)者)為個(gè)人、家庭或者家居目的進(jìn)行交易所產(chǎn)生的爭議而訂立的協(xié)議;(b) 與家庭法、繼承法或者就業(yè)法有關(guān)的協(xié)議。”可見尋求執(zhí)行的和解協(xié)議除應(yīng)體現(xiàn)國際性外,還應(yīng)當(dāng)體現(xiàn)商事性。《公約》基于以下考量未對“商事”作出明確的定義:首先,在《公約》產(chǎn)生前,貿(mào)法會(huì)于2002年制訂的《國際商事調(diào)解示范法》(Model Law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ncili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下文簡稱《示范法》)已然對“商事性”作出界定,《公約》顧及已經(jīng)適用《示范法》的國家,在該點(diǎn)上不作新的規(guī)范以保障《公約》與《示范法》一脈相承;其次,各國對“商事”的界定有差異,《公約》不作過于精細(xì)的定義,以減少適用阻力;最后,保留關(guān)于“商事性”的要求有助于發(fā)展國際貿(mào)易,避免過多的非商業(yè)因素進(jìn)入爭議解決過程。(22)See Eunice Chua, The Singapore Convention on Mediation—A Brighter Future for Asian Dispute Resolution, As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9. (2019), p. 197.
《紐約公約》第3條規(guī)定了締約國得在加入《紐約公約》時(shí)聲明商事保留:“任何國家亦得聲明,本國只對根據(jù)本國法律屬于商事性質(zhì)的法律關(guān)系所產(chǎn)生的爭議適用本公約,不論為契約性質(zhì)與否。”我國于1986年加入《紐約公約》時(shí)亦聲明我國僅對我國法律認(rèn)為屬于“契約性和非契約性商事法律關(guān)系”所引起的爭議適用《紐約公約》。(23)關(guān)于我國商事保留的具體范圍,參見《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執(zhí)行我國加入的〈承認(rèn)及執(zhí)行外國仲裁裁決公約〉的通知》{法(經(jīng))發(fā)[1987]5號(hào)}。該《通知》規(guī)定:“所謂‘契約性和非契約性商事法律關(guān)系’,具體的是指由于合同、侵權(quán)或者根據(jù)有關(guān)法律規(guī)定而產(chǎn)生的經(jīng)濟(jì)上的權(quán)利義務(wù)關(guān)系,例如貨物買賣、財(cái)產(chǎn)租賃、工程承包、加工承攬、技術(shù)轉(zhuǎn)讓、合資經(jīng)營、合作經(jīng)營、勘探開發(fā)自然資源、保險(xiǎn)、信貸、勞務(wù)、代理、咨詢服務(wù)和海上、民用航空、鐵路、公路的客貨運(yùn)輸以及產(chǎn)品責(zé)任、環(huán)境污染、海上事故和所有權(quán)爭議等,但不包括外國投資者與東道國政府之間的爭端。”此外第二工作組在起草《公約》時(shí)也參考了《聯(lián)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Contrac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下文簡稱CISG)關(guān)于適用范圍的規(guī)定,認(rèn)為《公約》不應(yīng)將“當(dāng)事人意思自治因絕對強(qiáng)制性規(guī)則或因公共政策而受到限制”(24)聯(lián)合國國際貿(mào)易法委員會(huì)《第二工作組(仲裁和調(diào)解)第六十三屆會(huì)議(2015年9月7日至11日,維也納)工作報(bào)告》,聯(lián)合國文件A/CN.9/861,第42段。的事項(xiàng)納入和解范圍,換言之,無論是否體現(xiàn)經(jīng)濟(jì)關(guān)系,當(dāng)事人可得調(diào)解的事項(xiàng)至少應(yīng)當(dāng)是當(dāng)事人能完全依自己的意思處置的事項(xiàng)而非婚姻家庭、司法程序等受到法律或社會(huì)公共政策約束的事項(xiàng)。
另一個(gè)應(yīng)當(dāng)注意的特殊之處是,《公約》第2條并未將政府實(shí)體排除在適用范圍之外。不同于CISG完全排除對不平等主體之間貨物銷售合同的適用,《公約》并不認(rèn)為政府實(shí)體完全不能參與商事活動(dòng),而且鼓勵(lì)政府實(shí)體與其商業(yè)伙伴通過調(diào)解處理其商事糾紛。這也從側(cè)面反映出調(diào)解的獨(dú)特價(jià)值——政府實(shí)體傾向于排斥他種權(quán)力如仲裁權(quán)、司法權(quán)的管轄,調(diào)解則屬于平權(quán)結(jié)構(gòu),有助于在高效解決政商商事糾紛的同時(shí)維護(hù)其長期友好關(guān)系,為不平等主體之間的爭議提供了紓解通道。《公約》第8條第1款a項(xiàng)亦允許一國政府在加入《公約》時(shí)聲明保留:“對于其為一方當(dāng)事人的和解協(xié)議,或者對于任何政府機(jī)構(gòu)或者代表政府機(jī)構(gòu)行事的任何人為一方當(dāng)事人的和解協(xié)議,在聲明規(guī)定的限度內(nèi),本公約不適用”,政府實(shí)體對其是否接受《公約》的約束具有完全的自決權(quán)。由此可見,《公約》對調(diào)整國際商事活動(dòng)中的政商關(guān)系、提高爭議解決效率、改善營商環(huán)境是很有裨益的。
(三) 和解協(xié)議應(yīng)當(dāng)產(chǎn)生于獨(dú)立的調(diào)解程序
《公約》第1條第3款規(guī)定:“本公約不適用于:(a)以下和解協(xié)議:(一)經(jīng)由法院批準(zhǔn)或者系在法院相關(guān)程序過程中訂立的協(xié)議;和(二)可在該法院所在國作為判決執(zhí)行的協(xié)議;(b) 已記錄在案并可作為仲裁裁決執(zhí)行的協(xié)議。”《公約》通過之前,調(diào)解更多地作為仲裁和訴訟的附帶程序出現(xiàn),即訴訟中調(diào)解和仲裁中調(diào)解。該種做法的本意是通過調(diào)解和其他程序的結(jié)合提高爭議解決的效率,但也帶來裁判者中立性的爭議,其集中體現(xiàn)即是對仲裁中調(diào)解“私訪”的爭論——調(diào)解過程中仲裁員的身份經(jīng)歷了從單一仲裁員到仲裁員、調(diào)解員雙重身份的轉(zhuǎn)變,調(diào)解失敗后則回歸單一仲裁員身份作出裁決。(25)參見劉曉紅主編,林燕萍、劉寧元副主編:《國際商事仲裁專題研究》,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356頁。在作為調(diào)解員時(shí)仲裁員并不被禁止與當(dāng)事人私下接觸以促成調(diào)解,爭論焦點(diǎn)在于調(diào)解失敗后仲裁員在調(diào)解過程中獲取的信息是否會(huì)對仲裁員的中立性造成影響或剝奪另一方當(dāng)事人平等答辯的機(jī)會(huì)。《公約》規(guī)定調(diào)解具有相對于仲裁和訴訟的獨(dú)立性,也有助于上述問題的解決。
貿(mào)法會(huì)指出,一些法域的國家將和解協(xié)議記錄在仲裁裁決和法院判決中予以執(zhí)行,若規(guī)定該些和解協(xié)議得通過《公約》直接執(zhí)行將造成《公約》與國內(nèi)法、現(xiàn)有公約和未來公約如《選擇法院協(xié)議公約》的重疊與沖突,增加和解協(xié)議的執(zhí)行阻力,因此司法和仲裁過程中調(diào)解形成的和解協(xié)議應(yīng)當(dāng)排除《公約》的適用。然而《公約》的該項(xiàng)規(guī)定也受到一定質(zhì)疑,主要有:(1)要求執(zhí)行機(jī)構(gòu)根據(jù)適用于判決的公約或國內(nèi)法來確定和解協(xié)議的可執(zhí)行性會(huì)加大執(zhí)行機(jī)構(gòu)的負(fù)擔(dān);(2)可能造成立法上的漏洞,剝奪一些記作仲裁裁決或法院判決卻不能按仲裁或訴訟程序執(zhí)行的和解協(xié)議的執(zhí)行機(jī)會(huì),例如仲裁裁決不具有可執(zhí)行性或依被申請執(zhí)行國國內(nèi)法不允許該類和解協(xié)議的執(zhí)行。對此筆者認(rèn)為,首先,執(zhí)行和解協(xié)議雖然在形式上會(huì)增加執(zhí)行機(jī)關(guān)的審查程序,但實(shí)質(zhì)上并未增加執(zhí)行壓力,在爭議總量不變的前提下,調(diào)解反而是分流執(zhí)行壓力的良好渠道,因?yàn)闋幾h通過調(diào)解解決便意味著仲裁和訴訟壓力的減少,而且和解協(xié)議的有效性、終局性的舉證責(zé)任由當(dāng)事人承擔(dān);其次,《公約》規(guī)定和解協(xié)議執(zhí)行例外的目的是避免《公約》與其他執(zhí)行程序的競合,而不在于將調(diào)解與其他程序完全分離,《公約》并不禁止仲裁員或法官參與調(diào)解。2018年4月8日在布拉格發(fā)布的《關(guān)于國際仲裁程序高效進(jìn)行的規(guī)則》(Rules on the Efficient Conduct of Proceedings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以下簡稱“布拉格規(guī)則”)第9條(26)《布拉格規(guī)則》第9條“協(xié)助友好和解”: 9.1. 除非一方當(dāng)事人反對,仲裁庭可以協(xié)助當(dāng)事人在仲裁程序的任何階段達(dá)成爭議的友好和解。 9.2. 在雙方均事前書面同意的情況下,仲裁庭的任何成員都可以以調(diào)解員的身份協(xié)助案件的友好和解。 9.3. 如果調(diào)解沒有在雙方同意的期限內(nèi)形成和解,作為調(diào)解員的仲裁庭成員: a. 在獲得雙方于調(diào)解結(jié)束時(shí)的書面同意后可以繼續(xù)在仲裁程序中擔(dān)任仲裁員; b. 如果沒有獲取書面同意,應(yīng)當(dāng)根據(jù)適用的仲裁規(guī)則終止他/她的委任。 《布拉格規(guī)則》旨在提高仲裁程序效率,減少仲裁使用者在仲裁程序中所花費(fèi)的時(shí)間和費(fèi)用,系由來自大約30個(gè)國家(主要是大陸法系國家)的代表組成工作組,在工作組成員對其各自國家的國際仲裁程序傳統(tǒng)做法進(jìn)行調(diào)查的基礎(chǔ)上制訂的。《布拉格規(guī)則》已于2018年12月14日在布拉格開放簽署。也提及在在仲裁過程中,基于雙方合意由仲裁員主持調(diào)解是值得鼓勵(lì)的。因此,只要和解協(xié)議及其履行義務(wù)未以仲裁裁決或訴訟判決形式生效便沒有超出《公約》的適用范圍。
事實(shí)上,由于貿(mào)法會(huì)在起草《公約》時(shí)已征詢了中國政府的意見,《公約》第1條第3款也體現(xiàn)了對我國法律制度預(yù)留的“接口”。根據(jù)我國《民事訴訟法》《仲裁法》及其相關(guān)司法解釋的規(guī)定,訴訟和仲裁過程中產(chǎn)生的調(diào)解書與判決書、裁決書實(shí)質(zhì)上有同等效力,原本便不應(yīng)當(dāng)作為一般的和解協(xié)議對待,因此我國現(xiàn)行法律規(guī)定與《公約》不存在根本性的沖突。
三、和解協(xié)議執(zhí)行抗辯事由的相關(guān)問題
前文述及,《公約》在起草、制訂時(shí)對《紐約公約》多有借鑒,在規(guī)定執(zhí)行和解協(xié)議的執(zhí)行抗辯條件時(shí)亦沿用了《紐約公約》的反面列舉技術(shù),即不存在執(zhí)行抗辯事由的和解協(xié)議自動(dòng)獲得執(zhí)行效力。需要說明的是,《公約》第1條規(guī)定的適用范圍不屬于執(zhí)行抗辯事由,二者應(yīng)理解為遞進(jìn)式關(guān)系,不符合《公約》第1條的和解協(xié)議自始不屬于《公約》指稱的和解協(xié)議,肯定待執(zhí)行和解協(xié)議符合《公約》第1條規(guī)定的范圍后,方得進(jìn)一步考察其是否具有執(zhí)行抗辯事由;若無,則該和解協(xié)議具有可執(zhí)行性。
執(zhí)行抗辯事由主要規(guī)定在《公約》第5條第1款,包括:(1)一方當(dāng)事人無行為能力;(2)和解協(xié)議依據(jù)的法律失效、和解協(xié)議不具有終局性、和解協(xié)議被修改;(3)和解協(xié)議義務(wù)已經(jīng)履行或不明晰;(4)準(zhǔn)予救濟(jì)有悖和解協(xié)議;(5)調(diào)解員嚴(yán)重違背調(diào)解準(zhǔn)則以致誤導(dǎo)當(dāng)事人訂立和解協(xié)議;(6)調(diào)解員未恰當(dāng)履行信息披露義務(wù)并因此誤導(dǎo)當(dāng)事人訂立和解協(xié)議。此外,該條第2款規(guī)定,若執(zhí)行地國主管機(jī)關(guān)認(rèn)為執(zhí)行和解協(xié)議將違反其公共政策或和解協(xié)議不具有可執(zhí)行性,亦可主動(dòng)拒絕執(zhí)行和解協(xié)議。然而《公約》第5條明確說明其適用需以《公約》第4條作為前提,因此筆者認(rèn)為《公約》實(shí)際上存在一個(gè)隱含的執(zhí)行抗辯事由——和解協(xié)議不產(chǎn)生于調(diào)解過程。綜合貿(mào)法會(huì)制訂《公約》過程中的爭點(diǎn),筆者認(rèn)為在理解和解協(xié)議的執(zhí)行抗辯條件時(shí)有如下三點(diǎn)應(yīng)予特別說明。
(一) 和解協(xié)議產(chǎn)生于調(diào)解過程的證明
《公約》第1條和第2條定義了和解協(xié)議的形式要求——和解協(xié)議須以書面形式作成。為適應(yīng)互聯(lián)網(wǎng)線上調(diào)解的發(fā)展需求,此處的“書面形式”包含電子通信記錄。(27)See Eunice Chua, Enforcement of International Mediated Settlement Agreements In Asia: A Path Towards Convergence, 15 A. I. A. J. (2019), p. 7.《公約》第2條第3款對“調(diào)解”做出如下定義:“‘調(diào)解’不論使用何種稱謂或者進(jìn)行過程以何為依據(jù),指由一名或者幾名第三人(‘調(diào)解員’)協(xié)助,在其無權(quán)對爭議當(dāng)事人強(qiáng)加解決辦法的情況下,當(dāng)事人設(shè)法友好解決其爭議的過程。”《公約》第4條則規(guī)定,可資證明調(diào)解過程存在的依據(jù)既可是調(diào)解員在和解協(xié)議上的簽名、調(diào)解員簽署的表明進(jìn)行了調(diào)解的文件、調(diào)解過程管理機(jī)構(gòu)的證明,也可是識(shí)別當(dāng)事人或者調(diào)解員的身份并表明當(dāng)事人或者調(diào)解員關(guān)于電子通信所含信息的意圖的、并經(jīng)被申請執(zhí)行地國主管機(jī)構(gòu)認(rèn)可的其他形式的證據(jù)。
由此可見,《公約》對“調(diào)解”的要求是:(1)具備三方結(jié)構(gòu),不屬于當(dāng)事人之間自行協(xié)商達(dá)成的和解協(xié)議,必須有調(diào)解員或調(diào)解機(jī)構(gòu)居中斡旋;(28)《公約》審議過程中,有觀點(diǎn)認(rèn)為自行協(xié)商達(dá)成的和解協(xié)議也應(yīng)當(dāng)納入《公約》適用范圍,但貿(mào)法會(huì)普遍認(rèn)為這將使《公約》與締約國國內(nèi)的《合同法》產(chǎn)生沖突,因?yàn)殡p方當(dāng)事人協(xié)商達(dá)成的和解協(xié)議具有明顯的合同屬性,而可供執(zhí)行的和解協(xié)議應(yīng)當(dāng)具有相對于一般和解協(xié)議優(yōu)先的效力。(2)基于平等自愿原則,調(diào)解員無權(quán)強(qiáng)制當(dāng)事人達(dá)成和解協(xié)議;(29)參見聯(lián)合國國際貿(mào)易法委員會(huì)《解決商事爭議:國際商事調(diào)解/調(diào)停所產(chǎn)生和解協(xié)議的可執(zhí)行性——秘書處的說明》,聯(lián)合國文件A/CN.9/WG.II/WP.195,第22~24段。(3)解決爭議應(yīng)出于友好協(xié)商而不得帶有爭訟性質(zhì),否則亦不作為和解協(xié)議予以執(zhí)行。“產(chǎn)生于調(diào)解”是和解協(xié)議可執(zhí)行性的實(shí)質(zhì)要求之一,證明和解協(xié)議產(chǎn)生于調(diào)解過程則是其形式要求。在規(guī)定和解協(xié)議的書面形式和調(diào)解過程的證明方式時(shí),貿(mào)法會(huì)第二工作組認(rèn)為應(yīng)當(dāng)遵循“最低限度的形式要求”,(30)聯(lián)合國國際貿(mào)易法委員會(huì)《解決商事爭議:國際商事調(diào)解/調(diào)停所產(chǎn)生和解協(xié)議的可執(zhí)行性——秘書處的說明》,聯(lián)合國文件A/CN.9/WG.II/WP.198,第26~27段。以求保障當(dāng)事人意思自治的自由,具體形式以能證明其系自愿參加調(diào)解過程并在調(diào)解員或調(diào)解機(jī)構(gòu)參與下達(dá)成和解協(xié)議為準(zhǔn)。
調(diào)解員的證明作用也帶來了防范虛假調(diào)解的問題。《公約》的“三方結(jié)構(gòu)”要求意味著調(diào)解員應(yīng)當(dāng)有獨(dú)立的職權(quán)與資格,否則若一方當(dāng)事人與任意第三人串通,達(dá)成形式上符合調(diào)解要求而實(shí)質(zhì)上損害另一方當(dāng)事人利益的“和解協(xié)議”并請求執(zhí)行,勢將使《公約》的爭議解決作用落空,具備獨(dú)立資格的調(diào)解員本身也可能成為虛假調(diào)解的加害人。規(guī)制虛假調(diào)解實(shí)際上已經(jīng)超越《公約》的適用范疇,《公約》也沒有賦予和解協(xié)議來源地國或執(zhí)行地國管轄虛假調(diào)解的權(quán)力,甚至沒有說明虛假調(diào)解的效力。若虛假調(diào)解以我國為執(zhí)行地,當(dāng)事人可通過《民事訴訟法》第112條駁回其執(zhí)行申請,甚至依《刑法》第307條追究加害方虛假訴訟罪的責(zé)任;(31)參見孫巍:“《新加坡調(diào)解公約》與我國法律制度的銜接”,www.ccpit.org/Contents/Channel_3453/2019/0306/1136454/content_1136454.html,最后訪問時(shí)間:2019年7月26日。是否有必要在《公約》中補(bǔ)充虛假調(diào)解約束規(guī)范,有待《公約》生效后考察其實(shí)際運(yùn)行情況。
(二)和解協(xié)議終局性的判斷
《公約》第5條b款第(二)、(三)項(xiàng)規(guī)定:和解協(xié)議非終局性協(xié)議或被修改的,執(zhí)行機(jī)關(guān)不予執(zhí)行。該條實(shí)質(zhì)上反映了符合條件的和解協(xié)議是自動(dòng)具有執(zhí)行效力還是經(jīng)和解協(xié)議來源地國審查后方具有執(zhí)行效力的爭議。《公約》制定過程中,有觀點(diǎn)提出符合《公約》要求的和解協(xié)議應(yīng)當(dāng)自動(dòng)獲得執(zhí)行效力,另一方觀點(diǎn)則認(rèn)為應(yīng)當(dāng)加入和解協(xié)議來源地國的復(fù)審機(jī)制保障和解協(xié)議的真實(shí)性和終局性。貿(mào)法會(huì)最終基于下列理由未將和解協(xié)議來源地國的復(fù)審機(jī)制寫入《公約》:(1)和解協(xié)議的來源地往往難以確認(rèn),“因?yàn)殛P(guān)聯(lián)因素可能是以不同方式確定的”(32)聯(lián)合國國際貿(mào)易法委員會(huì)《第二工作組(仲裁和調(diào)解)第六十三屆會(huì)議(2015年9月7日至11日,維也納)工作報(bào)告》,聯(lián)合國文件A/CN.9/861,第81段。;(2)加入復(fù)審機(jī)制會(huì)增加和解協(xié)議的執(zhí)行阻力,等于要求申請人提交“雙重執(zhí)行確認(rèn)書”,不利于救濟(jì)當(dāng)事人的權(quán)利,也不符合調(diào)解“簡便高效”的價(jià)值追求;(3)直接執(zhí)行不一定會(huì)剝奪當(dāng)事人尋求救濟(jì)的機(jī)會(huì),對于當(dāng)事人救濟(jì)機(jī)會(huì)的關(guān)切完全可以通過增加相應(yīng)的執(zhí)行抗辯理由予以解決。事實(shí)上,《公約》第6條規(guī)定的并行申請制度也為當(dāng)事人尋求司法救濟(jì)開辟了路徑,當(dāng)事人既可向執(zhí)行機(jī)關(guān)主張存在《公約》第5條規(guī)定的執(zhí)行抗辯事由,也可就和解協(xié)議中的爭議事項(xiàng)提起訴訟或仲裁。訴訟和仲裁在程序上對和解協(xié)議的執(zhí)行有優(yōu)先性,起訴或提起仲裁將中斷執(zhí)行和解協(xié)議的進(jìn)程,相應(yīng)的代價(jià)是提起訴訟或仲裁的當(dāng)事人需適當(dāng)具保,以免減損和解協(xié)議的執(zhí)行效力。由此可見《公約》不必增加執(zhí)行前和解協(xié)議來源地的復(fù)審機(jī)制以確認(rèn)和解協(xié)議的終局性,而應(yīng)當(dāng)保障當(dāng)事人事后抗辯救濟(jì)的權(quán)利,由當(dāng)事人決定和解協(xié)議的救濟(jì)程序。
應(yīng)當(dāng)認(rèn)識(shí)到,相較于仲裁和訴訟,調(diào)解具有顯著的保密性、靈活性、意定性,因此執(zhí)行機(jī)關(guān)在審查和解協(xié)議時(shí)很難準(zhǔn)確探究、評估調(diào)解過程是否完全體現(xiàn)當(dāng)事人內(nèi)心的意思,更應(yīng)關(guān)注調(diào)解結(jié)果即和解協(xié)議是否符合當(dāng)事人合意。將一部分和解協(xié)議執(zhí)行效力的審查義務(wù)分配給當(dāng)事人可實(shí)現(xiàn)執(zhí)行機(jī)構(gòu)審查工作與當(dāng)事人意思自治之間的平衡,當(dāng)事人應(yīng)當(dāng)保證其簽署的和解協(xié)議是基于其合意作出的終局協(xié)議,不再反復(fù),不再修改。執(zhí)行地國主管機(jī)構(gòu)既不便,也不應(yīng)主動(dòng)審查當(dāng)事人之間是否仍有未盡爭議,和解協(xié)議來源地國自然也不承擔(dān)該項(xiàng)義務(wù);若當(dāng)事人在仍有未盡爭議的情形下簽署了和解協(xié)議,則應(yīng)當(dāng)承擔(dān)相應(yīng)的不利后果,因?yàn)檎{(diào)解中當(dāng)事人具有完全的意思自治,應(yīng)當(dāng)對自己的權(quán)利義務(wù)負(fù)責(zé)。在當(dāng)事人自查不存在《公約》第5條所述的執(zhí)行抗辯事由即不提出抗辯后,和解協(xié)議自動(dòng)獲得執(zhí)行效力,除非執(zhí)行機(jī)關(guān)援引《公約》第5條第2款主動(dòng)拒絕執(zhí)行該和解協(xié)議。
(三) 調(diào)解員的中立性對和解協(xié)議效力的影響
《紐約公約》中并未特別規(guī)定仲裁員行為對仲裁裁決的承認(rèn)與執(zhí)行產(chǎn)生的消極影響,而《公約》則在第5條中分列(e)、(f)兩款規(guī)定了調(diào)解員違反行為準(zhǔn)則或不當(dāng)履行信息披露義務(wù)構(gòu)成和解協(xié)議的執(zhí)行抗辯事由。不同于仲裁和訴訟嚴(yán)格的程序規(guī)范性,調(diào)解尤其注重爭議解決過程的高效性和保密性,因此現(xiàn)行調(diào)解立法和各調(diào)解機(jī)構(gòu)的調(diào)解規(guī)則皆未對調(diào)解員的行為作出深入明晰的程序約束,以便利調(diào)解員靈活運(yùn)用各種方式達(dá)成爭議解決目的。然而調(diào)解手段和調(diào)解活動(dòng)的界限止于法律規(guī)定和當(dāng)事人的意思自治,調(diào)解員只應(yīng)促成而非誤導(dǎo)當(dāng)事人達(dá)成協(xié)議。
《公約》審議過程中曾提出“調(diào)解結(jié)果顯然不公”的措辭,但貿(mào)法會(huì)討論后認(rèn)為“顯然不公”的證明門檻過高,應(yīng)當(dāng)調(diào)整為“不當(dāng)影響”,由當(dāng)事人自行裁量和解協(xié)議是否符合其真實(shí)意愿并決定是否達(dá)成合意,而不應(yīng)在事后以客觀標(biāo)準(zhǔn)評價(jià)和解協(xié)議對當(dāng)事人的影響。(33)參見聯(lián)合國國際貿(mào)易法委員會(huì)《第二工作組(爭議解決)第六十六屆會(huì)議(2017 年2月6日至10日,紐約)工作報(bào)告》,聯(lián)合國文件A/CN.9/901,第43~44段。調(diào)解的事中規(guī)制應(yīng)當(dāng)著重關(guān)注調(diào)解員的信息披露義務(wù),以保障各方當(dāng)事人的知情權(quán)為調(diào)解員促成和解所采行動(dòng)的底線,(34)See Klaus Peter Berger, Common Law v. Civil Law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The Beginning or the End?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Vol.36, No. 3. (2019), p. 309.新加坡國際調(diào)解中心(Singapore International Mediation Centre,下文簡稱SIMC)所制訂的調(diào)解規(guī)則即明確要求當(dāng)事人在調(diào)解開始前互換案件陳述及有關(guān)文件,并允許當(dāng)事人和調(diào)解員組織調(diào)解前會(huì)議商討調(diào)解方式以保證當(dāng)事人對調(diào)解過程的主導(dǎo)權(quán)與知情權(quán)。(35)《SIMC調(diào)解規(guī)則》第6.4條:“各方當(dāng)事人應(yīng)在預(yù)定調(diào)解之日前至少十天或調(diào)解員可能規(guī)定的其它時(shí)間前,將其案件陳述和任何有關(guān)文件提交SIMC并互相交換該等文件。”第6.5條:“SIMC可在適當(dāng)?shù)那闆r下安排調(diào)解前會(huì)議,以商討調(diào)解的進(jìn)行方式及程序,包括設(shè)定相關(guān)時(shí)間表等。為避免歧義,調(diào)解前會(huì)議可通過面議、電話會(huì)議或其它電子通訊方式進(jìn)行。”當(dāng)事人在充分知悉調(diào)解情況的前提下將理性評估爭議解決結(jié)果,因此對調(diào)解員的約束應(yīng)集中在避免扭曲當(dāng)事人的真實(shí)意思而非對調(diào)解員的行為制訂完整的行為準(zhǔn)則。
四、 我國現(xiàn)行制度的矛盾及與和解協(xié)議執(zhí)行的銜接
《公約》與當(dāng)下我國調(diào)解發(fā)展現(xiàn)狀有一些不相匹配之處。從立法角度看,缺乏一部統(tǒng)一的《商事調(diào)解法》始終滯后于我國調(diào)解快速發(fā)展的需求,而且不同于1994年我國制訂《仲裁法》時(shí)《紐約公約》已經(jīng)生效,《仲裁法》可充分考慮與《紐約公約》的銜接問題,《公約》生效時(shí)我國已有《民事訴訟法》《仲裁法》《人民調(diào)解法》等規(guī)定調(diào)解協(xié)議效力的國內(nèi)法律法規(guī),因此我國現(xiàn)行法律體系中并未留足執(zhí)行和解協(xié)議的“接口”;從調(diào)解實(shí)踐看,目前我國已基本形成“以人民調(diào)解、行政調(diào)解、司法調(diào)解‘三調(diào)聯(lián)動(dòng)’為基礎(chǔ)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jī)制工作格局”,(36)參見龍飛:“‘多元化糾紛解決機(jī)制’正鋪開宏偉畫卷”,載《人民法院報(bào)》2017年10月17日。產(chǎn)生了行業(yè)調(diào)解、聯(lián)合調(diào)解、訴調(diào)對接、調(diào)裁結(jié)合、特邀調(diào)解等諸多具有中國特色的調(diào)解方式。在調(diào)解機(jī)構(gòu)上,除了傳統(tǒng)的各級(jí)法院、人民調(diào)解委員會(huì)及消費(fèi)者協(xié)會(huì),近年來還涌現(xiàn)了“一帶一路”國際商事調(diào)解中心、中國國際貿(mào)易促進(jìn)委員會(huì)調(diào)解中心、上海經(jīng)貿(mào)商事調(diào)解中心等一批專業(yè)的調(diào)解機(jī)構(gòu),此外中國經(jīng)濟(jì)貿(mào)易仲裁委員會(huì)、上海國際仲裁中心等仲裁機(jī)構(gòu)甚至各地的商會(huì)組織也承擔(dān)著一部分調(diào)解職能。調(diào)解機(jī)構(gòu)“遍地開花”也從側(cè)面反映出我國調(diào)解制度不統(tǒng)一的困境,事實(shí)上ADR發(fā)展成熟的國家和地區(qū)大都擁有代表性的調(diào)解立法和專業(yè)的調(diào)解機(jī)構(gòu),如美國國會(huì)1998年即通過《替代性爭議解決方案》(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Act of 1998),實(shí)踐上也有司法仲裁調(diào)解服務(wù)有限公司(Judicial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Service, Inc. 以下簡稱JAMS)承擔(dān)調(diào)解的實(shí)際運(yùn)作,英國則有著名的英國有效爭議解決中心(Centre for Effective Dispute Resolution,以下簡稱CEDR)承擔(dān)民商事調(diào)解職能。我國調(diào)解發(fā)展的現(xiàn)狀決定了《公約》與我國現(xiàn)行制度的銜接是一個(gè)系統(tǒng)性的問題,既要考慮法律適用層面,又要考慮機(jī)構(gòu)設(shè)置和實(shí)務(wù)操作層面。
明確《公約》在我國的適用效力是探討我國現(xiàn)行制度與《公約》銜接的基礎(chǔ)和前提。即便按《民事訴訟法》第260條規(guī)定,(37)《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260條:“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jié)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同本法有不同規(guī)定的,適用該國際條約的規(guī)定,但中華人民共和國聲明保留的條款除外。”《公約》與我國法律規(guī)定不一致時(shí),《公約》具有優(yōu)先適用效力,也仍有必要理清執(zhí)行和解協(xié)議與“確認(rèn)調(diào)解協(xié)議效力”(38)與《公約》相異,我國現(xiàn)行立法中并無“執(zhí)行和解協(xié)議”的表述。為免歧義,本文在論及和解協(xié)議在我國的執(zhí)行情況時(shí)依然沿用“執(zhí)行調(diào)解協(xié)議”的表述,除非聯(lián)系到《公約》語境。等我國現(xiàn)行法律規(guī)定中和解協(xié)議的處理方法之間的關(guān)系。在《公約》審議過程中,貿(mào)法會(huì)針對當(dāng)事人適用《公約》的效力曾有兩種觀點(diǎn);一派認(rèn)為符合《公約》的和解協(xié)議自動(dòng)適用《公約》獲得執(zhí)行效力以利和解義務(wù)的履行、落實(shí),另一派觀點(diǎn)則認(rèn)為應(yīng)由當(dāng)事人自行決定是否適用《公約》,以減少《公約》與執(zhí)行地國的法律沖突。(39)參見聯(lián)合國國際貿(mào)易法委員會(huì)《第二工作組(爭議解決)第六十六屆會(huì)議(2017 年2月6日至10日,紐約)工作報(bào)告》,聯(lián)合國文件A/CN.9/901,第36~37段。最終《公約》第8條第1款b項(xiàng)規(guī)定:“本公約適用,唯需和解協(xié)議當(dāng)事人已同意適用本公約。”可見《公約》系由當(dāng)事人的合意選擇適用而非自動(dòng)適用。基此筆者認(rèn)為,當(dāng)事人不必因《民事訴訟法》260條之規(guī)定直接選擇適用《公約》,《公約》與我國相關(guān)國內(nèi)法的規(guī)定應(yīng)理解為“雙軌并行”的關(guān)系:當(dāng)事人可依《公約》申請執(zhí)行和解協(xié)議,此時(shí)《公約》便具有優(yōu)先于國內(nèi)不一致規(guī)定的效力;當(dāng)事人也可沿用《公約》通過前我國處理調(diào)解協(xié)議效力的辦法,如向司法機(jī)關(guān)申請確認(rèn)調(diào)解協(xié)議的效力等。目前我國法律僅規(guī)定了訴訟中調(diào)解、仲裁中調(diào)解和人民調(diào)解委員會(huì)調(diào)解中形成的調(diào)解協(xié)議的處理辦法,《公約》具有填補(bǔ)我國立法空白的作用。然而“雙軌并行”的處理辦法亦存在一定矛盾,主要表現(xiàn)在如下方面。
(一) 商事調(diào)解立法缺位,執(zhí)行抗辯事由不一致
我國現(xiàn)行法律體系中缺失統(tǒng)一的商事調(diào)解立法是造成我國調(diào)解“多而不專”現(xiàn)狀的根本原因,這或?qū)⒅苯訉?dǎo)致今后司法實(shí)踐中《公約》的實(shí)際適用出現(xiàn)矛盾。事實(shí)上,早在2009年最高法就已在《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建立健全訴訟與非訴訟相銜接的矛盾糾紛解決機(jī)制的若干意見》(法發(fā)[2009]4號(hào))中提出了豐富多樣的調(diào)解協(xié)議執(zhí)行方法,(40)參見《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建立健全訴訟與非訴訟相銜接的矛盾糾紛解決機(jī)制的若干意見》(法發(fā)[2009]45號(hào))第10條、第12條、第13條、第15條、第26條、第27條。包括肯定調(diào)解協(xié)議的合同效力、將調(diào)解協(xié)議申請公證、依調(diào)解協(xié)議申請支付令、確認(rèn)調(diào)解協(xié)議效力等多種方式,也提及了立案前委托調(diào)解、建立調(diào)解員名冊等先進(jìn)的舉措,堪稱完備;2016年最高法發(f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人民法院進(jìn)一步深化多元化糾紛解決機(jī)制改革的意見》(法發(fā)[2016]14號(hào))則進(jìn)一步提出建立“一站式”的糾紛解決綜合服務(wù)平臺(tái),要求加強(qiáng)與綜治組織、行政機(jī)關(guān)、商事調(diào)解組織、公證機(jī)構(gòu)及其他社會(huì)組織的對接,確保調(diào)解協(xié)議的落實(shí)。上述兩份文件的精神和方向已經(jīng)與《公約》十分接近,但皆屬于方向性的司法政策而非具有法律效力的規(guī)范性文件,(41)參見姚遠(yuǎn)、謝綺雯:“商事調(diào)解及其司法確認(rèn)的發(fā)展現(xiàn)狀反思與制度設(shè)計(jì)建議”,載《寧波廣播電視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19年第2期,第36~37頁。而現(xiàn)行具有法律效力的實(shí)操規(guī)范又和《公約》的執(zhí)行抗辯事由存在一定矛盾,主要表現(xiàn)如下。
《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審理涉及人民調(diào)解協(xié)議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規(guī)定》(法釋[2002]29號(hào))第5條規(guī)定:具有損害國家、集體或第三人利益,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損害社會(huì)公共利益,違反法律、行政法規(guī)的強(qiáng)制性規(guī)定的調(diào)解協(xié)議無效;第6條規(guī)定:因重大誤解訂立或在訂立調(diào)解協(xié)議時(shí)顯失公平的,當(dāng)事人一方有權(quán)請求人民法院撤銷或變更。《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人民調(diào)解協(xié)議司法確認(rèn)程序的若干規(guī)定》第7條規(guī)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不予確認(rèn)調(diào)解協(xié)議效力:(一)違反法律、行政法規(guī)強(qiáng)制性規(guī)定的;(二)侵害國家利益、社會(huì)公共利益的;(三)侵害案外人合法權(quán)益的;(四)損害社會(huì)公序良俗的;(五)內(nèi)容不明確,無法確認(rèn)的;(六)其他不能進(jìn)行司法確認(rèn)的情形。”(42)該條規(guī)定被中國政府在回應(yīng)貿(mào)法會(huì)向各國征詢對執(zhí)行和解協(xié)議的意見時(shí)予以援引,說明我國司法中也以主要依據(jù)條規(guī)定處理和解協(xié)議的執(zhí)行問題,具有代表性,詳見聯(lián)合國國際貿(mào)易法委員會(huì)《解決商事爭議國際商事調(diào)解/調(diào)停所產(chǎn)生的和解協(xié)議的執(zhí)行——從各國政府收到的評論意見——秘書處的說明》,聯(lián)合國文件A/CN.9/846/Add.2,第4~5頁。可見目前我國立法對調(diào)解協(xié)議仍是作為當(dāng)事人之間的契約處理,注重其“合同效力”而未明確提及“執(zhí)行”,在確認(rèn)效力的事由上也大體照搬了當(dāng)時(shí)《民法通則》的規(guī)定,更多依靠客觀標(biāo)準(zhǔn)認(rèn)定調(diào)解協(xié)議的效力。對此筆者認(rèn)為:我國上述立法與《公約》實(shí)無本質(zhì)沖突,只是在“客觀”與“主觀”的取向上有所差別,上述規(guī)定可納入《公約》第5條第2款的“公共政策”范疇,而我國的規(guī)定也可起到規(guī)制虛假調(diào)解的作用,彌補(bǔ)了《公約》的立法漏洞。
執(zhí)行抗辯事由沖突帶來的另一個(gè)問題是:“雙軌并行”的適用規(guī)則下,當(dāng)申請執(zhí)行的和解協(xié)議因存在《公約》第5條規(guī)定的執(zhí)行抗辯事由被裁定不予執(zhí)行后,能否再依我國《民事訴訟法》的規(guī)定申請確認(rèn)調(diào)解協(xié)議的效力后執(zhí)行?從現(xiàn)行《公約》文本看,《公約》對此并無明確的規(guī)定,并且《公約》第7條規(guī)定《公約》不限制當(dāng)事人在有法律或國際條約依據(jù)的情況下保有“援用該和解協(xié)議的任何權(quán)利”,應(yīng)認(rèn)為《公約》對該問題持開放態(tài)度。我國《民事訴訟法》第124條第5款也僅規(guī)定:“對判決、裁定、調(diào)解書已經(jīng)發(fā)生法律效力的案件,當(dāng)事人又起訴的,告知原告申請?jiān)賹彛嗣穹ㄔ簻?zhǔn)許撤訴的裁定除外”,而《公約》所述的和解協(xié)議本不包括法院制作的調(diào)解書。因此筆者認(rèn)為,就現(xiàn)有法律規(guī)定看,《公約》和我國關(guān)于和解協(xié)議的規(guī)定應(yīng)當(dāng)是“雙向選擇”的關(guān)系,若待執(zhí)行的和解協(xié)議符合我國相關(guān)法律規(guī)定,按《公約》申請執(zhí)行和解協(xié)議被拒絕執(zhí)行不排除當(dāng)事人向我國法院再行提起確認(rèn)調(diào)解協(xié)議程序的權(quán)利,反之亦然。
(二)調(diào)解機(jī)構(gòu)和調(diào)解人員的獨(dú)立性不明顯
前文已述,《公約》要求可得執(zhí)行的和解協(xié)議應(yīng)產(chǎn)生于獨(dú)立的調(diào)解過程,而該過程必然有賴于調(diào)解機(jī)構(gòu)或調(diào)解員的獨(dú)立證明。貿(mào)法會(huì)在就執(zhí)行和解協(xié)議的事宜征詢各國意見時(shí)也包含了“和解協(xié)議是否應(yīng)以書面作成,并且是否應(yīng)由當(dāng)事人或其代表以及調(diào)停員/調(diào)解員簽署”(43)聯(lián)合國國際貿(mào)易法委員會(huì)《解決商事爭議國際商事調(diào)解/調(diào)停所產(chǎn)生的和解協(xié)議的執(zhí)行——從各國政府收到的評論意見——秘書處的說明》,聯(lián)合國文件A/CN.9/846,第3段。的問題,可見按照貿(mào)法會(huì)的設(shè)想,應(yīng)當(dāng)由具有獨(dú)立職權(quán)的調(diào)解機(jī)構(gòu)或調(diào)解員證明和解協(xié)議的來源,并以此作為執(zhí)行和解協(xié)議的前提條件。
在我國統(tǒng)一的商事調(diào)解立法缺位、法律對調(diào)解機(jī)構(gòu)和調(diào)解員賦權(quán)不足,而調(diào)解需求旺盛的現(xiàn)狀下,推動(dòng)“訴調(diào)對接”“調(diào)裁對接”成為普遍的應(yīng)對方式,例如一帶一路國際商事調(diào)解中心對接北京市第四中級(jí)人民法院、深圳國際仲裁院對接廣州海事法院等。(44)參見龍飛:“‘一帶一路’戰(zhàn)略中多元化糾紛解決機(jī)制的地位”,載《人民法院報(bào)》2017年7月14日。目前該種辦法對法院、仲裁機(jī)構(gòu)和調(diào)解機(jī)構(gòu)是雙贏關(guān)系,但根本上還是體現(xiàn)了調(diào)解機(jī)構(gòu)缺乏獨(dú)立的職權(quán)的弱項(xiàng),長遠(yuǎn)來看仍是制約了調(diào)解獨(dú)立價(jià)值的發(fā)揮。現(xiàn)行的“訴調(diào)對接”“調(diào)裁對接”制度雖能提高爭議解決效率,卻并非全無弊端:首先,缺乏統(tǒng)一的對接規(guī)則,爭議解決效果不確定。以法院為例,一些法院的“訴調(diào)對接”系通過委托調(diào)解或特邀調(diào)解(45)參見《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人民法院特邀調(diào)解的規(guī)定》(法釋[2016]14號(hào)),該《規(guī)定》要求建立特邀調(diào)解組織和特邀調(diào)解員名冊。建立名冊的法院應(yīng)當(dāng)為入冊的特邀調(diào)解組織或者特邀調(diào)解員頒發(fā)證書,并對名冊進(jìn)行管理。可見賦予專業(yè)的調(diào)解機(jī)構(gòu)和調(diào)解員以獨(dú)立職權(quán)系一種趨勢。引入外部專業(yè)的調(diào)解機(jī)構(gòu)或調(diào)解人員幫助解決爭議,也有一些法院依靠設(shè)在法院內(nèi)部的調(diào)解委員會(huì)實(shí)現(xiàn)“訴調(diào)對接”,該些調(diào)解委員會(huì)往往由離休法官組成,反而給當(dāng)事人造成“二次審判”的壓力;其次,由于我國現(xiàn)行立法對“訴調(diào)對接”“調(diào)裁對接”產(chǎn)生的爭議解決結(jié)果的性質(zhì)規(guī)定不明,《公約》對我國生效后,一些實(shí)際由調(diào)解達(dá)成卻產(chǎn)生于訴訟或仲裁過程的和解協(xié)議可能在申請執(zhí)行時(shí)造成認(rèn)定上的混亂和矛盾。可以預(yù)見,《公約》對我國生效后,機(jī)構(gòu)設(shè)置上的“調(diào)裁分離”“審調(diào)分離”將成為主流,如此一方面可以避免“仲裁中調(diào)解”“訴訟中調(diào)解”造成的調(diào)解員中立性的困局,另一方面也順應(yīng)了調(diào)解員專業(yè)化的趨勢。事實(shí)上,上海國際仲裁中心等仲裁機(jī)構(gòu)已經(jīng)著手推動(dòng)調(diào)解員與仲裁員的分立,(46)《上海國際經(jīng)濟(jì)貿(mào)易仲裁委員會(huì)(上海國際仲裁中心)調(diào)解員名冊》已于2018年5月1日起施行,www.shiac.org/SHIAC/mediators.aspx?flag=1,最后訪問日期:2019年7月27日。法院系統(tǒng)也逐漸在內(nèi)部開始組建專業(yè)的爭議解決平臺(tái),減少法官兼任調(diào)解員的情況。(47)參見《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設(shè)立國際商事法庭若干問題的規(guī)定》(法釋[2018]11號(hào))第11條、第12條。
從調(diào)解員的職業(yè)要求看,調(diào)解員也應(yīng)當(dāng)具有獨(dú)立的職權(quán)和執(zhí)業(yè)要求。有學(xué)者指出,調(diào)解員的職業(yè)化是社會(huì)發(fā)展的必然趨勢,調(diào)解員應(yīng)當(dāng)具備專業(yè)的工作技能與調(diào)解素養(yǎng)、統(tǒng)一的職業(yè)行為規(guī)范、系統(tǒng)的職業(yè)教育和培訓(xùn)和穩(wěn)定的職業(yè)群體。(48)參見廖永安、劉青:“論我國調(diào)解職業(yè)化發(fā)展的困境與出路”,載《湘潭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6年第6期,第48頁。近年來國內(nèi)各調(diào)解機(jī)構(gòu)亦重視專業(yè)調(diào)解員職業(yè)技能的培養(yǎng),中國國際商會(huì)調(diào)解中心(49)參見王芳:“中國國際貿(mào)易促進(jìn)委員會(huì):商事調(diào)解是高效解決涉外商事糾紛的鑰匙”,載《中國社會(huì)組織》2019年第8期,第28~29頁。和上海經(jīng)貿(mào)商事調(diào)解中心(50)參見張巍:“商事調(diào)解領(lǐng)域不一樣的‘老娘舅’——記上海經(jīng)貿(mào)商事調(diào)解中心的創(chuàng)新與創(chuàng)意”,載《中國社會(huì)組織》2015年第3期,第39頁。皆積極開展職業(yè)技能培訓(xùn),并與CEDR、SIMC等著名國際調(diào)解組織展開合作,以期培養(yǎng)能勝任獨(dú)立行使調(diào)解職權(quán)的調(diào)解人才。調(diào)解機(jī)構(gòu)對專業(yè)調(diào)解員的“求賢若渴”也反映出商事調(diào)解立法的長期缺位使我國專業(yè)調(diào)解人才的數(shù)量遠(yuǎn)落后于調(diào)解的現(xiàn)實(shí)需求,調(diào)解機(jī)構(gòu)通過與國外機(jī)構(gòu)開展聯(lián)合調(diào)解補(bǔ)強(qiáng)跨境爭議解決能力,(51)參見王芳:“建設(shè)具有獨(dú)特優(yōu)勢的商會(huì)調(diào)解機(jī)制”,載《人民法院報(bào)》2017年9月1日。一些外商貿(mào)易頻繁而缺乏專業(yè)調(diào)解機(jī)構(gòu)、調(diào)解人才的地區(qū)如浙江義烏則采取聘請外商作為調(diào)解員、“以外調(diào)外”等方式滿足調(diào)解需求。(52)參見吳卡、張洛萌:“涉外商事糾紛調(diào)解新模式探尋——以義烏市涉外糾紛人民調(diào)解委員會(huì)為例”,載《浙江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7年第2期,第62~63頁。
調(diào)解員和調(diào)解機(jī)構(gòu)作為調(diào)解中不可或缺的一方,在將來的統(tǒng)一商事調(diào)解立法中應(yīng)有專門的地位。具體而言,筆者認(rèn)為應(yīng)當(dāng)著重關(guān)注三點(diǎn):首先,明確調(diào)解員或調(diào)解機(jī)構(gòu)的賦權(quán)問題。將來的立法中,首要解決的問題應(yīng)當(dāng)是調(diào)解員或調(diào)解機(jī)構(gòu)職權(quán)薄弱、獨(dú)立性不足的問題。職權(quán)獨(dú)立性的核心是調(diào)解員或調(diào)解機(jī)構(gòu)的證明力,配套制度為調(diào)解員名冊制度或員額制度,即“具有正式調(diào)解員身份者簽署的調(diào)解協(xié)議可依照《公約》獲得獨(dú)立的執(zhí)行力”;其次,規(guī)定法律服務(wù)滿一定年限者方具備授予調(diào)解員身份的資格。豐富的實(shí)踐經(jīng)驗(yàn)是調(diào)解成功的決定性因素,這是調(diào)解員獨(dú)特的執(zhí)業(yè)需求決定的;最后,妥善處理法律規(guī)定和行業(yè)準(zhǔn)則對調(diào)解員行為的規(guī)制程度,法律的強(qiáng)制性規(guī)定應(yīng)當(dāng)主要關(guān)注調(diào)解員是否在調(diào)解過程中存在故意舞弊行為或故意不履行信息披露義務(wù)的行為,具體的行為要求可留待調(diào)解員行業(yè)準(zhǔn)則加以規(guī)定,以免對調(diào)解員施加過多不合理的限制阻礙調(diào)解效率。
(三) 調(diào)解事項(xiàng)民商不分
調(diào)解的靈活性使其幾乎得以運(yùn)用于所有行業(yè)的爭議解決,但在調(diào)解事項(xiàng)方面,我國僅專門規(guī)定了人民調(diào)解委員會(huì)調(diào)解協(xié)議的效力,卻并未明確規(guī)定諸如中國國際貿(mào)易促進(jìn)委員會(huì)調(diào)解中心、行業(yè)協(xié)會(huì)調(diào)解機(jī)構(gòu)等專業(yè)商事調(diào)解機(jī)構(gòu)產(chǎn)生的調(diào)解協(xié)議的效力,而后者才是解決國際商事爭議的主要機(jī)構(gòu)。此外,人民調(diào)解委員會(huì)是“依法設(shè)立的調(diào)解民間糾紛的群眾性組織”,(53)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調(diào)解法》第7條。附屬于村民委員會(huì)、居民委員會(huì)、企業(yè)事業(yè)組織等,其解決的多是民事性糾紛甚至是不具有法律意義的日常糾紛,而國際商事調(diào)解的專業(yè)性、復(fù)雜性決定其形成的和解協(xié)議難以直接按照《人民調(diào)解法》的規(guī)定認(rèn)定執(zhí)行效力。
從調(diào)解發(fā)展的現(xiàn)狀看,在調(diào)解領(lǐng)域堅(jiān)持“民商合一”是難以為繼的,商事調(diào)解的爭議層級(jí)、專業(yè)程度、復(fù)雜程度、覆蓋行業(yè)的廣度和深度遠(yuǎn)高于一般的民事調(diào)解。北京法院發(fā)布的2018年度多元調(diào)解典型案例中即提及通過行業(yè)調(diào)解妥善處理標(biāo)的額高達(dá)人民幣3.2億、涉及七方當(dāng)事人、最終通過調(diào)解引導(dǎo)當(dāng)事人X基金公司完成對企業(yè)債券發(fā)行人“E機(jī)床”破產(chǎn)重整的債權(quán)申報(bào)工作的案例。(54)參見王元義:“北京法院發(fā)布2018年度多元調(diào)解十大典型案例”,http://bjgy.chinacourt.gov.cn/article/detail/2018/11/id/3564051.shtml,最后訪問時(shí)間:2019年7月25日。可見現(xiàn)代商事糾紛的專業(yè)性、復(fù)雜性并不是傳統(tǒng)的人民調(diào)解委員會(huì)或消費(fèi)者協(xié)會(huì)所能承擔(dān)的,(55)參見龍驍:“我國金融中心金融調(diào)解機(jī)制的困境與對策”,載《財(cái)經(jīng)科學(xué)》2015年第6期,第46頁。而目前我國商事仲裁機(jī)構(gòu)達(dá)到250多家,現(xiàn)有行業(yè)協(xié)會(huì)、商會(huì)近7萬家,建筑工程、物業(yè)、保險(xiǎn)、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證券期貨、電子商務(wù)等各類行業(yè)協(xié)會(huì)也紛紛建立各自的糾紛解決中心,(56)參見龍飛:“‘多元化糾紛解決機(jī)制’正鋪開宏偉畫卷”,載《人民法院報(bào)》2017年10月17日。例如2013年9月開始運(yùn)作的深圳證券期貨業(yè)糾紛調(diào)解中心即是中國證監(jiān)會(huì)深圳監(jiān)管局和深圳國際仲裁院共同推動(dòng)設(shè)立的緊密結(jié)合仲裁、調(diào)解、行業(yè)自律和行政監(jiān)管的爭議解決機(jī)構(gòu)。(57)參見劉曉春:“中國商事調(diào)解的最新發(fā)展——以深圳國際仲裁院的創(chuàng)新為視角”,載《中國法律》2014年第4期,第39~40頁。如此規(guī)模的專業(yè)商事調(diào)解機(jī)構(gòu)在立法上無獨(dú)立地位,既與調(diào)解的發(fā)展現(xiàn)狀不匹配,也不利于商事爭議的解決。
在將來的立法中,商事調(diào)解必然將從民事調(diào)解中獨(dú)立出來。調(diào)解領(lǐng)域的“民商分立”,首要問題是識(shí)別爭議的“商事性”,CISG、《公約》和《示范法》等現(xiàn)有的法律規(guī)范已經(jīng)為“商事性”的認(rèn)定提供了較為成熟的標(biāo)準(zhǔn);其次,在執(zhí)行渠道上實(shí)現(xiàn)“民商分流”,民事調(diào)解協(xié)議按照現(xiàn)行的申請司法確認(rèn)等方法獲得執(zhí)行力,商事和解協(xié)議既可按《公約》直接申請執(zhí)行,也可按現(xiàn)有規(guī)定申請司法確認(rèn);最后,明確商事和解協(xié)議的救濟(jì)途徑,彌補(bǔ)一些《公約》的立法空白,例如按《民事訴訟法》的規(guī)定認(rèn)定虛假調(diào)解形成的和解協(xié)議無效。
結(jié) 語
調(diào)解是國際商事爭議的重要解決方式。高效性、靈活性、保密性、自愿性是調(diào)解作為爭議解決方式的獨(dú)特價(jià)值。保障調(diào)解形成的和解協(xié)議的執(zhí)行效力是發(fā)揮調(diào)解的獨(dú)特價(jià)值和爭議解決作用的根本。
執(zhí)行和解協(xié)議首先應(yīng)當(dāng)確認(rèn)和解協(xié)議具有國際性、體現(xiàn)商事性,并能證明其系產(chǎn)生于獨(dú)立的調(diào)解程序。《公約》視角下的和解協(xié)議有較為特殊執(zhí)行抗辯事由——不能證明和解協(xié)議產(chǎn)生于調(diào)解、不是終局性的和解協(xié)議、調(diào)解員未按調(diào)解規(guī)則行事或未盡信息披露義務(wù)以致誤導(dǎo)當(dāng)事人達(dá)成和解協(xié)議的,不得執(zhí)行基此產(chǎn)生的和解協(xié)議。
我國的統(tǒng)一商事調(diào)解立法與調(diào)解的發(fā)展相比具有極大的滯后性,《公約》的生效或?qū)⒋偈刮覈⒎ㄗ鞒龈淖円糟暯印豆s》的規(guī)范。在制訂統(tǒng)一的《商事調(diào)解法》的過程中,應(yīng)當(dāng)首先考慮賦予調(diào)解員或調(diào)解機(jī)構(gòu)以簽字證明權(quán)為核心的獨(dú)立職權(quán);其次應(yīng)當(dāng)區(qū)分民事調(diào)解和商事調(diào)解,提高爭議解決效率,使專業(yè)化的商事調(diào)解和《公約》更好地服務(wù)于我國建設(shè)“一帶一路”的進(jìn)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