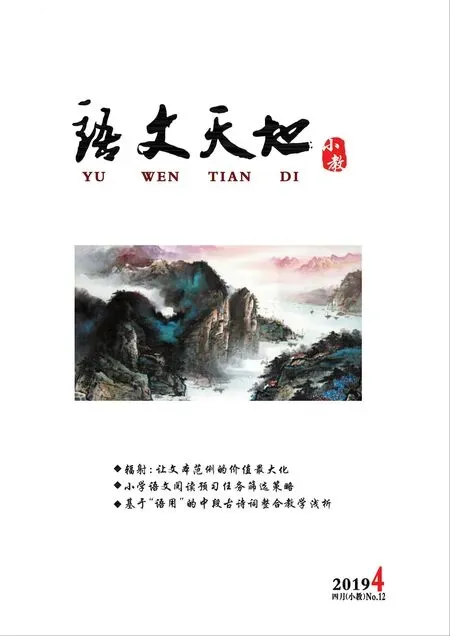作品意識:古詩文教學的應有視角
在古詩教學中樹立鮮活的作品意識,就是指在語文學習的過程中既要將古詩看成是文學作品被動的接受,同時也需要將古詩學習過程中的誦讀、解釋、體悟等環節視為自己主動完成的作品。借助這一過程,學生就需要將自身全部的精力、情感和創造融入到故事對象之中,激活他們學習古詩的主觀意識。
一、深情誦讀,創生自我的有聲作品
語文教育專家葉圣陶先生指出:吟誦是學習語文的重要方法,但不能是負擔,而應該成為一種享受,在一遍遍地誦讀中自然達成純熟的境界。葉老所說的“享受”,就是指要讓學生把誦讀看成是將文字性的古詩轉化為自己有聲的誦讀作品。只有形成了這種作品意識,學生才能緊扣古詩作品中內在的依據,將自己的情感、經歷全部融入到古詩之中,形成自己獨特的所思所感,經歷了與自身體驗碰撞交融之后,形成欲罷不能的情感沖動,才能真正體現出鮮明的作品意識。
就以張繼《楓橋夜泊》這首詩的教學為例,依照傳統教學理念就是讓學生在各種形式的朗讀中將古詩讀正確、讀熟練,但讀來讀去,還是讀的他人作品。如何才能讓學生在誦讀中樹立作品意識呢?筆者在教學中先講述了張繼趕考落榜的創作背景,然后相機進行語言的渲染與引導:失落、孤寂纏繞著張繼。靜夜,寒山寺的鐘聲傳來,劃破長空,擊中了身在異鄉的旅客愁緒,你們是否有過這樣的體驗,自由帶著這種體驗誦讀這首詩。此時的張繼除了對家鄉和親人的思念,更多的是落榜的愁緒,這鐘聲有著一種獨特的力量。結合自己的體驗再讀讀這首詩,此時,孩子們立刻有了自己的體悟:“鐘聲”重讀,寂靜的夜晚這聲音就像敲在我們的心門上;“客船”在水中搖晃,我們可以讀得低沉而輕緩,使得“鐘聲”綿延而不絕……
經歷了這樣的引導和點撥,學生自主進行誦讀,不僅感受到詩歌中所蘊含的獨特情韻,同時也融合了自己的情感體驗,從而將原本的古詩轉化成為自己的有聲作品。
二、思維辨析,創生豐厚的解讀作品
學生理解古詩常見的思維習慣就是將古詩看成一個普通的文本,古詩中寫了什么、展現了詩人怎樣的情感?誠然,這種思維模式之下,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古詩,但僅僅是憑借古詩的語言展開的。正所謂“詞傳情,詩言志”,每首古詩背后都蘊藏著濃郁的詩人情懷,如果不能站立在詩人視角,古詩的作品意識就難以真正形成。
如教學張志和《漁歌子》時,為了讓學生圍繞著詩歌中“漁翁”的形象揣摩詩人所表達的志向和情懷,教師就采用了拓展對比的方式展開教學,引導學生結合已經學習過的《江雪》和汪士禛的《題秋江獨釣圖》,對這三首詩中的“漁翁”形象進行比較辨析。學生發現《題秋江獨釣圖》中的漁翁且歌且飲,獨自欣賞秋天的美景,雖然孤寂,但卻有著一份逍遙;《江雪》中的漁翁在嚴寒的冬天,其實在用行動表達自己的不滿和抗爭,更借助于“漁翁”的形象展現了自己傲岸清高、無畏凜然的高貴品質;而這首《漁歌子》中漁翁則是縱情于山水,因為景色之美、鱖魚之肥已經不肯離去,就愿意在這“斜風細雨”之下垂釣,享受悠閑而自在的鄉村生活。
經歷了這樣的對比辨析,學生不僅發現這首詩中漁翁形象的不同,更將他們的認知深入到詩人的創作背景以及意欲表達的情懷中,強化古詩中的詩人情懷,對古詩進行了深入的洞察和解剖,學生的思維能力和語言素養都得到了較好地提升。
三、融通釋義,創生兒童意蘊的作品
由于古詩語言的凝練和表達習慣的差異,學生理解古詩有著一定的難度。為此,很多教師將古詩的理解作為教學的一個核心點。誠然,理解了古詩我們才能朝著古詩的深處進一步漫溯,但遺憾的是很多古詩理解顯得過于生硬而機械,無視學生的本體性認知。因此,我們就應該通過巧妙地融通,架構古今的鴻溝,讓學生在感知與理解的過程中創生出屬于兒童的意蘊性作品。
就以葉紹翁的《游園不值》這首詩的教學為例,對于后面的千古名句處理起來就具有一定的難度:如果不做拓展,僅僅從字面上解釋,這首詩的價值就會大打折扣;但如果要觸及其深入的一面,沒有好的方法引領勢必影響其效果。為此,教師就引導學生轉化視角,如果你就是那一株出墻來的紅杏,你從春色盎然的園子中來,又看到了在門口而不得入內的詩人,你會怎樣向詩人介紹園內的景色呢?此時,學生就通過視角轉變,一方面通過想象展現了園內的盎然春色;一方面在思考視角的置換中走進了詩歌的內核。為此,學生在解釋這句話時,就不再是機械的文字翻譯,而是融入了自身的認知形態,使得整首詩的解釋更加鮮活而靈動。
詩歌內蘊的感知與解釋,不是刻板而機械地文字直譯,教師可以通過角色置換的方式,基于文本的獨特視角,讓學生從一個鮮活的角度進行翻譯,不僅尊重并保存了作者的影子,更讓學生有了傾吐和表達自我的聲音,形成了對古詩的二度創造。
古詩教學呈現的是一個機械的文本,但語文教學的價值就是要讓學生在自己的誦讀、辨析和理解過程中,逐步轉化為形態多樣化的作品,不僅讓學生以客觀視角關照古詩,更結合詩人、兒童的視角來解構詩篇,可謂一舉兩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