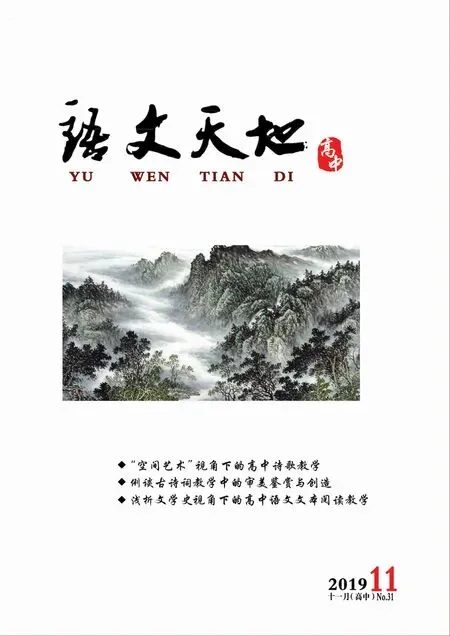“空間藝術”視角下的高中詩歌教學
沈括在《夢溪筆談》中談到自己的藝術主張——“以大觀小”,即畫山水并不能站在一個固定的點“仰畫飛檐”,而應運用心靈的眼,從全景觀部分。所謂全景,“天地際也”,要有氣韻、節奏。這不僅是畫作的構圖原理,更是詩歌的構圖原理。詩人也用心靈之眼觀宇宙萬象,并從對全景的了解來組織可入詩的景物,使之有節奏,有氣韻,表現詩人的宇宙感。可以說,詩人在詩中無不表現一種空間的意識,教師可以圍繞這一點進行高中詩歌教學,讓學生從詩人空間藝術的表現入手,解其心境。
一、解讀全景對詩人情感的勾勒
藝術是沒有界限的,尤其是對于詩和畫這兩種藝術而言,幾乎可以用一種構圖原理去創作,就是“以大觀小”的方法,從全景出發,使眼睛“流動飄瞥上下四方”,“把握全景開闔”。可以說,許多中國詩人無不采用此原理投入創作,借著全景的布局來表現自己的心境,是孤寂,是蒼茫,是慷慨,是激越,通過游目詩篇的整個景象,便見端倪。這一點,為教師的詩歌教學提供了靈感,教師可圍繞對詩歌全景的解讀,引導學生賞析詩人的心境情感。
以杜甫的《登高》為例,詩人游目騁懷從全景出發去構篇,上至天空盤旋的白鳥,下至水中的小島、沙灘,遠及滾滾的長江、無邊無際的落木,近到獨登臺、繁霜鬢的自己,整個天地運行于筆下,恢弘萬千,宗炳的話——“身所盤桓,目所綢繆,以形寫形,以色貌色”——說的便是此理。可以說,一首詩是否成功,便是看詩人對全景的掌控和表現出的宇宙感。當然,宇宙感并不是詩中好看的擺設,它對詩人的情感表現發揮著重大作用。所以,教師可引導學生圍繞對詩歌全景的解讀,賞析詩人的心境。在這里,教師可以讓學生在閱讀詩文后,用自己的語言描繪詩的全景,感受詩人的心境,也可以讓學生勾勒出這幅景色,感受詩人對空間藝術的表現。
二、解讀部分景物對詩人情感的表現
沈括說:“大都山水之法,蓋以大觀小。”對于詩文創作也是如此。而所謂大,便是大的眼界,即杜甫所說的“乾坤萬里眼,時序百年心”,是詩人、畫家所尊崇的“全局觀”。而小,是指從全景出發,對各個部分的決定和組織。比如畫一條龍,畫家首先勾勒出這條龍的輪廓,表現出龍的動作氣勢,這便是對整體的呈現,但這還不夠,還要從動作和氣勢切入來組織龍的眼、爪、須、麟,只有實現整體到局部的統一,龍的形象才會活靈活現。詩歌也是如此,全景的確定只是為了給詩歌情感提供大的方向,而真正細化這種情感的則是全景的各個局部。因此,教師在引導學生解讀詩人對全景的勾勒之后,還要以大觀小,解讀詩人對各個部分景物的描繪,從中賞析詩人的情感。
還以杜甫的《登高》為例,作者為了抒發自己晚年遲暮孤寂多病的哀愁,確定了整首詩的全景,風、天、猿、水中的陸地、沙灘、鳥、落木、長江,所有能體現秋天特質的景物構思在一幅畫面中,并足夠將詩人吸入這一空間中,與詩人心境呼應。但全景只能起到奠定感情基調的作用,還不能將詩人的情感細膩化,所以,教師還要引導學生從全景的解讀過渡到對各個部分景物的解讀上。例如,教師可讓學生思考:“我們賞析完詩中的全景,確定詩人描繪了一幅蕭瑟的秋景,那么為了突出蕭瑟的感覺,與自己的內心世界相呼應,詩人是怎樣描繪局部的景物的?”學生紛紛依據首聯、頷聯做出回答。如有學生說:“詩人分別用急、高、哀,來描繪風、天、猿嘯,肅殺之氣一覽無余。”
三、解讀詩人位置對詩人情感的凸顯
詩歌強調有“我”之境和無“我”之境,這個“我”多數情況是指詩人自己。也就是說,詩人在構境的時候,會將自己也作為一個意象,時時刻刻表現自己的在場,而有時候則將自己的蹤跡隱藏起來,萬物自在自說。但無論哪種,通過解讀,我們都可見詩人在詩中出入。簡而言之,詩中永遠留有詩人的位置,而且,其位置的安排,也表現出詩人的宇宙感,也是詩人創作時空間藝術的表現,不僅如此,詩人的位置還表現出詩人的情感。所以,教師可引導學生通過對詩人位置的解讀感悟詩人的情感。
以毛澤東的《沁園春·長沙》為例,“獨立”“看”“問”“攜”“憶”“揮斥”“指點”“激揚”“到”等動詞,皆說明詩人的在場。那么詩人處在哪個位置呢?教師可引導學生結合創作背景和詩詞中的字句進行分析,并將詩人的位置畫出來,分析詩人處在這個位置的心情是怎樣的?學生通過分析,了解詩人能看到北去的湘江、橘子洲、紅遍的萬山、爭流的百舸,說明是站在高處。有學生又聯想到王安石的“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緣身在最高層”,登高望遠,視野開闊,大好河山盡收眼底,革命的前景一片光芒,沒有東西可以阻礙和蒙蔽理想。還有學生從空間的層面分析詩人的位置,詩人站在高處,俯仰無礙,一切都盡收眼底,一切都掌控眼底,更能凸顯詩人的胸懷志向。
無論畫作還是詩作,空間的構思最主要。所以有人用看畫的方式去讀詩,希望通過對全景的解讀感受詩人的心境;通過對局部景物的解讀感受詩人細膩的情感;通過對詩人位置的解讀,感受詩人的志向。這對教師的詩歌教學而言無疑是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