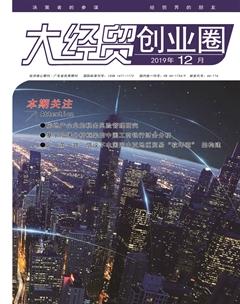英美兩國在電信領域的“提速降費”政策過程及啟示
【摘 要】 隨著我國經濟發展,從2015年李克強總理提出電信行業提速降費要求,到現在的2020年,提速降費已經進入到全面實施的第六個年頭。而以英美兩國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在電信領域的資費調整已經持續了相當長的時間并且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他們的經驗和教訓為我國相關政策措施的制定和調整提供了可參考的意義。本文采取公共政策過程理論的視角,去探究兩國在“提速降費”問題上所采取的措施以及取得的成效,進而對我國的相關政策推進提出合理性意見和建議。
【關鍵詞】 電信領域 英美兩國 提速降費 政策過程
提速降費是近幾年老百姓非常關心的一個話題,涉及到國民的根本利益,也是人民群眾茶余飯后的熱點話題,從國務院最開始提出,到工信部的調研確立,再到三大運營商的具體落實,已經進行了五六年的相關探索,人民群眾也得到了切身利益。但是,政策實施過程中,仍有很多質疑的聲音出現,那么以英美兩國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是如何進行相關探索的,他們取得的成效如何,對我國相關政策的推進有何借鑒意見,將是本文著重討論的。
一.英國在電信資費領域的探索
英國電信是歐洲領先的電信業務提供商之一,原來是一家全業務電信運營商,于2001年降低負債并優化了財務結構,剝離了移動通信部門。后因為固話收入下滑,2003年重返移動市場。他們的資費在很長時間保持了相對較低的水平,一個最主要原因是能夠破除壟斷,保證充分的市場競爭。2005年,英國在進行市場評估后,要求電信拆分其接入網設施,組建獨立子公司Open reach,確保網絡運營與業務運營分開,并以公開方式向母公司BT(British Telecom,簡稱 BT)等提供接入網的租賃服務。
英國是世界上第一個開放電信業市場準入、實施私有化的國家,在過去對電信業的規制中有著成功的經驗。英國電信改革的主旨在于達到雙重目的,一是要提高主要運營商的積極性和高效率,二是鼓勵企業之間的競爭。基于這兩個主要的目的,英國政府對電信業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對不同相關主體也進行了相應的調整,確立了以客戶為核心的理念,冰冰綜合信息服務提供商轉型發展。在實現制度目標上積極完善法律和規制制度體系,以實行激勵性價格規制來逐步引入競爭并促使主導運營商有更多的靈活度來改善經營效率。
英國電信在1984年之后經歷了由國有企業轉向私有化的過程,并且直到1998年,英國電信公司BT仍然在本地電話業務中占據市場主導地位。當時政府采取在一定時期內建立雙寡頭壟斷結構的電信市場,幫助后來者 Mercury 公司增加市場份額。1991 年,隨著英國政府發布《競爭與選擇:20 世紀 90 年代的電信政策》打破了雙寡頭壟斷結構,新進入者逐漸被允許進入市場,直到本世紀初,英國在短短十年左右就擁有超過 200 家電信運營商,形成了完全競爭的市場氛圍。
英國電信改革中最重要的措施就是實施了激勵性的價格規制手段。在 BT 私有化最初幾年,BT 在各項業務中依然占據市場主導地位,公司壟斷經營就要求政府防止企業濫用市場權力。最終用最高限價法進行規制,即 RPI-X 模型,按照零售價格指數和一定時期內企業的生產效率增長率進行比較,當企業的實際生產率高于規定的增長率時,企業就可以獲得因降低成本而帶來的利潤。之后在 1984年電信法案中引入價格上限的規制方式,并且根據不同業務的競爭程度實施保護上限規制,還有放松價格規制。
英國電信市場完全開放、引入競爭已經二十多年,目前英國電信資費基本上是西方國家中最低的,且寬帶速度已經是十年前的 10 倍。可見,英國的經驗總結下來,是在國內市場中有序地引入競爭,以更多地引入外資和合作伙伴為目標,適時逐步放松規制,一方面開放市場,另一方面通過有效監管維護市場競爭的公平性。
二.美國在電信資費領域的探索
美國是全球電信業起步最早的國家,是目前電信市場化程度最高、產業體系最發達、市場監管制度最完善的國家。美國在電信產業規制改革的過程中,電信資費是最早開始實現規制改革的領域之一,其發展路徑與英國的規制路徑不盡相同。美國電信企業從一開始就具有私有性質,是在尋求私人競爭市場的格局下,通過對企業行為的合法化規制來促進消費者福利最大化的。
美國的電信規制改革首先對主導運營商 AT&T 進行拆分,引入競爭,之后采取放松管制的方式促進。以美國長途電信業務為例,美國管理機構在 1981 年將AT&T 定為主導運營商,實行資本回報率管制,因為它控制了全美的電話線和幾乎全部的長途電話業務。1984 年 AT&T 的本地電話被分拆出去成為七家地方運營公司,AT&T 只在競爭性的長話市場占有控制地位,聯邦監管條例進行了相應調整并逐漸放松對 AT&T 的管制。其后,長話市場的競爭性不斷增強,1989 年聯邦通信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簡稱 FCC)停止對 AT&T的回報率價格管制,開始采用最高限價管制。1991 年,又取消了以最高限價法對競爭較為激勵業務的管制,而只需備案。1995 年,FCC 把 AT&T 劃為非主導國內電信運營商。
美國電信業發展的兩個里程碑是 1934 年和 1996 年的《電信改革法案》構建了其國內電信市場的管制框架和競爭體制,極大促進了電信市場的發展。1996年的《電信法》中規定互聯互通要按照前瞻性長期增量成本定價,進入了全面競爭時代。FCC 開始允許地區性本地電話運營商進入長話市場,長途電話公司和本地運營商之前經營業務互不相通的情況被打破。這一舉措使長途電話和移動電話等領域競爭加劇,促使電信市場競爭格局發生變化,規制機構對電信資費采取開放性規制手段,允許各運營商進行備案制自行制定資費。然而,由于這一時期出現了大批新進入者,競爭壓力日趨增大,而規制機構幾乎沒有采取相應的措施,使得市場供過于求,惡性競爭加劇,導致其國內電信業因過度競爭陷入了混亂之中。于是,2006 年美國電信法規做出了重大調整,對傳統電信公司進行整合,保留競爭空間,FCC 通過了 AT&T 收購南方貝爾公司的提案,重新形成寡頭競爭的局面,避免單個公司在與新進入者進行競爭時,造成盈利困難,重蹈過度競爭的惡果。
如今,FCC 對電信資費實行不規制,依然由運營商在不損害消費者權益和公共服務目標的情況下自行制定標準。在電信規制制度改革的歷程中,美國與英國最大的不同點在引入競爭的方式上,是逐步將主導運營商 AT&T 進行分解來增加競爭者。1984 年 AT&T 將原下屬的 22 個貝爾業務運營公司重組成 7 個地區運營公司,由這 7 個公司向其他長途運營商提供本地接入服務。
2015 年1 月,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經過投票,將2010 年設定的下載/ 上傳速度為4Mbps/1 Mbps 的寬帶基準提高到25 Mbps/3Mbps。在美國市場,寬帶價格近兩年也呈現下降態勢,但這更多依靠市場手段,也就是競爭帶來的價格下降。
三.英美兩國的電信產業資費改革對我們的啟示
(一)健全的法律法規體系。健全的法律法規體系是電信資費規制效果實現的根本。不難看出,上述兩國經驗中均提到《電信法》對各國電信規制的具體作用。相比較下,我國目前沒有《電信法》,只有《電信條例》這一綜合性法規作為電信資費規制的法律基礎,且自 2000 年第一次頒布之后僅經歷過 1 次修訂,缺乏系統的法律基礎支撐。另外,《價格法》對電信資費的管理描述只涉及基本管理原則,不夠具體,缺乏專業性的監督程度和標準來指導電信資費規制和企業行為。因此《電信法》亟待出臺,通過專業的法律來理清電信監管部門和電信企業之間的關系,特別是在電信價格管理權限逐步放開的今天,專業法律對規范電信市場的資費行為、促進市場的公平競爭、增進社會福利顯得尤其重要。
(二)構建有效監管體系。目前我國電信業劃歸于工業和信息化部(簡稱工信部)進行管理,其中信息通信發展司和各地市的通信管理局的監管職能與企業運營存在互相影響,作為電信監管部門其監管角色定位不明確,兼顧多重規制目標,無法有針對性地進行系統監督與管理。特別是我國目前的電信運營商均為國有企業,而電信監管部門既是規制政策的制定者,又是政策的執行者,在政策執行中難以避免的帶有行政干預的色彩。因此,監督機構需要從政府部門中剝離出來,確保其獨立性,既不受政府部門的行為影響,又不受電信運營商的尋租影響,客觀地從專業角度監督電信資費市場行為和動向。
(三)實施電信資費規制。逐步推進放松規制,根據電信業發展的不同階段因時制宜地實施資費規制政策。目前我國已經實現將定價權還給市場,企業自主定價,但是由于目前還未成熟,僅放開了部分基礎電信業務,政府的規制重心應當轉移到對企業經營行為的規范上來,這樣有利于形成有效的競爭市場。
(四)以消費者利益為導向。規制的最終目的是在促進社會生產效率的同時提升社會福利水平,增進公眾利益。目前我國電信資費規制政策的調整中還沒有將消費者納入監管體系中,消費者的議價能力和對資費水平的影響能力水平不是很高,在電信價格規制中沒有更好的發揮監督作用,特別是在放松規制的進程中,保護消費者利益是實現市場競爭的一個重要導向。因此,接下來電信資費規制與放松規制舉措中可以采取重視消費者信息、增進了解消費者在電信資費調整的訴求等舉措,進一步推進電信市場化。
四.結語
綜合國內外研究情況,提速降費作為電信運營商提供普遍服務的重要手段,維系著國家經濟發展、實現社會平等公平,受到包括歐美等經濟發達國家的重視。直接關對正處于經濟轉型發展,建設全面小康社會關鍵時刻的中國來說更具有里程碑一樣的重要意義。
【參考文獻】
[1] 王海燕.英國電信全業務資費策略案例研究[R].工業和信息部電信研究院.2009.
[2] 牛銳. 我國電信資費規制政策效果評價研究[D].上海交通大學,2018.
[3] 馮劍. 電信行業提速降費政策執行效果與對策研究[D].山西師范大學,2017.
作者簡介:胡亞楠(1990—),性別女,籍貫安徽宿州,民族漢,工程師,本科,中國人民大學,研究方向:公共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