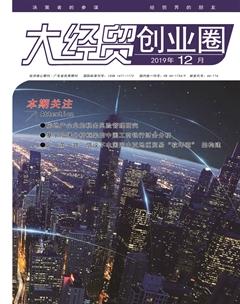死者人格權(quán)益的法律保護(hù)研究
【摘 要】 從死者人格權(quán)益的基本理論出發(fā),介紹死者人格權(quán)益的概念內(nèi)涵以及法律對(duì)其保護(hù)的發(fā)展過程。分析了現(xiàn)行法律規(guī)定的死者人格權(quán)益的具體內(nèi)容,對(duì)比分析一般死者人格權(quán)益和英雄烈士等人格權(quán)益的相同之處以及區(qū)別,并提出對(duì)英雄烈士給予特殊保護(hù)是否違反公平原則這一問題。對(duì)于民法典有關(guān)死者人格權(quán)益的內(nèi)容進(jìn)行對(duì)比分析,提出了完善保護(hù)死者人格權(quán)益制度的建議。
【關(guān)鍵詞】 人格權(quán) 人格權(quán)益 一般死者人格權(quán)益 英烈人格權(quán)益
一、死者人格權(quán)益法律保護(hù)存在的問題
(一)人格權(quán)益的概念厘定
人格是人生而為人理所應(yīng)當(dāng)具有的一個(gè)內(nèi)容,人格并非法律專有概念,而是人類社會(huì)發(fā)展初始就已經(jīng)存在的固有概念,它極具倫理價(jià)值性,是一個(gè)動(dòng)態(tài)的概念。[1]通俗來說,人格就是一切普通人類能夠成為人所必備的多方面要素內(nèi)容的集合,它并不像有些法律專有名詞一樣是伴隨著法律的發(fā)展才出現(xiàn)的,具有天然性和固有性的特征。
與人格這一非法律專屬用語不同,人格權(quán)是伴隨著法律制度逐漸進(jìn)步發(fā)展才出現(xiàn)的一個(gè)用語,是一個(gè)民事主體所應(yīng)當(dāng)具備的一種權(quán)利。人格權(quán)是體現(xiàn)一個(gè)民事主體所具有的獨(dú)立的法律人格的支配性權(quán)利,具有專屬性和固有性。[2]
人格利益主要包括以下內(nèi)容:生命、身體、健康、姓名、名稱、名譽(yù)、榮譽(yù)、肖像、隱私等。人格利益的客體不同于財(cái)產(chǎn)利益,后者通常以實(shí)物、貨幣等具有有形性特點(diǎn)的內(nèi)容為客體,人格利益通常以名譽(yù)、肖像、隱私等內(nèi)容為保護(hù)對(duì)象,具有精神上的利益和價(jià)值。自然人的民事權(quán)利始于出生終于死亡,當(dāng)人死亡后就不再享有人格權(quán),然而人格權(quán)益并不一定因?yàn)樽匀蝗怂劳龆麥纭M谧匀蝗怂劳龊蟮囊欢螘r(shí)間或者很長(zhǎng)時(shí)間里,仍然具有人格權(quán)益,法律仍然應(yīng)當(dāng)給予保護(hù),這是保護(hù)人格權(quán)延續(xù)下來的人格利益所必須要做到的。即自然人死亡后,死者的人格權(quán)益作為自然人人格權(quán)的延續(xù),仍然受到法律保護(hù)。[3]
(二)死者人格權(quán)益的法律發(fā)展過程
過去我國法律并不承認(rèn)死者的人格權(quán)益保護(hù)的問題,法律上對(duì)于這一權(quán)益并沒有給予其應(yīng)有的保護(hù)。打破這一局面是歷史性案件是“荷花女”案件,該案是中國死者名譽(yù)權(quán)保護(hù)的“第一案”,此后法學(xué)界開始重視死者名譽(yù)權(quán)保護(hù)的問題,進(jìn)一步推動(dòng)了我國以名譽(yù)權(quán)為首的各項(xiàng)人格權(quán)立法研究活動(dòng)。由此可見我國對(duì)死者人格權(quán)益的法律保護(hù)的發(fā)展最先起源于對(duì)死者名譽(yù)權(quán)的保護(hù),此后在保護(hù)死者人格權(quán)益的發(fā)展道路上還出現(xiàn)許多案例,這些典型案件極大推動(dòng)了我國司法實(shí)踐進(jìn)步和死者人格權(quán)益法律制度的發(fā)展。目前來說,死者人格利益應(yīng)當(dāng)?shù)玫椒杀Wo(hù)在學(xué)界實(shí)踐中并無太大分歧,而關(guān)于法律應(yīng)當(dāng)對(duì)何種范圍內(nèi)的死者人格權(quán)益進(jìn)行保護(hù)、法律保護(hù)期限如何作出明確以及通過何種方式對(duì)死者人格權(quán)益實(shí)行最大保護(hù),這些問題仍有待解決。
二、死者人格權(quán)益的具體內(nèi)容
(一)一般死者人格權(quán)益的內(nèi)容
侵害死者人格權(quán)益的行為行為時(shí)有發(fā)生,然而法律沒有對(duì)此作出明確規(guī)定,司法實(shí)踐中處理這類案件沒有統(tǒng)一標(biāo)準(zhǔn),不利于法律適用的同一性和穩(wěn)定性。《民法總則》對(duì)一般人格權(quán)和具體人格權(quán)做出規(guī)定,這些法律規(guī)定是人格權(quán)益在法律上的具體化,也是死者人格權(quán)益的基礎(chǔ)和前提。分析具體的人格權(quán)益,法律明確規(guī)定的人格權(quán)益的性質(zhì)也各有區(qū)別,例如姓名權(quán)、肖像權(quán)這種權(quán)益的客體通常不會(huì)發(fā)生變動(dòng),姓名和肖像一直伴隨一個(gè)自然人的一生,這種利益是固定的權(quán)益。而像名譽(yù)權(quán)、榮譽(yù)權(quán)等權(quán)益有所不同,他們雖然同樣依附于自然人的人身而產(chǎn)生,但是卻不會(huì)一成不變。
死者的人格權(quán)益當(dāng)然地要被保護(hù)。關(guān)于死者的姓名權(quán)益,著作權(quán)法關(guān)于署名權(quán)的規(guī)定是自然人享有姓名權(quán)的具體體現(xiàn)。署名權(quán)具有永久性,因此這一權(quán)益在著作權(quán)人死亡后其仍然享受該權(quán)益,一個(gè)作品的作者的姓名不可能因?yàn)樽髡咚劳龆鴨适Щ蛘甙l(fā)生繼承。這體現(xiàn)了死者人格權(quán)益中的姓名這一權(quán)益,不僅僅是作品的著作權(quán)人的姓名權(quán)在死亡后得以延續(xù)成姓名權(quán)益繼續(xù)被法律保護(hù),普通人死亡后其姓名權(quán)益依然受到法律保護(hù),任何人不得侵犯死者的姓名權(quán)益。
除姓名權(quán)益外,死者的肖像權(quán)益同樣受到法律保護(hù)。法律對(duì)死者的肖像進(jìn)行保護(hù)歸功于一個(gè)重要案件——“魯迅肖像權(quán)”案。最高人民法院對(duì)此案作出答復(fù):公民死亡后其肖像權(quán)仍然受到法律保護(hù)。肖像權(quán)具有部分財(cái)產(chǎn)性質(zhì),自然人肖像的財(cái)產(chǎn)價(jià)值不僅存在于其生存期間,而且在其死亡后仍然具有財(cái)產(chǎn)價(jià)值,因此保護(hù)死者的人格權(quán)益中必然要保護(hù)死者的肖像權(quán)益。肖像利益和姓名利益在性質(zhì)上都屬于靜態(tài)的人格權(quán)益,雖然自然人死亡后其肖像權(quán)不存在,但是一個(gè)自然人的肖像和姓名這種靜態(tài)性要素并不會(huì)因?yàn)樽匀蝗怂劳龆シ傻谋Wo(hù),這種利益仍然有法律保護(hù)的必要性。
死者的名譽(yù)權(quán)益是由于“荷花女案件”發(fā)生,隨后法律對(duì)此最先作出規(guī)定,強(qiáng)調(diào)要保護(hù)死者的名譽(yù)權(quán)益。一個(gè)人的名譽(yù)取決于其自身的行為、人品等方面的內(nèi)容,社會(huì)公眾對(duì)民事主體自身行為、品行道德做出評(píng)價(jià)從而形成屬于自己的名譽(yù),這種評(píng)價(jià)并不會(huì)因?yàn)樽匀蝗怂劳龊缶褪ヒ饬x。對(duì)死者的名譽(yù)作出正當(dāng)或者不合理的評(píng)價(jià)仍然會(huì)影響到死者延伸下來的名譽(yù),甚至這種影響也會(huì)對(duì)死者的近親屬的名譽(yù)造成影響,更嚴(yán)重的會(huì)損害死者近親屬的合法權(quán)益。
因此,一般死者人格權(quán)益的的內(nèi)容包括死者的姓名權(quán)益、肖像權(quán)益、名譽(yù)權(quán)益等不因自然人物理客體而消失的人格權(quán)益。
(二)英雄烈士的人格權(quán)益
《民法總則》增加“英雄烈士條款”,與《精神損害賠償司法解釋》第三條體現(xiàn)對(duì)死者人格權(quán)益的間接保護(hù)不同,該條直接明確地對(duì)英雄烈士的人格權(quán)益作出保護(hù)性規(guī)定。
這一條款實(shí)際上是關(guān)于死者人格權(quán)益的特別規(guī)定,即當(dāng)死者是英雄或者烈士等對(duì)國家社會(huì)有重要貢獻(xiàn)的人物時(shí),法律對(duì)于其人格權(quán)益是如何進(jìn)行保護(hù)的特殊規(guī)則制度。制定這一條款的目的是為了保護(hù)死者的人格權(quán)益以及其近親屬的利益,同時(shí)基于死者是英雄烈士等這些特殊身份,以此來保護(hù)社會(huì)集體的共同利益和國家民族利益。該條明確法律保護(hù)的對(duì)象,包括精神性權(quán)益,如名譽(yù)權(quán)益、榮譽(yù)權(quán)益,也包括財(cái)產(chǎn)性權(quán)益,如肖像權(quán)益、姓名權(quán)益。由于英雄烈士等人的身份、地位的特殊性,他們不僅代表個(gè)人,更代表一個(gè)國家、一個(gè)民族、一個(gè)時(shí)代,因此法律認(rèn)定一個(gè)人的行為是否侵害了英雄烈士等的人格權(quán)益需要綜合社會(huì)公共利益來考量。他們?yōu)閲液腿嗣褡鞒鲐暙I(xiàn)甚至貢獻(xiàn)出自己的生命,基于這些特殊性,立法者對(duì)這些人的死后人格權(quán)益做出了相較于一般死者更為明確的法律保護(hù)規(guī)定。除上述規(guī)定,《英雄烈士保護(hù)法》明確了英雄烈士的人格權(quán)益具體包括哪些內(nèi)容,對(duì)侵害英雄烈士的人格權(quán)益的行為如何進(jìn)行訴訟救濟(jì)作出規(guī)定,創(chuàng)新性地建立了英雄烈士人格權(quán)益保護(hù)的公益訴訟制度。
然而隨著法律對(duì)死者人格權(quán)益的細(xì)化規(guī)定,有些學(xué)者提出疑問,即法律單獨(dú)對(duì)英雄烈士等人的人格權(quán)益作出詳細(xì)的保護(hù)規(guī)定,這種做法是否違反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正當(dāng)性價(jià)值基礎(chǔ)在于何處?筆者認(rèn)為,考慮到英雄烈士人物身份的特殊性,對(duì)其給予特別的保護(hù)存在合理之處,但這并不意味著法律對(duì)于一般死者人格權(quán)益就不予以保護(hù)。[4]相反,法律應(yīng)當(dāng)對(duì)一般死者人格權(quán)益作出更加詳細(xì)且恰當(dāng)?shù)谋Wo(hù)規(guī)定,只有對(duì)一般死者人格權(quán)益加以細(xì)化規(guī)定才能解決普遍死者人格權(quán)益問題。
三、死者人格權(quán)益法律保護(hù)問題
(一)現(xiàn)行法對(duì)死者人格權(quán)益的保護(hù)規(guī)定
盡管對(duì)死者人格權(quán)益應(yīng)當(dāng)給予法律保護(hù)并無太大爭(zhēng)議,但是對(duì)死者人格權(quán)益進(jìn)行保護(hù)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種不同的觀點(diǎn)。
第一種觀點(diǎn)認(rèn)為,保護(hù)死者人格權(quán)益是為了保護(hù)死者近親屬的權(quán)益,[5]認(rèn)為保護(hù)死者人格權(quán)益是為了保護(hù)其近親屬對(duì)死者的追思情感。[6]此種觀點(diǎn)有其合理性,《精神損害賠償司法解釋》第三條體現(xiàn)了法律對(duì)其近親屬權(quán)益的保護(hù)。然而這種觀點(diǎn)并不全面,混淆了死者人格權(quán)益和近親屬利益兩種不同的利益。如果認(rèn)為保護(hù)死者人格權(quán)益僅僅是保護(hù)其近親屬的利益,那么當(dāng)出現(xiàn)如下情況時(shí):例如近親屬與死者的社會(huì)關(guān)系并非十分親密甚至互相仇視,或者死者人格權(quán)益受到損害但不存在任何近親屬時(shí),甚至實(shí)施侵害行為的主體就是死者的近親屬,此時(shí)就不能有效保護(hù)本應(yīng)受到保護(hù)的死者自身的人格權(quán)益。第二種觀點(diǎn)認(rèn)為,法律保護(hù)死者人格權(quán)益的規(guī)定就是為了保護(hù)死者的人格利益這種法益本身。這種學(xué)說揭示了法律保護(hù)的真實(shí)對(duì)象即為死者人格權(quán)益這種利益本身,然而在實(shí)際司法實(shí)踐操作中又會(huì)出現(xiàn)民事主體資格不明的問題,并非每個(gè)人都可以成為維護(hù)某一死者人格權(quán)益的主體,因此如何平衡保護(hù)對(duì)象的范圍與行使權(quán)力的主體仍然是需要探討的問題。
除了以上兩種觀點(diǎn)外,還有一些其他觀點(diǎn),如人身權(quán)延伸保護(hù)說[7],該觀點(diǎn)模糊了生者的權(quán)利與死者的權(quán)益的界限,過于抽象;人身利益繼承說[8],這種觀點(diǎn)把人格利益等同于財(cái)產(chǎn)利益,完全忽略了人身權(quán)益不同于財(cái)產(chǎn)利益的特征,即人身權(quán)益具有“專屬性”這一重要特征。在司法實(shí)踐中,還有觀點(diǎn)法律保護(hù)死者人格權(quán)益的目的是維護(hù)社會(huì)利益和公共利益。[9]
筆者認(rèn)為,上述幾種學(xué)說綜合起來,即認(rèn)可法律保護(hù)死者本身的人格權(quán)益、特殊情況下與死者有特定關(guān)系的近親屬的人格權(quán)益兼保護(hù)社會(huì)公共利益。[10]此種混合說的觀點(diǎn)相較于其他理論更具有合理性和正當(dāng)性,揭示了法律保護(hù)死者人格權(quán)益的本質(zhì)。理論學(xué)說是指導(dǎo)司法實(shí)踐的重要標(biāo)準(zhǔn),對(duì)于死者人格權(quán)益的學(xué)說研究尚不完善,有待學(xué)者進(jìn)一步分析保護(hù)死者人格格權(quán)益的理論基礎(chǔ)問題,對(duì)法律作出恰當(dāng)解釋,從而更好地指導(dǎo)司法實(shí)踐。
(二)民法典人格權(quán)編草案對(duì)死者人格權(quán)益的保護(hù)規(guī)定
《侵權(quán)責(zé)任法》第二條的兜底性規(guī)定解釋應(yīng)當(dāng)為包括死者人格利益的人身權(quán)益。[11]而《精神損害賠償司法解釋》第三條可以解釋為,死者近親屬因侵害死者人格權(quán)益的行為遭受精神痛苦時(shí),有權(quán)請(qǐng)求賠償精神損失,而針對(duì)死者本身的人格權(quán)益被侵犯卻不能主張如消除影響、恢復(fù)名譽(yù)等請(qǐng)求。對(duì)此《民法典人格權(quán)編《草案》(三次審議稿)》(以下簡(jiǎn)稱三審稿)做出了相應(yīng)的改變,標(biāo)志著未來民法典人格權(quán)編的發(fā)展方向。
三審稿第七百七十七條規(guī)定有很強(qiáng)的創(chuàng)新性,其最大的改變?cè)谟谡?qǐng)求權(quán)基礎(chǔ)成立的前提不同。這一規(guī)定擴(kuò)大了死者人格權(quán)益的保護(hù)范圍,不局限于在精神受到損害時(shí)才能主張損害賠償,只要死者的人格權(quán)益遭受損害,即可要求行為人承擔(dān)相應(yīng)的民事責(zé)任,更有利于保護(hù)死者的人格權(quán)益。第七百七十八條對(duì)請(qǐng)求行為人承擔(dān)哪些民事責(zé)任不受訴訟時(shí)效限制也做出了不同規(guī)定,三審稿在請(qǐng)求停止侵害、排除妨礙、消除危險(xiǎn)時(shí)不受訴訟時(shí)效的限制的基礎(chǔ)上,新增了恢復(fù)名譽(yù)請(qǐng)求權(quán)不受訴訟時(shí)效限制。實(shí)踐中侵害人格權(quán)益的行為對(duì)受害人造成持續(xù)性精神性損害,因此恢復(fù)名譽(yù)這類請(qǐng)求權(quán)不應(yīng)受到訴訟時(shí)效的限制,只有這樣才能有效的保護(hù)被侵害人的人格權(quán)益,恢復(fù)其受損的人格權(quán)益。除上述條款以外,三審稿第七百八十一條還對(duì)侵害人格權(quán)益行為的責(zé)任認(rèn)定問題做出新的規(guī)定。侵害人格權(quán)益的行為在認(rèn)定責(zé)任時(shí)應(yīng)當(dāng)考慮的因素遠(yuǎn)遠(yuǎn)多于一般侵權(quán)行為,這是由被侵害對(duì)象的性質(zhì)所決定的,人格權(quán)益與人身密不可分且多屬于精神利益,因此認(rèn)定責(zé)任需要考慮的因素也更加豐富,這一規(guī)定符合人格權(quán)益的特征,能夠更恰當(dāng)?shù)胤峙湄?zé)任。
四、完善死者人格權(quán)益法律保護(hù)制度的建議
(一)確定死者人格權(quán)益的內(nèi)容
首先可以確定死者的人格權(quán)益包括死者的名譽(yù)權(quán)益、姓名權(quán)益、肖像權(quán)益、隱私權(quán)益,這些權(quán)益是明確被法律所例舉出來的死者人格權(quán)益,當(dāng)然地包括在死者人格權(quán)益內(nèi)容的范疇之內(nèi)。除此之外,司法實(shí)踐還出現(xiàn)了很多惡劣行為,例如破壞尸體遺骨等,這些行為輕則損害死者近親屬對(duì)死者的緬懷紀(jì)念之情,重則破壞公序良俗,影響社會(huì)風(fēng)氣。因此死者的遺體、遺骨、骨灰等死者的身體利益也應(yīng)當(dāng)納入死者人格權(quán)益的保護(hù)范圍之中。同時(shí),現(xiàn)代人格權(quán)理論承認(rèn)了人格權(quán)的財(cái)產(chǎn)性部分,[12]因此有必要將死者人格權(quán)益的財(cái)產(chǎn)性部分也納入法律的保護(hù)范圍。
(二)確定死者人格權(quán)益的保護(hù)期間
法律上對(duì)多種權(quán)利的行使都規(guī)定了訴訟時(shí)效,說明法律對(duì)權(quán)利的保護(hù)大多存在一個(gè)固定的保護(hù)期間。參照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中的著作權(quán),對(duì)著作財(cái)產(chǎn)權(quán)和著作人身權(quán)中的發(fā)表權(quán)都規(guī)定了固定保護(hù)期間。法律對(duì)這些權(quán)利進(jìn)行保護(hù)一方面是為了鼓勵(lì)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人的創(chuàng)造積極性,但出于社會(huì)整體公共利益和人類社會(huì)進(jìn)步的考量,發(fā)表權(quán)不宜永久被法律保護(hù),把發(fā)表權(quán)的保護(hù)期也規(guī)定為固定的時(shí)間可以兼顧和兩方面的目的。而對(duì)其他著作財(cái)產(chǎn)權(quán)就明確規(guī)定只在固定的保護(hù)期間給予法律保護(hù)。
死者的人格權(quán)益是依賴于死者生前的人格權(quán)利益所產(chǎn)生的,在其死亡后,這種與生前人格的聯(lián)系將會(huì)隨著時(shí)間推移逐漸變淡,死者近親屬對(duì)于死者的情感牽連也會(huì)慢慢減少,因此有必要對(duì)死者的人格權(quán)益的保護(hù)規(guī)定一個(gè)明確合理的時(shí)間。從死者人格權(quán)益保護(hù)的范圍來看,大多屬于精神性利益,而姓名權(quán)益和肖像權(quán)益可能包含一些財(cái)產(chǎn)性部分,無論是精神性利益還是財(cái)產(chǎn)性利益都應(yīng)當(dāng)在一定的時(shí)間內(nèi)給予保護(hù)。但是由于英雄烈士具有身份和地位的特殊性,其人格利益內(nèi)含社會(huì)公共利益和國家利益,因此對(duì)社會(huì)一般公眾和英雄烈士等知名人物的保護(hù)期間應(yīng)當(dāng)允許存在差異。英雄烈士等人物對(duì)社會(huì)和國家的貢獻(xiàn)是不會(huì)隨時(shí)間改變,因此對(duì)于英烈人格權(quán)益應(yīng)當(dāng)給予長(zhǎng)久的保護(hù),不應(yīng)設(shè)置固定的保護(hù)期限,即任何時(shí)候都不允許他人侵害英雄烈士人格權(quán)益。
除了區(qū)分一般死者和英雄烈士要規(guī)定不同的保護(hù)期間,對(duì)于不同形式的責(zé)任承擔(dān)方式也應(yīng)當(dāng)區(qū)分不同的保護(hù)期間。賠償損失請(qǐng)求權(quán)應(yīng)當(dāng)在一定的期間內(nèi)給予認(rèn)可,而對(duì)于賠償損失以外的其他責(zé)任,如停止侵害、恢復(fù)名譽(yù)、賠禮道歉這些精神方面的補(bǔ)償應(yīng)當(dāng)給予永久認(rèn)可。我國死者人格權(quán)益受損是由死者的近親屬主張行為人承擔(dān)責(zé)任,法律對(duì)近親屬的范圍做出了明確的規(guī)定,因此保護(hù)期間相應(yīng)依附于近親屬的存活期間。許多國家都認(rèn)可應(yīng)當(dāng)在一個(gè)固定的期間對(duì)死者的人格權(quán)益進(jìn)行法律保護(hù),對(duì)此,建議參考著作權(quán)的保護(hù)期間,統(tǒng)一采用固定50年保護(hù)的標(biāo)準(zhǔn)。[13]
(三)完善死者人格權(quán)益保護(hù)的請(qǐng)求權(quán)歸屬
從我國現(xiàn)行法律可以看出,有權(quán)要求侵權(quán)死者人格權(quán)益行為人承擔(dān)責(zé)任的人主要是死者的近親屬,并且法律明確規(guī)定了近親屬行使權(quán)力的順位。這種規(guī)定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yàn)榉缮弦?guī)定順位是根據(jù)近親屬與死者的血緣關(guān)系和身份關(guān)系的親疏遠(yuǎn)近來劃分的,往往第一順位的人對(duì)死者人格權(quán)益的重視程度高于第二順位。然而這種順位規(guī)定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實(shí)際存在例外情形,出于各種原因第一順位的人未必對(duì)死者人格權(quán)益是否受到侵害有關(guān)注,或者第一順位的人知道侵權(quán)行為的發(fā)生卻怠于為死者維護(hù)人格利益,此時(shí)這種順位要求就成了阻礙維護(hù)死者人格權(quán)益的規(guī)定,不能使死者的人格利益得到最優(yōu)保護(hù)。
基于上述原因,在死者人格利益遭受侵害的情況時(shí)可以適當(dāng)賦予第二順序的近親屬一定的跨越權(quán)。這種跨越權(quán)主要是為了應(yīng)對(duì)死者人格權(quán)益不能得到第一順位人的保護(hù)的情況,此時(shí)賦予第二順位近親屬權(quán)利,由第二順位近親屬要求侵害死者人格權(quán)益的人承擔(dān)民事責(zé)任,維護(hù)死者人格權(quán)益。
(四)建立死者保護(hù)人制度
上述規(guī)定對(duì)于沒有近親屬的死者或者死者全部近親屬均沒有提出訴訟的,不能對(duì)死者人格權(quán)益提供有效的法律保護(hù)。因此除了要明確死者人格權(quán)益請(qǐng)求權(quán)歸屬,可以建立死者保護(hù)人制度。即當(dāng)死者人格權(quán)益受到侵害,且死者沒有近親屬或者其近親屬怠于行使權(quán)利時(shí),參照監(jiān)護(hù)和遺囑制度由法律規(guī)定的特定機(jī)關(guān)對(duì)死者人格權(quán)益進(jìn)行保護(hù),保護(hù)人可以以法定和意定相結(jié)合、意定優(yōu)先的規(guī)則選擇。指定的保護(hù)人應(yīng)當(dāng)參加維護(hù)死者人格權(quán)益的訴訟,沒有指定保護(hù)人的死者由法律規(guī)定的有權(quán)近親屬成為其保護(hù)人,沒有近親屬的,參照監(jiān)護(hù)制度由死者生前所在居委會(huì)、村委會(huì)等機(jī)構(gòu)作為死者的保護(hù)人,達(dá)到全面維護(hù)死者人格權(quán)益的目的。除了上述建議外,還可以通過對(duì)侵害行為應(yīng)承擔(dān)的責(zé)任類型作出明確規(guī)定來保護(hù)死者人格權(quán)益,針對(duì)不同對(duì)象的不同行為分配相應(yīng)的責(zé)任承擔(dān)方式,更有利于權(quán)益的保護(hù)。
【注 釋】
[1] 參見劉召成:《民法一般人格權(quán)的創(chuàng)設(shè)技術(shù)與規(guī)范構(gòu)造》,載《法學(xué)》,2019年第10期,第38頁。
[2] 參見王澤鑒:《人格權(quán)法:法釋義學(xué)、比較法、案例研究》,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3年版,第44~47頁。
[3] 參見朱曉峰:《侵權(quán)可賠損害類型論》,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740頁。
[4] 參見楊立新:《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要義與案例解讀》,中國法制出版社2017年版,第246頁~247頁。
[5] 參見葛云松:《死者生前人格利益的民法保護(hù)》,載《比較法研究》2002年第4期。
[6] 參見劉召成:《部分權(quán)利能力制度的構(gòu)建》,載《法學(xué)研究》2012年第5期。
[7] 參見王利明:《中國民法案例與學(xué)理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00~102頁。
[8] 參見郭明瑞、房紹坤、唐廣良:《民商法原理(一):民商法總論人身權(quán)法》,中國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1999年第468頁。
[9] 參見奚曉明主編:《侵權(quán)責(zé)任法條文理解與適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年版,第27頁。
[10] 參見張紅:《死者人格精神利益保護(hù)——案例比較與法官造法》,載《法商研究》2010年第4期。
[11] 參見劉穎:《民法總則中英雄烈士條款的解釋論研究》,載《法律科學(xué)(西北政法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18年第2期,第102頁。
[12] 參見劉召成:《死者人格保護(hù)的比較與選擇:直接保護(hù)理論的確立》,載《河北法學(xué)》,2013年第10期,第92頁。
[13] 參見周志勇:《死者人格利益之保護(hù)研究》,載《學(xué)理論》,2014年第25期,第136頁。
【參考文獻(xiàn)】
[1] 王澤鑒.人格權(quán)法:法釋義學(xué)、比較法、案例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3.
[2] 楊立新.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要義與案例解讀[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17.
[3] 朱曉峰.侵權(quán)可賠損害類型論[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7.
[4] 張千帆主編.憲法學(xué)[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
[5] 王遷.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法教程(第五版)[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16.
[6] 張新寶.侵權(quán)責(zé)任法(第二版)[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10.
[7] 王利明.人格權(quán)法[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09.
[8] 劉召成.民法一般人格權(quán)的創(chuàng)設(shè)技術(shù)與規(guī)范構(gòu)造[J].法學(xué).2019,10.
[9] 趙志.我國英烈名譽(yù)榮譽(yù)保護(hù)焦點(diǎn)探析—以系列英烈毀譽(yù)案為邏輯起點(diǎn)[J].法律適用(司法案例).2018,18.
[10] 劉召成.死者人格保護(hù)的比較與選擇——直接保護(hù)理論的確立[J].河北法學(xué).2013,10.
作者簡(jiǎn)介:張淑賢(1997—),女,漢族,安徽省合肥市人,法律碩士,中央財(cái)經(jīng)大學(xué),民商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