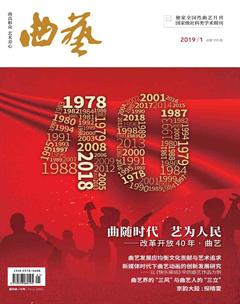追憶與貴田先生的二三事
2018年11月30日,在相聲前輩常寶華先生駕鶴西去84天后,相聲“二常”中的另一位,相聲表演藝術家常貴田也永遠離開了喜愛他的觀眾和他所鐘愛的相聲事業(yè)。與88歲的常寶華比較,76歲的常貴田走得有些匆忙,這就讓相聲業(yè)內(nèi)同仁和熟悉他的朋友們,更增加了幾許惋惜和懷念。
在中國,提起相聲就不能不提到“常氏相聲家族”,而常貴田就是這個相聲家庭的重要成員。常貴田是北京啟明茶社創(chuàng)辦人常連安的長孫,是在朝鮮戰(zhàn)場為國捐軀的常寶堃烈士的長子,海政文工團國家一級演員,雖是文職軍銜,相聲界同仁有時也不無調侃地稱他為“將軍”;說到社會職務,他還是中國曲藝家協(xié)會相聲藝術委員會原主任。可不論在舞臺上,還是生活中,在他身上人們既看不到“著名相聲表演藝術家的光環(huán),也看不出他有什么顯赫的家族史”,總之,他給人的共同印象就是:低調謙和、平易近人。正是有了這種做人的準則,他才能把根據(jù)傳統(tǒng)相聲改編的《攀龍附鳳》這類段子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入木三分。
中央電視臺中文國際頻道有一檔《重訪》欄目,我作為主持人,曾采訪過馬季、常貴田等相聲名家。言談中,常貴田沒有知名藝術家的架子,發(fā)表感言也不居高臨下,而是以一種探討的口吻講述自己對相聲這門藝術的感悟和評判。在錄制節(jié)目的間隙,他還不忘向欄目組的朋友介紹說:崔琦是曲藝雜家,書法是啟功先生的門下等。
我與貴田先生平時見面的機會不多,但也不算少,在演出、會議、拜師儀式等活動中時而碰面,但很少打電話。只有一次,是他打給我的。他問我:“我們常說的‘十樣雜耍,究竟是數(shù)字‘十呢,還是什么的‘什?”我根據(jù)自己的理解,并依據(jù)資料中記載的如實相告,“兩種寫法都曾出現(xiàn),各有道理,‘十樣雜耍是指舊時‘說學逗唱吹打彈拉變練的十種形式;而‘什樣雜耍則是泛指,不一定是準確的數(shù)字。”貴田兄在電話里還跟我客氣呢,“哦,領教了,領教了!”
我和貴田兄多次擔任曲藝賽事的評委,如北京青年相聲節(jié)和“藝韻北京”的活動。在點評的環(huán)節(jié),他表現(xiàn)出了既有原則性,又有靈活性,對選手段子中出現(xiàn)的“硬傷”和明顯的錯訛,他會一針見血指出;而對于有些不同風格和見仁見智的東西,他會在提出意見和建議后,往往還要補充說:“你們這樣使不能說不對,但也可以根據(jù)場合變換使法,剛才我說的只是供你們參考。”
有一次在北京市群藝館,我和貴田兄又同時擔任評委,工作人員在統(tǒng)計分數(shù)時,舞臺上不能空著,便臨時安排評委老師即興表演一段,貴田兄就拉著我一起上了臺。我們在這之前沒有合作過,那一次我們上臺后先是共同點評節(jié)目,隨后自然入活,說了一段《蛤蟆鼓》,他逗我捧,由于是從小打基礎的活,所以雖然沒對活,仍然是珠聯(lián)璧合,取得了很好的示范效果,那場景至今記憶猶新。
2014年,拙作《相聲三字經(jīng)》出版之前,我請了業(yè)內(nèi)人士姜昆、李金斗、常寶華、馬志明等分別寫了評語,那幾天恰巧又遇到了貴田兄,他說:“我在《曲藝》雜志上看了你寫的《相聲三字經(jīng)》連載,不錯!”我說:“那您給我寫幾句評語吧,捧捧我。”貴田兄有些賣派地一笑,從上衣兜里掏出一張紙:“早就給您寫好了。”說著,他將寫好的“三字經(jīng)”的評語,讀給我聽:
三字經(jīng),講相聲,傳知識,育兒童。
弘歷史,揚傳統(tǒng),樹規(guī)范,教基功。
論新作,擴繼承,淺出入,深其中。
促發(fā)展,攀高峰,載文冊,留美名。
2018年10月,在繁星戲劇村再度舉行了“藝韻北京”曲藝展演,評委有我和高洪勝、楊菲、劉洪沂、王文長,當時也沒聽到貴田兄生病或住院的消息,可才過了一個多月,11月30日凌晨,噩耗傳來,確實突然,令人扼腕痛惜不已。
斯人已去,世事無常,悲痛之余,匆匆寫下這篇小文,以為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