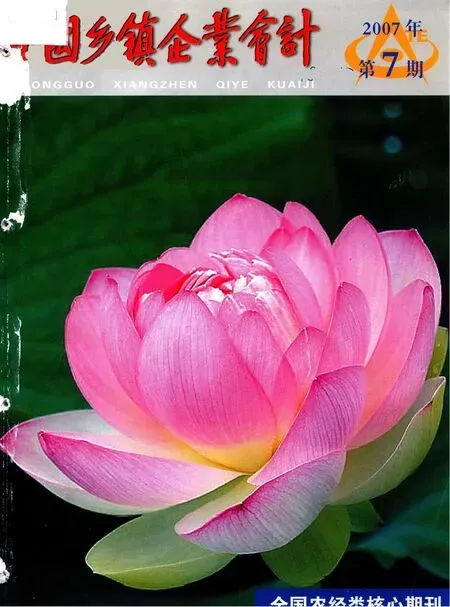我國消費稅改革的文獻綜述
謝敏妮
隨著我國深化改革的全面推進,稅制改革中全面“營改增”的落實,消費稅的改革迎來新契機。“消費型經濟”的興起與人民群眾消費結構、內容等方面發生著深刻的變化,變化過程存在著信息不對稱和矛盾,這影響著我國消費稅改革和發展的方向。為了配合國家改革的深入推進,我國對消費稅的現狀所存在的問題和改革的方向都有了比較深入的相關研究,本文對現有的學者關于消費稅改革的問題進行整理并形成文獻綜述,并對相關問題進行總結。
一、回顧消費稅的改革歷史
消費稅是以消費品的流轉額作為征稅對象的各種稅收的統稱,是政府向消費品征稅的稅項,可從批發商或零售商征收的間接稅,是屬于中央稅。我國的消費稅制度始于1994年,是僅次于增值稅、營業稅、所得稅的第四大稅種,稅源集中,征收環節單一。消費稅制度的建立,標志著我國稅收制度的一大進步。消費稅自建立開始,隨著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費水平和消費結構也隨之做出相應的調整,在2006年和2009年先后對稅收的范圍、稅率進行調整,這表明時代在進步,社會消費趨向合理性。同時,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對消費稅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完善地方稅體系,逐步提高直接稅比重。調整消費稅征收范圍、環節、稅率,把高能耗、高污染產品及部分高檔消費品納入征收范圍。”
二、消費稅的功能定位
1. 組織財政收入
在我國,主要有三大流轉稅,全面“營改增”之后,就剩下增值稅和消費稅兩大流轉稅,增值稅是實行普遍征收的原則,擔當著籌集財政收入的職能,消費稅選擇部分消費品征收,配合著增值稅,進行稅負調節。
2. 調控經濟
“寓禁于征”,對高耗能、高污染、高投入的產品征稅,同時可以節約資源,重在糾正消費者的偏差愛好,引導消費行為,糾正負外部性,保護資源環境。
3. 調節收入分配
將部分高消費品納入消費,通過這種方式實行財富的二次分配,調節貧富差距,調節居民收入分配,促進收入公平和社會和諧。
三、消費稅存在的問題
1. 消費稅征收范圍狹隘、缺位問題凸顯的問題
我國消費稅雖然經過多次改革,征稅范圍逐步擴大,但是改革的步伐跟不上經濟的發展。我國的產業結構由第一產業向第三產業邁進,工業化向服務化邁進,人們的消費水平和結構也發生較大變化,但我國消費稅的征稅范圍和目標仍以1994年設立的為基礎,并未與時俱進,例如高奢消費品界定不清,很多以前認為是奢侈品的東西現在看來是日用品,但例如飛機、高檔住宅等新興奢品并未納入征稅范圍,應該對日常消費品和奢侈品予以重新分類,并對類似輪胎和小汽車這種重復征稅的稅目,同時綠色稅目征稅范圍不足,對于“三高”產品的產業未納入消費稅征收范圍,嚴重阻礙產業結構升級,不能起到環保功能。
2. 消費稅稅率設置不科學的問題
現有的消費稅稅率不能完全體現消費稅的調節目標,應對部分偏高和偏低的消費品的稅率應該予以重新設置,如機動車的稅率并未與環保掛鉤,而且機動車的購置稅與消費稅具有重復征收的嫌疑,而且如一次性筷子具有鼓勵節約資源的資源性消費品和不可再生資源和奢侈品的稅率偏低,稅率設計存在嚴重的問題,不能達到消費稅的調節目的。
3. 消費稅征計方法不合理的問題
我國消費稅采取的是價內稅的計價方式,消費者在消費應稅消費品的時候對于產品的價格和稅費是不清楚的,這有悖于消費稅的引導消費方向的功能,節約資源,減少污染,也不利于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
4. 消費稅征稅環節單一的問題
我國消費稅是征稅環節除了少部分金銀飾品是采用生產和零售兩個環節征稅的,其余大部分都是在生產環節征稅,這種征稅環節單一,很多企業都在生產環節做手腳,導致稅基小,稅源流失,企業存在逃稅漏稅的弊端,而且容易給企業造成負擔,容易造成消費稅的引導功能喪失。
四、消費稅改革的建議
1. 關于消費稅的收入歸屬和劃分比例機制的研究
谷彥芳(2017)從消費稅的特點、消費稅收入能否彌補地方財政缺口、消費稅的不確定性和不可持續性、收益原則、稅收分布等方面分析得出消費稅不適合成為地方主體稅種,即時改革更適合作為中央和地方的共享稅。李升、寧超、盛雅彬(2017)從消費稅的調控功能、征稅范圍和長期不穩定性闡述了消費稅作為地方的主體稅種不具有可行性。儲德銀、韓一多、姚巧燕(2015)從理論層面和實踐層面分析認為消費稅劃為中央和地方的共享稅更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否則由于消費稅的征收范圍、稅目和分布不均的特性,將不利于消費稅發揮調節功能。龔輝文(2015)認為消費稅分布不均衡,范圍窄,更適合作為中央稅。
2. 關于調整征稅范圍的研究
張翼、陳清晰(2017)認為對現行征稅范圍進行“加減”結合,取消生活必需品的征稅,擴大奢侈品和“綠色”稅目的征稅范圍。谷彥芳(2017)認為以高消費、高耗能、高污染為標準適當增加稅目,范圍的確定堅持動態調整與相對穩定向結合的原則,發揮消費稅的調節和導向功能。田效先、鮑洋(2016)堅持“有增有減,以增為主”的原則,增加與資源和環境有關的稅目和提高稅率,同時賦予地方政府可以開征本地特色的消費稅權限,提高收入。楊芷晴(2013)認為應該根據有增有減的原則合理調整消費稅的征稅范圍,例如將一次性餐具、電池等高能耗、飛機等新興奢侈品納入征稅范圍,取輪胎等已經成為大眾消費品的稅目。
3. 關于調整稅率的研究
張翼、陳清晰(2017)認為細分奢侈消費的稅率層級,參照“營改增”前后娛樂業的節稅空間,設置浮動稅率,同時對于機動車借鑒歐盟的征稅調整制度引導綠色消費,對新能源給予補貼或免稅,同時提高一次性消耗品的稅率,減少浪費。谷彥芳(2017)認為依據多重標準設計稅率可以兼顧消費稅的職能實現,例如可以環境效應與價格水平雙重標準,我國2016年對豪華小汽車消費稅的改革正好體現這一點。儲德銀、韓一多、姚巧燕(2015)建議結合我國國情統籌考慮消費結構、收入分配、生態保護等調控,建立動態稅率機制。徐梅、劉芬紅(2016)建議根據產業結構升級導向對消費稅的稅率進行調整,從而促進人們保護環境和節約資源,也能促進產業的發展。
4. 關于征稅環節的研究
張翼、陳清晰(2017)認為對某些應稅消費品參照卷煙的征管辦法,或者改為零售環節征收。谷彥芳(2017)認為可以通過源頭控管、信息控稅、強化納稅意識等渠道把消費稅的征稅環節由生產環節調整到零售環節,以減少稅收流失。李升、寧超、盛雅彬(2017)認為征稅環節從生產環節轉變為消費環節,難以轉變政府職能,而且雖然有效率損失的問題,但至少不存在征稅難、生產地稅收與消費地稅源背離等問題。孟瑩瑩(2016)建議所有的商店按照稅控裝置系統以使征稅環節調整到零售環節,不僅能減少企業負擔和偷稅漏稅,也能達到調節收入分配的目的。徐梅、劉芬紅(2016)建議根據消費品的性質,區別對待采取不同的征稅環節,例如電池等應該在消費環節征收,而“三高”重金屬工業等應在生產環節征收。龔輝文(2015)認為生產環節征稅效率更高,也不容易產生稅源流失。楊芷晴(2013)建議采取多環節征稅,例如對煙酒等消費品實行生產和消費兩道環節征收,對成品油、啤酒等建議在零售環節征稅。
5. 關于是否把價內稅變成價外稅的研究
谷彥芳(2017)認為把消費稅的計征方式由價內稅改為價外稅,增強消費稅的調節功能,也避免重復征稅和便于征收管理和監督。儲德銀、韓一多、姚巧燕(2015)建議把消費稅改為價內稅能更好發揮調節經濟的功能。楊芷晴(2013)建議學習日本和美國等國家把價內稅改為價外稅,可以提高消費的透明度和引導消費。
6. 關于消費稅功能定位問題
莊佳強(2017)認為消費稅的改革應該立足于長期確保稅收收入的穩定性和可預測性,保障收入的可持續性,加強消費稅的福利改進功能,更好引導消費和糾正負外部性。馮俏彬(2017)認為消費稅與增值稅具有協同功能,應當以調節經濟為主要目標。楊芷晴(2013)認為消費稅的基本職能是組織財政收入,是一種輔助型稅種,同時還能促進節能減排和引導消費的作用。
7. 關于優化消費稅稅款的使用問題
儲德銀、韓一多、姚巧燕(2015)認為針對非煙酒類商品可建立環保發展基金,專門用于地方環境保護和生態建設。高陽(2014)認為應該提高財稅運營的透明度,使得稅制改革得以順利進行,減少阻力,同時要重視相關配套的改革,例如收取的稅費的支出渠道等。楊芷晴(2013)建議借鑒美、日等國經驗,把消費稅收入建立政府特殊基金,實行專款專用,例如補貼低收入人群以減少貧富差距或者建立環保基金以推進經濟轉型。
五、總結
關于我國消費稅改革的方向,應該結合我國的國情并分析我國經濟和產業發展所處的階段,從消費稅在功能定位出發,著手于應稅消費品的征稅范圍和稅率的調整,把消費稅的價內稅改為價外稅,并把征稅收入作為中央和地方的共享稅,并把稅費收入設置專項資金并專款專用,從而能夠彌補地方財政的缺口和更好的調動地方政府的積極性,發揮消費稅的調節作用,減少偷稅漏稅,以提升制度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