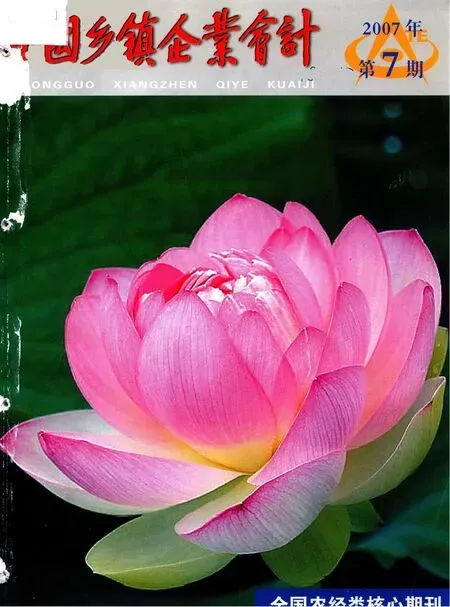水資源資產負債表研究進展綜述
胡亞玲 劉 琳
引言
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在關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中明確提出要“探索編制自然資源資產負債表,對領導干部實行自然資源資產離任審計”。這意味著,自然資源資產負債表的編制已經成為了國家全面深化改革在生態文明制度建設上的戰略需求。基于此,包括水資源、土地資源等在內的自然資源資產負債表的理論與應用研究成為了學者們探討的熱點。然而,水資源資產負債表作為我國新近提出的特有概念,國外并沒有成熟的理論方法可供借鑒,這導致編制工作缺乏指導,研究進展緩慢。因此,本文通過對“中國知網”在2016年1月1日至2019年2月10日收錄的關于水資源資產負債表的58篇文獻進行梳理,從編制基礎、計量單位、報表體系、構成要素、編制實踐等方面歸納總結了理論研究與實踐應用成果,以期為進一步完善我國水資源資產負債表編制工作提供參考。
一、水資源資產負債表編制理論研究
(一)編制基礎
水資源資產負債表的編制基礎涉及會計主體、會計期間和會計平衡原理。
倪書陽等(2016)認為水資源核算的會計主體比企業會計主體更為復雜,從國民經濟核算、流域水資源管理、自然資源離任審計三個角度,會計主體分別可以是國家、流域和行政區域[1]。
對于會計期間的選擇,考慮到與會計年度相適應,大多學者提倡采用日歷年為單位。但李莉(2017)認為根據水文年進行資源數據統計更符合自然規律,由于水文年起止時間存在不固定性,因此建議綜合采用日歷年和水文年兩種方法。田貴良等(2018)提出還可以以領導干部的任期為單位,便于考察任職期間水資源、水生態環境的變動情況。
國內學者對會計平衡原理的看法主要可以分成兩種。黃溶冰等(2015)認為水資源資產負債表的編制原理同企業資產負債表的編制原理一致,即“資產=負債+所有者權益”。耿建新等(2015)通過對比國民經濟核算體系(SystemofNationalAccounts,SNA)和環境經濟核算體系(AystemofEnvironmentandEconomicAccounting,SEEA)報表平衡原理,認為雖然SNA按照“資產=負債+所有者權益”的會計恒等式進行構建,但SEEA提出的按照“資產分布=資產占用”進行報表設計更符合水資源核算的實際情況。
(二)計量單位
計量單位的選擇是對水資源資產負債表原始數據進行會計處理的關鍵。柴雪蕊等(2016)認為資產負債項目暫時以物理量來表示能剔除價格變動對估值的影響,直觀地反映資源數量的變動情況。閔志慧等(2018)提出實物量計量便于縱向比較不同時期自然資源間的差異,價值量計量則可以實現不同地區自然資源間差異的橫向對比。由于資源價值化憑借現有技術水平難以全面推廣,因此,目前水資源最好先采用實物量計量,待條件成熟再加入價值量計量。
(三)報表體系
不同于企業資產負債表是一張單一的報表,水資源資產負債表是一套能全面反映三大構成要素在數量、價值量、質量、流量、存量五個方面變化的綜合報表體系。2015年由水利部發布的《水資源資產負債表編制方案》提出,水資源資產負債表應包含水資源資產及變動表和水質變動表。封志明等(2017)認為水資源資產負債表報表應由“總表+分類表+輔助表”三層體系構成。朱婷等(2018)認為水資源資產負債表報表包括資產表、資產綜合核算表、負債表、負債綜合核算表、凈資產表五張表格。
(四)構成要素
類比自然資源資產負債表,大多數學者認為水資源資產負債表也應囊括水資源資產、水資源負債、水資源凈資產三大基本要素,并對三大要素的定義、分類展開了深入細致的研究。
1.水資源資產
水資源資產概念的界定及分類一直是國內學者研究探討的焦點問題。柴雪蕊等(2016)認為水資源資產是指具有經濟性、收益性、有償性、權屬性和稀缺性5個特征的水資源,因此能被植物直接吸收的天然降水不能算作水資源資產。
沈菊琴(2018)通過探析水資源及水資源資產的關系提出,水資源具有自然屬性而水資源資產具有商品屬性,由水利工程供給且按現有技術可以被使用、能以貨幣計量、預期會帶來經濟效益的水資源才能作為水資源資產。
對于水資源資產的分類,陳燕麗等(2016)將水資源資產劃分為存量資產和債權資產。其中,存量資產是指地表水以及地下水的存量總和;債權資產包含讓渡使用權取得的收入、獲得的生態補償經濟效益、政府提供的稅收優惠及保證金等。倪書陽等(2017)認為水資源資產應根據需求劃分為工業用水、農業用水、生活用水、生態用水等。同時,只有水質達到規定標準才可被視為資產。
2.水資源負債
水資源負債是否應該被確認是編制過程中的一大爭議所在。以耿建新等(2015)為代表的學者認為SNA在提供的國家資產負債表的一般格式中,并不承認包括自然資源在內的非金融性資產存在負債項,為了符合國際慣例,我國暫時也不應確認負債。但多數學者認為,水資源負債是體現資產負債表功能完整性的必備要素。李志堅等(2016)認為必須確認水資源負債,否則資產負債表的稱呼就名不副實,失去意義。柴雪蕊等(2016)從水資源“過耗”的角度出發,認為水資源負債不等同于環境成本,而是資源實際使用情況與國家宏觀確定的資源環境生態紅線之差。徐琪霞等(2018)則認為水資源負債既包含資源耗減負債也包含環境保護負債。其中,資源耗減負債是指當代人過度消耗自然資源,透支后代人使用額度所形成的負債;環境保護負債是人類活動導致環境破壞形成的責任,包括水資源管理成本、水污染治理成本和水生態維護成本等。
3.水資源凈資產
水資源凈資產是水資源資產減去水資源負債后的剩余權益。張友棠等(2016)認為應該將其視為所有者權益,并從國家、管理者和經營者三個層次進行價值量核算;陳燕麗等(2016)認為自然資源的權屬難以界定,用“凈資產”來描述更符合實際意義;閔志慧等(2018)認為由于我國水資源所有權與管理權界限不清晰,導致水資源權益主體投入的“資本”和“留存收益”無法直接計算得到,因此用凈資產表示更為準確。
二、水資源資產負債表編制的實踐研究
在國務院辦公廳發布的《編制自然資源資產負債表試點方案》的指導下,各地區的編制工作陸續開展。謝瑩瑩等(2017)通過梳理國內學者關于自然資源資產表編制框架體系、要素確認、計量方式等方面觀點,以膠州市水資源為例,編制水資源資產流量表及資產負債表。陳龍等(2017)以深圳寶安區境內的茅洲河為研究試點,將水資源資產價值拆分為實物資產價值和生態服務價值,運用市場價格法、替代成本法、影子工程法等,得出2016年茅洲河水資源資產總價值。楊艷昭等(2018)以水環境損害、水資源過耗和水生態破壞三個指標作為水資源負債的核算范疇,在實物核算的基礎上,采用模糊數學模型將水資源資產價值化,編制了湖州市2006—2013年的水資源資產負債表。李婉瓊(2019)基于環境重置成本法,從生態環境維護層成本、生態環境恢復層成本、生態保護戰略層成本三個層次計算出了海南省2015年每類水資源的價值總量并繪制了海南省的水資源資產負債表、水資產變動明細表和負債明細表。
三、評述與展望
迄今為止,國內學者在理論層面對水資源資產負債表的編制基礎、報表體系、構成要素等方面開展了研究,圍繞三大要素的概念界定、分類標準、價值化方法等具體內容構建了一定的理論框架。在實踐層面,一些學者采用他們認為合理的方法編制了目標地區的水資源資產負債表,進一步充實了應用研究的成果。但由于水資源的數據來源廣、學科交叉性強,致使水資源資產負債表的編制難度非同一般,現階段編制完成的報表仍存在一些缺陷,如對水資源資產認定標準不一致導致報表科目設置差異過大,缺乏水質核算等。筆者認為,未來還應繼續朝以下方面展開深入研究:(1)水資源資產內涵界定的角度問題。部分學者認為水資源資產不僅包含存量價值,還包括讓渡水資源使用權取得的收入等。然而從會計學角度考慮,收入是存在于利潤表中的動態要素,不能與資產合并列示在靜態的資產負債表中。(2)報表中是否反映水資源的質量問題。雖然在理論層面早已有學者提出對水資源質量的核算與數量核算、價值量核算具有相同地位,但在編制實踐中,質量指標往往被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