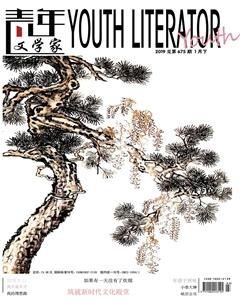論五四時期女性寫作中的“姐妹情誼”
廖思琦
摘 要:在五四時期,伴隨著啟蒙主義而來的是對“人的發現”,而女人作為“人”中最收到壓迫的群體,也是最亟待于被發現的群體,當以凌叔華為代表的一批女作家開始登上歷史的舞臺后,有關“姐妹情誼”的寫作實踐是女作家們在新舊交替時代中為女性群體所謀求的“可能”:對女性而言,是否可能存在一種比起異性戀更為平等、和諧、深刻的情感關系?女性在逃離男權話語的陰影遮蔽之后是否還有可以容納她們的其他空間?對“姐妹情誼”的書寫是五四女作家們反抗傳統性別秩序的一種表達策略,但是作為建立在女性共同經驗和共同需要上的“方舟”,“姐妹情誼”在五四時期的女性寫作中究竟形成何種面貌,又迎來何種結局?女性作家是否在其中為女性群體找到了歸處?
關鍵詞:姐妹情誼;五四文學;凌叔華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9)-03-0-02
在凌叔華的《說有這么一回事》的正文前面有一段附言,是當時的另一位男作家楊振聲寫的,他言明凌淑華是應他的邀約,重作他之前發表的一篇小說《她為什么忽然發瘋了》。同樣的一個關于“姐妹情誼”的故事題材,在男女兩位作家的筆下卻呈現出了微妙的不同。
主人公曼影和云羅的愛情開始于學校的話劇排練,通過體味羅密歐與朱麗葉之間異性戀的角色扮演,兩個人的情感逾越單純意義上的友誼,走向了一種更為親密的關系。在楊振聲的文本中,“姐妹情誼”建立起來的心理動機是來自于女性對異性戀的求而不得,實際上作者對于女同性愛,或者說這樣一種存在女性之間的排男性關系,是站在一種男性立場的統攝之下進行理解的。文中云羅的那種光彩照人的美麗使曼影情難自禁,同性間的欲望使她們意識到了兩個人之間的于傳統兩性關系的不合理性,甚至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一種對于男性的艷羨和渴求,曼影兩次說到:“可惜我不是個男子”[1]就連人物自身都不認同這段情感的合理性,而這場愛情悲劇直到終結也不被周圍的任何一個人所理解。在這篇小說中,我們看不到楊振聲對“姐妹情誼”的存在有任何的同情和理解,處處都是傳統男性話語對兩個人的粗暴質問,雖然小說的主旨在于批判包辦婚姻對人的戕害,但是文中的姐妹情誼卻是非常虛無的。
同一個故事,通過凌叔華以女性視角重新觀照,曼影和云羅的感情呈現出了十分不同的意味。凌叔華雖然敘事一向理性節制,但是對于女性的情感心理把握之細膩足以使整個故事從楊振聲的冷漠觀看中生動真實起來。故事的一開始,作者就描寫了云羅心中對于曼影的那些小小悸動:“云羅往常遇見她從不敢同她說話,這兩天因為練習戲,被她當著許多同學取笑,弄得她非常局促,覺得有些厭恨她;但不知道為什么,每逢聽她高聲喊朱麗葉的時候,她的心就有些跳,卻不是那種生氣的暴跳。”[2]凌叔華把兩個人的情感發展處理得既自然又合理,就像一對異性戀人一樣逐漸地情動,而不是像楊振聲那樣簡單地歸結于一種對異性戀的補償和替代。
凌叔華在小說中花大量的筆墨來描寫了曼影和云羅的相知相愛,著重強調了其感情的真切,許多細節都和異性戀別無二致,“云羅半夜醒來,躺在暖和和的被窩里,頭枕著一致溫軟的手臂,腰間有一只手搭住,忽感到一種以前未有過且說不出來的舒服。往常半夜醒來所感到的空虛、恐怖和寂寞的味兒都似乎被這暖融融的氣息化散了。她替曼影重新掖嚴被筒,怕她肩膀上露風。”這個片段充分的表現了兩個人帶給彼此的那種慰藉填補了心靈上的空洞,不僅是她們對彼此的理解和珍愛,還有作者對這種姐妹情誼的充分理解和認同,既有相知的友誼,又有相伴的親情,更有相守的愛情,這種情誼在凌叔華的筆下顯得如此和諧、美好,不會讓讀者覺得怪異突兀或者另類,而是一種非常單純而深厚的感情。
總的來說,對于這個故事,凌叔華把它盡量處理得唯美動人,主要是集中渲染這種情感在精神的可貴,對于欲望的描寫是非常少的。小說中有一個細節,是云羅靠在曼影的懷中,曼影從她的領口中望去,看見了她光潔的皮膚和線條優美的乳房。這是小說唯一一個直露了欲望的地方,本身從領口看進去的這個動作就充滿了性暗示,這是一個經常由男性對女性發出的一種“窺視”,但是凌叔華沒有對此做太多的渲染,曼影在“看”的時候內心也沒有太多的沖動或是其他心理活動,而是通過她對云羅身體的同性間的審美表現出對云羅的喜愛,把欲望純潔化了。在此可以比對楊振聲的文本,曼影注視的是云羅微微張開,等著親吻的嘴唇,這也是一個有性暗示的“看”的動作,作者的描述是“她生了無限的憐惜,心真個嘭嘭跳了起來。”曼影心里甚至想:“可惜我不是個男子,不然,我現在可要真個銷魂了!”這一句話實際上暴露了曼影對云羅的欲望并非是女性與女性間的審美與欣賞,而是一種男性對女性的欲求,這應該是楊振聲自己站在男性立場上觀照人物的結果。
除了《說有這么一回事》以外,五四女作家的寫作中涉及到了有關“姐妹情誼”題材的創作還有《我的教師》、《我的同學》、《玉薇》、《或人的悲哀》、《麗石的日記》、《漂泊的女兒》、《暑假中》、《歲暮》等等。縱覽文本,“姐妹情誼”在五四時期的女性寫作中呈現出的狀態是復雜的,不能簡單地解釋為“女同性戀”。女性作家顯然是在“姐妹情誼”中寄托了自己對于女性同盟的許多理想,這是一種驅逐了男性霸權的女性烏托邦,在這里女性團結在一起,相互理解、相互呵護、相互珍愛,同樣的性別身份使得她們天然地可以互相體諒,這種平等、和諧、美好的關系是當時的女性難以和異性建立的。但是這樣的女性烏托邦終究是一種虛構,一種理想,在現實中難以實現。
在《說有這么一回事》中,曼影和云羅如此相愛,但最后也無法逃離注定悲劇的結局。那么女性烏托邦破滅的阻力到底來自哪里?文中云羅曾向曼影哭訴,她無法違逆自己的母親和哥哥,她們可能最終會分離,也曾表示如果曼影是男人就好了。可見導致悲劇的原因主要有兩重,其一,是傳統異性戀所帶來的世俗規約的壓力,盡管彼此深愛,但還是在不合法中惴惴不安;其二,是來自于家庭的壓力,在這里重點需要指出的是男性家庭成員尤其是父親或者兄長所帶來的壓力。在小說的最后,曼影從同學口中得知了云羅的婚姻情況,云羅最后被迫嫁給了自己哥哥的上級,一個太太剛過世就到處說親的科長,這樣一個與云羅毫不般配的老男人卻成了她的令人稱羨的歸宿,云羅在同學的口中甚至是一個甜蜜微笑著的美麗新娘。而事實卻是云羅抵抗無果,最終淪為了你爭我斗的男權社會中一個可憐的犧牲品,曼影也只能被動接受殘酷的現實。而廬隱的小說《麗石的日記》中則是女性主動向異性戀和家庭妥協。文中的麗石和沅青也像云羅和曼影一樣,是女校里的一對親密無間的戀人,可是后來這段戀情最終卻因為沅青的妥協而宣告破滅。可見看似美好的“姐妹情誼”有時候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堅定,甚至比異性戀還要更加容易破碎。沅青和麗石兩個人其實都一直承受著這段不倫之戀帶來的巨大壓力,這段感情的發生本來就是很朦朧的,兩個人對其的認識也是曖昧不清,既有對真愛的渴望,也有傳統男權話語所帶來的內心煎熬,在這種猶豫不決之中,“姐妹情誼”當然很難長久地走下去。
在這些作品當中,我們可以看到男性是離間“姐妹情誼”的最終元兇,而異性戀的傳統則是那個戴在女性頭上的緊箍咒,時時告誡她們不要“越軌”。歸根結底,在男性話語服從下的社會是不可能為“姐妹情誼”的存在開辟任何可能的空間。作為社會性別主體的男性,異性戀傳統本身就是他們得以操控女性的強有力的工具,使得女性始終不能擺脫異性婚姻關系的束縛,更無法擺脫在這種婚姻關系中男性對女性上下操控。在這種社會現實之下,“姐妹情誼”似乎成為了溺水中的女性們的諾亞方舟。面對兩性之間的矛盾束手無策,似乎只有另辟蹊徑,才能為女性的崛起掙得一線希望,也是她們心中溫柔的避風港。當新時代的女性們想要以“姐妹情誼”的方式反抗男性霸權,渴望擺脫被男性主宰的不能自決的“異性戀”婚姻命運之時,她們的聯盟是否真的足夠堅強到可以與之抗衡?
注釋:
[1]楊振聲著 .她為什么忽然發瘋了.楊振聲隨筆[M].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2]凌叔華 .說有這么一回事. 繡枕[M]. 江蘇文藝出版社,2009.
參考文獻:
[1]楊振聲著 .她為什么忽然發瘋了.楊振聲隨筆[M].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2]凌叔華著 .說有這么一回事. 繡枕[M]. 江蘇文藝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