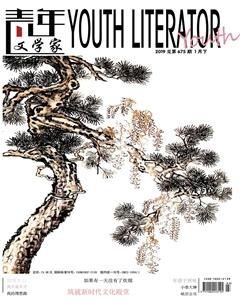徐訏小說浪漫主義問題研究
摘 要:徐訏的新浪漫主義小說繼承了相對早期浪漫主義的傳統,同時又因為現代性的融入、充滿細節的敘事等特征而具有了新的面貌與風格,在《鬼戀》中,他以具有現代性的人物形象,以及細節與現實的融入,在浪漫傳奇中融入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的成分,使自身的浪漫主義創作具有獨特的風格與個性。
關鍵詞:新浪漫主義;現代性;《鬼戀》
作者簡介:蒲敏(1991.7-),女,漢,四川省南充市人,碩士,云南師范大學新詩研究院研究員,研究方向:打工詩歌和打工文學研究。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9)-03-0-02
徐訏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新浪漫主義的代表作家,自其于十九世紀三四十年代浪漫主義文學的“日暮之時”[1](p254)蜚聲文壇起,便成為我們討論中國浪漫主義文學無法繞開的存在。五四以后、建國以前的中國向來不乏浪漫主義作家,郭沫若的狂放躁動,郁達夫的悲郁暴露,都足以在現代文學史上留下濃重的一筆。而徐訏卻以自己具有獨特個性的浪漫主義,成為一個區別于文壇前輩的特殊存在,對于他的小說創作,評論家們更傾向于使用“新浪漫主義”一詞,用以概括他作品中浪漫主義與現代主義的粘連與融合。
一、繼承傳統
徐訏的新浪漫主義無疑是繼承了相對早期浪漫主義的傳統的,與早前的浪漫主義作品相似,他的作品也具有強烈的主觀性,注重心理描寫,不遺余力地挖掘人物的心理體驗。他曾說:“我作的心理活動本身也是一種生活,情感上憎厭、憫憐、愛恨、憤怒、焦慮、憂愁、苦悶都是內心生活。”這種“自我表現”式的心理刻畫,使徐訏的小說與其它浪漫主義作品一樣,具有較強的主觀性與濃烈的情感氛圍。同時,作為傳統浪漫主義文學的重要特征的“理想化”,在徐訏的小說文本中隨處可見。他常常在作品中構造近乎完美的女性人物,設置唯美而富有神秘感的場景,并安排一場奇幻浪漫的邂逅。徐訏曾說:“我是一個企慕于美,企慕于真,企慕于善的人,在藝術與人生上,我有同樣的企慕;但是在工作與生活上,我能有的并不能如我所想有的。”[2]現實生活是缺憾與不完滿的,同時也從反面推動了作者將自己的“理想與夢”投射到藝術作品當中,“從人性中提煉真的、善的、美的成分,讓它們在適當的作品中表現出來”[2],以“在空幻的夢想中”“填補生命的殘缺”。因此,徐訏筆下的女性多是近乎完美的,如《鬼戀》中的“鬼”、《阿拉伯海的女神》中的女神、《精神病患者的悲歌》中的海蘭, 她們美艷絕倫、博學廣才,或純真或神秘,并且都心地善良,被成為了真善美結合的典范。這使得“他小說中大部分女性人物一看便知純屬虛構……每一個都可以打上某種極致美好的標簽,視作某種理想化的呈現。”[3](p60)這種“理想化”便是對傳統浪漫主義的一種繼承。
二、新的突破
徐訏的小說繼承了早期浪漫主義的傳統,同時又因為現代性的融入、充滿細節的敘事等特征而具有了新的面貌與風格。
1.具有現代性的人物形象
徐訏曾留學法國,并獲巴黎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對西方康德、伯格森的唯心主義哲學以及行為主義心理學、行為主義分析學等都有較高的興趣,這一背景使他的作品無論是風格還是敘事手法都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現代主義的影響。作為徐訏小說創作重要開端的《鬼戀》,便是三十年代在巴黎求學期間創作的。
小說寫“我”在一個夜晚,于上海南京路上邂逅一名“有一百三十分的美”的神秘黑衣女子,她“銀白的牙齒像寶劍般透著寒人的光芒,臉凄白得像雪,沒有一點血色”,“嚴肅而敏利”,她美麗異常,在“我”眼中甚至“有幾分仙氣”,卻又堅決自稱為“鬼”。“我”一直對她“鬼”的身份心存懷疑并互相探討許多“于己無關”的科學和哲學,發現她極富智慧與學識,隨后“我”不可自抑地傾慕于她,她卻堅決地拒絕了“我”的表白,一再對以“人鬼殊途”。“我”只好黯然消沉,開始在凡庸的都市里追尋刺激,到最后終于決定“將我心底的情愛升華成荒謬的友誼”之時,她卻突然離開。當“我”兩個月后在一座寺廟里再次遇到她,她向“我”講述了她的身世:她曾是一個地下工作者,暗殺過許多人,坐過牢,也曾亡命國外,最后感到自己“歷遍了這人世,嘗遍了這人生,認識了這人心”,便決心把自己當作鬼,游離于世外,“冷觀這人世的變化”。可是“我”并沒有完全理解她,還是堅持要她做“我”的愛人。于是她選擇在“我”病愈之后,徹底地離開,只給“我”留下無盡的憂傷和懷念。
中國自古就不缺少“人鬼相戀”的故事,也同樣具有浪漫傳奇色彩,而徐訏《鬼戀》的獨特之處,則在于人物形象與故事情節的哲理性與象征性。在中國傳統社會嚴重的性壓抑之下,社會中下層的才子們往往通過“人鬼相戀”的傳說,來寄托心理與生理上的寂寞,傾注些“紅袖添香”的愿望。因此傳統小說中的女鬼形象,往往容貌絕艷,知書達理,善解人意,還很喜歡自薦枕席,并且總是心心念念地想要做人,想要“長伴君側”,真可謂“身是陰間的身,卻有一顆陽間的心”[4](p57)。這一類舊式浪漫小說,在徐訏眼里,是“格局既狹,而情操低卑,愛之結果,也只是討來做姨太太,上侍翁姑下奉元配而已”[5](p298)與此相反,徐訏筆下這個“超人世的,沒有煙火氣”的,“動的時候有仙一般的活躍與飄逸,靜的時候有佛一般的莊嚴”的女“鬼”,生而為人卻心甘情愿要做“鬼”,實際上是一種“對于人事都已厭倦的生存”。她曾經是最入世的人,卻在經歷“一次次的失敗,賣友的賣友,告密的告密,做官的做官,捕的捕,死的死”之后,感到“同儕中只剩我孤苦的一身!我歷遍了這人世,嘗遍了這人生,認識了這人心。”[6]因此發出“我要做鬼,做鬼”的誓愿。小說中的“鬼”對人世的失望與淡漠,已達到極端程度,在極度悲觀中達到無欲無求的境界。“鬼”的處境和選擇,實際上是對現實生活中人的生存困境的折射與隱喻。徐訏通過夸張和傳奇的手法,對這種失望、厭倦進行了極端的處理。《鬼戀》中的哲學思考與藝術手法,使其不同于傳統愛情浪漫小說,而成為具有現代性哲理的新浪漫主義小說。
2.細節與現實的融入
浪漫主義的作品“往往醉心于奇人、奇事、奇境”[7],徐訏的作品無疑是浪漫的,他的小說中故事發生的地方,總是在“海島烏托邦、馬賽小旅館、異國大別墅”[3],在茫茫的阿拉伯海上,與一位美麗少女發生纏綿的戀情(《阿拉伯海的女神》),或是在孤島上的“世外桃源”,經歷曲折而神秘的故事(《荒謬的英法海峽》)或是在巴黎富商的法式莊園,經歷糾結交錯的邂逅(《精神病患者的悲歌》)……都是充滿了奇特的想象,常常使主人公“分不清真幻”、“時時醒來還覺在夢中”,但徐訏又熱衷于在浪漫傳奇中融入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的成分,通過許多的細節描寫混淆真實與虛構的界限。小說的情節似乎都是“虛構的謊言”,而他擅長在小說里添加“謊言中的細節”,使它更具有打動人心的力量。例如他的開場:
有一天,我去訪一個新從歐洲回來的朋友,他從埃及帶來一些紙煙,有一種很名貴的我在中國從未聽見過的叫做Era,我個人覺得比平常我們吸到的埃及煙要淡醇而迷人,他看我喜歡,于是就送我兩匣。記得那天晚上我請他在一家京菜館吃飯,我們大家喝了點酒,飯后在南京路一家咖啡店閑談,直到三更時分方才分手。[6]
開場雖是作為為偶遇創造契機的一個存在,卻是那般“瑣碎的、溫和的、如家常般的敘述語調”,就如同我們平時在現實生活中和身邊一個朋友的交往那樣真實、平凡。以這樣家常的開端,誰又會想到接下來會是一段奇幻的邂逅呢。接下來,在“我”與“鬼”的相遇中,作者“極認真”地交代了“南京路”、“斜土路”、“霞飛路”等地名,曾有研究者注意到:“畫出二十世紀二十年代《鬼戀》故事的街道圖”“將之與現今的上海街道圖對照,竟然大致吻合”[8]。徐訏小說的細節,除了體現在物名、地名、房間布置的細心敘述上,還體現在對人物感情與心理活動與環境的真實刻畫上,在描述“我”對“鬼”的無望的思念時,他寫道:
但我無法停止對她的思念,在湖邊山頂靜悄悄旅店中,我為她消瘦為她老,為她我失眠到天明,聽悠悠的雞啼,寥遠的犬吠,附近的漁舟在小河里滑過,看星星在天河中零落,月兒在樹梢上逝去,于是白云在天空中掀起,紅霞在山峰間涌出……[6]
因為極度的思念,導致時間在感覺中發生變形,變得尤其緩慢起來,但在這緩慢的“失眠到天明”中所體驗的每一道風景,從雞鳴到星星的零落,從月兒逝去到紅霞涌出,無不在淡淡的寂寥哀傷的氛圍中透出日常的氣息來。徐訏認為“浪漫主義的基本特點是以現實生活為依據,依照假想的邏輯,構造形象,以表現作者的理想與希望”[9],并通過浪漫故事的編織,對現實人生進行“自我療傷”[10](p84)。
當然,徐訏的新浪漫主義小說創作也有一定的局限,從《鬼戀》之后便基本囿于奇幻愛情或是奇遇的寫作,雖然兼顧了小說的文學性與易讀性,使其在三四十年代得以一次次成為暢銷的通俗讀物,但是終歸會限制作品的路數與格局,難以進行更具有創造性的改變。
三、結語
“現代主義就是關于焦慮的藝術,包含了各種劇烈的感情、焦慮、孤獨,無法言語的絕望”[11](p167)《鬼戀》中超越于一般奇情奇戀的哲學構思與人生思考,是徐訏對自身孤獨生活的填補,他曾在《一家》的后記中說:“我愛生活,在凄苦的生活中我消磨我殘缺的生命,我還愛夢想,在空幻的夢想中,我填補我生命的殘缺”。正是徐訏在奇情奇戀的浪漫主義小說中,融入了現實主義的成分,并表達不同于普通戀愛小說的人生哲思,才使他的小說具有一定的現代性與更高的哲學價值。
參考文獻:
[1]朱曦,陳興蕪.中國現代浪漫主義小說模式[M].重慶:重慶出版社,2002.
[2]徐訏.風蕭蕭[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
[3]袁堅.徐訏小說的細節與情調[J].書城2009年第3期.
[4]嚴明.文言小說人鬼戀故事基本模式的成因探索[J].文藝研究2006年第2期.
[5]徐訏.兩性問題與文學[C].徐訏代表作,北京:華夏出版社,1999.
[6]徐訏.鬼戀[M].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1996.
[7]茅盾.夜讀偶記[M].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58.
[8]王璞.一個孤獨的講故事人——徐訏小說研究[M].香港:香港里波出版社.2003.
[9]徐訏.徐訏給朱光潛的信[A].王一心.30年代徐訏與朱光潛的通信交往[C].新文化史料[J].2000.
[10]葛俊俠.論徐訏小說的浪漫主義藝術[J].內蒙古財經學院學報2005年第3卷第1期.
[11]弗·杰姆遜.后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M].陜西:篩析師范大學出版社,1986.法言語的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