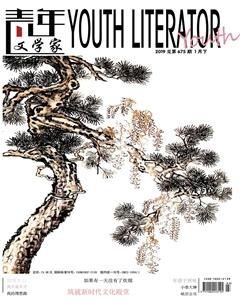西漢《詩經》學視域下“《詩》無達詁”說的內涵初探
摘 要:西漢董仲舒的“《詩》無達詁”說在后世引起了多元的經學和文學闡發、演變。它本指西漢當時學者根據各自所持的思想和需求闡釋《詩》,以實現經世致用,并沒有固定的辭義解釋。本著“從變而易,一以奉天”的原則,“《詩》無達詁”最終體現了“天人合一”“獨尊儒術”的政治思想,并歸屬于漢代經學闡釋為主的《詩》學發展。
關鍵詞:《詩》無達詁;董仲舒;經學;《詩》學
作者簡介:張玥(1995-),女,滿族,北京人,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二年級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藝理論與批評。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9)-03-0-02
西漢武帝時期,董仲舒吸收百家思想,創立了適應大一統國家建設的新儒學。《漢書·董仲舒傳》“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①,強調其他學說不能和儒學處于同樣高的發展地位和態勢,以儒學為主、百家為輔,對原始儒家更新改制。兼容變革思想作為董仲舒的總體學術精神,對“《詩》無達詁”說的生成有重要意義。
一、“不任其辭”的經學闡釋思想
在兼容變革思想統攝下,董仲舒獨創了“名號”“辭指”“經權常變”等與“《詩》無達詁”相關聯的具體理論。
1.名號論
《春秋繁露·深察名號》提出“治天下之端,在審辨大。辨大之端,在深察名號。”②儒者要重視辭文表述,洞悉孔子的微言的大義。“名號”是以語言的形式對事物進行概括、分辨;它被抬到治理天下的高度,由圣人依據天意制定,具有判定是非進而規整世界的功能。
原則是“《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③對于“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一事,楚君行動有禮、晉君相反,因此即使按照寫作慣例楚國作為夷狄國君不被稱爵位,《春秋》記敘時根據“禮”的標準變通了語言規則,“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也”。“從變而移”要求根據歷史條件和具體語境變化,靈活解釋《春秋》的意味。這為引《詩》來闡釋《春秋》、表達政治文化訴求奠定了基礎,可看做后面“《詩》無達詁”的伏筆。
2.辭指論
具體到言意關系,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竹林》篇提出“辭不能及,皆在于指”“見其指者,不任其辭”。根據清代蘇輿疏釋,“指,即孟子之所謂義”“任,用也,旨有出于辭之外者”。由文字所表達的意義,指向文字所不能表達的意義;在重視表露于外的意思的基礎上,理解者發揮主觀能動作用,由表及里,追求“言外之意”。這種《春秋》意義觀和理解觀是“《詩》無達詁話”話語生成的理論環境。
3.“經權常變”論
《春秋繁露·玉英》曰:“《春秋》有經禮,有變禮。為如安性平心者,經禮也。至有余性,雖不安于心,雖不平于道,無以易之,此變禮也……明乎經變之事,然后知輕重之分,可與適權矣。”④常變關系,乃一般與特殊、原則性與靈活性之間的關系。“對‘權的嚴格框限實質是就是對‘經的至上地位的尊重”⑤;將經權意識直接落實到經學解釋的意義觀上,就是常辭與變辭,常義與變義。根據蘇輿的注疏,常變皆要因時因地而運用,不可拘執一端而不化。
總之,董仲舒在《春秋》探微、史實索引、和引《詩》推衍等闡釋行為中始終求“變”,實現了儒學釋義,客觀上促進了“《詩》無達詁”命題的孕育和生成。
二、歷史語境中的 “《詩》無達詁”內涵
“《詩》無達詁”最早明確見于《春秋繁露·精華》篇:
難晉事者曰:“春秋之法,未踰年之君稱子,蓋人心之正也。至里克殺奚齊,避此正辭而稱君之子,何也?”曰:“所聞‘《詩》無達詁,《易》無達占,《春秋》無達辭,從變從義,而一以奉人。”⑥
根據《說文》《爾雅》,“詁”可訓為“古”和“故”,引申為解釋和理解。劉向《說苑》稱引時“達”作“通” , “通”與“達”都是明白、通曉之意, 可以互訓。[1]“《詩》無達詁”即《詩》沒有通達曉暢的確定含義,辭文蘊含著可探尋的意境空間。就董氏主觀意圖來說,“詁”還包括史實和義理的推衍。“所聞”二字證明“《詩》無達詁”并非原創;而作為一種引起人們重視的理論,從董仲舒始。
它其實是董仲舒對西漢初至武帝階段《詩》學發展現狀的描述和總結。西漢武帝之前,《詩》學發展呈多樣化格局和形態,:不僅齊詩、魯詩、韓詩、毛詩(四家詩)各有其面貌和師承系統, 在篇章字句的解釋方面“文字或異,訓義固殊”⑦;就是同一家詩之中也有學術的分野。基于不同學術背景的詩學流派也形成了對《詩》的不同闡釋觀念,正可謂“《詩》無達詁”。然而董仲舒的所指不止于此,“《詩》無達詁”與后面兩部經典都要“從變從義,而一以奉人”。“人”字,后代學者普遍認為應為“天”字,即天道、天意。解《詩》“使學者有所統一”,遵循“天”的統一哲學原理,以服務于大一統的政治文化建設需要。這里“經”成為了闡釋的“可以然之域”,闡釋的根本在“經”而不在《詩》。
更深層次上,“《詩》無達詁”說有兩層含義。(一)根據“經”與“權”,“常”與“變”的辯證關系,闡釋者要突破經典文本的文字界限,“借古喻今”,賦予經典新的理解。(二)相比于《春秋繁露·竹林》,“從變”納入了“從義”“一以奉人”的原則中。“義”指六藝大義。徐復觀說:“仲舒無達辭、無通辭之言……是他要突破文字的藩籬, 以達到其借古喻今, 由史以言天的目的。”[2]將對歷史、時代的認識統攝在天的哲學精神下, 以天道來言人事, 體現出“天不變, 道亦不變”的絕對權威和意志。
董仲舒用《詩》、引《詩》時也運用“《詩》無達詁”原理。例如 “采封采菲,無以下體(《鄴風·谷風》)”句:《竹林》篇用“取其一美,不盡其失”的興喻之意,采葉喻取其美,不采下體喻不記其失;旨在贊揚子反具有對百姓的仁愛體恤之心,即使背叛了國家。《度制》篇取其字面意,采封菲之菜僅采其葉即可,不要將根莖一起采去,此乃遺民以利。
面對不同語境和事項,借用《詩》的經典權威性來為天道政治儒學立名,似乎只有“《詩》無達詁”才能為相互矛盾的微言大義闡發提供合理性。
三、“《詩》無達詁”與《詩》學史
(一)“《詩》無達詁”的歷史淵源與背景
“《詩》無達詁”說并非董仲舒始創,可溯源至先秦的政治文化現實。《詩》的產生與流傳方式包括周代王官采詩和列國獻詩,例如“雅”和“頌”這類王權貴族的宮廷禮樂和祭祀用歌,賦予《詩》為王者觀風教、為后人垂范的先王政典功用。章學誠說:“古人不著書,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先王之政典。”[3]
《詩經》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權威地位可以說自西周初年周公“制禮作樂”之后漸漸確立。“而‘禮樂作為周代制度化的意識形態,是一個整體,對整個周代社會政治制度的建立和文化生活的形成均有著根本上的影響。”[4]因此《詩》是涵蓋制度、儀式、文化的綜合典籍。春秋至戰國先后發展出“賦詩”“引詩”活動,繼承《詩》的經典權威性并深化主觀維度,稱為“賦詩斷章”,明確記載于《左傳·襄公二十八年》,是春秋時代《詩經》闡釋的普遍原則。
可見,從產生起,《詩經》就被賦予特殊的意識形態和文化政治含義;其經典性和道德教化意味逐漸醞釀,促成了漢代《詩經》道德化政治化的思考習慣和審美形態。
根據西漢的學術文化現實,百家并進的環境消失,儒家在鞏固君權至尊和避免暴政的矛盾境遇中繁衍生存,生發出天人感應、災異示警等真理性認知。四家詩以“經”解《詩》甚至以《詩》為諫書,將政教闡釋落到最實處。因此,毛湛侯說,“漢代是《詩》經學化的時代”。
(二)《詩》學史視域下的“《詩》無達詁”評價與思考
“《詩》無達詁”說體現了董仲舒對《詩》的功能觀念。《春秋繁露·玉杯》曰:
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以惡服人也,是故簡六藝以贍養之。《詩》《書》序其志,……六學皆大,而各有所長。《詩》道志,故長于質……《春秋》正是非,故長于治人。⑧
此外,《史記·太史公自序》轉述董仲舒的關于《詩》的論述有“《詩》記山川溪谷禽獸草木北肚雌雄,故長于風”“《詩》以達意”。《詩》有“長于質”和“長于風”兩特點。“長于質”繼承春秋時代“詩言志”的傳統,其內涵包括作詩言志和賦詩言志。“長于風”繼承儒家“《詩》以載道”思想,指《詩》的道德教化作用。對于“詩”無達詁與“從變從義,一以奉人” 的六藝致用原則,變是對“引譬連類”的認可和肯定;“一以奉人”的義又是對“《詩》以載道”的發揚,“道”就是每個用《詩》人心目中的真理正道。
董仲舒“《詩》無達詁”說可以看成是闡釋型“用詩”行為,歸屬于“以經解《詩》、以用解《詩》、以諫解《詩》、以禮解《詩》和以美刺解《詩》”[4]。按照現代文學審美標準,這是理解與闡釋的局限性,但也是理解與闡釋的歷史性,更是西漢特定歷史境遇中《詩》學發展的真實性。這種先入為主的政教美刺的說《詩》理念和模式在中國詩學史上一直綿延不絕。“《詩》無達詁”說與所屬的漢代《詩》學經學化一道為《詩》學史貢獻了一段以政治教化歸旨釋《詩》的學者闡釋歷史,進而在中國傳統詩學領域衍生了更寬泛多元的意義。
注釋:
①(漢)班固:《漢書》卷五十六《董仲舒傳》,中華書局,1983年,第2523頁。
②(清)蘇輿撰;鐘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中華書局,1992年,第284頁。
③(清)蘇輿撰;鐘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中華書局,1992年,第46頁。
④(清)蘇輿撰;鐘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中華書局,1992年,第74-75頁。
⑤李有光:《中國詩學多元解釋思想研究》,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第206頁。
⑥(清)蘇輿撰;鐘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中華書局,1992年,第94-95頁。
⑦陳喬樅:《齊詩遺說考自序.續修四庫全書總76 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年,第1163頁。
⑧(清)蘇輿撰;鐘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中華書局,1992年,第35-36頁。
參考文獻:
[1][4]毛宣國. “《詩》無達詁”解[J].中國文學研究. 2007(01).
[2]徐復觀.兩漢思想史第2卷[M].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2001.
[3]《文史通義·易教上》[M].中華書局,1985,第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