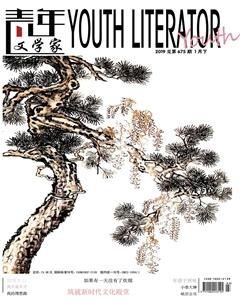例談佛教對宋代話本小說影響
摘 要:“說話”源于唐代,與佛教僧俗講淵源頗深;話本小說誕于宋代,正因始自于唐的佛教世俗化促進了以適應廣大市民階層欣賞趣味為主的宋話本小說的發展,佛教故事豐富了宋話本小說題材與內容,佛教輪回、禁欲等思想影響了話本小說的文化趣味、敘事模式。
關鍵詞:佛教;宋話本小說;影響
作者簡介:蘇換著(1990-),女,河南濮陽人,大理大學民族學專業2016級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宗教、研究領域家族佛教、佛教文學。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9)-03--01
一、佛教世俗化促進話本小說誕生
源于唐代的“說話”,從“說話”內容與形式看,僧俗講是“說話”藝人的主要表演形式。“俗講”只針對普通信眾,目的是通過講說讓聽眾為寺廟募捐;“僧講”不集俗人,主要對象是寺院內部僧徒。[1]269可知唐朝“說話”僧俗講均與佛教有密切關系,聽眾參與過程自然也對佛教產生一定的認同心理。這是佛教披著“文藝活動”的外衣行的是傳法和募捐的活動。此時的說話為了調動聽眾興趣,不得已也要努力進行藝術上的加工創造,此時的“說話”藝術性與文學性可謂是粗糙的。“說話”藝人表演需要底本,稱為“話本”,由于話本內容偏重于敘事,與小說性質相同,又稱“話本小說”。因用白話文寫成,也稱“白話小說”,話本小說出現在宋代。[2]244正是從唐代起佛教的世俗化促使了適應市民階層欣賞趣味的話本小說的產生和發展。
二、佛教故事充實了宋話本小說題材與內容
在《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中,“說話”者給定聽眾的是虛實兩種情形的結合,實是指陳玄奘其人其事是有史記載的;虛是指在詩話中加入了作者對取經所聞見的虛構,從而使得該詩話具備人文與宗教雙重屬性。將歷史上的人物加入到宗教神話傳說故事中加強作品藝術魅力的同時也提升讀者的欣賞趣味。[1]271《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在中國整個文學發展的歷史中具有明顯承前啟后的作用。所謂承前,一是指此故事對佛經內容的承襲,二是指對以前文學作品中類似故事的借鑒。如其中“人大梵天宮第三”中的“毗沙門天王”一段,則是出自《毗沙門儀軌》及《北方毗沙門天王隨軍護法儀軌》這樣兩部佛教經典。
三、佛教場所開拓了話本小說敘事空間
南宋說話除在勾欄瓦舍作場以外,還在寺廟等處作場。明人編輯的話本小說總計或選集中收錄到的宋代話本小說有《西湖三塔記》(《清平山堂話本》)、《白娘子永鎮雷峰塔》(《警世通言》卷二十八)等,均涉及佛教場所,且是宋代有名寺塔。[3]204話本小說事件發生地點的真實性,往往更能提升文化修養不甚高深的市民階層的欣賞心理。
四、佛教僧侶階層拓寬了宋代說話藝人隊伍
《都城紀勝》載宋代“說話”主要有“四家”:小說、說鐵騎、說經、講史書。[1]270其中與佛教淵源較深的是說經。“說經”類包含“說諢經”與“說參請”兩種,說經,謂演說佛書。說參請,謂賓主參禪悟道等事。[3]137說參請的說話藝人有喜然和尚等。說諢經的有戴忻庵。可見說經藝人除了出家僧人或可還有信佛崇佛的在家居士。在《西湖老人繁勝錄》中,說經、諢經的說話藝人也有女性,如陸妙慧(原注:女流)。[3]130《醉翁談錄·小說開辟》列舉的《陶鐵僧》,[3]217《花和尚》、《簡帖和尚》[3]218均以佛教僧人為話本主人公,突出了宋朝佛教的興盛豐富了話本小說人物的形象,《簡帖和尚》描寫僧人騙人妻室,無疑反映了宋朝由于統治者對佛教徒的驕縱導致僧侶階層惡性膨脹和為非作歹的社會現實。[3]222
五、佛教思想滲透話本小說文化內核
宋代是一個崇道重儒尚佛的時代。最高統治者對于佛教采取扶植的政策。佛教在宋代得到大規模發展,佛教也為這個階段的中國文化以及話本小說帶來了極大影響。因果業報與輪回思想深深影響了神怪類話本小說的創作。[4]50
宋話本小說中勸人戒淫戒色的說教,符合佛教“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的禁欲思想。《寶文堂書目》著錄的《三夢僧記》寫主人公吳山在病中曾三次夢見水月寺僧,該僧曾因犯色戒自縊身亡,要拉吳山去做替身,[3]215這染上了勸誡世人警戒色欲的佛教思想,以水月寺為故事發生地點,更突出世間男女執著的癡情怨意便如水月般虛無縹緲。
《五戒禪師私紅蓮記》多處表現出南宋說話人聲口,文中提到的撇骨池竟然是宋代浙右民間火葬后撇骨灰的池塘,[3]235可見當時浙右民間深受佛教火葬習俗影響,從側面也反映出佛教文化已深深滲透民間,佛教的大肆興盛必然影響到下層民眾的意識形態,而話本小說又是最能迎合處于底層階級社會的市民大眾的欣賞趣味,這就不難理解宋代佛教題材話本小說興盛的原因了。《五戒禪師私紅蓮記》將北宋大文豪蘇軾以及與其交往密切的詩僧佛印二者的前生假托為杭州凈寺兩個高僧,雖然小說也滲透著佛教戒色禁欲的思想,但從中也看出佛教輪回的三生三世世界觀、宇宙觀已開拓了話本小說敘事的時間與空間,從而使得小說敘事情節更加曲折有致,耐人回味的同時更能激發讀者的閱讀興趣。把歷史真實人物托幻于佛教題材的話本小說雖不免荒誕,但也透露出宋代士大夫樂于與僧人交往的生活情趣。
可能為南宋作品的《花燈轎蓮女成佛記》[3]236在小說開頭便點出詩句是大宋皇帝宋仁宗做的,這就給說話人公開宣講佛教思想故事戴上了一頂合法的官方帽子,從中也可看出宋代佛教興盛離不開最高統治者的大力扶持與認可。小說中提到司公念攔車詩賦,這是宋代民間一些地區比較流行的障車婚俗的記錄,攔車詩賦無疑指的就是敦煌文中保存較多的障車文。藝術來源于生活,這是一部記敘女性虔誠信佛并得到佛果善報的小說,突出了父權社會尤其是代表封建思想桎梏的宋明理學出現的南宋時期佛教對廣大婦女的麻痹作用。
綜上所述,由于宋代統治者對于佛教的支持,使得宋朝民眾對佛教文化在主觀和客觀上皆有不同程度接受,亦令話本小說在形式和內容上均體現著佛教文化的痕跡,即“話本在形式上承襲了佛教變文的形式;內容上以佛教的因緣觀和報應觀為主要內容和結構模式。”[5]70-74同時,佛教故事、建筑、人物無疑豐富了宋話本小說的敘事題材,僧侶階層也擴充了宋代說話藝人隊伍。宋話本小說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佛教發展狀況。
參考文獻:
[1] 王連儒著.志怪小說與人文宗教[M]. 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 2002.
[2] 沈祥源編著.宋元文學史[M]. 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 2009.
[3] 蕭欣橋,劉福元著. 話本小說史[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3.
[4] 張一.宋元神怪類小說話本研究[D].南寧:廣西大學,2014.
[5] 張躍生.佛教文化和宋話本[J].寶雞文理學院學報,20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