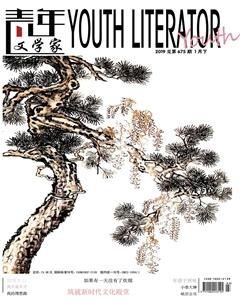從熱奈特敘事理論看帕特?巴克《鬼途》的敘事策略
摘 要:帕特·巴克的《鬼途》是1995年英國布克獎獲獎作品。本文運用熱拉爾·熱奈特的敘事理論對該作品進行敘事策略分析。文章從敘事時間和敘述聚焦兩方面切入小說文本,解讀巴克描寫戰爭的獨特技巧,揭示小說的創傷主題。
關鍵詞:《鬼途》;敘事時間;敘事視角
作者簡介:宋娟莉(1994-),女,甘肅通渭人,西安外國語大學16級研究生,研究方向:英語語言文學。
[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9)-03--02
法國結構主義敘事學杰出代表熱奈特在1972年發表的《敘事話語》中指明了“敘事”包含的三層概念:“敘事”(敘事話語,指陳述一個或一系列事件口頭或書面的話語)、“故事”(敘事話語陳述的真實或虛構的事件)、“敘述”(講述話語產生的敘述行為),以“敘事”為核心重點研究了“敘事”和與其相關的另外兩個層面—“故事”和“敘述”間的復雜關系。同時,他主張將敘事策略從敘事時間、語式、語態三個層面來衡量。
1995年英國布克獎獲獎作品《鬼途》是英國當代重要女作家帕特·巴克《重生》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小說共十八章,通過虛構軍官普瑞爾和歷史真實人物里弗斯兩條主線交替敘事來展開故事情節。奇數章描述了軍官普瑞爾返回戰場后的軍旅生活,并且從第七章開始以日記的形式給讀者展現了一幅幅殘忍的戰爭畫面;偶數章以愛丁堡的克萊格洛哈特軍醫院為主要場景,描寫了一群在一戰期間患上炮彈休克癥的士兵在后方軍事醫院接受治療的過程,讀者透過軍醫里弗斯的視角目睹了戰爭帶給士兵們身體和精神的巨大創傷。同時,小說運用大篇幅的插敘回顧里弗斯在太平洋西南部美拉尼西亞地區進行考察業的經歷,帶領讀者進入人類原初的生存現實,并進行跨時間、跨地域、跨種族的歷時對位思考。本文基于熱奈特敘事理論來分析小說的敘事時間和敘事聚焦,幫助讀者進一步地理解小說的戰爭創傷主題。
1.敘事時間的運用
在敘事時間上,熱奈特從時序、時距、頻率三方面分析了敘事話語和故事事件的不同,總結出了文學敘事在時間處理上的一套具體方法。
1.1時間倒錯
熱奈特指出“時序”是事件在敘事中排列的順序。通俗講,就是故事時間在敘述時間上的排列關系,常見有時間倒錯、預敘等敘事手法。熱奈特將“時間倒錯”定義為“故事時序與敘事時序之間各種不協調的形式。”(1990:14)《鬼途》中的時間倒錯主要有士兵們在接受里弗斯談話治療時,通過回憶講述炮彈休克癥的由來。士兵溫斯貝克在行兵途中因殺害俘虜而患上了臆想癥;普瑞爾在戰場上無意中發現一只被炸飛的眼睛,精神崩潰后出現了失憶失語等癥狀。種種創傷性經歷都是通過回憶式倒敘的方式真實地呈現在讀者面前,使得敘事內容更加完整。另外時間倒錯也體現在醫師里弗斯對美拉尼西亞經歷的回憶敘述。在醫治士兵的同時,里弗斯夢回以戰爭文化為主的原始部族,在那里一旦戰爭被禁止,部落就會了無生機。巴克把這一部分插敘到小說中使得內容更為豐富,引發讀者對戰爭更深層次的思考。
1.2時距
時距是故事真實發生的時間段與敘事的時間段之間的對比。熱奈特根據兩者之間的比較,將時距分為四個類型:概要(敘述時間短于故事時間)、省略(敘述時間為零,故事時間無窮大)、停頓(敘述時間無窮大,故事時間為零)和場景(敘述時間基本等于故事時間)。《鬼途》中最為顯著的時距則是場景。依照熱奈特的看法,最常見的場景是人物對話。而小說中醫師里弗斯采用的是“談話療法”來治愈士兵,因此文中有大篇幅的文本是軍醫與士兵之間的對話。這些對話是里弗斯和讀者了解創傷性經歷最主要的途徑,對話讓創傷細節得到了還原,迫使讀者身歷其境得感受創者的痛苦與壓抑。
1.3頻率
頻率問題指事件發生的次數與敘述這個事件的次數之間的關系。依照這種關系,熱奈特區分了三種方式:單一敘述(敘述一次發生過一次的事件),概括敘述(敘述一次發生過多次的事件),重復敘述(敘述多次發生過一次的事件)。具有創傷主題的《鬼途》最具特色的便是重復敘述,這里的重復指的是創傷事件的重復。這與創傷后壓力癥有著密切的聯系,患者頻繁地受到噩夢和幻覺的騷擾。盡管這些患者努力控制自己痛苦的回憶,不讓它浮現腦海,但是這些痛苦的經歷卻以噩夢或幻覺的方式多次重現。士兵溫斯貝克由于在戰場上殺死了一個德國俘虜,從而患上了臆想癥。“每晚都做噩夢,即使夢醒之后他也會看到那個已經死去的德國犯人站在他的床前,而且,每次出現都比前一次變得更腐爛,聞起來更臭。更糟糕的是,他甚至開始感覺到自己身上也散發著可怕的惡臭。而且他總認為別人會聞到他身上根本不存在的臭味。無論別人怎么告訴他,他的身上根本就沒有臭味,他還是盡可能地避免與他人近距離的接觸。”(劉胡敏,2008:70)創傷事件通過軀體語言多次的重現反映出戰爭帶來的創傷是無法治愈的,揭露戰爭殘酷的同時喚起人們對戰爭的深入思考。
2.內聚焦為主的敘事視角
熱奈特在《敘事話語》中采用了“聚焦”一詞,他根據敘述焦點對人物的限定程度不同,把敘事視角分為零聚焦型(敘述者比任何一個人物知道得都多,即全知的敘述者)、內聚焦型(敘述者知道的同某個人物一樣多)和外聚焦型(敘述者知道的不比任何一個人物多)三種。內聚焦則是小說《鬼途》采用的主要視角。
2.1第三人稱內聚焦
前文已提到,《鬼途》是兩條敘事線交替進行的。奇數章的敘事線描寫的是軍官普瑞爾返回戰場后的軍旅生活。而且在第七章之前是以人物普瑞爾的視角給讀者展現返回前線之前所做的準備。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普瑞爾去女朋友莎拉家的畫面。通過普瑞爾的視角我們了解到莎拉是軍工廠里的普通女工,看到了她那因硫磺而發黃的床單。跟普瑞爾一樣,我們也好奇莎拉蠟黃的皮膚在戰前是否也是健康粉嫩的。可以看出一戰期間男性奔赴戰場,女性成了主要勞動力在軍工廠生產軍工用品。惡劣的工作環境嚴重摧殘著女性的身體,使他們淪為戰爭機器的一部分。可見不管是前方浴血奮戰的士兵還是后方軍工廠里的女工都是戰爭的犧牲品。
此外,偶數章敘事線也是以人物里弗斯的視角來展開的。讀者借助軍醫的眼睛目睹了士兵們精神和肉體上的痛苦,當他將“治愈了的”士兵送往前線時,明知是徒勞的但出于職責不得不服從命令,通過內聚焦讀者可以感受到里弗斯的內疚與煎熬,正因如此,他也染上了創傷后壓力癥,變得口吃而且經常做噩夢。同時讀者跟隨他進行了一趟原始部落之旅,體驗當地的非正常死亡儀式,通過對比引發人們對人性和戰爭間關系的追問。
2.2第一人稱內聚焦
小說普瑞爾這條敘事線從第七章開始便是以日記的形式展開的。日記中普瑞爾通過第一人稱“我”記錄了一戰結束前夕前線大反攻的情況,真實地再現了戰爭給人類帶來的災難和痛苦。讓讀者直面觸目驚心的戰爭場景,眼睜睜看著士兵們一個個踏上鬼途。同時讀者可以直接接觸人物細致復雜的內心活動,“我真心認為如果戰爭再進行一百年,另外一門語言將會產生,這門語言是可以用來描述轟炸聲或是索姆河上空炎熱八月天里蒼蠅的嗡嗡聲。沒有言語可以用來表達看到太陽升起來時我的感受。”(Barker,1995:198)可見,戰爭帶來的創傷是無法言說的。巴克運用第一人稱視角極力地控訴了戰爭的殘酷。
《鬼途》采用前方士兵和后方軍醫兩個不同的視角,全面真實地再現了一戰的血腥場景,并運用回憶倒敘、重復敘述等的方式揭示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給人類社會所造成的心理恐怖和精神創傷。帶領讀者從多角度深入領悟小說深刻的內涵,認真思考戰爭給人類帶來的災難。
參考文獻:
[1]Barker, Pat. The Ghost Road [M].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5.
[2]程瑤 . 熱奈特敘事理論[J]. 文學評析,2009(5):75-76.
[3]劉胡敏. 試論巴克《再生》三部曲對‘創傷后壓力癥的描寫[J]. 華南師范大學學報, 2008(2).
[4]熱拉爾·熱奈特 . 敘事話語[M]. 王文融,譯.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