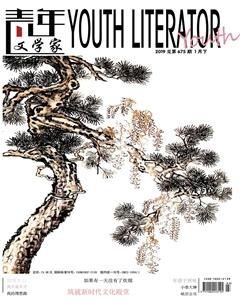《大偉人江奈生?維爾德》中亨利?菲爾丁的濟貧思想
摘 要:亨利·菲爾丁是一位熱衷改善社會制度,心系底層人民生活的現實主義作家,在小說中就借用了“大偉人”這個角色披露了英國因濟貧問題治理不當,流民和貧民迫于環境壓力成為強盜而滋生犯罪行為的現實,從而間接提高了社會治理成本;在治理方法上,由于強盜的類型不盡相同,只有分門別類實施接濟和安置這些人才能提高社會救助效率;從根源上看,兩位主角間的對立思想就強調了濟貧本身的價值,因為救濟貧民所產出的價值遠高于政府事后用于治理犯罪的消耗。因此社會的和諧共榮不僅需要貧民的道德自救,更需要制度的規范實施和符合人性的濟貧思想。
關鍵詞:菲爾丁;大偉人江奈生·魏爾德;濟貧
作者簡介:鄭孟娜(1995-),女,南通大學外國語學院研究生在讀,研究方向:英語語言文學。
[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9)-03--02
一、失敗救濟與貧民困境
17世紀前期,許多無業游民仰賴慈善救濟院為生,這不僅導致各地濟貧支出的增長和濟貧稅的提高,還使得慈善救濟院成為了社會不穩定的因素之一。因為人員管理以及人群分類復雜,而且還會使得人均救濟資源變少[2]。英國的貧困問題反復持續發生,但從未根本上解決過。畢竟在不允許奴隸存在的自由民族中,最可靠的財富就是眾多的勤勞貧民[3]。但也有抱有人文主義觀念的人,伯利就指出:“每個人都不能泯滅了道德的范疇……,如果在教區濟貧院雇傭貧民,就將極大地促進英國的商業、財富與和平[4]。”菲爾丁很贊同此類觀點,他也不止一次地提到貧民應該潔身自好,規避各種奢侈消耗和陋習。不管是出于道德考慮,富人對窮人得具有社會責任感;還是出于法律考量,貧民是可利用的潛在勞動力。
小說的主人公是以歷史的真實人物為原型寫成的,江奈生·魏爾德(1682-1725)是一個深知自己富有能言善辯、運籌帷幄的才能并借此偷蒙拐騙,實行自己的巧妙犯罪的人。勃里格斯認為,窮人的性質分類復雜,在緩解貧困的問題上,政府所能做的事情是有限的,經濟政策與社會政策不可能永遠朝著同一方向發展[5]。“大偉人”之所以能夠橫行霸道肆無忌憚地行騙和掠奪財富,不僅是因為他的天賦,高超的演技和敏捷的應變能力,還“得益于”當時英國社會的對窮人和失業人口的管理混亂。除長期固有的貧困問題外,圈地運動使英國大量人口失去土地成為流民、罪犯。正如芒圖所言:“一部分農村人口像被從曾經養活他們的土地里拔出來似的[6]。”他們有人成為了廉價的勞動者,也有人成為了流民,甚至是罪犯、強盜。社會悲劇的一方面是“大偉人”的本性使然,對于“掠奪”的天賦和從不“給予”的習慣;另一方面則是當時的社會并沒有給勤勞的貧民足夠機會去養活自己,社會的不安定只能把他們推向犯罪的邊緣。兩大因素都讓魏爾德在貧富差距懸殊,濟貧法律不完善,社會救濟不夠深入人心的社會現狀中如魚得水。
二、等級分類與有效濟貧
在菲爾丁提出關于對窮人的分類前,政府就實施了勞動救濟和區別救濟。主要有:無能力的貧困者,依靠社會的救濟;有能力且愿意工作的貧困者,給予適當的安排,學習社會上的職業技能;有能力但是不愿工作的人,應該強迫他們成為學徒或者仆人,若是不愿意,讓他們蹲監獄直到服從[7]。在強盜思想上和魏爾德不謀而合的人,拉·魯斯,別稱伯爵。一有閑錢就拿去賭博,常年奮斗在賭桌上,某次大贏特贏之后被魏爾德的同伙搶劫“伯爵只好把在賭場上很斯文地贏過來的錢讓人家暴力拿走[1]”。即使被幽禁,伯爵也不忘賭博“杯盤散去,小姐們剛退席,伯爵就提議賭錢,座上的客人立刻都表示贊同[1]”。對于民眾自身來說,首先一般良民不該有奢侈的愛好,過于奢侈就是道德的腐敗,如娛樂消遣、嗜酒、賭博。菲爾丁認為昂貴和頻繁的娛樂消遣是不必要的,而且敗壞了社會風氣,藝術家和勇士都會變成流民,思想簡單和意志薄弱的人會變成乞討者[7]。而且從12到60歲的人都該在社會上被人雇傭,但要減少勞務的工資,降低開銷,以便雇傭更多的窮人[8]。若是有能力勞動但卻刻意逃避社會責任一心想著不勞而獲的懶人,只有被關進感化院直至屈服才能改造才能奏效。另外對于犯罪者,若把他們驅逐出境、絞死以及游街示眾還不如考慮一下公共利益,改造他們之后重新投放回社會補充勞動力。
由于濟貧實施的方法落后和力度不夠,魏爾德在自己做起強盜的同時也利用了在困境中兩難的流民和貧民。像馬里布恩認為“……他也不必裝得比別人更正派些。可是叫他去殺人,他無論也不肯干,那是最兇惡的罪,因此,一定會遭到天罰……[1]”。因此魏爾德也不需要這樣“半吊子的流氓”,不久他就被控告處以死刑。其中還有一個叫布留斯金,他本身是個屠戶,以宰牛羊為生,但“在他看來,一般轉移財產的買賣方式太麻煩了,因此,他決定放棄經商這一行……于是,他就攜帶武器入了伙[1]。”正當的謀生方式再也進行不下去的時候,犯罪就成了唯一的選擇。這類人要是放著不管,他們的自我道德約束只會越來越松懈直至走到絕路。由于一般貧民缺乏領導和歸屬,因此集中收納進濟貧院和統一改造,簽訂合同出租勞動力才是最有效的方式。
在社會等級制度明確和貧富貴賤一目了然的情況下,菲爾丁認為窮人和濟貧院的類型也應該要分個清楚,既能方便管理又能讓他們各司其職。其中可利用四種有效的政治力量:健碩的身軀、智慧、金錢以及武器。主要是“棍棒加面包”政策,殘酷的血腥法令與扶危濟因措施同時并舉,在一定時期內取得了某些效果[9]。在對人口的利用方面,菲爾丁可謂是一個物盡其用的經濟家,他曾寫道:“真實的原因是……這些窮人找不到工作或合適他們的工作,是因為他們沒聚到一起來。”他在十八世紀的英國就想建設人才市場(labor pool)了,只不過這只針對窮人開放。此外他還具有勞務合同的概念,一個在濟貧院接受救濟的人,可以到外面去參加工作,到勞務期滿之后,必須要回到濟貧院直到有下一份工作[7]。但這一切,都需要走法律程序和有相關的書面文件,否則就是非法雇傭。菲爾丁非常強調要看住抑或是監視他們(窮人),送往看管權利最有效的“福利機構”——濟貧院。
三、強盜思想與貧民價值
江奈生·魏爾德時一個奸詐又聰明,輕諾寡信,無惡不作但又有人性的弱點。同時他具備完善系統的政治觀點和為人處事之道,不僅是對自我的才能,也會對社會現狀進行思考。“大偉人”的強盜哲學理論在他小的時候就已經潛移默化的生根發芽了。“我記得上學堂的時候聽人念過幾句詩:空中的飛鳥,田里的畜生,它們都不是為自己而工作的。同樣,莊稼人、牧人、織布的、蓋房子的、當兵的,都不是為了自己,都是為了別人[1] ……”因此,他堅信從他人地方竊取勞動果實是正常、合理的。這套邏輯不僅能適用在大自然法則中,同樣也能運用到人類社會中。那些莊稼人、牧人、手工勞動者都是“牛羊”,他們的“主人”把榨干他們的勞動成果后,又循環往復壓榨剩余價值,最后還逃不過任人宰割的命運,同時也淪為了魏爾德實行“偉大”行徑的工具。魏爾德毫不客氣地“拿走”一切,從來都不“給予”,難道不是對濟貧最大的反諷。首先我們要清楚,即使窮人和富人的差距固然存在,但“掠奪”讓平民被“變窮”甚至被“餓死”,而濟貧法只是為彌補這樣的后果去制定、實施和修繕。菲爾丁關注的并不是魏爾德這個強盜,而是強盜行為本身,就像是他并不關注這一個“偉人”,而是所有“偉人”。看輕對占有社會比例最高的大多數是小說最大的諷刺,也是對道德和法律的褻瀆。
哈特弗利在書中就是一個不可多得的善良人的典型,他誠實但愚蠢,富有道德感但又愚昧無知。哈特弗利是個少數不多的正面人物,善良就是他的本性,堅持道德就是他的信仰,但在文中更像是光芒過甚魏爾德的陪襯。作為一個誠實的納稅人、優秀的丈夫、正直的公民,可以讓社會現狀變得安定可控的良民,但這類人太少了,若通過合法途徑,利用道德教育的方式把流民、貧民變成創造價值的良民也太慢了。菲爾丁不像是其他理論家如阿瑟·揚:“除了白癡沒有人不知道必須使那些勞動下層階級處于貧困之中,否則他們將不會勤奮工作[10]。”他認為窮人中也是有一部人有著優秀的品質,十分符合接受濟貧的道德標準,算是“合格”的平民。哈特弗利是菲爾丁眼中善良的“小人物”,而且菲爾丁是肯定他們的,贊揚這種樂于助人,會去接濟遇到貧困無助的人。哈特弗利又是一位理想的被救濟者,他的善良本質,自食其力的意志,崇高的價值觀和實際的道德行為都符合一個被救濟的人的形象。同時哈特弗利對社會勞動產出作出的貢獻更大,作為一個貧民的價值要遠高于一個“偉人”。兩主角間的兩種對立思想的較量就是犯罪治理與根源上緩解犯罪的對比。一般貧民在面對衣食堪憂的情況下,得不到政府的救濟,只有犯罪的成本最低且收益最大,若貧民有了適當的救濟,也不會去觸碰最后道德的底線。相比與后期治理罪犯問題不如從根源入手預防流民、貧民成為罪犯。
日漸惡化不可控的社會環境、貧民分類含糊難以對癥下藥的救濟措施以及忽視犯罪的預防和貧民的價值都造就“大偉人”的一生。因此重視濟貧思想,對貧民的道德約束、人文關懷以及依法救濟正是菲爾丁對英國福利社會的終極理想。
注釋:
①負債人監獄是給無力償還債務的人的監獄。在19世紀中之前,負債人監獄是解決欠債的常見方法。透過少量的金錢,負債人便可取得一定程度的自由。
參考文獻:
[1]亨利·菲爾丁:《大偉人江奈生·魏爾德傳》,蕭乾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2]丁建定:《英國社會保障制度史》,人民出版社,2015,89-120
[3]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74頁。
[4] Paul A. Slack. Poverty and Policy in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 Longman. 1988. pp.12-20
Parkes Christopher. Studies in the Novel. Joseph Andrews and the Control of the Poor.
[5]阿薩·勃里格斯《英國社會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p126
[6]保爾·芒圖:《十八世紀產業革命:英國近代大工業初期的概況》,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140-141頁。
[7]HenryFielding."A Proposal for Making an Effectual Provision for the Poor." 1753. Ed. William Ernest Henley. The Complete Works of Henry Fielding: Legal Writing. Vol. 13. London: Frank Cass, 1967. 200-294.
[8]HenryFielding. "An Enquiry into the Late Increase of Robbers." 1751. Ed. William Ernest Henley. The Complete Works of Henry Fielding: Legal Writing. Vol. 13. London: Frank Cass, 1967. 5-127.
[9]尹虹:“16世紀和17世紀前期英國的流民問題”,《世界歷史》2001(04):30-37. 11.
[10]丁建定:《英國濟貧法制度史》,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