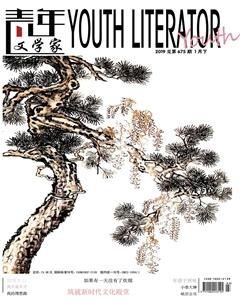在“康德”語境下對“后現代”藝術的反思
摘 要:在“后現代”話語體系中的藝術雖然在其創作方法上不守常規,別出心裁,獨自構建一條全新的創作模式,但其藝術作品往往以奇異、荒誕甚至惡心的形象出現。因此,引起了當代人基于傳統理念上對于“后現代”藝術的強烈反思。在后現代這種“讓一切事物都有可能成為藝術”的創作模式下,藝術已經逐漸從高雅走向了平凡、大眾,未來的發展不得而知。所以,回歸康德,回歸“美”的藝術,成為當今藝術界熱議的話題。
關鍵詞:“后現代”;康德;“美”的藝術
作者簡介:陳崢旭(1993-),男,漢族,江蘇宜興人,江蘇師范大學藝術學理論專業,研究方向:漢畫像研究。
[中圖分類號]:J0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9)-03--03
導語:
康德美學是西方美學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它從鑒賞判斷的角度揭示了美的主體性以及真、善、美的關系問題,無非是對于真、善、美本質最完美的闡釋。同時,后現代藝術中所表現的“美”的特征嚴重脫離了康德美學中對于美的構建和解釋,呈現出“反康德”,“反美學”的趨勢。傳統美學與藝術的主體位置產生了嚴重偏移,藝術主體性被當代花樣繁多的媒介所邊緣化。“然而大眾的,個性的主題所帶來的刺激和悅目的表面浮華的形式,卻帶不走藝術家的內在智慧,修養,和獨立而艱難的精神探索。”[1]故,喚醒藝術家自我意識,重塑藝術的精神面貌,讓美和藝術回歸康德,脫離當下“畸形”的藝術發展,尤為重要。
一、后現代藝術的“界限”
后現代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美術界最時髦的話題,但是后現代藝術這個源自于西方的美學專業性用卻沒有一套屬于自己權威性的理論支撐,而被賦予了歧義性和多義性。無所不包,無所不有的后現代宛若一個雜貨鋪,許多藝術家到那以后,盡顯潑皮無賴式的玩世不恭、道德淪喪和崇高精神的喪失。
杜尚的《泉》,這個作品雖然已經過去了大半個世紀,可是這個具有“革命意義”的先鋒藝術行為,至今的影響還沒消沉,反而愈演愈烈。雖然當下人們對
《泉》這件作品的認識已經從其正面轉向其消極一面,但仍然有多數當代歐洲藝術史中將《泉》列在突出的位置上,否則就可能造成藝術史的缺失,由此可見,這件藝術作品在藝術界中舉重若輕的地位。作為后現代的“開山之作”,杜尚和《泉》的影響力可見一斑,不過,筆者認為,這種影響力的體現僅局限于杜尚和泉的“獨一無二”性,杜尚創造力的別具一格與《泉》新奇的外形特征成功吸引了當時人們的關注,勾起了人們心中對于藝術的“期待視野”。確實,不難想象,在那個人們看慣了現代主義潮流與“藝術終結”論萌芽的年代,杜尚的這次偉大的嘗試會為“藝術”創作再指引出一條新的道路。
杜尚站在現代主義運動的“內在能量”逐步消耗的時代邊緣宣布:“現代主義階段已經結束,成為了歷史”。后現代藝術在而后的50多年內呈雨后春筍般飛速發展。達達主義,未來主義,象征主義,波普藝術,激浪派藝術等藝術門類的出現無不宣揚“后現代”所彰顯的獨特個性和它們站在“新”的語境中別樣的世界觀。藝術的特征和本質內涵在這些“后現代”藝術門類中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拿波普藝術和激浪派藝術來說,波普藝術即“pop art”,“pop cultural”,意在說明,“這種藝術是一種‘大眾傳媒的產品,而并非是借用了流行文化的藝術作品。”[2]對于這種流行而言,它處于高級文化和通俗文化的比較之中,可用于描述對于“人們為自身而制造”的文化,這就意味著各種大眾傳媒通過“藝術商業化”所得到的利益增強。藝術不再是“天才”的專屬,成為了人人都可以為之付諸的游戲。“激浪”派中“激浪”一次有著抹去“界限”的意思。在“激浪派”藝術中的“行為”和“事件”的藝術形式,實則就是一種“造反精神”,這種“造反精神”使得藝術不再擁有品味的專業化,而走向非專業化的道路。“激浪”所要表現的流動與變化的主題究其根本是要破壞藝術與生活中既定的中產階級的規律程序。并且,激浪派藝術品所采取的從音樂、舞蹈、表演、詩歌、電影、出版物到郵寄物這些變化的形式,都指向一種宗旨——讓藝術從“高高在上”轉化為平常,讓藝術“超離生活”。[3]
二、后現代藝術之“美”與康德美學的背離
“什么是美”,“美是什么”。這兩個看似一致的問題實則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問題,前者是一個“歸納式”的提問范式,這里的“什么”可以窮盡任何使其成為美的自身的事物;后者則是“演繹式”的提問范式,這里的“什么”實則是一個理論的抽象性問題,即對于“美”的本質的提問。
“為了判別某一對象是美或不美,我們不是把[它的]表象憑借悟性連系與客體以求得知識,而是憑借想象力(或者想象力和悟性相結合)連系于主體和它的快感和不快感。鑒賞判斷因此不是認識判斷,從而不是邏輯的,而是審美的。”[4]所以。從這里可以看出,美是一種不自覺的沒有目的性的與自身的感覺的事物。我們無法有意識地,有目的地去特意發現美的存在,如果我們通過自己的某些行為或方式想要對于美做出詮釋和客觀具象化的表現,這無非是錯誤的,這些過程都不自覺地給美摻和進了邏輯思維與理性辯證的因素,因此不是鑒賞判斷,即不是美的。想要獲得真正的美和真正的美感體驗,只有通過主體所感受到的快感和不快感來區分,快感,則是美,不快感,則不是美。此外,在康德美學中,美又是道德的象征。“康德提出‘美是‘無目的的合目的性,乃是說明美在直觀上是形式的,但在本質上絕不是空洞的、孤立的,而是積極指向道德——即終極目的”。[5]康德認為藝術的形式是一種融合著精神理念的形式,是體現在外觀中的理念,它要合乎人們提高文化修養和道德的目的。他反對一切和道德諸觀念相分離的藝術,認為這類藝術只是用來消遣。“人們越利用它們來消遣,就越會需要它們,以便驅散心意對于自己的不滿。”[6]這樣就會使人陷入無盡的貪婪和欲望之中,藝術也就喪失了自己的審美價值。最后,“美”還是無功利的,“一切的利害感都敗壞著鑒賞判斷并且剝奪了它的無偏頗性,尤其是當它不是像理性的利害觀念把合目的性安放在快樂的情感之前,而是把它筑基于后者之上;這種情況常常在審美判斷涉及一事物給予我們以快感或痛苦的場合時出現。”[7]利害感會給鑒賞判斷一種企圖滿足人的欲望的空間,讓我們認為我們是為了利害才對某種藝術或者某種美表現出激動和刺激的情態,來混淆我們感受到快感或痛苦時對于“美”的純粹性的理解。
然后,反觀“后現代”藝術,在反映“美是什么?”的問題上卻顯得雜亂無章,軟弱無力。其一,在其藝術形象上看,扭曲、變形、荒誕、驚奇甚至惡心,暴力等與傳統審美觀念背道而馳的消極性因素層出不窮。與康德美學所闡釋的“給人以快適”,“無功利的”,“無目的的”,“代表道德”的“美”的特點截然不同。“后現代”藝術家們自稱站在世界的前列,一邊表現出抨擊傳統藝術的行為方式一邊又想著如何界定“后現代”藝術的邊界,以及“后現代”藝術與傳統藝術之間的某種聯系,企圖蒙騙大眾的視野,將“后現代”藝術形象與傳統混為一談。當然,筆者以為,這有其好的一面,也有著消極可怖的一面。造成這種局面主要是出于對于藝術創作的出發點不同。傳統藝術發展至今,已經逐步從興盛走向了衰弱的過程,“后現代”的出現無疑讓藝術創作有了新的視野,新的創作方式,新的發展方向,所以在很多藝術家眼里,這無疑是一個重新振新藝術的絕佳機遇,它們寄希望于“后現代”這個時代契機,讓藝術從“死亡”中涅槃重生。這就是基于“后現代”藝術家在“藝術創作”的契機之上對于藝術的重新認定和擴展。但是往往在其進行“后現代”藝術創作的時候,忘卻了“藝術”與“美”的主體性和本質,偏離了藝術發展的正軌,導致藝術的發展產生了消極的一面。
其二從藝術理論中看,維特根斯坦在其《家族相似》中指出:“藝術是不可定義的,藝術的本質無從尋起。”他以他的家族相似論和開放概念觀為支撐,試圖證明藝術的定義是無法實現的。威廉·肯尼克、保羅·齊夫、莫里斯·魏茨等理論家認為過去的藝術理論試圖從紛繁復雜的藝術品中提取一個共有的屬性,并認可這種屬性或者特征是獨一的而且普遍存在于藝術品之中。而當蘇珊朗格將藝術品歸結為一種情感的形式,克萊夫·貝爾把藝術當作有意味的形式,魏茨則指出憑借單一的條件所支撐的藝術品是不堪一擊的。“后現代”藝術理論家之間的相互斗爭和批評致使后現代的藝術思想很多,但是卻始終沒有誕生令人信服的關于后現代“藝術本質”的系統性理論著作。筆者看來,雖然在“后現代”理論探索的過程中,我們不可否認藝術理論家對于藝術本質的追溯和無比可貴的探索精神。不過,這些人的初衷只是在于對“后現代”藝術的堅定與不放棄的態度,而并非基于傳統的藝術理論之上來評判“后現代”藝術的存在意義與其美學本質,所以始終無法找到“后現代”藝術與傳統藝術本質上相同或者類似的東西。在其理論建構的方法程序上,多以現代化的,科學的,邏輯的方法來對藝術進行“符號推衍”,在符號系統中,藝術已經不是研究的中心,而是成為了一種“科學符號”的附屬。故,此些對于藝術進行演繹的法門,不會讓藝術歸根于傳統之上,歸根于康德之上,只會使其背離康德,與傳統意義上的藝術和美愈行愈遠。
三、回歸康德——對后現代的反思
康德對于美學的貢獻,在于其理論出發點和理論成果都在于一個轉折時期,其理論發展成為德國古典美學,集古典美學之大成,從其批判精神出發,發展成為近代的非理性思潮。康德美學的影響力和豐富性與后世哲學的發展有頗有淵源。所以,只有懂得康德,才能懂得西方美學。
在現代社會飛速發展與巨大變革之中,藝術形式同樣也在隨著時代的演變而不斷地與時俱進。“現代工業社會的經濟利益思想不斷擠占人們的精神空間,人們的精神自由狀態也越來越多地讓位于以經濟利益及其規律所支配的秩序井然的社會精神狀態,因此,也導致了現代人在心理上承受過大的壓力,以及隨之而來的一些心理問題。”[8]反映在藝術形式上也表現出人們工作的繁忙和心理上的壓抑。如弗朗克·蒙克的一系列藝術作品。故而,藝術的回歸不但是對于藝術與美的本質的探索,還是一種幫助人們調整失衡心理、釋放心理重壓、排解心理困惑、建構和諧的精神世界的理想。
朱新建在《打回原形》中說:“藝術作為個人語言實際應當是排斥大眾的,是一個相對自我的游戲。”[9]朱先生的這番話其實是在指證當下的藝術亂象問題,“書里這種多少有些反現代、反社會傾向的觀點,被包裹在一種語言魅力之下,好像還挺容易被接受,并不令人感覺到被冒犯。”[10]朱先生所說的“反當下”,“反社會傾向”的觀點實則就是向我們提出了復歸傳統藝術的建議。
“美、審美和藝術歷史形態的發展變化,都是一個似乎‘之字形或螺旋形的路,都大體經歷了一個否定之否定的圓圈。古樸和諧的美是藝術最簡單、最抽象的規定性,也是藝術最早的歷史存在形態,經過近代偏重崇高美的兩極對立所造成的不和諧狀態,趨向于綜合統一為現代或當代的對立統一的和諧美的藝術,這是對藝術本質特征的更復雜、更本質、更深刻的規定性。”[11] “命歸于靜,靜曰復命”,藝術的回歸在哲學上來看是一個必然的過程,而只有經歷過這個“否定之否定”的過程之后,“傳統”與“后現代”藝術之間才會有所比較,傳統藝術所包含的某種不為人所知的精神才會真正被人所發現,傳統藝術的抽象、簡單的特征也才能更加被世人所珍惜。筆者認為,藝術回歸康德并非對于傳統藝術以及康德美學單純地形式,內容上的模仿和之前固有程式的一種延續,這種復歸應該是基于傳統藝術以及康德美學基礎之上再經過“后現代”思考之后對于藝術的再理解,再創造。其藝術精神應該繼承傳統藝術的美學造詣與之帶給人們的種種歡快感,擯棄“后現代”藝術消極的一面,展現出藝術積極上進的一面,在畫作形式上也應該多表現社會大眾良好的方面。
結語:
人們對于“后現代”藝術中所表現出的消極的方面產生了疑惑,所以才會對“后現代”藝術進行反思。反之,如果后現代一如既往良好地發展,沒有打破人們傳統上對于藝術的認識,人們也就沒有必要對其進行批判指責。當然,“后現代”的出現并不是一無是處,其對于人們對藝術本質的思考和對于藝術理論的挖掘以及藝術研究方法上的創新都提供了寶貴的經驗,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但是,“后現代”藝術與傳統藝術的背離使人們不得不重新審視康德美學中對于美與藝術的評價標準。復歸康德美學,讓藝術“葉落歸根”,在傳統的方向上不斷豐富自身的內涵,就是對于藝術的界定和藝術的發展最有效的幫助,更是我們對于藝術與美最發自內心的愛。
注釋:
[1]陳亞民:《康德美學的當代意義》,鄭州大學學報,2005年9月版,第38卷第5期。
[2]劉悅笛:《藝術終結之后》,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年9月版,第48頁。
[3]劉悅笛:《藝術終結之后》,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年9月版,第108頁。
[4][德]康德:《判斷力批判》,宗白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3年12月第1版,第34頁。
[5]陳亞民:《康德美學的當代意義》,鄭州大學學報,2005年9月版,第38卷第5期。
[6][德]康德:《判斷力批判》,宗白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3年12月第1版,第173頁。
[7][德]康德:《判斷力批判》,宗白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3年12月第1版,第55頁。
[8]秦曉春:《論康德美學的心理和諧思想及其現實意義》,廣西師范大學學報,2008年8月第46卷第4期。
[9]朱新建:《打回原形》,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2月第1版,代序第2頁。
[10]朱新建:《打回原形》,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2月第1版,代序第2頁。
[11]藝術學編委會:《后現代思考,藝術的本質與未來》,上海:學林出版社,2006年5月第1版,第81頁。
參考文獻:
[1]陳亞民:《康德美學的當代意義》,鄭州大學學報,2005年9月版,第38卷第5期。
[2]劉悅笛:《藝術終結之后》,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年9月版。
[3]秦曉春:《論康德美學的心理和諧思想及其現實意義》,廣西師范大學學報,2008年8月第46卷第4期。
[4]朱新建:《打回原形》,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2月第1版。
[5]藝術學編委會:《后現代思考,藝術的本質與未來》,上海:學林出版社,2006年5月第1版。
[6][德]康德:《判斷力批判》,宗白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3年12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