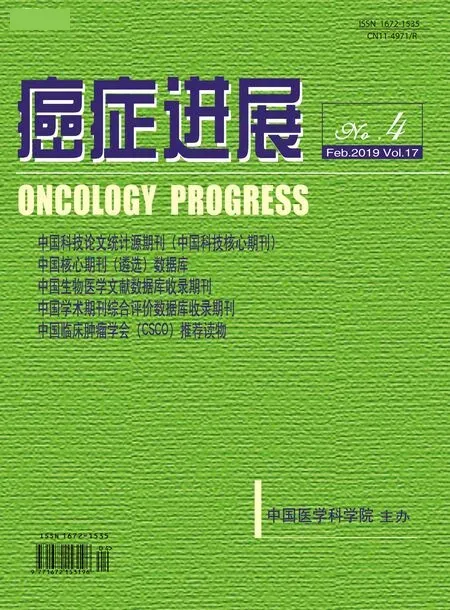cGAS-STING信號通路與腫瘤關系的研究進展
陳娟娟,張平安
武漢大學人民醫院檢驗科,武漢 430060 00
環磷酸鳥苷-腺苷酸合成酶(cyclic guanosine monophosphate-adenosine monophosphate synthase,cGAS)作為廣泛的DNA識別受體,能夠識別腫瘤DNA、病原體DNA、線粒體泄露DNA等而引發宿主防御功能。cGAS識別DNA后能夠催化合成第二信使環二核苷酸(cyclic guanosine monophosphate-adenosine monophosphate,cGAMP),隨后cGAMP活化干擾素基因刺激因子(stimulator of interferon gene,STING),促進Ⅰ型干擾素(interferon,IFN)的表達以調節固有免疫功能。一方面,Ⅰ型IFN能夠增強抗腫瘤細胞毒性T淋巴細胞免疫應答;另一方面,Ⅰ型IFN也能促進STING信號通路的激活,招募效應T細胞在腫瘤微環境(tumor microenvironment,TME)中殺傷腫瘤細胞。相關研究表明,STING信號通路可以通過腫瘤類型和免疫檢查點封鎖在天然抗腫瘤免疫中發揮關鍵作用[1]。然而,也有一些腫瘤能夠逃避這一信號通路所介導的免疫應答,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進腫瘤的發生、生長和轉移。因此,本文對有關調控STING信號的腫瘤治療途徑,以及將基于STING的靶向治療方法整合到組合療法中以獲得持久的抗腫瘤免疫應答等研究進行綜述。
1 天然抗腫瘤免疫應答
腫瘤細胞在生長過程中,經過多次分裂增殖,其子細胞會呈現出分子生物學或基因方面的改變,這一變化可使腫瘤細胞逃避機體的免疫應答,降低機體對抗腫瘤藥物的敏感性;同時,還可導致宿主針對腫瘤細胞產生相對低效的免疫應答。若能增強機體的天然免疫應答能力以清除腫瘤細胞,那將大大減少化療、放療帶來的不良反應。細胞因子,包括白細胞介素-6(interleukin 6,IL-6)、IL-10、腫瘤壞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和轉化生長因子-β(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TGF-β)等[2-3],在腫瘤生長和轉移的后期可以對其進行包括免疫逃避、血管生成和轉移前TME在內的調控。這些過程可以受IFN、細胞信號轉導及轉錄激活因子3(signal transduction and activator of transcription 3,STAT3)、干擾素調節因子 3(interferon regulatory factor 3,IRF3)、IRF7及核因子-κB(nuclear factor-κB,NF-κB)等多種因子的影響[4],尤其以Ⅰ型IFN最為重要[5]。Ⅰ型IFN可以在細胞因子的介導下對腫瘤的轉移產生促進作用,同時也可產生抗腫瘤免疫應答。研究表明,STING是Ⅰ型IFN重要的上游調節分子,可由IRF3及NF-κB核轉移信號轉導誘導Ⅰ型IFN的產生,最終促進腫瘤細胞和鄰近細胞表達干擾素刺激基因(interferon stimulating gene,ISG)[6]。雖然已經發現了多種細胞內DNA感受器,但體內敲除試驗表明核苷酸轉移酶cGAS是細胞質中感受雙鏈DNA(double-stranded DNA,ds-DNA)主要的、不可缺少的傳感器[7],當dsDNA被cGAS識別后,能夠催化合成cGAMP,隨后cGAMP激活STING,促進Ⅰ型IFN的表達以調節固有免疫功能。cGAS-STING信號通路不同于其他通路,它不通過蛋白質與蛋白質相互作用轉導,而是通過由cGAS催化合成的第二信使cGAMP轉導[8],然后直接傳遞至STING[9]。且cGAMP并不受限于固有的細胞信號轉導方式,并可以通過縫隙連接介導的信號轉導產生更廣泛的區域免疫應答[10]。
2 cGAS-STING信號通路與抗腫瘤免疫
當腫瘤細胞細胞質DNA泄露后,易被cGAS識別,激活強有力的下游IFN應答[11]。相關研究發現,微核在腫瘤細胞中普遍存在,當腫瘤細胞中的DNA損傷,染色體錯誤分離和細胞周期停滯引起微核泄露后,cGAS-STING信號通路即被激活[12],隨后機體表達大量Ⅰ型IFN,通過調節固有免疫應答來清除腫瘤細胞。而腫瘤細胞為了逃避這種DNA識別機制,則通過基因變異來破壞cGAS-STING信號軸并使Ⅰ型IFN基因座發生突變和缺失[3]。在人結腸腺癌和黑色素瘤細胞系中,腫瘤細胞能通過多種機制導致cGAS-STING信號轉導異常,包括STING轉移至高爾基體的信號傳輸中斷,cGAS和STING啟動子區域的超甲基化以及cGAS和STING蛋白表達降低導致的IFN和下游ISG的表達降低[13]。有研究證實了STING依賴性腫瘤細胞滲透的直接抗腫瘤作用,在前列腺癌小鼠模型中使用免疫排斥試驗,發現與注射后的野生型細胞相比,STING基因敲除的腫瘤細胞優先富集[13]。同樣該項研究也顯示,當敲除小鼠細胞內的STING時,其體內巨噬細胞吞噬作用降低[13],這表明STING除了能調節樹突狀細胞(dendritic cell,DC)及CD8+T細胞的功能以外,還能對其他免疫細胞群的功能產生影響。
隨著機體對DC-CD8+T細胞的交叉呈遞和啟動,浸潤的淋巴細胞能夠調節cGAS-STING介導的IFN表達。在體內試驗中,cGAS缺陷型小鼠體內DC表達IFN-γ的能力下降[14],STING缺陷型小鼠體內適應性免疫反應顯著受損,IFN-γ應答能力下降,腫瘤特異性CD8+T細胞浸潤減少,且出現細胞毒性功能缺陷型淋巴細胞[14]。機體能通過調節cGAMP的含量促進腫瘤特異性CD4+T細胞、CD8+T細胞、巨噬細胞及DC的浸潤,增加Ⅰ型IFN和ISG的表達[15]。過繼轉移實驗證實了cGAS-STING通路與淋巴細胞浸潤的相關性,在二甲基苯蒽(dimethylbenanthracene,DMBA)模型中STING缺陷型野生小鼠的骨髓能夠抵抗腫瘤發展[16]。已有研究表明STING能夠調節T細胞的表達,組成型激活的突變體STING會導致T細胞增殖下降,記憶表型偏移[17]。在前列腺癌細胞中,通過DNA結構特異性酶切割基因組DNA,可促使細胞質中DNA積累,隨后激活STING,表達大量Ⅰ型IFN,促進T細胞的免疫應答[18]。在急性粒細胞白血病(acute myeloblastic leukemia,AML)中,內源性cGAMP的合成促進了抗腫瘤免疫。此外,外源性注射cGAMP可以誘導惡性細胞凋亡,通過STING通路調節T細胞應答,增強抗腫瘤反應[19]。在腫瘤細胞中激活STING后其抗腫瘤細胞增殖和促進腫瘤細胞凋亡能力仍需進一步探索;如果激活STING后的這些免疫應答能夠在腫瘤細胞中實現,那么將有望通過調節STING信號通路來阻止腫瘤細胞的免疫逃逸。
3 cGAS-STING信號通路與腫瘤的發生和發展
Ⅰ型IFN應答能夠作為刺激腫瘤反應的關鍵誘導劑,且其上游cGAS-STING信號通路也可以在特定階段促進腫瘤的發生和發展。
在炎性結腸炎相關腫瘤小鼠模型中發現,STING缺乏與腫瘤發展的易感性有關,且小鼠體內IL-22以及調節性IL-22結合蛋白的表達均下降[20]。而在非炎性路易斯肺癌(Lewis lung cancer,LLC)小鼠模型中STING激活與腫瘤生長有關[21]。鑒于cGAS-STING在病毒感染中的明確作用,推測這條途徑可能與病毒誘發腫瘤產生有關;與此一致的是,STING缺陷型結直腸癌和黑色素瘤細胞對病毒感染的易感性增加[22-23]。另外,已知的病毒致癌基因人乳頭狀瘤病毒E7(human papilloma virus E7,HPV E7)和腺病毒E1A通過直接結合STING抑制cGAS-STING通路[24]。在HPV感染的舌鱗狀細胞癌中STING的表達和活化與調節性T細胞浸潤和IL-10分泌增加有關[25],STING缺陷型骨髓來源樹突狀細胞(bone marrow-derived dendritic cell,BMDC)表達的炎性調節蛋白IL-22結合蛋白減少[20]。慢性幽門螺桿菌感染是誘發胃癌的高危因素,它能引起體內STING上調和下游IFN信號轉導;然而,同一項研究還指出,胃癌患者的STING表達下降,且與腫瘤大小、發展和轉移相關[26]。
4 cGAS-STING信號通路與腫瘤轉移
cGAS-STING除了在腫瘤發生和發展中起作用外,還與腫瘤轉移有關。STING依賴性腫瘤的發展可以通過免疫性調節吲哚胺2,3-雙加氧酶(indoleamine 2,3-dioxygenase,IDO)來調節,該酶可被STING激活[21]。IDO能夠催化L-色氨酸轉化為N-甲酰犬尿氨酸促進腫瘤細胞免疫逃逸并限制T細胞增殖[27]。值得關注的是,IDO的表達在腫瘤引流淋巴結中升高,并且STING和IDO同時缺陷的小鼠更能抵抗LLC的遠處轉移。連接蛋白43和原鈣黏蛋白7介導cGAMP通過縫隙連接從腫瘤細胞轉移到星形膠質細胞,隨后誘導IFN和NF-κB的表達,促進腦轉移[28]。與cGAS-STING信號轉導一致的是,當敲低腫瘤細胞中cGAS的表達時,會導致共培養星形膠質細胞中IRF3和Ⅰ型IFN磷酸化的減少。相反,Demaria等[29]證明在腫瘤內注射cGAMP可使小鼠肺轉移瘤幾乎完全消融并延遲對側腫瘤生長。由于cGAS-STING的激活可以對腫瘤轉移產生旁分泌作用,進一步探索以確定這種組織特異性的作用及在臨床治療中的應用有重要意義。該組織特異性可以被器官特異性驅動,促進腫瘤細胞轉移;這一過程是由TME中的細胞因子介導的,其可以通過上調內皮細胞中黏附因子的表達促進黏附作用[30]。雖然仍不確定旁分泌信號、縫隙連接介導的cGAMP轉移及尚未發現的機制對腫瘤轉移的影響,但cGAS-STING介導的調節性免疫功能和基于cGAS-STING通路的靶向治療值得進一步探索。
5 cGAS-STING信號通路與腫瘤靶向治療
在腫瘤內給予cGAMP和其他環狀二核苷酸刺激后,機體表現出顯著的抗腫瘤反應,這是cGASSTING參與抗腫瘤免疫的最有力證據。盡管化療和放療并未靶向cGAS-STING信號通路,但是這些藥物和射線可能會誘導損傷的DNA激活cGASSTING信號通路并增強抗腫瘤免疫反應導致腫瘤細胞死亡。目前化療藥物順鉑和依托泊苷均可通過引發DNA損傷和細胞溶質DNA滲漏誘導cGAS-STING的激活,在實驗室中,依托泊苷被廣泛應用于研究DNA受損途徑,以及探討與DNA識別、修復和炎性反應有關的基因表達,這些基因包括Ⅰ型IFN、抗病毒Mx基因家族,以及Mbd21d1(即cGAS)和Tmem173(即STING)[31]。最新研究表明,化療藥物多柔比星和柔紅霉素能夠通過抑制拓撲異構酶Ⅱ和dsDNA斷裂有效激活STING[32]。
在發現STING之前,5,6-二甲基黃酮-4-乙酸(5,6-dimethylxanthone-4-acetic acid,DMXAA)是一種非常有前景的化療藥物,對晚期肺癌、前列腺癌和乳腺癌均有療效。隨后有研究報道,DMXAA能激活STING,使其誘導IFN-β的表達和CD8+T細胞的增殖和浸潤[33]。但DMXAA在Ⅲ期臨床試驗中失敗了,因為DMXAA僅能激活小鼠體內的STING功能,而對人類和大鼠的STING無激活作用[34]。為此許多科學家開始對STING激活劑進行研究,包括瘤內注射MIW815的Ⅰ期臨床試驗以及利用免疫療法對惡性實體腫瘤進行檢查點封鎖[35]。據研究報道,人工合成的環狀二核苷酸衍生物能夠激活所有已知的人類STING等位基因,但仍需在臨床試驗中進一步探索[6]。這些合成衍生物在小鼠骨髓源巨噬細胞(bone marrow-derived macrophage,BMDM)和原代人細胞中能誘導IFN-β的合成,當將該藥物注射到小鼠黑色素瘤、結腸癌和乳腺癌腫瘤中時,能夠減小腫瘤體積,并在腫瘤消退后誘導抗腫瘤免疫記憶形成[36]。環狀二核苷酸似乎增強了各種現有的和前瞻性的抗腫瘤療法的效果,包括疫苗、CD47阻滯劑、氟二氧嘧啶和尿嘧啶[37]。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小鼠的B16黑色素瘤模型中發現,cGAS和STING對程序性死亡受體配體-1(programmed cell death 1 ligand 1,PDCD1LG1,也稱PDL1)拮抗劑的抗腫瘤作用至關重要,然而當小鼠體內的cGAS或STING被敲除時,抗PD-L1療法對腫瘤體積或生長無影響[1]。
目前許多常見的病毒載體,包括單純皰疹病毒1(herpes simplex virus-1,HSV-1)、腺病毒和痘苗病毒等dsDNA病毒均能夠激活cGAS-STING信號通路[38]。cGAS和STING在HSV-1感染中起關鍵作用,能夠增加Mb21d1和Tmem173型小鼠的致死易感性[39-40]。此外,HSV-1能夠根據細胞類型調節STING的穩定性和功能[41]。在黑色素瘤細胞系中,cGAS-STING缺陷型和相關的Ⅰ型IFN缺陷型細胞信號的轉導與溶瘤細胞內HSV-1復制的增加和細胞溶菌作用增強有關[23]。自從發現溶瘤細胞內HSV-1變體能夠治療黑色素瘤后,有研究者推測cGAS-STING有可能成為預后和療效監測的生物標志物。由于微小RNA(microRNA,miRNA)的分子量小、特異性強,可在腫瘤治療中作為腫瘤標志物或者腫瘤治療劑[42]。有研究報道,miRNA-27能夠靶向STING的3'UTR位點,并且miRNA-27的表達水平降低與舌鱗狀細胞癌的發展相關[25]。同時,miRNA-27的轉染降低了STING的表達和下游信號的轉導,因此被認為是調節cGAS-STING信號轉導的另一種潛在治療劑。
另據研究報道,cGAS-STING激活劑能夠促進輔助性T淋巴細胞1(helper T lymphocyte 1,Th1)的佐劑效應,因此可以與腫瘤的各種治療方案聯合使用。體內小鼠試驗研究表明,STING激活劑可以增加放療、疫苗療法及免疫療法的效果,除了輔助作用外,cGAS-STING信號通路也可以被溶瘤病毒激活以用于新的治療方案;如上所述,研究cGAS-STING對腫瘤發展的影響必須考慮腫瘤細胞的特異性。cGAS-STING介導的腫瘤發生、發展和轉移的新興作用仍需在臨床試驗中進一步探索。與任何類型的免疫療法一樣,cGAS-STING介導的靶向治療依賴于誘導機體產生強大的抗腫瘤免疫反應,同時盡量減少腫瘤的炎性反應。
6 小結
cGAS-STING信號通路與腫瘤的發生、發展及轉移有關,機體能夠通過調節STING信號通路的激活,增強天然抗腫瘤免疫。對cGAS-STING信號通路的深入研究,不僅可以加深對固有免疫抗感染機制的理解,而且為腫瘤免疫的藥物設計提供了理論基礎,使其在基礎免疫學、腫瘤生物學及腫瘤臨床治療中發揮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