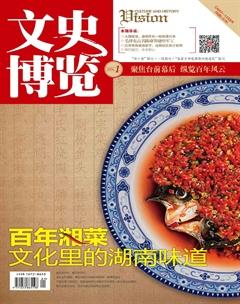譚嗣同引導我祖父林圭走上革命道路
林利
筆者祖父林圭,字述唐,別號悟庵。1875年10月12日出生于湖南岳陽湘陰樟樹港鎮一個較殷實的商人家庭,家中有兄妹四人,他排行第三。林圭天資聰穎,勤奮好學,成績優異。在鎮上讀私塾時,其父林松桂由人介紹認識了一位在長沙教書的黃先生,又經黃先生介紹,林圭與長兄林紹敏寄住在長沙東茅巷96號歐家,與歐陽植齋同受業于黃先生,食宿俱在歐家,歐陽植齋的祖父是長沙岳麓書院的山長、安仁人歐陽厚均老師,學風優良。歐陽植齋的母親歐陽寶珍見林圭聰明懂事,特別喜愛,還將其收為義子。
其后,為求學業更大進展,林圭與長兄又轉到長沙黎家坡族兄林世燾家附讀,林世燾系貴州巡撫林宗伯之子,湖廣總督張之洞的侄女婿,光緒欽點翰林。林圭在這里接受了更高層次的教育,為日后以優異成績考取“維新思想的溫床和搖籃”——湖南時務學堂打下了堅實基礎。
譚嗣同評林圭:“侃侃而談,深中時弊”

1897年11月29日湖南時務學堂成立之際,正是德國強占膠州灣,新一輪民族危機又卷起之時。學生們邁向接受新知識、鑄造新觀念、尋找救亡圖存的課堂。而遇上奮發蹈厲,閱歷豐富的青年才俊譚嗣同、梁啟超、唐才常、熊希齡等先生,更讓學生們如魚得水。教習們把時務學堂的辦學與整個湖南的開化緊密聯系起來,并在經世致用之學上又增加新的篇章,十分注重學習西方社會政治方面的學說,推行“以政學為主義”的教學方針,愛國主義思想和民族主義精神得到渲染和升華,讓學生們認為政學乃治國之道。
光緒二十四年三月十五日(1898年4月5日),林圭以優異成績考入時務學堂,成為二班內課生,年輕、求知若渴的林圭倍加珍惜。恰好這年春,譚嗣同返湘,全力投入湖南新政。
譚嗣同是湖南時務學堂的九位紳董之一,兼學堂總監,并擔任時務學堂教習。在時務學堂開辦之時,有地方議會性質的南學會也在譚嗣同的倡導下應運而生,維新派利用《湘學報》及《湘報》鼓吹民權,互相呼應。學堂的學生也常去南學會聽演講。后又將學堂“季課改為南學會日課”,并由南學會學長命題,交學堂“核原”,由南學會派人“應此題”。這樣密切了時務學堂與南學會的關系,更大地發揮了兩個維新機構的作用。
譚嗣同、唐才常等先生大膽而激烈地批判傳統封建文化、君主專制的弊端,引起學生們強烈反應。林圭以其敏銳的觀察力與穎悟的頭腦接受老師們授予的新知識與新觀念。他不僅成績優異,還深受老師們的喜歡,多年后,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一文里稱:“李炳寰、林圭、蔡鍔稱高才生焉。”
譚嗣同在看清帝國主義列強的野心后曾說:“時局之危,有危于此時者乎?圖治之急,有急于此時者乎?”學生們受到先生愛國情懷影響,經常談論國事,愛國情愫日增。林圭常跟人說:“朝廷綱紀敗壞,達于極點……吾人今日求學,應以挽救國家為第一要義。”唐才質(清末維新派領袖唐才常之弟)曾回憶:“這在當時確是非常大膽的話。”
學生們不僅其言緊跟教習,還在行動中緊密配合。如林圭就不僅在家鄉湘陰開設“廣益會”,還于光緒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二日(1898年4月12日)加入了譚嗣同等人創建的不纏足會。
林圭誓言:“中國流血自譚君始,我隨其后矣”
戊戌五月,譚嗣同應詔入京,離湘北上。行前給時務學堂學生臨別贈言:“我不病,誰當病者。”言下之意,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譚嗣同無私無畏、勇于擔當的精神無時無刻不在感染著學生。因抵武漢時生了一場大病,譚嗣同七月初五日方才到京。不知是出于請教還是關心時局和老師,據譚嗣同的一位后人追憶,林圭與同班同學及好友范源濂當時曾寫信給譚嗣同。然而誰也沒有想到,這次離湘,卻成了譚嗣同與家鄉永遠的別離、與學生的訣別,更成了林圭鐫骨銘心的痛……
譚嗣同進京參與變法第33天,維新派人士遭慈禧下令被捕。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十三日(1898年9月28日),清廷在未經任何審訊的情況下,將譚嗣同等六君子殺害于北京宣武門外菜市口。百日維新以失敗告終。
譚嗣同犧牲的消息傳來,林圭“君不勝痛憤,而種族革命之志益堅”。從此以革命自任,并且宣稱:“中國流血自譚君始,我隨其后矣。”他在1899年3月28日(改正范氏日記及批札)寫道:“孟子之道,仁義而已矣。……今之所言仁義之國,則泰西諸國是也。國勢之強,人才之盛,以治國而論,則有八事,為天下之公理。” 并發出了“自求富強,即為國為民之公理。……若中國君臣,徒知擁高位,厚精祿,朘民之脂膏,壞國之基礎,則是利一身、利一家之獨夫民賊也,未有不敗亡者也”的呼聲,更加認清了清政府的腐敗無能,反清復仇之心日劇。
1898年6月,在湖南保守勢力的攻擊下,時務學堂風波驟起。于形勢所迫,湘撫陳寶箴7月2日免去熊希齡時務學堂總理職。隨之,韓文舉、葉覺邁、歐榘甲迫于壓力,請辭時務學堂分教習職,離開長沙。戊戌變法失敗后,清廷懲辦了湖南維新黨人和支持維新變法的官員,早已是眾矢之的時務學堂于10月中旬交守舊人士接管,原有的學生皆離開。1899年春,時務學堂易名為湖南求實書院。

離開時務學堂的林圭和幾位志同道合的同學幾經輾轉,又投身于梁啟超在日本創辦的東京高等大同學校學習。日本留學期間,這群志存高遠的學生與其他學校留學的青年們“日夕高談革命”,救亡圖存之意更堅。他們滿懷激情,除了正常的文化學習外,還積極進行組團活動壯大革命隊伍。“湖南留日學生中最早出現的團體是由蔡鍔、林圭等于1898年組織的東京九段體育會,該會主要是團結志士,練習日本兵式體操、射擊打靶等。他們立下蹈厲之志,磨礪以須,枕戈待旦。”
為秉承譚嗣同未了的救國宏愿,“唐才常憤國事之日非,慟友仇之未報,乃奔走各地,聯絡同志”。1899年5月,由唐才常倡議、梁啟超取名的自立會在日本橫濱成立。康有為任會長,梁啟超、唐才常任副會長,革生為稽查會員,林圭、汪堯成、王翼之等三人為議事會員。林圭以其卓越的見識,走上了歷史舞臺。自立會雖有保國勤王之說,但年輕的林圭更趨激進,他曾對梁啟超說:“國勢至此,而有志之士,方孜孜焉以求學,學成而國已燼矣。……誠問救火急乎?抑耕急呼?”林圭恨不能早日將一腔愛國熱情付諸實踐,決意扛起義旗,堅定地走向反清復興的革命道路。
1899年11月,唐才常、林圭、吳祿貞、傅慈祥等回國舉事。當林圭等歸國時,梁啟超、沈翔云等設宴餞行,孫中山、陳少白、平山、宮崎皆在坐。“林于行前,親詣孫中山請益,中山為之介紹漢口某俄國商行買辦、興中會員容星橋。”容星橋為容閎之侄,“其后林在漢口大得容助,中山介紹之力也”。這天的餞別,大有“風蕭蕭兮易水寒”的氣氛,據與會者陳少白(資產階級革命家,1895年入興中會)說:“大家見過面,把酒暢談,真是悲壯淋漓,激昂慷慨都兼而有之了。”
回國后的林圭等在自立軍統領唐才常的領導下,利用自立會建立體系龐大的富有山堂,發放富有票,聯絡會黨,并在清廷的新軍中發展會員。經過不懈努力,當時自立會東至蘇、皖,北達豫、陜,西及巴蜀,南貫兩粵,而尤以兩湖為盛,為發動武裝起事聯絡了十幾萬人。“當唐才常活動于上海之時,林圭、傅慈祥等則著力在武漢經營,做軍事發難的準備。林圭是自立會中的激進人物,其興革時政的決心比唐才常更堅決。其人才識干練,人以‘豹子頭稱之。林圭受畢永年影響較深,和孫中山的主張比較接近。”自立軍先后成立中、前、后、左、右五軍,均由林圭、秦力山、田邦璇、陳猶龍、沈藎等統之。五軍之外,另有總會親軍、先鋒營二軍,共計七軍,兵力約2萬人。還有會黨成員10多萬人作為后援力量。唐才常擔任自立軍總糧臺。中軍為自立軍本部,集結在武漢,統領為林圭(會中人稱之為大帥)和傅慈祥,李炳寰為總文案。一場以時務學堂師生為主力的自立軍起義即將揭竿而起。
1900年,已計劃于8月9日舉事的自立軍因軍費不繼一再展期。而安徽大通的自立軍前軍在不知起義展期,事機又已泄露的情況下,統領秦力山便決定即時起事,一舉占領大通,由于孤軍奮戰,幾天后逐漸轉為敗局。8月21日晚,湖廣總督張之洞派清兵包圍了自立軍總部寶順里四號,逮捕了唐才常、林圭、傅慈祥等自立軍將領,又在李慎堂逮捕了包括時務學堂學生在內的多名自立軍負責人,并于8月22日深夜殘酷地將他們殺害于武昌紫陽湖畔。時年唐才常33歲,林圭尚未滿25歲。
譚嗣同是林圭在時務學堂最早接觸的老師之一,也是林圭走向反清革命道路的第一位引領人,“林圭素仰慕譚嗣同之為人,譚亦甚器重之”,被恩師譚嗣同“常許為造世之雄”。最終,林圭追隨先生,蹈鋒飲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