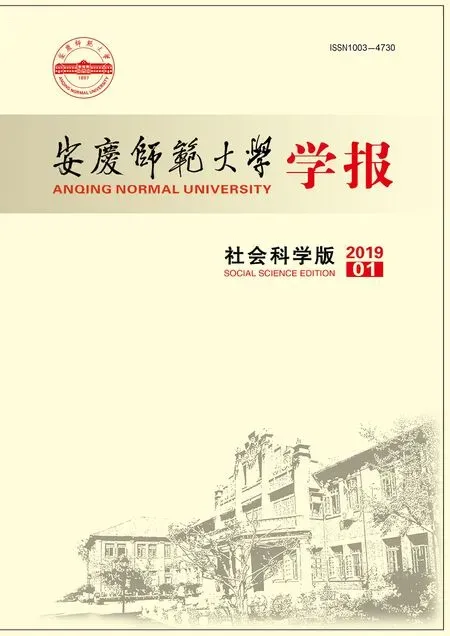《女孩和女人們的生活》中的“生態(tài)智慧”
張 瓊
(1.安徽大學(xué)文學(xué)院,安徽合肥230601;2.南京大學(xué)文學(xué)院,江蘇南京210046)
發(fā)表于1971年的短篇小說集《女孩和女人們的生活》是加拿大當(dāng)代女作家艾麗絲·門羅(1931—)最富自傳色彩,也極具地域性的一部作品,它生動再現(xiàn)了門羅出生成長的加拿大西南部鄉(xiāng)鎮(zhèn)特有的自然風(fēng)光。針對《女孩和女人們的生活》中的自然描寫,國內(nèi)學(xué)者的研究大多從生態(tài)女性主義的角度出發(fā),致力于揭示門羅對動物生命以及女性的關(guān)懷,但同時,在這些觀點的非人類中心主義的立場中,都不同程度隱含著把自然與自我相對立,借戰(zhàn)勝自然的“他者”性,來宏大自我、關(guān)懷自我長遠利益的理性傾向,例如認(rèn)為黛爾與自然環(huán)境、其他生命形式的融合,就意味著“自然、非人類物種不再是‘他者’”[1];又或者,把門羅對女性生活的關(guān)注,等視為“征服自然、征服世界的男性偉業(yè)”[2],而事實上,門羅的生態(tài)觀,擺脫了基于理性的二元對立傾向,作品中的女主人公黛爾,在用心觀察生活之后,不僅領(lǐng)悟到自然與人同等擁有的“內(nèi)在價值”,也進而能夠主動融入自然,發(fā)掘出人與自然息息相關(guān)的內(nèi)在聯(lián)系,從而逐步走向自我的成熟。
一、直覺到自然生命的“內(nèi)在價值”
日常所充斥的功利和漠然,使得黛爾一度把自然視為消遣的對象,但是,在第一次目睹了人與自然的融洽之后,受到觸動的黛爾,開始下意識地把自然與人等同視之,并直覺到自然固有的“內(nèi)在價值”。
挪威著名哲學(xué)家阿倫·奈斯在他的“生態(tài)智慧T”思想中提出,生物圈中的一切生物,都擁有平等的“內(nèi)在價值”,基于眾多“內(nèi)在價值”的平等共在,才有了整個地球的生態(tài)系統(tǒng)的豐富性和穩(wěn)定性。之所以稱為“內(nèi)在價值”,源于它與人眼中的“價值”的根本不同,阿倫·奈斯極力主張“內(nèi)在價值”客觀內(nèi)在于一切生物自身,不訴諸人的任何需求,換言之,“這些價值與非人類世界對人類所認(rèn)為的有用性無關(guān)”[3]18,由此,他徹底否定了人類在地球的中心地位。同時,阿倫·奈斯把一切生物的“內(nèi)在價值”視為不言自明的客觀事實,認(rèn)為它們無需邏輯來證明,是可以被直覺到的東西,這就意味著,基于理性的以人類為中心的預(yù)設(shè),很容易會造成對非人類自然的“內(nèi)在價值”的無視。
起先,年幼的黛爾耳濡目染了叔叔班尼對自然一貫的冷漠處置,也在對自然的凌駕中尋求樂趣,從而使得她不可能發(fā)現(xiàn)自然的“內(nèi)在價值”。班尼叔叔處于社會的下層,也缺乏足夠生存智慧,在與自然的相處中,他唯有自我利益的考慮。為了生計,他可以無動于衷地剝?nèi) ⒓庸にZ養(yǎng)的狐貍的毛皮,也可以因為一個“來自底特律的美國人”的空頭允諾,立刻打算不遺余力地去捕捉海龜。年幼的“我”,經(jīng)常追隨在班尼叔叔的身邊,也想當(dāng)然地隨意傷害自然,并樂在其中,為了給班尼叔叔準(zhǔn)備魚餌,“我”就曾興致勃勃地把捕獲來的幼小青蛙“捏碎,扔進蜂蜜桶里”。
姑媽們認(rèn)真耕耘、收獲喜悅的生活場景,卻向黛爾展現(xiàn)了人與自然的和諧統(tǒng)一。不同于班尼叔叔對動物們的犧牲,姑媽們樸素傳統(tǒng)的生活方式,在更大程度上尊重了自然本身,使自然和她們自我的成長發(fā)展都得到了滿足。她們勞作于田間、牛棚,精心照料土地上的各種生物,并靜靜守候大地生物的生長、成熟,當(dāng)自然最終呈現(xiàn)出勃勃生機時,她們也收獲了來自自然的饋贈。與自然的緊密相依,使姑媽們深感慰藉,所以,在“我”面前就出現(xiàn)了這樣充滿歡樂的場景:姑媽們常常一邊“給漿果去籽、豆子剝殼、蘋果削核”,一邊開心地講著故事,在給奶牛擠奶的時間里,她們大聲地唱著歌兒,“喜氣洋洋”。
黛爾切身感受到姑媽們心靈的深層滿足,產(chǎn)生了親近自然的生命沖動,從而第一次領(lǐng)悟到自然的“內(nèi)在價值”。與姑媽們朝夕相處了一段時日后,當(dāng)“我”和埃爾斯佩思姑媽在“樹林的邊緣”發(fā)現(xiàn)一只野鹿,她立刻“伸出棍子像君主一般命令我不要動”時,此時的“我”,不再如先前那般,一心占有和處置眼前的自然生命,而是不由自主地屏住呼吸,認(rèn)真注視著這只野鹿,于是,氣氛驟然變得寧靜而祥和,在“我”和野鹿之間,距離拉近了,隔膜被打破了,彼此的毫無罅隙,使“我”切身體驗到野鹿作為一個完整生命的存在,在這一刻,它躍起離去的一個身姿,給“我”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好像在空中劃了半個圓圈,就和跳舞的人一樣”[4]42。把身姿優(yōu)美的野鹿比作“跳舞的人”,這個比方飽含著“我”對野鹿同等擁有的“內(nèi)在價值”的強烈認(rèn)同。
二、發(fā)掘人與自然不可分割的內(nèi)在聯(lián)系
就黛爾的成長而言,與林中野鹿的美麗邂逅,具有標(biāo)志性的意義,它第一次顯示了在黛爾與自然之間,一切隔閡的消除,以及彼此實質(zhì)上的平等,同時也預(yù)示了黛爾的自我與自然的內(nèi)在聯(lián)系的被發(fā)現(xiàn)。
阿倫·奈斯認(rèn)為,生物圈中的任何生命存在,不管有多么微小,都必然基于各自的“內(nèi)在價值”,與周圍所有的生命物發(fā)生聯(lián)系,這種聯(lián)系,把一切生命納入一個不可分割的生態(tài)系統(tǒng),這種聯(lián)系,也是內(nèi)在的,它會對一切生命的本質(zhì)產(chǎn)生影響,使它們具有整體的特征。一旦能夠明確這種整體上的聯(lián)系,人們就不會肆意破壞自然生態(tài),因為這樣做就等于傷害人的自我。那么,如何使人真正把握這種聯(lián)系呢?在阿倫·奈斯看來,如果只借助理性去分析生態(tài)環(huán)境的各個組成部分,一定會不可避免地屏蔽這種內(nèi)在聯(lián)系,把有機的生態(tài)整體變成許多碎片的組合,但是,若能“僅僅去看自然”,“在自然中做事、生活、沉思和行動,以完成對自然的體驗”[5]63,就有助于發(fā)掘出人與自然的聯(lián)系。阿倫·奈斯認(rèn)為他工作的目的之一就是盡可能多地發(fā)掘這種聯(lián)系。
正是在直覺到野鹿的生命存在之后,黛爾的非理性主義立場漸趨清晰。當(dāng)母親“小心翼翼”地向“我”轉(zhuǎn)達克雷格叔叔去世的消息時,“我”的反應(yīng)完全出乎母親的預(yù)料,“我”并沒有流露出理應(yīng)有的傷心難過,而是堅持不懈地向母親追問克雷格叔叔死去時的細(xì)節(jié)。“我”的舉動看似缺乏人道情感,實則是出于對克雷格叔叔之死的“共情”,從這種情感上的共鳴出發(fā),才喚起了“我”對死的無限恐懼。正如“我”向母親解釋的,“沒有什么能夠保護我,除非讓我明白”,于“我”而言,只有通過細(xì)節(jié)來確證克雷格叔叔的死亡,才能中止關(guān)于他的死的身臨其境的可怕的想象和體驗,以走出死亡的陰影,也是從這種生命共鳴出發(fā),“我”意識到了母親的理性的冷漠:
自然的一切都是生生不息,一部分壞死——不是死,而是改變,我想說的是改變,變成別的,所有組成人的元素改變,再次回歸自然,在鳥類、動物和花草身上一再重現(xiàn)——克雷格叔叔不一定是克雷格叔叔!他可能是一種花[4]56!母親的這一番回答,是在向“我”解釋,死亡并不意味著結(jié)束,而是預(yù)示著向自然的回歸和重生,就像“死”去的克雷格叔叔可能變成花一樣。母親的觀點不乏道理,卻隱含著一種居高臨下的理性主義立場,唯此母親才能理所當(dāng)然地忽略克雷格叔叔所走過的生命歷程,才會對鳥類、動物和花草的“內(nèi)在價值”視而不見,并把克雷格叔叔的逝去,輕描淡寫地描述為人向花的轉(zhuǎn)變。“我會暈車的”、“我會嘔吐”,當(dāng)“我”編織謊言來敷衍母親時,“我”顯然是為了盡快逃脫母親的說教。
如果說對野鹿生命之美的共鳴,第一次顯現(xiàn)出黛爾與非人自然的某種內(nèi)在聯(lián)系,那么對克雷格叔叔的死的油然而生的懼怕,則是黛爾切身感受到自我與一切生命的內(nèi)在聯(lián)系的被強行切斷的結(jié)果。最終,黛爾選擇把溫情的目光投向自然,主動與自然相擁,并因為從中感受到生命的完整,使得自我與自然的內(nèi)在聯(lián)系被真正發(fā)掘。“干草垛還在那里。”[4]58與母親的溝通失敗之后,之前收割卷成的“干草垛”重新引起了“我”的注意,凝視著它在落日中的身影,“我”仿若看見了親切而又熟悉的“村子”和“城市”;“我”感受到它的“柔軟而殘敗”,怦然心動,情不自禁地縱身跳入它的深處。夕陽余輝下的“干草垛”默默無語,但是,當(dāng)“我”全身心地融入其中,就好像被賦予了某種神奇的力量,使“我”能夠重新確認(rèn)自我生命的充滿能量而又完整的存在,也恰是如此,在與“干草垛”相擁的時刻,“我”不再感受到來自死亡的威脅,使“我”銘刻于心的反倒是“干草垛”“它還是溫暖的,散發(fā)著正在生長的草的氣息”。“干草垛”正是以它的身影身姿,它的“柔軟”且“溫暖”的存在,與“我”的生命,發(fā)生息息相關(guān)的“內(nèi)在聯(lián)系”。
三、走向“生態(tài)自我”并漸趨成熟
與自然的親密相擁,平息了黛爾人生中的第一次心理危機,也促使黛爾感知到與整個世界緊密相依的“生態(tài)自我”。在之后的成長歷程中,這個必然在聯(lián)系中得以實現(xiàn)的“生態(tài)自我”,往往會為她指明方向。
奈斯以“生態(tài)自我”代表自我的成熟形態(tài),區(qū)別于社會屬性的、理性的自我,并分別用大寫的“Self”(“大我”)和小寫的“self”(“小我”)來予以指稱。奈斯認(rèn)為,隨著人自身與自然界中其他生命存在物的“內(nèi)在聯(lián)系”的不斷被開掘,“小我”就會發(fā)展為成熟的“生態(tài)自我”。“小我”往往忽視了人類所屬的自然環(huán)境和非人類的生命存在物,“生態(tài)自我”卻因為意識到自身不可能與自然分離,能夠把自身與自然中的一切生命存在物視為一個整體。奈斯曾把“生態(tài)自我”描述為是“與周圍一切事物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的自我”[5]80。有學(xué)者則進一步理解為是“人的原初狀態(tài)”[6]。如果說原初狀態(tài)下的人,與自然有著天然的聯(lián)系,并因此始終能感受到生命的完滿和諧,那么在現(xiàn)代社會中,高度發(fā)達的理性的備受推崇,所帶來的后果之一就是,現(xiàn)代人與自然漸行漸遠,并不可避免地會常常陷入精神孤立無依的緊張之中,無法真正實現(xiàn)生命的全部潛能。在奈斯看來,只有走向“生態(tài)自我”,才能最大程度地實現(xiàn)所有生命存在物包括人類自身的“內(nèi)在價值”。
正是出于對“生態(tài)自我”的追尋,黛爾自發(fā)地走上信仰探索之路,完成了精神成長的一段重要歷程。在小鎮(zhèn)的宗教氛圍中,當(dāng)“我”開始苦苦地追尋上帝,“我”的初衷就是要在自身與上帝之間,發(fā)掘新的聯(lián)系,來竭盡所能地在自我與這個世界的聯(lián)系中實現(xiàn)生命的完整,如“我”所言,“如果能找到或回想起上帝,一切都將是安全的[4]117。”然而,作為人類純粹理性的產(chǎn)物,上帝根本不可能如同自然那樣,向“我”展現(xiàn)自身,并與“我”溝通會意,這就注定了“我”的一廂情愿。“我”先是希望上帝“像一道光亮,耀眼和清晰地出現(xiàn),出現(xiàn)在現(xiàn)代的靠背長凳上”或“像一片萱草在管風(fēng)琴下突然開花”,緊接著,“我”又“要求上帝回應(yīng)我的祈禱來證明自己”[4]113。事實卻是,上帝這個神秘的存在,毫無生命的氣息和溫度,也不可能與人面對面地互動交流。當(dāng)“我”清醒地意識到上帝的虛妄,意識到上帝的超乎自然,“我”終于否定了與上帝之間的一切可能的聯(lián)系的存在,“看到有人有信仰,接近信仰,比看見有人把手指剁掉更難受”[4]134,這是從“我”的心底蹦出的對上帝充滿失望憤怒的怨語。
也是在“生態(tài)自我”的指引下,在觀察周遭現(xiàn)實時,黛爾的所思所想,更加情真意切,也更為自覺深刻。當(dāng)父親決定殺死家中一只老狗梅杰時,“我”第一次敏感地意識到,大人在做出選擇時,也有可能犯錯,并開始認(rèn)真思考個中緣由。父親之所以要殺死梅杰,是因為年邁衰弱的它染上了追羊的嗜好,接連咬死了鄰居家的兩只羊,并且它的這一舉動將使父親一貧如洗。在這整個事件中,“我”始終是一個旁觀者,但是“我”從未真正缺席,“我”一直在反思和質(zhì)疑,而“我”所有的思考,唯一的出發(fā)點就是人與非人自然的緊密聯(lián)系。“我”并沒有無視父親的損失,去為梅杰的胡作非為,做任何辯護,但是,“我”不得不為梅杰的必須受死,而憤懣不平。在梅杰的生死時刻,自始至終困擾“我”的,并不是在動物與人類的生存沖突中何從選擇的問題,而是人對動物的為所欲為的處置方式,是人對動物的最基本的生存權(quán)的肆意剝奪,“我反復(fù)思索的是這種故意性”,是誰賦予父親裁決梅杰生死的權(quán)利?為什么父親要選擇結(jié)束它的生命?“不是因為這不可避免,而是因為人們想要這么做——那些大人、管理者、劊子手們想要這么做,帶著善良卻毫不留情的面容”[4]132。在這里,“我”所有的苦惱和不滿,都確切地指向,父親與梅杰之間征服與被征服、掠奪與被掠奪的錯誤關(guān)系。
四、結(jié) 論
阿倫·奈斯把他的“深層生態(tài)學(xué)”概括為“生態(tài)智慧T”,就是為了表明,“生態(tài)智慧T”只是奈斯本人的生態(tài)智慧,而其他每個人都可以提出自己的生態(tài)智慧(即生態(tài)智慧A、B、C……),同時,他也深信,人們終將“經(jīng)由對某些價值和信念(它們通過深層生態(tài)學(xué)的綱領(lǐng)而得到表達)的共識”走到一起。在自傳性作品《女孩和女人們的生活》中,黛爾初具雛形的“生態(tài)智慧”,正是對阿倫·奈斯的“生態(tài)智慧T”思想的生動演繹:一方面,黛爾的“生態(tài)智慧”,是她自己的“價值規(guī)范”、自己的“一種世界觀”;另一方面,黛爾的“生態(tài)智慧”與阿倫·奈斯的“生態(tài)智慧T”的基本綱領(lǐng)不謀而合:把自然生命的“內(nèi)在價值”視為不可求證的既定事實;否定人與自然的二元對立,重新發(fā)現(xiàn)人與自然的“內(nèi)在聯(lián)系”或者說原始統(tǒng)一;在與自然的緊密相依中,感知到“生態(tài)自我”,從而找到了實現(xiàn)生命“內(nèi)在價值”的人生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