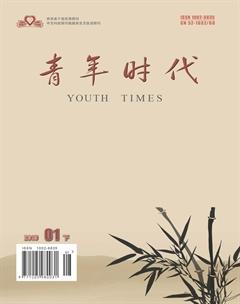心理傳記學方法論的文化心理視角
吳毓清 楊旭
摘 要:心理傳記學主要用心理學理論來解釋人格特征,且文化對人格、自我的發(fā)展影響深遠。心理傳記學的研究對象是代表性的杰出人物,僅用西方普適性的人格理論難以挖掘傳主人格的形成和發(fā)展的文化濡化過程。另外,中西文化價值體系存在明顯差異,中國人的自我是復數(shù)自我,根據(jù)不同的社會角色而變化。因此,本文旨在中國人的心理傳記學研究方法上,探討中國傳統(tǒng)儒家文化的“自我”觀,主要從個人自我,家庭自我和社會自我三方面闡述。
關鍵詞:心理傳記學;文化;人格;自我;儒家
一、引論
在心理傳記學的研究中,主要以大五人格理論對傳主進行人格特質的分析。我們知道,以五因素人格模型為代表的特質取向不考慮文化,更關注所有人類的人格的普遍性。在反映普遍人格特質的五因素理論中,其基本特質主要指以生物學為基礎的行為的內在傾向性。根據(jù)文化與人格研究的先驅馬林諾斯基(B·Malinowski)和米德(M·mead)認為,不同的文化背景對人格的形成和發(fā)展起到?jīng)Q定性作用。個體的人格結構既是社會文化塑造的結果,同時又作為文化的一部分影響其他個體的人格形成。因此,人格既有普遍性又有文化特異性。
二、中國文化下的“自我”觀探索
(一)自我的中西文化差異
第一,在西方文化背景下,人們崇尚民主法制以及倡導個人的自由和平等,其自我表現(xiàn)為“重我”,注重個人的自由權利和成就;然而,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人們過去一直受傳統(tǒng)禮教的洗禮、等級統(tǒng)治思想的渲染和封建君主制度的管治,中國人的自我更多地表現(xiàn)為“抑我”,以犧牲“小我”來滿足“大我”的需求,同時注重自我與社會的關系。在這種社會取向下自我與社會關系強調個人與社會的高度融合性,依照一定的社會規(guī)則與規(guī)范要求,通過表現(xiàn)出適宜的行為來順應環(huán)境,完成個人被社會或團體所賦予的角色責任,并借由自我批評、自我改善等道德修為的努力,來贏得社會的肯定(楊國樞, 2004)。同時,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提到“存天理,滅人欲”的思想,要求我們戒除“私欲”,達到“忘我”的境界,以滿足 “抑我”的文化取向。
第二,在西方“重我”的文化背景下,強調自我是獨立的、穩(wěn)定的自我,表現(xiàn)出自我的一致性。但在中國“抑我”的思想文化下,其自我會隨著不同的情境要求而發(fā)生改變,具有彈性調節(jié)性,是一種彈性自我的表現(xiàn)方式。
Hall曾引入情境(context)這個重要的維度,以此說明不同文化情境下對思想行為一致性的影響。情境可分為高低兩種水平,在高情境文化下,行為和認知可以隨情境和背景的改變而做出調整,不強調跨情境的一致性。在低情境文化下,更多地強調在任何情境下保持一致性和穩(wěn)定性。在中國這種高情景的文化下,用心理傳記學分析中國傳主的人格特質時,單純運用反映普遍人格特質的五因素理論來解釋是不完整的、有失偏頗的。我們應該深入到中國文化中把握中國人彈性自我的表現(xiàn)形式來探索中國人的獨特人格魅力。
第三,相對于西方強調的純粹自我,其社會的治理更多是依靠法制來維系。在中國儒家文化下,中國人更講究自我與他人的關系,強調以人情和倫理為核心的人際關系網(wǎng)絡,用人情網(wǎng)絡來治理社會。顯然,中國人根據(jù)自我與他人的關系作為“差序格局”中人與人相處的規(guī)則,以“親親尊尊”、“孝弟忠信”、“三綱五常十義”為倫理體系,由此形成以自我為中心,從血緣關系的親人向無血緣關系的陌生人層層遞推形成同心圓結構。因此,中國人的自我是區(qū)別于西方獨立的自我,它是一個復數(shù)的“自我”,根據(jù)不同的社會角色形成不同的自我,以不同的社會關系組成的人際網(wǎng)絡結構。
(二)中國傳統(tǒng)儒家文化下的“自我”觀
儒家文化作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中流砥柱,對中國人的自我形成和發(fā)展必然起到潛移默化的影響力。中國人以“禮”作為行為準則,要求自己應該以不失身份的角色及角色期望為內容。《禮記》提到“凡治人之道,莫基于禮”。儒家文化的價值體系注重人與社會的關系,主要體現(xiàn)為以“五倫”“三綱”為核心的道德價值體系和倫理秩序(郭斯萍, 2012)。在中國特有的人情或人倫的社交網(wǎng)絡里,家庭是自我的發(fā)源地。根據(jù)費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論,這種人際網(wǎng)絡以自我為中心,從血緣關系的親人向無血緣關系的陌生人層層遞推形成同心圓結構。因此,與西方文化價值體系中強調“真我”的自我觀不同,中國人的“自我”是一個復數(shù)的人格結構。因此,在儒家傳統(tǒng)文化下的自我,我們可以分為個人自我、家庭自我和社會自我三個部分來闡述。
第一,個人自我。主要表現(xiàn)在自我的更高層次的追求上,通過修身養(yǎng)性,不斷超越自我,使自己通往更美好的自我。
儒家“人人皆可成圣賢”的理念構想認為,成圣人賢人是每個人與生俱來的天性,但是否如愿取決于“自己”的努力和恒心,是否具有向上追求的心態(tài)及“自己”希望達到什么樣的修養(yǎng)程度。在這個理念構想中,“自己”不斷地向上追求更高的自我水平,在“修己”及“克己”中逐漸內化社會禮義的規(guī)范及價值觀。同時,在儒家思想中,強調主體把“知天”、“窮理”,把“天道”、“天理”的覺悟作為自我修養(yǎng)的目標。因此,心理傳記學的研究,可以在儒家的傳統(tǒng)價值觀中探尋對傳主人格的發(fā)展和形成有影響作用的個人修養(yǎng)追求,關注傳主修養(yǎng)追求的發(fā)展水平,以求得到不同的解讀。
第二,家族自我。要求我們注重人倫綱常,親親之愛,家族榮譽感。
“家”作為社會生產的基本單元,以血緣親情為紐帶,家與家之間的網(wǎng)絡結構形成社會關系的“家庭”,進而拓展為整個社會關系的“國家”。“家”作為聯(lián)通自我與社會的橋梁,是自我形成的根源。個體作為家族的重要成分,賦予每個家庭成員相應的家庭責任和義務,家族自我?guī)в屑易骞餐谕湍繕说氖姑小H绱梭w現(xiàn)“吾喪我”的境界,拋棄“小我”,完成“大我”,以家族的榮譽感和使命感為己任,使自己的理想追求符合家族期望。所以,在心理傳記學的研究中多關注傳主所在家庭生活中雙親兄長的倫理綱常對其人格形成發(fā)展的影響,同時挖掘傳主是否有背負著家族寄予的期望,找出其使命感的由來。
第三,社會自我。中國人的自我角色還會考慮到他人或社會的要求,其自我的道德修養(yǎng)程度在不同的社會情境中表現(xiàn)出來,依照一定的社會規(guī)范來順應社會的要求。通過在心理傳記學的方法下,考究當時的文化情境下的社會背景和時代要求,挖掘社會文化對傳主人格特征的影響因素。
因此,中國人的自我通過強調自身的修身養(yǎng)性,要求主體通過“內省”、“盡心”或“格致”、“窮理”,才能真正體悟天道、確認天理,完成“修身,治國,平天下”的人生修為。自我的發(fā)展經(jīng)歷從個人自我的修養(yǎng)提升,到完成家族的期望和使命中獲得榮譽感,再到遵循社會規(guī)范來順應社會時代要求,不斷從純自我不斷向外擴張,在不同角色及角色期待中,尋求升化自我追求的過程。
三、總結
心理傳記學主要用心理學理論來解釋人格特征,心理學的研究離不開個人與其所處文化之間復雜的關系,且文化對人格、自我的發(fā)展影響深遠。在對中國傳主進行心理傳記學的分析時,中國傳統(tǒng)儒家文化對人格與自我的形成和發(fā)展有著密不可分的聯(lián)系。通過三種不同的自我形式來剖析傳主的人格特征,使傳主的生平和背景的故事更有意義,更加了解其背后的心理動態(tài)。
參考文獻:
[1]郭斯萍,林蓉.(2012).中國人自我觀理性分析—基于儒家倫理文化的視角.戰(zhàn)略決策研究,3(4),72-77.
[2]舒爾茨(SchulTz, W. T. )主編, 鄭劍虹等譯. (2011).心理傳記學手冊.廣州: 暨南大學出版社, 24-26.
[3]楊國樞.(2004). 華人自我的理論分析與實證研究:社會取向與個人取向的觀點.本土心理學研究, 22:1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