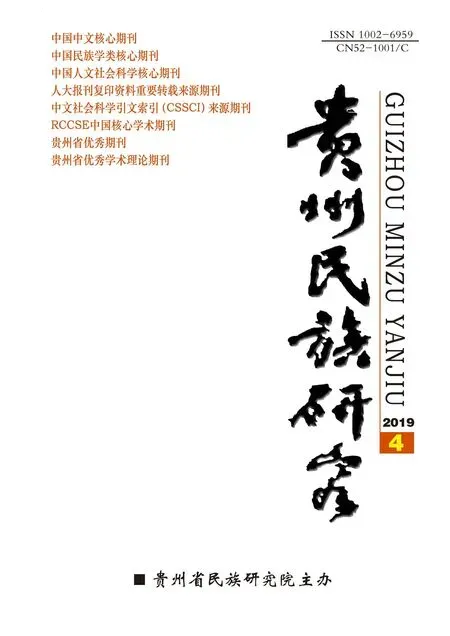西南少數民族武術文化空間探究
劉堯峰
(湖北民族大學 體育學院,湖北·恩施 445000)
近代以來,隨著社會變遷的不斷加劇,我國少數民族武術文化展現出的文化場域逐漸式微,生存空間越來越狹窄,許多彌足珍貴的少數民族武術文化正悄然淡出人們的視線。文化場所作為少數民族武術文化得以存活的關鍵場域,一方面使得少數民族武術文化得以產生并世代沿襲,另一方面也給予了少數民族武術文化得以保存和再現的文化土壤,失去了文化場域也就失去了存活的依托。本文以西南少數民族武術文化空間為對象,探究其文化空間的類型及其表現特征,對于守護民族文化基因,保護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特色文化及其文化的傳承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武術文化空間的界定
“文化空間”亦稱“文化場所”,是傳統文化得以產生、存活與傳承的時空場域,擁有時間與空間的雙重屬性。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來看,文化空間是同一類文化所在的生存空間及場所[1]。武術文化空間作為武術文化的依托,是武術文化所賴以存在的時空場域,它是在“文化空間”概念的基礎上衍生出來的。根據相關學者的描述,武術文化空間一般特指“某個集中展示武術文化活動或武術文化元素的地點,或確定在某一周期舉辦與武術文化有關的一段時間。”[2]包括時間性武術文化空間與空間性武術文化空間兩種類型。
二、西南少數民族武術的文化空間
根據文化空間及其武術文化空間的界定,西南少數民族武術文化空間主要包括西南地區的傳統節日、宗教祭儀、傳統賽事等時間性武術“文化空間”,以及廟會、村落及其學校等空間性武術文化空間,兩者成為西南少數民族武術文化寄寓的主要文化場域。
(一)西南少數民族時間性武術文化空間
1.西南少數民族武術的傳統節日文化空間
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素有“節日之鄉”的美譽,擁有眾多傳統節日,諸如彝族的火把節、虎節,傣族的潑水節、送龍節,傈僳族的盍什節、刀桿節,瑤族的盤王節、達努節,景頗族的目瑙縱歌節,苗族的花山節、趕秋節,土家族的舍巴節、龍袍節,白族的三月街、繞三靈等節日,不勝枚舉。
傳統節日是展示民族民間文化藝術的“大觀園”。“千百年來,各種民族民間藝術在這里展現、交融、競爭、錘煉,從而鑄造了一代又一代、一批又一批藝術珍品,流傳后世。”[3]西南少數民族的傳統節日是西南少數民族地區各種民俗活動傳承與發展的載體,而其中的某些節日更是為西南少數民族武術文化提供了展演的舞臺,尤其是在一些重大的傳統節日上,往往都會有精彩絕倫的武藝展示,抑或是富含武術技擊動作的傳統舞蹈表演。例如景頗族的目瑙縱歌節上就有精彩絕倫的景頗刀舞,其單刀舞和雙刀舞均有成熟的套路,景頗刀舞威猛迅疾,剛勁有力,充分展現出景頗男子勇猛彪悍的英武形象。傈僳族于每年農歷二月初八舉行的刀桿節上,亦有“挑花、點刀、抹刀、耍刀、上刀、折刀”等傳統刀術絕技展演,刀風嗖嗖、刀光閃閃,刀花如萬朵梨花一片;彝族、白族、納西族等少數民族每年農歷六月的火把節上,一般都會舉行賽馬、摔跤、射箭、拳術表演及其上刀梯等絕活。苗族趕秋節上,苗族勇士光膀赤腳如履平地般攀爬上高聳入云霄的刀梯,并在刀梯上表演單飛燕、倒掛金鉤、觀音坐蓮、大鵬展翅、古樹盤根等驚險刺激的武術動作。土家族“龍袍節”上也會安排各種耍拳、打飛棒、使刀槍、舞流星錘等武術展演活動。由此可見,傳統節日作為時間類武術文化空間,成為了西南少數民族武術文化的重要繼承方式之一。
2.西南少數民族武術的宗教祭祀類文化空間
受歷史發展及其自然環境等因素的影響,西南少數民族地區歷史上是一個巫風濃烈,原始宗教盛行的地方,素有“巫風野火出西南”之說。西南少數民族的宗教祭祀儀式繁多,而其中的巫儺祭儀和喪葬祭儀中,都蘊含著豐富的武術文化元素。宗教祭儀不僅是西南少數民族武術文化產生的一個重要原發性要素,同時也是其賴以生存的文化空間場域。
巫儺祭儀作為在西南少數民族地區普遍流傳的一種原始宗教形態,擁有豐厚的歷史文化積淀,對西南少數民族地區民眾的生產生活產生著重要的影響作用。西南少數民族巫儺祭儀中除了常規的祈禱以及供齋蘸神等儀式外,還有較多的武術打斗場景,亦武亦巫,巫武結合是其特色。例如納西族原始巫教東巴跳中就有各種單打、群打、刀對刀、劍對劍、三斗打、四破門、五佛跳,擒勾術等帶有濃郁民俗色彩的武術表演,每當祭風、消災、祭山神與龍王、除穢、開喪、走薦、求壽等七大道場時,一般都要進行東巴跳。尤其是在云南巨甸一帶傳統集會上,幾十乃至上百個東巴手持刀、劍、斧、叉、盾牌、矛法杖和降魔杵等武器和法器,進行對打、擲刀、飛矛、投叉等各種練武動作,整個表演氣勢如虹,威武雄壯。土家族苗族還儺愿的祭儀中巫師往往都要進行各種上刀梯、踩地刀、趟鏵犁、翻叉絕技以及套路武術的展演,在驅(殺)鬼儀式中,巫師“圍繞某種假想敵——‘鬼魂’來表演各種攻防搏殺的技巧與場景”[4]。又如貴州安順地戲(跳神)儀式中,場上演員手持刀、槍、劍、戟等兵器,進行各種驚險刺激的打、殺、劈、刺等武術動作。
西南少數民族的喪葬習俗,承載著豐富的武術文化內容。其祭儀往往以武事活動為媒介,例如彝族、哈尼族葬儀的送葬儀式中,為了祛邪驅鬼,讓死者平安到達天國,就有武藝隊揮舞雙刀、大刀、小龍頭等邊走邊演練。[5]云南羅平彝族的鬧喪活動中,亦有各種大刀、大鞭、連枷、金錢棍、奇門棍等莊嚴激勵的練武場面。鄂西南土家族地區喪葬儀式中為悼念亡靈而進行的各種跳武喪、打廩、繞棺表演等,則是將歌舞與武技交匯在一起的一種古老葬俗,武喪表演中的“猛虎下山”“燕兒銜泥”“犀牛望月”“鷂子翻身”以及繞棺舞的典型動作“彎弓射月”“懶龍翻身”“換邊拳”“倒立豎”等,動作粗狂豪邁,剛柔相濟,不乏武術文化的蹤影。而打廩過程中唱跳的動作和內容亦全是反映軍旅征戰、沖鋒陷陣、英勇殺敵等古老戰舞,是其民族武術文化的另類表達。喪葬習俗作為西南少數民族武術文化的特殊留存方式,為西南少數民族武術文化提供了相對廣闊的生存空間。
3.西南少數民族武術的賽事文化空間
武技競賽歷史久遠,相關典籍記載頗豐。從戰國莊周《莊子·說劍》:“日夜相擊于前……好之不厭”,到三國曹丕《典論·自序》:“下殿數交,三中其臂”,再到北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兩人出陣……或以槍對牌、劍對牌之類。”[6]及至民國時期,在“強國強種”的時代語境下,各級各類國術競賽接踵而至,使得流傳了千年之久的中國武術真正登上了體育競技的大雅之堂。新中國成立后,在黨和國家的關懷下,武術競賽的開展如火如荼,武術比賽業已形成了一整套科學規范、系統完善的賽事體系。
當前,少數民族的武術賽事主要集中于全國及其各省市少數民族傳統體育運動會的武術比賽中,而全國少數民族武術比賽作為單項賽事的發展步伐則較緩慢。作為時間性武術文化空間,各級少數民族傳統體育運動會為少數民族武術提供了文化交流與技藝展演的平臺。西南少數民族武術更是借助于各級民運會的大舞臺來展示自身獨特的魅力,例如在第九屆全國少數民族傳統體育運動會上,就有《布依族貓叉》《巴子刀》《孔雀棍》《仡佬族武術》《哈尼族武術》《龍渣瑤拳》等精彩絕倫的西南少數民族武藝展演。而在湖北省第八屆少數民族傳統體育運動會上,土家族武術運動員所表演的《土家白虎拳》《土家扁擔拳》《土家板凳拳》《土家降魔棍》《土家雞公鏟》《土家羊角叉》等珍貴稀有的原生態武術拳械,其原始古樸的技術風格讓人耳目一新,對傳播與推廣土家族武術文化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全國以及西南少數民族地區各省市舉辦的少數民族傳統體育運動會作為固定時間類文化空間,成為了當今西南少數民族武術文化交流、傳承與傳播的重要文化空間場域。
(二)西南少數民族空間性武術文化空間
1.西南少數民族武術的傳統廟會文化空間
“廟會”又稱“廟市”或“節場”,是我國民間廣為流傳的一種古老的民俗活動,多在春節和元宵節等節日內舉行。傳統廟會活動期間往往都會舉行各種祭神、娛樂及其商貿活動。建國后的“四清運動”和“文化大革命”期間,廟會曾被視為是滋生封建迷信活動的溫床而被禁止,失去了在公共場合存在的合法地位。改革開放以后,隨著國民思想的解放以及文化需求的不斷升溫,各地廟會再度興盛起來,“現今的地方廟會大多已經發展成為集民間文藝表演、民間武術、民間手工技藝、商貿旅游為一體的民間傳統盛會。”[7]廟會已經成為傳統民俗中的一種地方性文化標志。
西南少數民族地區是我國宗教信仰最為普遍,宗教品系最為齊全的地區,不僅保存有各少數民族的特色宗教,諸如東巴教以及各種祖先崇拜與自然崇拜等宗教信仰,同時還有漢族流傳而來的宗教,呈現出一種兼收并蓄的宗教文化特征。由于宗教品系的繁盛,伴隨而來的便是廟宇林立,各種廟會活動興盛的獨特景象。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的傳統廟會活動不僅在滿足人們的信仰需求、增強鄉土意識、推動地區貿易、繁榮市場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同時形形色色的鄉村廟會也為各種民俗活動提供了展演的舞臺,各種雜耍絕活、舞龍舞獅、武術展演等大都借助傳統廟會這一平臺得以亮相,并成為廟會活動中最能吸引眼球的活動。例如在湘西土家族地區廟會上舞獅擲繡球者,開場前往往都要表演“四門架子”“蘇公背箭”“猛虎跳澗”“五虎群羊”“八虎拳”“白虎拳”等土家族拳術。而云南民族村滇池廟會上,一般都有水族套吞口、苗族吹槍、傈僳族射弩等原生態的少數民族武藝展示。又如擁有千百年歷史的云南大理白族“三月街”廟會集市,期間除了常規的物資交流以外,還有賽馬、摔跤、射箭、打拳等精湛絕倫的傳統武藝展演,使得整場演出高潮迭起。在過去的西南少數民族地區,某些江湖藝人會將傳統廟會視為自己的“金飯碗”,廟會表演成為他們賺錢養家糊口的良機。為了尋覓演出機會,他們對地區傳統廟會的時間與地點了如指掌,逢會必演,正是在這樣的天地里,少數民族武術得以留存與承傳。傳統廟會作為地區民俗文化交流的載體,為西南少數民族武術提供了獨特的文化空間場域。
2.西南少數民族武術的村落文化空間
村落作為傳統農村的一種社會組織形式與社會結構單位,是廣大農民生存與發展的基本生活空間,同時也是滋生各種村落文化的根本領域。村落武術作為村落文化的重要載體,是村落組織的文化代言,而村落則為村落武術提供了賴以生存的文化土壤,是村落武術的文化空間所在。
長期以來,西南少數民族武術文化的延存,同樣離不開傳統村落這一特定的文化空間,鄉村拳場是人們練拳習武的重要場域,在村落這一特定的時空場域中,村落武術作為慰藉情感精神與維護鄉村秩序的重要手段,在西南少數民族村落中不斷地傳承和綿延。例如梅山武術作為在梅山當地農村廣為流傳的鄉土武術,就屬于典型的村落武術,擁有濃厚的群眾基礎。當地民間很早就有“設廠習武”的傳統,村落拳師一般會在農閑之際開廠授徒,“忙時耕田、閑時練拳”已成為地區村落的一種文化生活模式。與此同時,村落在一些重大喜慶節日中往往都會組織一班拳套人馬進行武術表演,各村落拳師還常常以武會友,切磋技藝,梅山武術成為了地區村落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成為村民個人身份的象征。又如湘西花垣縣麻栗場鎮金牛村,作為西南地區一個偏遠的苗民聚居村落,其村民尚武之氣蔚然成風,無論男女老幼都會耍上幾套拳腳。該村世代流傳著一種苗族上古拳術蚩尤拳,自清代乾嘉苗民起義以來,金牛蚩尤拳即聲名大震。上百年來,蚩尤拳在金牛村村民中世代承襲,成為村落文化的一大特色。平日里,無論田地村頭還是屋角院落,往往都有練習蚩尤拳的村民身影,而到了農閑時期,武術愛好者更是立堂開練,切磋技藝,練拳習武成為了金牛村村民的一種日常生活方式。村落作為空間性的武術文化空間,使得西南少數民族武術文化得以世代存續和綿延。
三、結語
西南少數民族武術文化空間為西南少數民族武術提供了生存與展演的平臺,正是具備了各種文化空間的載體,西南少數民族武術才得以擁有頑強的生命力而世代承襲。然而近代以來,隨著社會的變遷與商業經濟的發展,在多元型現代文化的沖擊下,西南少數民族武術賴以生存的原始文化土壤不斷消失,文化活動場域逐漸呈現出衰微的景象。因此,在社會變遷日益加劇的當下,加強西南少數民族武術文化空間的保護與傳承已成刻不容緩之事,這就需要發動地方政府與社會民眾的雙驅動聯合力量,在保護現有文化空間的基礎上,不斷拓展出新的生存空間。唯有這樣,西南少數民族武術文化的傳承與發展之路才能越走越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