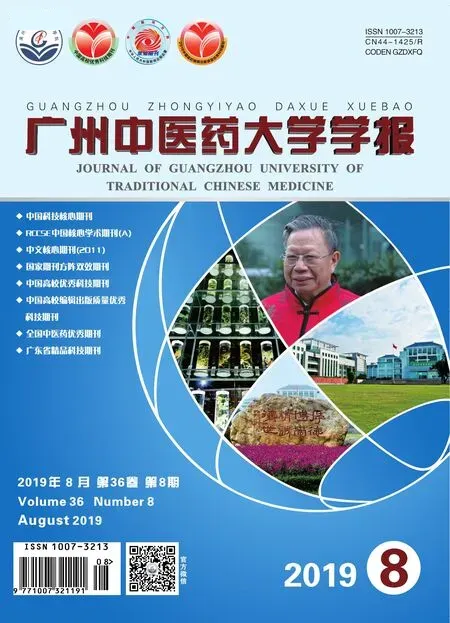嶺南中醫對腎病的辨治特色
張禮財, 湯水福
(1.廣州中醫藥大學第一臨床醫學院,廣東廣州 510405;2.廣州中醫藥大第一附屬醫院,廣東廣州 510405)
嶺南中醫為我國中醫最具特色的地方流派之一。明清時期,隨著嶺南地區經濟文化的發展,嶺南中醫有了較快的發展;至民國時期,嶺南中醫發展達到了高峰。據統計,歷代廣東中醫藥文獻約有408部,其中明代以前65部,清代230部,民初113部;歷代嶺南醫家大約有953人,其中明代以前74人,清代429人,民初有450人[1]。
傳統中醫雖無明確的腎病學分科,但對于腎系疾病的認識有著悠久的歷史,并積累了較豐富的治療經驗。根據腎臟疾病的臨床癥狀,多將腎系疾病歸于“水腫”、“關格”、“腰痛”、“虛勞”等范疇。嶺南中醫作為我國中醫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腎系疾病的治療亦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同時具備鮮明的地方特色。以下通過總結以廣東省為代表的歷代嶺南代表性醫家對腎系疾病的認識與治療特點,特別是通過對廣東省近現代主要中醫腎病名家的治療經驗進行整理,以總結嶺南中醫治療腎病的基本特點。
1 嶺南中醫繼承中原醫學對腎病的辨治思路
嶺南中醫是發源于中原文化的醫學體系。歷史上,中原士民經過數次南遷,在此過程中把中原文化帶入嶺南地區,中醫學也隨著此過程而傳入嶺南。最典型的例子是東晉著名醫家葛洪,其出身于江南士族,晚年隱居于嶺南羅浮山,在嶺南醫學史上居重要地位。其所著《肘后備急方》中的《治大腹水腫方》,多選用峻下逐水之藥治療水腫。清代醫家何夢瑤,其代表作《醫碥》將水腫稱為腫脹,對于水腫的治療,強調“治水當分陰陽”,書中還引用了《金匱要略》對于水腫的分類及方藥。
從嶺南醫家的相關論著中不難看出其受中原醫學影響的痕跡。如近現代嶺南著名溫病學家劉赤選,認為水腫與肺、脾、腎有關,特別是與脾腎的關系最為密切[2]。著名老中醫張階平提出治療腎炎水腫的“治水七法”[3],其中利尿、消導、發汗三法,實乃“開鬼門,潔凈腑,去菀陳莝”的具體體現。著名老中醫何汝湛,精于《金匱要略》,擅長于腎系疾病的治療,基于《靈樞·五癃津液別論》中“邪氣內逆,則氣為之閉塞而不行,不行則為水脹”論述,臨床善用行氣利水法治療尿毒癥[4]。何炎燊基于葉天士“邪干陽位,氣壅不通”的理論,于《黃帝內經》治水三法之外,善用清肅上焦法治療腎炎水腫[5]。上述醫家雖非腎病專科醫生,但對于腎系疾病的治療積累了豐富的臨床經驗。上述醫家均精通于中醫經典著作,其辨治腎病的思路明顯受中醫經典的影響。
新中國成立以來,繼各中醫院校成立之后,各地中醫院先后成立了腎病專科,中醫開始有了腎病專科醫生。著名的嶺南中醫腎病專家如葉任高、洪欽國、楊霓芝等,其對腎病的辨治思路雖各有特色,但一致認為慢性腎病的病機為本虛標實,這與中原醫學對于本病的基本認識相一致,亦體現出嶺南醫學繼承性的一面。
2 嶺南中醫開創中西醫結合療法治療腎病
明清以后,嶺南成為我國對外交流的主要窗口。近代以來,西學東漸也主要經海路進入我國。嶺南瀕臨南海,是我國最早接觸西方醫學的地區之一。中西方醫學的碰撞,使不少嶺南醫家嘗試把西方醫學知識運用到中醫腎病的辨證治療上來。著名中西醫結合醫學的先驅黃省三,以西醫解剖、生理、病理等知識解釋腎系疾病,治病強調專病專方,著有《腎臟炎腎變性實驗新療法》一書,并創制“黃氏腎臟炎腎變性有效湯方”,取得了良好的效果[6]。
著名腎病學家葉任高,師從黃省三學習中醫治療腎病,成為我國著名中西醫結合專家。葉任高通過臨床觀察,認為慢性腎炎的血尿、蛋白尿、高血壓、腎功能減退與中醫的證型有一定的關系,可將其作為中醫辨證依據之一。對于腎病綜合征采用激素治療的患者,葉任高分階段運用不同的中醫治法與激素配合,減少了激素的副作用[7]。黃春林對于腎病治療強調辨證與辨病相結合,臨床用藥多結合現代中藥藥理知識,主張根據慢性腎病的分期及并發癥的不同而采用不同的中醫治法[8]。楊霓芝主張中醫辨證與實驗室檢查相結合,認為患者尿液檢查結果以蛋白尿為主者宜以益氣健脾補腎為主,而以血尿為主者當以養陰清熱活血為主;腎臟病理檢查結果以增生為主者以清熱解毒利濕為主,以硬化為主者當以活血化瘀為主[9]。由此可知,在中、西方醫學的接觸過程中,嶺南腎病醫家積極吸納西方醫學知識,拓展了中醫辨證論治的內涵,在采用中西醫結合療法治療腎病中作出了新的嘗試。
3 嶺南中醫對腎病的辨治特色
3.1 重補益脾腎 中醫認為腎炎水腫與肺、脾、腎三臟功能失調有關。慢性腎病虛實夾雜之病機已成為醫家之共識,其中尤以脾腎虛損為常見。而嶺南地處我國大陸最南端,氣候炎熱潮濕,濕重則礙脾。獨特的氣候特點,致使嶺南人多見脾氣虛弱兼痰濕的體質特點[10]。脾為后天之本,脾氣虛損,久則必然及腎。所以嶺南醫家治療腎病尤重補益脾腎。如劉赤選論水腫之治療,認為本病初起多傷脾,遷延日久必傷腎;張階平“腎炎水腫七法”中包括健脾、補虛、溫補三法[3],并自擬“虛腫方”、“腎損方”,分別用于治療腎炎水腫及尿毒癥[3];梁端儕善用人參培本固元以治療慢性腎炎[11];國醫大師鄧鐵濤認為腎炎早期表現為脾虛濕困,中后期表現為脾腎陽虛,后期表現為肝腎陰虛,而脾虛是本病的共性,主張治療過程中應注重調理脾氣,其所擬“消尿白方”及“尿毒癥方”亦重在補益脾腎[12];林品生對于慢性腎炎水腫的治療,十分推崇張景岳“溫補即所以化氣,氣化而愈者,愈之自然,攻伐所以逐邪,逐邪而愈者,愈之勉強”,主張用溫補法治療慢性腎炎,并把“扶正”的觀點貫穿于治療的始終[13];梁劍波精通東垣學說,臨證治療慢性腎病尤其重視脾胃功能的調治[14];葉任高認為慢性腎衰存在著虛、濁、瘀、毒四大病理機制,以脾腎虛衰,濁毒潴留為病機關鍵[15];黃春林治療慢性腎病強調“扶正不戀邪,祛邪不傷正”,用藥重視調補脾腎,并提出調脾七法[16];沈英森治療腎炎水腫亦強調健脾補腎以固本[17];劉恩祺認為蛋白尿是內、外因共同作用的結果,其中肺、脾、腎虛為病之本,尤其是氣虛[18];楊霓芝認為慢性腎炎為本虛標實之證,而本虛以脾腎虧虛最為常見,故治療尤重補益脾腎之氣[19]。此外,李俊彪、羅仁等嶺南中醫腎病名家對慢性腎病的治療均無不重視補益脾腎。
3.2 重清利濕熱 嶺南氣候屬熱帶、亞熱帶氣候,春夏多雨,天熱地濕,故《嶺南衛生方》提出“嶺以外號稱炎方,又瀕海,氣常燠而地多濕,與中州異。氣燠故陽常泄,而患不降;地濕故陰常盛,而患不升”。腎系疾病又多因脾腎功能失調。脾主運化,腎主水。脾腎功能失調,則外濕易感而內濕易生。濕郁化熱或濕熱相熏蒸,故成濕熱之候。嶺南醫家基于當地氣候特點,認為濕邪或濕熱之邪是慢性腎病最重要的實邪之一,故臨證治病無不強調祛濕藥的運用,其中尤以清利濕熱之藥為多。張階平治療腎炎蛋白尿提出“濕熱不除,蛋白難消”的理論[3],足見其對清利濕熱之重視。劉仕昌治療慢性腎炎尤其重視濕邪對于疾病的影響,強調濕與熱合,膠結難解,使病情纏綿[20]。黃春林治療慢性腎病的“調脾七法”中有清熱利濕和溫陽化濁二法以治療濕熱及寒濕之邪[16];楊霓芝治療慢性腎炎也十分重視濕熱之邪的致病作用,認為濕熱是慢性腎病發病的一個重要因素,故臨證強調清熱利濕之法的運用[19]。劉恩祺、梁宏正、李俊彪等醫家均強調濕邪是慢性腎病邪實之一,認為臨證當在扶正的同時兼顧祛濕,方能獲得較好的效果。由此可見,因嶺南獨特的氣候特點以及慢性腎病的病機特點,嶺南中醫對于運用清利濕熱法治療慢性腎病已基本達成共識。
3.3 重通腑泄濁 慢性腎病發展至后期,脾腎由虛及損,由損及敗,痰濕濁毒之邪充斥三焦,變證蜂起。葉任高治療慢性腎衰曾于方中加用大黃,認為大黃可清熱解毒、行瘀通便,具有推陳出新、安和五臟、延緩腎功能進展之功,尤其對于年輕體壯者效果尤佳[7]。洪欽國治療本病本著“祛邪以扶正,泄實為先”的觀點,根據《素問》“大腸者,傳導之官,變化出焉”。認為糟粕化成糞便而排出是脾胃降濁功能的延伸,故臨床多喜用大黃、虎杖以通腑泄濁,使邪有出路[21]。黃春林治療本病亦善用通腑法,并根據慢性腎病分期的不同,配合不同的治法,如氮質血癥期以健脾補腎法配合通腑化濁,尿毒癥期以溫陽化氣法配合通腑降濁[8]。駱繼杰認為人體臟與腑之間生理上相互聯系,病理上相互影響,治療上可通過治臟病以治腑病,治腑病以治臟病,故治療慢性腎衰強調“通腑健臟”的思想,臨床上靈活運用生大黃、熟大黃或加用潤腸通便藥以達到通腑之功[22]。楊霓芝治療慢性腎功能衰竭多配用大黃膠囊通腑以泄濁,或配合灌腸法以增加通腑泄濁之功[23]。盡管不少嶺南醫家都重視通腑法的作用,然而他們均強調慢性腎病以正虛為本,所以通腑不可使排便次數太過,以每日排便2~3次為宜,太過反而于患者不利。
3.4 重活血化瘀 慢性腎病多脾腎虧虛,氣不行血,因虛成瘀,加之病情纏綿,久病則入絡。而嶺南之地炎熱多雨,患者多濕多痰,痰濕阻滯氣血,可因滯成瘀;痰濕郁而化熱,熱蒸血脈,亦成瘀血。故嶺南腎病醫家尤重視活血化瘀法的運用。劉仕昌認為慢性腎炎的治療切忌一味扶正或只顧攻邪,需在補脾腎的基礎上,加用益母草、郁金、丹參等藥以起活血化瘀之功。林品生用藥力主精專,尤善用益母草,對于慢性腎炎多重用益母草配以黃芪,再結合其自擬固守丸或其他益精補虛、益氣養血之品進行治療[24]。葉任高從西醫病理出發,結合臨床經驗,認為慢性腎病自始至終都有血瘀的存在,并認為血瘀是本病持續發展及腎功能進行性衰竭的重要原因[25],其自擬“腎衰方”采用大黃、丹參、當歸、赤芍配伍以獲活血化瘀、改善高凝狀態、延緩腎功能衰竭之功[26]。楊霓芝治療慢性腎炎以擅長運用益氣活血法著稱,認為慢性腎炎的邪實雖然有瘀血、濕熱、濕濁之分,然而以瘀血最為關鍵,并認為氣虛血瘀是慢性腎炎的基本證型,故主張將活血化瘀法貫穿在慢性腎炎治療的始終[19]。洪欽國重視祛邪以扶正,其中活血化瘀是最常用的祛邪法之一。沈英森、劉恩祺、李俊彪、羅仁等在治療慢性腎病的過程中也均強調活血化瘀法。
由上可知,治療腎臟疾病時對于活血化瘀法的重視程度,年輕一輩嶺南醫家要強于老一輩醫家,而腎病專科醫生的重視程度又強于非腎病專科醫生。
3.5 善用嶺南地方草藥 嶺南草木蕃盛,可用藥材資源豐富。歷史上有何克諫《生草藥性備要》、趙寅谷《本草求原》、肖步丹《嶺南采藥錄》、胡真《山草指南》等一批嶺南草藥醫家及本草論著。嶺南醫家在治療腎病時,亦多配用地方草藥。如鄧鐵濤運用三葉人字草治療血尿,運用珍珠草、小葉鳳尾草治療慢性腎盂腎炎;洪欽國治療腎病善用積雪草、腎茶等;梁宏正家學淵源,其治療腎病尤喜用嶺南特色草藥,如用三白草、珍珠草、腎茶、葫蘆茶、塘葛菜等利水通淋,以磨盤草、金櫻根治療腰痛、耳鳴、遺精,用山地稔、大血藤、花生衣治療腎性貧血,用馬纓丹、小飛楊治療皮膚瘙癢[27]等。除此之外,嶺南草藥如五指毛桃、牛大力、火炭母、布渣葉、救必應等均為嶺南中醫治療腎病的常用藥。
總之,嶺南中醫淵源于中原醫學,在長期的實踐過程中,本著中醫因時、因地、因人而異的治療理念,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特點。中醫治療腎系疾病源遠流長,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嶺南中醫對于腎臟疾病的認識及治療有繼承于中原醫學的一面,如對于慢性腎病基本病機的認識、對于脾腎的重視等均與中原中醫對于本病的認識相一致。同時,因嶺南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前沿陣地,嶺南中醫治療腎病積極吸納現代西方醫學知識,并將其運用于中醫腎病的辨證治療的實踐中。嶺南獨特的地理位置及氣候特點以及嶺南人獨特的體質特點,促使嶺南中醫治療腎病尤重視補益脾腎及活血化瘀。嶺南草木蕃盛,藥用資源豐富,嶺南醫家對于地方草藥的運用有悠久歷史,并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嶺南醫家將嶺南草藥運用到腎病的治療上,取得了良好的療效,成為其鮮明的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