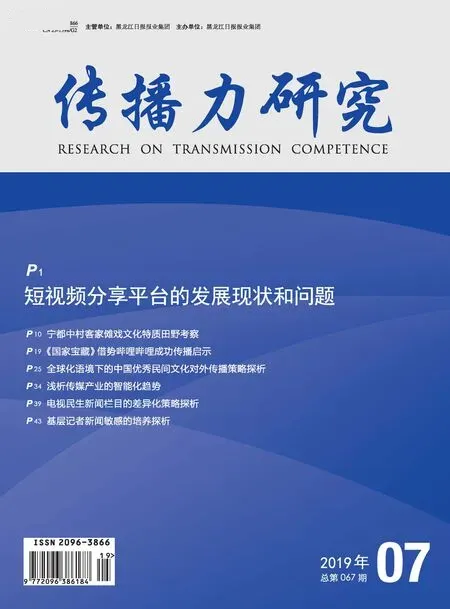熱門網絡綜藝背后的傳播學視角分析
牟茜薇 上海大學
近年來,隨著現代生活節奏的加快,人們對于娛樂化內容的消費需求也隨之旺盛。國內綜藝節目有如“雨后春筍”般層出不窮,網絡媒體技術的發展更是給了網絡綜藝節目廣闊的創作空間,各類“網綜”應運而生,其中不乏收視和口碑皆不俗的“現象級”綜藝的誕生,如《向往的生活》系列、《這!就是街舞》、《創造營2019》等等。
網絡綜藝節目一方面滿足看受眾視覺欣賞的需求,豐富了受眾的精神文化需求,另一方面也顯示出我國娛樂文化產業強大的發展動力,本文將對當下熱門“網綜”展開分析,運用傳播學視角探究其“火熱”背后的原因。
一、網絡綜藝節目的發展現狀分析
從2014年起,我國網絡綜藝節目的數量與播放量就一直保持增長態勢,歷經五年多的高速發展,當下中國的網絡綜藝市場進入了激烈競爭的時代。2018年,新播國產網綜數量為162 部,網綜投資規模達68 億,同比增長超58%,在政策趨嚴的調控下,大量資本涌入網綜市場,網綜內容實現了質的飛躍。(1)
超級網綜數量大幅提升,涌現出《創造101》、《偶像練習生》、《這!就是街舞》、《向往的生活》等具有廣泛影響力的作品。頭部網綜重視開發長尾效應,推出衍生節目進一步擴大影響,同時,腰部內容針對不同用戶持續深耕,類型趨于多元。網綜付費模式逐漸形成,商業化能力不斷增強,網綜產業鏈不斷完善,網綜市場的生態進一步形成。
二、網絡綜藝節目的“火熱”原因
(一)官方發力,內容制作精良
資本投入是決定網綜內容質量高低的關鍵,當下,大熱的“現象級”網綜無一例外都是“大廠出品”。網綜觀看量Top20 的節目,幾乎都來自于騰訊視頻、愛奇藝、優酷這三大頭部視頻網站。官方大手筆的投入,保證了整個綜藝節目制作過程的環節的順利進行,而優質的節目輸出也為收視率和點擊量提供了保證,同時有利于后期的廣告招商,這也為優質綜藝的良性制作循環打下了基礎。[1]
(二)技術賦權背景下的多渠道傳播
移動端的普及和互聯網的技術賦權都為網綜的“火熱”提供了技術加持。網絡自制綜藝不僅限于同一終端設備,伴隨移動終端的普及,電腦網站、智能手機和APP 的使用,實現了受眾隨時隨地觀看網綜的可能性,甚至成為用戶打發“碎片化”時間的利器。[2]技術賦權的大背景下,用戶可以參與到網綜制作的過程中,《創造101》作為一部“現象級”網綜,再度掀起了“全民造星”的浪潮,用戶可以主動為自己喜愛的選手“打Call”,充分滿足用戶的互動參與感。
(三)內容多元,充分考慮受眾需求
弗洛伊德說:“一個幸福的人從來不會幻想,幻想只會發生在愿望得不到滿足的人身上”。大眾媒介無疑具有這樣一種“造夢”屬性,個體無法實現的愿望,可以在媒介塑造的“擬態環境”中,通過觀看網絡綜藝得以實現自我愿望的“替代性滿足”。當前,網絡綜藝節目的類型豐富多樣,既有《偶像練習生》,《這!就是街舞》等選秀類節目,也有《向往的生活》,《親愛的客棧》等主打“詩與遠方”的“慢綜藝”節目。受眾的需求得到了極大的滿足,現實生活中受眾無法體驗的生活方式,無法抵達的“詩和遠方”都可以在網絡綜藝中得到實現,喚起受眾的“共情式體驗”。
(四)消費社會下的粉絲經濟“變現”
法蘭克福學派思想家洛文塔爾指出,20世紀美國流行雜志中的傳記作品越來越傾向于“消費偶像”,即娛樂明星。這與消費社會的塑造有很大關系,鮑德里亞曾在《消費社會》中提出,身體是最美的消費品。于是,網絡綜藝開始毫不吝嗇的販賣偶像們帥氣的外形,將身體編碼為欲望符號供粉絲消費。網絡綜藝瞄準了“粉絲經濟”強大的變現能力,重構了偶像與粉絲之間的關系,從消費偶像向創造偶像轉變。[3]《創造101》,《明日之子》等綜藝主打“養成系偶像”的路線,將處于培訓成長期的藝人投放到媒體上進行粉絲積累,在這個過程中借助網絡綜藝串聯了偶像和粉絲的互動關系,完成了“粉絲經濟”帶來關注度以及流量的持續變現。
(五)亞文化傳播的主流化呈現
伴隨生產方式與文化形態的變遷,互聯網時代的媒介文化也發生著相應的變化。最為典型的就是一些亞文化的主流化。當下,社會化網絡構建的媒介環境讓原本處于小眾和邊緣地帶的亞文化有了展現自我的舞臺,新興的網絡亞文化不僅在受眾的大規模參與中能迅速走向大眾,也逐漸在多種力量的推動下向主流靠攏。[4]《這!就是街舞》作為一檔推廣傳播街舞文化的綜藝,一方面通過明星導師自帶的IP 吸引流量,一方面將原本小眾的街舞文化以一種專業又不失主流化的形式呈現在受眾面前,完成了網絡綜藝節目在內容類型垂直細分上的一份出色答卷。隨后的“全民皆舞”活動的發起,又成功的完成了圈層突破,帶動更多受眾參與關注節目,實現了網絡綜藝的長尾效應。
三、結論
需要指出的是,盡管我國網絡綜藝在未來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但在發展的過程中仍要注意,綜藝節目重要的是凸顯差異,營造獨特的受眾體驗,一味跟風而上,推出同質化的內容并不可取。同時,對于海外節目的引入也要強調社會性,人文性與本土創新的結合,在堅持“內容為王”的前提下兼顧受眾需求,做到網絡綜藝節目文化性與娛樂性的協調同步發展。
注釋:
(1)數據來源于藝恩咨詢《2018年中國網絡綜藝市場白皮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