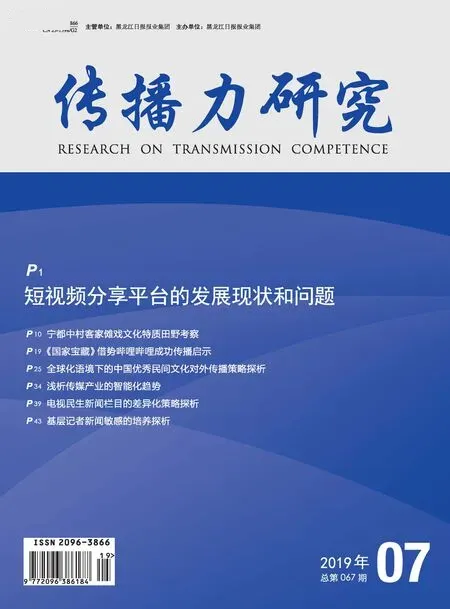新媒體時代第一人稱紀錄片的創新與發展
——以《四個春天》為例
張羅羅 山東師范大學新聞與傳媒學院
第一人稱紀錄片是借助電影、手機、DV 等電子媒介,在敘事過程中采用第一人稱的聲音,引領觀眾進入講述者的世界,是一種真實展現生活和社會的影視藝術呈現形式。但由于諸多現實狀況,第一人稱紀錄片的影響力始終有限,大多是在獨立紀錄片的圈層中進行傳播。新媒體時代下,如何利用新媒體的優勢來提高第一人稱紀錄片的傳播力和影響力,是急需解決的問題。
一、新媒體時代第一人稱紀錄片生產方式的創新
(一)質樸真實的鏡頭語言
為了打破傳統家庭錄像的細碎感,第一人稱紀錄片《四個春天》在鏡頭語言上,使用了多角度多景別的鏡頭對于父母的詩意生活進行了展示。與傳統第一人稱紀錄片描寫苦難不同,對姐姐的離世導演只通過零碎鏡頭的拼貼完成敘事。這種鏡頭處理方式,使得鏡頭量增多節奏加快,適合新媒體時代受眾接受信息的方式。影片還多次使用了長鏡頭,真實地展示了家庭生活情境。如:父親在右深情投入唱《朋友》,母親在左安靜認真地縫衣服,整個畫面像一個舞臺一樣,上演著不同的生活戲碼,供觀眾領悟。此外,影片多次運用了空鏡頭,注重鏡頭的寫意性。例如:開放的迎春花、空曠的大山等,這些質樸真實的鏡頭語言為觀眾提供了在日常生活中常被忽視的情感體驗。
(二)碎片化的敘事手法
第一人稱紀錄電影由于個人化視角的限制,在主題上往往具有單義性的特征,但主題的單義性不等于敘事的單調性。為了符合新媒體時代受眾的碎片時間,碎片化的敘事手法在紀錄片中被廣泛使用。傳統的第一人稱紀錄片的敘事往往是針對個人的獨特價值或者敏感話題來進行隱私討論,來著重彰顯個體隱私。《四個春天》重在通過碎片化的敘事手法,將家庭生活與社會現實相勾連,拉近影片與觀眾的心理距離,比傳統紀錄片冗長的敘事更容易讓觀眾產生代入感。
(三)充滿質感的聲音表達
傳統的第一人稱紀錄片的聲音大多是體現沉重感為主體訴求。但《四個春天》在聲音表達上充滿了質感,也是影像的情感宣泄口。在影片中導演并未使用太多的背景音,更多的是以母親和姐姐的歌聲、父親的樂器聲為主。例如:在第一春天,姐姐在向父母講述自己在車上遇到的事情時,幽默的聲音演繹讓觀眾啼笑皆非。面對姐姐去世,回憶的畫面與遺留的歌聲交織在一起,歡樂與悲痛在觀眾心底激起強大的情感漩渦,聲音的流動打破了觀眾的心理防線。
二、新媒體時代第一人稱紀錄片傳播方式的創新
(一)利用社交媒體,進行多向傳播
隨著互聯網技術的發展,社交媒體成為了用戶發表意見的主要渠道。紀錄片《四個春天》在未播出之前,就有一批潛在的粉絲。導演陸慶屹曾經在豆瓣上寫過兩篇短文《我爸》和《我媽》被網友轉發、評論,看似簡單的互動,便可形成爆炸式效應。同時,導演還在微博、微信上發起話題討論,引來了大量用戶的圍觀討論,這也在無形之中擴大了影片的影響力。此外,觀眾可以在視頻網站利用彈幕發表見解,其話語權在社交媒體平臺上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因此,社交媒體的運用,推動了影片和受眾的雙向傳播,以此擴大紀錄片的傳播力。
(二)媒介融合,進行大眾傳播
傳統第一人稱紀錄片在傳播平臺上往往具有單一性,平臺與平臺之間缺乏互動聯系。隨著媒介融合的深入推行,拓寬了第一稱紀錄片的傳播平臺,能夠將紀錄片的有效信息傳遞給目標受眾。《四個春天》形成了媒介融合的立體化傳播,最大化獲得了輿論傳播效果。它促進了第一人稱紀錄電影由“私人化”影像到“公開”轉變,擴大了受眾群體。同時導演還利用新媒體平臺,進行了線上與線下的互動,全方位對影片進行宣推。因此,新媒體時代中的多渠道的融合,實現了大眾傳播。
三、新媒體時代第一人稱紀錄片價值建構的創新
(一)新視角構建家庭價值觀
有學者認為:“紀錄片創作,不僅要提供視覺上的美感,還要具備有價值的思想,讓觀眾能夠通過鏡頭洞察社會”[1]。在中國,家庭始終是延續親情關系的場所。《四個春天》以巧妙的視角建構了受眾的家庭價值觀。如:在展現父母與孩子之間的價值觀的差異和鴻溝時,導演并沒有從沉重悲慘的基調過多著墨,而是以溫暖輕松的筆觸讓觀眾眼前一亮。此外,影片打破傳統第一人稱紀錄片常見的賣慘式主題,以一種溫暖的筆觸面對人生的悲歡離合。影片通過新的敘述視角對于家庭生活的講述,為觀眾建構起一種既宏大又微觀的新的家庭價值觀,對第一人稱紀錄片的價值導向提供借鑒。
(二)私人影像加強文化認同
第一人稱紀錄片用私人影像喚起觀眾的生活記憶,構建新的家庭責任觀,最根本的在于用影像加深文化認同,這種文化認同直觀地體現在私人影像之中。在第三個春天,導演使用了大量的歷史私人影像,例如:《1997年春節上墳》、《2008年11月上山砍柴》等,這些影像的呈現讓觀眾具有強烈的文化認同。在新媒體時代下的私人影像進一步強化這種認同,更好地發揮了第一人稱紀錄片的精神引領作用。
正如海德格爾所說:一切藝術本質上都是詩。第一人稱紀錄片《四個春天》正是一部充滿詩意的家庭式紀錄片,它始終聚焦在平凡的生活之中,帶給觀眾久違的感動。紀錄片創作者應該從生活中發現詩意與美,因為生活本身就是一件不可多得的藝術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