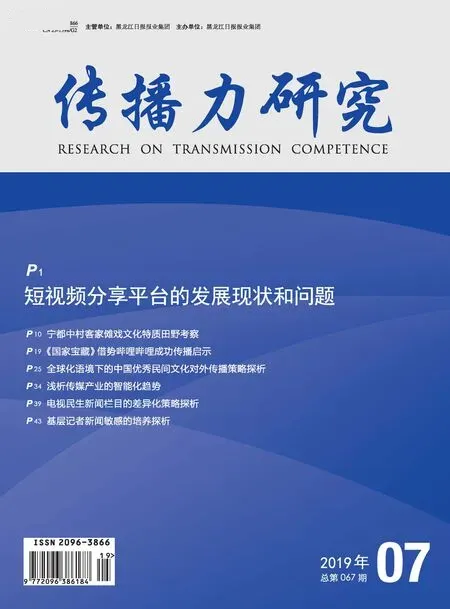我國數字勞工領域研究狀況綜述
翟晨肖 中央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
一、數字勞工之前:數字時代“勞動”概念的爭論
數字勞動是數字時代馬克思勞動價值論拓展的重要范疇。由于國內外學者對于“數字勞動”概念的理論建構各不相同,沒有達成統一的定義。因此在總結數字勞工相關研究之前有必要厘清關于數字勞動的不同觀點。
依據對數字勞動的屬性的不同看法,國內外學者對數字勞動概念的界定產生了分歧,這個分歧主要是兩方面的。一些學者將數字勞動看作是非物質性的,是當代社會的一種新形式;而另一些學者則人為不管是在虛擬空間中的勞動還是在現實生活中的勞動,它們本質上還是物質性的。
基于學界的這種不同看法以及我國關于該話題的研究現狀,本文將國內的數字勞工研究進行了研究對象上的分類,即“作為受眾的數字勞工”和“專業數字勞工”。專業數字勞工是指在整個與數字技術相關聯的數碼產品流水線上的勞工。
二、作為受眾的數字勞工
基于不同的受眾觀,傳播政治經濟學以及文化研究學派之間對于數字勞動也有著兩種不同的研究路徑。汪金漢將這兩種不同的研究路徑分為“剝削觀”與“參與觀”。[1]剝削觀下很多的數字勞動問題最后的落腳點都在剝削以及如何進行剝削的問題上;文化研究學派則持一種“受眾參與”的觀點。他們認為受眾在參與的過程中,別人的評論、轉發等都可以成為一種回報。
(一)“被剝削”:我國傳播政治經濟視角下的受眾角色
與國外學者對于數字勞動議題研究邏輯的爭辯狀況不同,我國關于受眾數字勞工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從傳播政治經濟學視角出發的。這個視角下的學者認為受眾(用戶)在互聯網平臺上的內容生產和個人信息數據被平臺利用,受到了網絡資本的剝削。
其一,國內學者選擇網絡直播平臺、字幕組、網絡社交平臺等作為研究對象,對數字勞工進行理論應用,驗證理論在中國本土的適用性。
曹晉和張楠華以中國大陸網絡字幕組為研究對象,結合傳播政治經濟學理論,認為網絡字幕組進行無償勞作的根本動因是極具隱蔽性的跨時空、跨國界、跨階級的資本剝削。在這之后,徐偲骕等人以“微差事”APP 為例,關注到了除了受眾生產的內容之外的被剝削資源——受眾數據,并認為對于用戶信息的監控成為新的經濟剝削形式。
其二,我國學者對數字勞工概念進行了理論探討和研究史方面的考察。
吳鼎銘從傳播政治經濟學視角出發呈現了傳媒“受眾”被互聯網產業勞工化的事實與趨勢,探索“數字勞工”的勞動形式、剝削機制與吸納機制。他認為在理論層面上“數字勞動”的視角呈現了更為豐富和多元的信息傳播景觀。[2]汪金漢的研究則區別于單純的理論介紹,他在文中以歷史性地眼光系統的呈現了數字勞工概念的背景和歷史發展狀況。
(二)“積極受眾”:傳播政治經濟學視角下的受眾角色的再討論
在傳播政治經濟學視角下用戶往往是被動的。然而有的學者認為受眾也扮演著積極的角色。
蔡潤芳認為被詬病為“經濟簡化論”、“被動受眾”是對斯邁茲傳統的誤讀,傳播政治經濟學強調“積極受眾”的生產性,受眾具有主觀能動性,是意義的真實制造者。[3]在傳媒經濟生產過程中,傳媒從業者的內容生產、受眾的免費勞動參與、以及受眾市場變化都將影響著總體剩余價值的實現。她在文章中提到,與許多批評受眾商品論為經濟簡化論的觀點相左,積極的受眾能動觀實際上強調了媒體的意識形態功能。
(三)尋找理論視角的融合:從傳播政治經濟學視角之外看數字勞工
不同于國內一些學者對數字勞動概念的政治經濟視角的解讀,汪金漢認為當前的社會環境已經和馬克思所在的時代明顯地不同了,所以不能簡單地將馬克思的勞動理論直接應用到當代社會中。因此,學界在研究數字勞動的相關問題時,不能僅僅遵循過去的研究框架,而是應該探尋新的研究路徑,嘗試將原先看起來對立的一些視角(如文化的和社會的)相結合。
三、專業數字勞工:值得被重視的數字勞工群體
雖然受重視程度不高,但作為數字時代互聯網產業中的主要角色之一,專業數字勞工的話題并未被完全忽視。
夏冰青以S 和X 兩家大型互聯網公司為案例,探究中國互聯網行業實習生在工作和生活方面的困難。她在文章提出了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誰才是真正值得關注的無酬勞工?”,并以此批判了當前社會的傳媒行業的實習生制度。邱林川則從歷史的角度切入,揭露了當前資本主義在網絡時代的剝削本質。他認為17世紀的奴隸制和我們現在所關注的富士康勞工制度并無本質的區別。他還提出了“反剝削”的議題,呼吁抵制數字剝削,這種反抗的意識在數字勞工話題中是少見但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