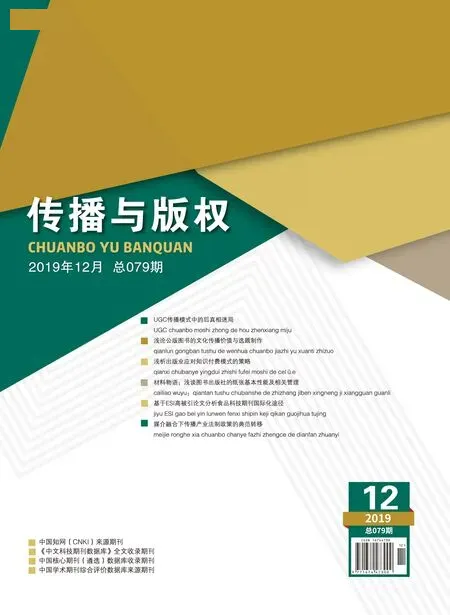媒介融合下傳播產業法制政策的典范轉移
李紅祥
(衡陽師范學院,湖南 衡陽 421002)
自20世紀90年代伊始,數字技術與網絡壓縮技術的普遍應用,使得傳播市場之間固有的界限日趨模糊,傳統通訊與媒介產業開始走向融合。然而,在傳播產業融合過程中,特別是通訊與傳媒產業跨業經營的興起,對各國原有的傳播產業法制產生了極大沖擊。蔡雯提出:“媒介規制的變革乃是媒介融合的必要前提。”[1]緣于此,世界發達國家無不對其傳統傳播產業法制進行調整,轉變其治理范式,以滿足媒介融合的需要。
一、傳播產業法制變革
一代有一代之法律,一代有一代之制度。傳統傳播產業法制在一定時期內曾很好地發揮了監管作用。然而,隨著傳播科技的發展,傳播經營格局的變化,傳統傳播產業法制日益陷入難以適應的困境,導致世界各國開啟了一輪新的傳播產業法制變革。
(一)傳統傳播產業法制面臨的挑戰
媒介融合到來之前,傳播產業之間的界限和功能涇渭分明。各國政府基于反托拉斯原則,大力扶持和保護初生產業,采取分業管制的政策,嚴禁跨業經營。具體體現在采用不同的監管機構對不同的傳播產業實行監管;同時不同的傳播產業采用不同的法律法規予以規范。毋庸置疑,這種因業施策和分業監管的模式,因其管制目的與對象明確,管制措施與方法針對性強,所以在一定時期內能夠發揮強大的監管效力,產生了較好的管制效果。
然而,隨著傳播科技的日新月異,傳統傳播產業之間的界限和功能日益走向融合,尤其是以互聯網和智能手機為代表的新媒體的出現,原先的管制模式與管制法規難以適應傳播科技的發展和傳播產業之間日益融合的需要。布朗斯康認為:“過去管制傳播傳輸工具的法律,特別是以郵件、電話、報紙、有線電視及廣播電臺為模式所發展出來的法規,在電子數字化的傳播時代將產生法律不適用的窘境。這種現象的出現是因為管制者無法判斷上面所傳輸的信息到底該歸那一種法律、那一種模式來管。”[2]
20世紀90年代,一些發達國家的傳播業界反對嚴禁跨業經營禁令的呼聲日益強烈,他們希望廢除阻礙媒介融合發展的相關法律政策,改變單一行政的治理模式,建立一個能整合各種資源,適應數字化、互聯網技術發展的傳播體系。于是,如何放寬分業管制,消除傳播產業之間壁壘就成為擺在各國傳播產業政策和相關法律制定者們面前的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二)發達國家傳播產業法制變革
面對傳統傳播產業法制難以適應社會發展的困境,許多發達國家開啟了傳播產業法制的變革,以適應媒介融合的需要。
20世紀90年代開始,美國聯邦通訊委員對施行長達半個多世紀的《1934年電信法案》進行了一次有史以來最大幅度的修訂。后經國會多次爭議與討論,最終于1996年2月8日由克林頓總統簽署發布。《1996年電信法案》被稱為推進美國媒介融合的基石,影響遍及全美通信、傳媒等傳播產業。
英國議會于2002年3月通過了一部《傳播通訊辦公室法案》。2003年12月23日,傳播通訊辦公室開始正式運作。2003年7月23日英國又通過了一部由貿易工業部與文化傳媒體育部共同研討制定的《2003年傳播法案》。該法案引入了歐盟對傳播產業實行的水平層級管制架構;并且該法案對《1949年無線電信法》《1984年電信法》《1998年無線電信法》三部法律進行了整合。另外,英國對《1990年廣電法》《1996年廣電法》中相關法律條文予以修正,并繼續實施。
2009年之前日本對傳播產業采取分業管制政策,不同的傳媒和電信產業制定相應的法律予以規范。其中廣播、電視和電信行業共有9部相關法律,包括《廣播法》《有線電視廣播法》《有線廣播法》《電信事業利用廣播法》《電信事業法》《有線廣播電話法》《電報電話公司法》《有線通信法》《電波法》。2009年8月日本信息戰略部和總務省召開兩次聯席會議,決定把以前的9部法律進行整合,最終制定了一部新的《信息通信法案》。
二、政策典范轉移
政策是靈魂,它體現一個國家在某一時期對某一事物的態度和治理思維;法制是載體,它是一個國家政策加以貫徹實施的具體體現。傳播產業法制的變革體現了傳播產業政策的典范轉移。20世紀90年代至今,發達國家的傳播產業法制變革體現了它們從加強行業保護到促進產業競爭,從單一行政過渡到復合行政的傳播管制新思維。
(一)從加強行業保護到促進產業競爭
發達國家一開始對傳播產業采取分業管制政策,出于對初生產業的保護,采取嚴禁跨業經營。然而,隨著傳播科技的發展,特別是光纖及寬帶網絡的崛起,電信與傳媒產業之間、傳媒產業內部之間的界限和功能日趨模糊,因此對傳統傳播產業法制予以修訂,放寬跨業經營的限制,希望促進產業相互競爭。
1996年之前,美國出于保護初生產業,長期嚴禁跨業經營。如《1934年電信法案》將電信管制區分為短途電話和長途電話,規定兩者不能跨界經營。有線電視出現后,為了防止已經發展壯大的電信公司,排擠初生的有線電視業,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于1970年頒布“禁止電信公司與有線電視交叉持有”的禁令,對電信業實行嚴格管制。出于同樣的目的,1984年美國國會通過《1984年有線電視通信政策法案》。該法案繼續對有線電視與電信事業跨業經營實行嚴格限制。然而到了1996年,美國通過了一部《1996年電信法案》。該法案出于促進媒介融合需要,解除有線與無線通信、電信與廣電、各傳統媒體之間的跨業經營限制,以自由競爭與市場機制為原則,開放通信與傳媒產業相互進入。
日本以前對廣播電視和電信的管制基于各傳播產業的技術特性,按照業別的形式分別制定相關法律進行縱向垂直管制,不同產業采用不同的法律政策,其制定相關法律共有9部之多。然而在2009年制定的《信息通信法案》中,它對傳播產業的區分進行了重新界定,把各傳播產業鏈統一劃分為“信息內容”“基礎設施”“傳輸設備”三大功能模塊,并把以前的9部法律整合進相應的部分,如把《電信事業利用廣播法》《有線廣播法》《廣播法》《有線電視廣播法》整合為管制所有“信息內容”功能模塊的法律;把《電信事業法》《電報電話公司法》《有線廣播電話法》整合為管制所有“基礎設施”功能模塊的法律;把《有線通信法》整合為管制所有“傳輸設備”功能模塊的法律。《信息通信法案》中對傳播產業的規制方式一改以往按照傳播業別區分的縱向管理方式,轉變為按照功能區分的橫向水平管理體系。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促進通訊與傳媒產業之間的融合,促進相互競爭。
(二)從單一行政到復合行政
媒介融合之前,發達國家跟世界各國一樣,對傳播產業采取單一行政的治理方式,每一個行業由專門的各自獨立的監管機構進行監管。然而,隨著傳播產業之間,尤其是廣播電視與通信事業之間邊界的日趨模糊,它們開始對傳播產業的監管機構進行整合,采取統一的監管機構監管,從而走向復合行政的治理之路。
英國2002年3月通過《傳播通訊辦公室法案》,籌備建立一個全國統一的傳播管制機構——傳播通訊辦公室。隨后《2003傳播法案》正式賦予傳播通訊辦公室的法律位階為處于獨立于政府機關的法人組織,取代原來分別監管廣播、電視和電信的5個監管機構:獨立電視委員會、廣播標準委員會、電信管理局以及兩個無線電管理機構無線廣播管理局和無線通訊管理局。傳播通訊辦公室于2003年12月29日正式開始運行。
2008年2月29日,韓國根據新通過的《廣播通信委員會組織法》,組建一個統一管制機構——廣播通信委員會。該委員會為韓國總統辦公室下屬的政府機構。成立后,它取代原來分別管制韓國的廣播電視與電信產業的廣播委員會和信息通信部,開始對全國的廣播、電視和電信實行統一監管。
2003年之前,新加坡的傳播產業一直采取單一行政治理的方式,每一個行業相應由單一的監管機構進行監管。為了促進傳播產業的融合,2003年1月新加坡電影委員會、電影與出版管理局以及廣播管理局整合為媒體發展管理局。如果說媒體發展管理局是對新加坡傳媒產業內部采取復合行政的開始,那么隨著通訊和傳播科技的發展,電信事業與傳媒產業之間的界限日益模糊,2016年8月,新加坡決定整合現有的資訊通信發展管理局和傳媒產業管制機構媒體發展管理局,重新組建新的資訊通信媒體發展局,對電信和傳播產業實行統一監管。
三、變革經驗與啟示
上述發達國家傳播產業法制變革,以及傳播產業法制變革中所體現的國家治理政策的典范轉移,為其他國家傳播產業法制變革帶來了一些有益的經驗與啟示。
(一)變革經驗
縱觀世界各發達國家媒介融合下的傳播產業法制變革,可以得出其傳播產業法制變革兩方面的經驗。
一是傳播產業法制變革的路徑是從分業管制到融合管制。在媒介融合之前,相關傳播產業法制都是基于媒介技術按照媒介業別制定相關法律規范。然而,隨著傳播科技的發展,為了適應媒介融合需要,各國紛紛把原先分業管制制定的法律進行拆分并整合成一部涵蓋各種傳播類別的法律,對傳播各產業實行統一管制。
二是傳播產業的管制模式是從垂直管理到水平管理。媒介融合之前,世界各國的傳播產業法律采用一種垂直管理的模式,按照傳播業別制定相關法律法規只局限于某一產業內部,對某一產業的各個產業鏈節實行縱向管制。而為了適應媒介融合需要整合修訂的傳播產業法律,不僅涵蓋了各個傳播產業,而且所有傳播產業按照基礎設施、媒介設備和信息內容劃分為各個產業鏈節,每一個產業鏈節有相應的法律規范,實行水平管理。在同一法律規范之下,各產業處于等同位置。
(二)變革啟示
世界各國媒介融合下傳播產業法制政策的典范轉移,可以為其他國家傳播產業法律的管制變革提供一些有益的啟示:
一是傳播產業法制的制定要因勢而變。從發達國家傳播產業法制政策的典范轉移可以看出,一個國家傳播產業法制的制定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動態變化的。隨著傳播科技的發展,傳播經營格局的變化,傳播產業法制必須因時而動,才能適應時代的脈動。
二是傳播產業法律的制定要因地制宜。世界上不存在一種普世適用的傳播產業法律管制模式。一個國家傳播產業法律的制定必須結合每一個國家的歷史與社會語境,傳播產業經營格局變化加以考量。如果一味地對其他國家傳播產業法制進行簡單的制度移植,必將導致水土不服,難以發揮應有的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