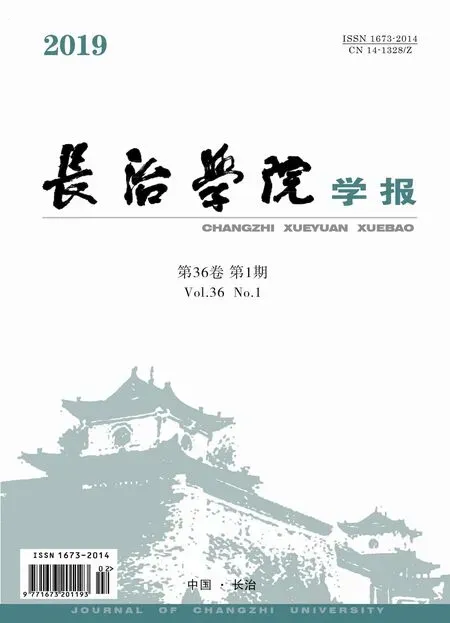傳統文化視域中人的自由全面發展解讀
——兼談傳統文化融入《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概論》教學
白立強
(衡水學院 董子學院,河北 衡水 053000)
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歸根結底體現在文化層面。《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概論》作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要課程在傳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方面擔負著不可或缺的責任。這既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向,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內在要求。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個基本要求就是“不僅在內容上、而且在形式上都要努力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1]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能夠在“內容”方面實現中國化,原因就在于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存在著契合點。
余秋雨認為,文化就是“由精神價值、生活方式所構成的集體人格”[2]3。“中國文化……主要在求完成一個一個的人。”[3]16或者說,“中國文化精神最主要的,乃在‘教人怎樣做一個人’。”[4]“以人為本的人文精神是中國文化最根本的精神”[5]46。同樣,“馬克思主義是人的解放學”[6],其最終目標就是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由是,無論馬克思主義還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都是將人的存在和發展作為基本關注點。
一、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著眼點是人
在中國文化之中,人(修身)既是成就事業、治國安邦的起點,也是事業發展的價值取向。人、事雙方在雙向互動過程中,相互促進、彼此助益、不斷優化、共同提高,從而形成了良性循環模式。正如《大學》所云:“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人之為人的第一要務即修身。唯此,方得以實現齊家、治國乃至平天下之作為。如果說修身是走向事業成功的保證,那么,事業成功也同時意味著對于生命自身的進一步促進與完善(修身)。故《大學》有言:“仁者以財發身”。歷史上范蠡于財用三進三出之事實就是典型例證。
《論語》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經典之作包含著豐富的人學思想,即處事做人之學[7]。如《論語·子路第十三》中,面對樊遲請教稼穡之事,孔子稱之曰“小人”。這當然并不意味著孔子輕賤稼圃,因為孔子也曾自言“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論語·子罕第九》)。孔子于樊遲所問之斷言,實際上表達了面對禮崩樂壞的社會現實寄希望其成為“弘道濟眾的有位君子”[8]491。唯有諸多君子人格式人物,才具有強烈的社會擔當意識、責任以及執行力,蓋所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即為此意。正是基于此,《論語》中一再強調君子之氣象格調,如:
君子之言行:子曰:“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論語·里仁第四》)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從之。”(《論語·為政第二》)
君子之氣象: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論語·述而第七》)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論語·子路第十三》)
君子之志趣:子曰:“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論語·里仁第四》)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論語·憲問第十四》)
君子之品格: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論語·子路第十三》)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論語·憲問第十四》)
君子之操守: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論語·公冶長第五》)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論語·季氏第十六》)
樊遲之關注非孔子之預期,即其屬于“小道”范疇。“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論語·子張第十九》)“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楊氏曰:‘百家眾技,猶耳目鼻口,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非無可觀也,致遠則泥矣,故君子不為也。’”[9]222稼穡紡織作為謀生技術乃不可或缺的生活手段,然而,對于君子而言,不應局限于此,而應志向高遠,心懷經世濟民之志,身具治國安邦之才。而不應該成為“見小暗大”“從物如流”的“庸人”。只有“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的士人,以及“仁義在身”“篤行信道,自強不息”的君子才是孔子所預期的基本人格。(《孔子家語·五儀解》)
中華傳統文化著眼點是人——不是物質意義上的人(此無異于其他生命現象),而是精神意義或者說價值意義上的人。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看一切問題都和人聯系在一起,都要思考它對人有何教益。”[5]78-79由是,“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論語·泰伯第八》)就是以非理性的“美學方式”發揮著“以美啟真”的作用[10]182。如同“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語·為政第二》)之內涵一樣,“詩三百”的人文意蘊即“無邪”,無邪乃“性之然”“真情、真性流露”[11]。總之,就是通過詩書禮樂之教化,使人成為具有真、善、美之生命品質的完美之人。
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著力點是成人
《荀子·王制》有言:“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這意味著,人之貴在“有義”。義者,宜也。人以內在之義實現著外在之宜,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為此,人首先須自立、自達,即成人(成己),方可成他人與物。在《論語·憲問第十四》,子路問及“成人”。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論語·憲問第十四》)
“成人,猶言全人。”“言兼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理,廉足以養心,勇足以力行,藝足以泛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于內,而文見乎外。……而其為人也亦成矣。”“程子曰:‘武仲,知也;公綽,仁也;卞莊子,勇也;冉求,藝也。須是合此四人之能,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然而論其大成,則不止于此。’”[9]167以當下言之,成人就是“成就人之所以為人者”[8]537。“猶完人,謂人格完備之人。”[12]361
同樣問“成人”,由于問者不同——顏淵與子路,孔子的回答也不同。如果據程子所言,于子路之問而所答為“小成”或“初成”,那么,孔子答顏淵之問則為“大成”。如:
顏淵問于仲尼曰:“成人之行何若?”子曰:“成人之行達乎情性之理,通乎物類之變,知幽明之故,睹游氣之源,若此而可謂成人。既知天道,行躬以仁義,飭身以禮樂。夫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說苑·辨物》)
“成人之行達乎情性之理,通乎物類之變”,“既知天道,行躬以仁義”等。正如《中庸》之成己、成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中庸》)
“誠雖所以成己,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于彼矣。仁者體之存,智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固有,而無內外之殊。既得于己,則見于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9]288-289一旦人以己之仁度物之義,則意味著人以自身之完美成就萬物之性天,即“與天地參”: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中庸》)
“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發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也。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9]287
《道德經》有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以法天則地為圭臬,上達天道,下合地道,中為人道。從而以自身之成實現、助推與成就著天地之間萬事萬物達致和合共生之情狀。
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價值取向是自由全面發展的人
“根據中國哲學的傳統,哲學的功能不是為了增進正面的知識(我所說的正面知識是指對客觀事物的信息),而是為了提高人的心靈,超越現實世界,體驗高于道德的價值。”[13]如: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論語·為政第二》)
“從心所欲不逾矩”即“一任己心所欲,可以縱己心之所至,不復檢點管束,而自無不合于規矩法度。此乃圣人內心自由之極致,與外界所當然之一切法度規矩自然相洽。”[12]29孔子以自身的生命歷程為中華文化塑造了人之價值意義上的生命,即自由與全面發展。
然而,現實的情況是,“當知人類盡向自然科學發展,盡把自然所與的物質條件盡量改進,而人類生活仍可未能獲得此一最高之自由。又若人類盡向社會科學發展,盡把社會種種關系盡量改進,而人類生活仍可未能獲得此一最高之自由。”[14]98
于此,馬克思主義也有類似的判斷。“自由王國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規定要做的勞動終止的地方才開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來說,它存在于真正物質生產領域的彼岸。……在這個必然王國的彼岸,作為目的本身的人類能力的發展,真正的自由王國,就開始了。”[15]顯然,在馬克思主義看來,自由的實現源于現實而又超脫于此,即源于物質層面而歸結為精神層面。這與中國文化具有異曲同工之妙。
錢穆先生如是說:“儒家種種心性論道德論,正與近代西方思想之重視自由,尋求自由的精神,可說一致而百慮,異途而同歸。”[14]98縱觀整個人類社會,其發展的基本路徑為由重視物質生產發展到依賴精神、信息生產;由關注外部世界到關注內在生命。其間,就是人類不斷追求自由全面發展的過程。這同時表明:“人類之追求自由,則只有……到達于精神我道德情狀的生活,才始獲得了我之人格的內在德性的真實最高的自由。”[14]96
故《中庸》有言:“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就在于外在之道德律令與君子之內在心性安守相浸相沁、優游涵泳、浹洽于中,從而達到道妙暗合之境。
就現實社會而言,“人既才性不同,則分途異趣,斷難一致。”[14]61但就人之價值生命而言,“人人各就其位,各有一恰好處,故曰中庸。不偏之謂中,指其恰好。不易之謂庸,指其易地皆然。人來做我,亦只有如此做,應不能再另樣做。此我所以為最杰出者,又復為最普通者。盡人皆可為堯舜,……即如堯舜處我境地,也只能如我般做,這我便與堯舜無異。”[14]61“堯舜為……人人所能到達之人格。……此種人格,為人人所能企及,故為最平等,亦為最自由。”[14]59-60
在中華文化語境中,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狀態不僅僅期于未來,更是立足當下。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讓文化浸潤生命,讓生命回歸文化。體會生命之初心,方得人生之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