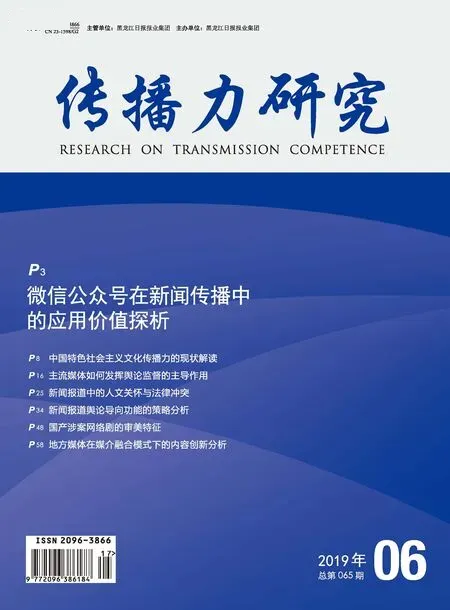互聯網對電影產業若干關鍵詞的影響
張欣宇 東北師范大學
隨著互聯網的高度發展以及與電影界的不斷融合,劇本創作、投資拍攝、宣傳發行、影院放映、周邊產品生產的傳統電影產業價值鏈越來越受到互聯網思維的沖擊,使其在電影生產發行的各個關鍵階段都受到互聯網特性的影響,并且在電影觀眾年齡構成、觀影行為方式上也起到了一定的影響作用。
一、互聯網下的“IP”改編現象
IP,即知識產權(Intellectual Property),其作為互聯網時代的產物,從2015年開始文學IP 改編影視作品之勢便愈發猛烈,不斷爆發出巨大能量,逐步沖擊著電影產業價值鏈的源頭。IP 可以是一個故事、一種形象、一件藝術品、一種流行文化。它是能被改編的知識產權內容,是適合被二次或多次改編的影視作品、動漫游戲等。“IP”影視則是在原先有一定粉絲數量的基礎上,以原創網絡小說、游戲等為題材創作改編的電視劇、電影①。文學IP改編影視劇本是基于原始文學IP 文本在互聯網平臺上累積的粉絲體量,通過影視語言改編成直觀、可見的影視作品,把原始粉絲引流到影視作品上,將原始IP 的影響力轉化為商業價值,互聯網語境下粉絲經濟所帶來的狂熱消費力是影視作品票房的有力保障。
二、互聯網下的電影宣傳
在互聯網尚未普及之前,電影的宣傳陣地尚在專業學者一方,曾有著名導演為《集結號》站臺,媒體競相轉載、引用。不可否認,在如今這種專業學者營造輿論格局成為普通公眾觀影指南的局面已然銷聲匿跡,取而代之的是各種由電影觀眾組成得影評社區、論壇,其強大的包容性、多元性和開放性吸引著有無專業知識背景的電影觀眾,使得用戶既是信息內容的接受者也是發布者,既充當著消費者也是宣傳者。
三、互聯網下的電影營銷
互聯網介入電影營銷環節最直觀的表現便是營銷手段越來越“新媒體化”。微博、微信、專業化網站等社交新媒體正在逐漸擴展電影營銷手段與方式,其借助互聯網大數據更能準確判斷互聯網用戶的觀影類型偏好、觀影時間偏好等,進而實現精準推送,使其利益最大化,使得新媒體營銷正在逐漸成為營銷重器。其次,新媒體平臺借助其強大的公開性、包容性和低門檻,正在吸引越來越多的用戶,在“影響力即貨幣”的網絡時代②,積聚的用戶便給票房的高漲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在網絡時代,新片的口碑經過新媒體的發酵會成倍增長,其中令人吊詭的是,越來越多的觀眾抱著“驗證爛片”的心態回歸影院,坐在大屏幕前一探新片的“爛度”。
四、互聯網下的電影觀眾
目前的電影觀眾主體是由互聯網網民組成,年齡偏中青年,觀看電影已經成為他們獲得娛樂的一種行為方式,其已經養成了一定的觀影習慣或自主觀影意識,已然成為新片票房保證的中堅力量。近年來,文化娛樂市場中“小鎮青年”一詞逐漸被提及,其是指包含二三線城市及以下城鄉的中國電影觀眾③。但無論是“都市青年”還是小鎮青年都是在互聯網時代下成長起來的一批觀眾,從選擇觀影目標、購票、電影觀后評價反饋等各個行為方式上都受到了互聯網的影響。需要指出的是,電影觀眾的年齡構成會逐漸下移,且越來越多的電影觀眾會受到互聯網的影響,因此電影觀眾的觀影喜好與習慣越來越會擺脫專業影評人士的語言束縛,而轉向依賴專業電影社區或其他電影觀眾的評價反饋,進而指導觀眾個體是否觀看影片。
五、互聯網下的觀影媒介
傳統觀影是通過電影觀眾自主購票走進電影院完成觀影行為,但隨著互聯網的滲透,觀影群眾在觀影媒介上也在逐漸變化。在互聯網的影響下,有一批視頻網站憑借為早期互聯網觀眾提供免費(盜版)視頻起家,在早期“原罪”的基礎上累積了最早的一批原始觀眾,也培養了一批觀影群眾的觀影偏好與網絡觀影習慣。在年輕觀影群體觀影習慣不斷改變的趨勢下,一些視頻網站憑借自身的便捷性、互動性和局限性低等特點,加持政策紅利與原始積累受眾,正在逐步重構觀眾觀影方式,因此更多的電影觀眾選擇在視頻網站上觀看電影,此種行為方式受時空限制較低,具有一定的隨時性、隨地性和可間斷性,一次觀影行為可由幾個時間段拼湊起來完成一部電影的觀看,這種特點是在傳統影院所不具備的。隨著視頻網站的崛起,也催生了微電影、網絡自制劇等新的影像呈現方式,涌現出了《老男孩》、《太子妃升職記》、《余罪》等一批受到觀眾歡迎的影像產品。
六、結語
在“互聯網+”的大背景下,云技術、網絡平臺、金融資本等新要素的不斷涌入使得傳統電影產業生產各個環節都發生了較大變化,同時在網絡時代下成長起來的年青觀影群體不斷成為中國電影觀眾的主體,倒逼著影像生產在題材、播出方式等方面發生變革。因此電影生產者應仔細把握互聯網影響下影像生產、傳播等方面的變化趨勢,通過不同方向上的創新和深耕細作來再次完成產業對焦,創制符合觀影主體審美習慣的影像作品,在“互聯網”潮流中實現與年輕觀影群體的審美互動。
注釋:
① 唐夢晨.媒體業發展下的IP 改編之風[J].西部廣播電視,2017(17):109-110.
② 陳曉云,蔡曉芳.新媒體語境下的影像生產與話語重構[M].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16.32-32.
③ 王貞瑾.消費文化背景下的小鎮青年電影[J].視聽,2016(11):1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