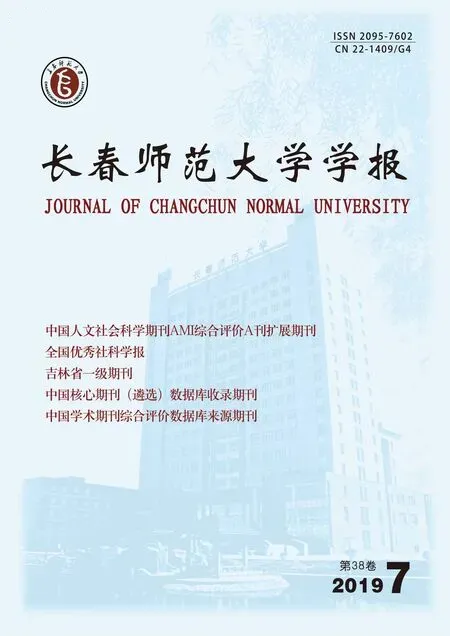“互聯網+”時代外國文學傳播渠道的革新
——以梭羅文學作品為例
采國潤
(滁州職業技術學院,安徽 滁州 239000)
伴隨著人類傳播技術的革新,文學作品的傳播經歷了口語傳播、文字傳播、電子傳播、互聯網傳播等幾個階段。新的傳播方式所具備的互動性、即時性、開放性,為外國文學在中國的傳播帶來了新的機遇。本文以美國19世紀超驗主義文學家和自然保護主義思想家亨利·戴維·梭羅的作品為例,分析“互聯網+”環境為外國文學作品在中國的傳播帶來的影響。
一、新媒體對梭羅作品的影響
早在1926年,《小說月報》第17卷第12期刊登的鄭振鐸《美國文學》一文就對梭羅作了粗淺的介紹。[1]這是梭羅第一次在中國被提及,然而在隨后的60余年里,梭羅的思想及其作品一直處于遇冷狀態,其著作《瓦爾登湖》僅被一位譯者翻譯,且發行量只有一萬余冊。
20世紀90年代后,梭羅的文學作品,尤其是他的集大成之作《瓦爾登湖》在中國出現了驟熱的現象。從傳播渠道加以分析可以發現,這一時期正是電子媒介尤其是新媒體快速發展的時期。新媒體涵蓋了口語、文字、圖像傳播的一切特點,并依靠娛樂性大大刺激了讀者的快感。但同時我們也要看到正是由于新媒體所具備的互動性、即時性、開放性特點,讀者的閱讀門檻降低,二次傳播更加便捷。經過多次傳播后,作品的真實性、內在價值易遭到誤解。此外,網絡媒介給了受眾更大的話語權,受眾對作品的評論也會為外國文學在中國的傳播帶來負面影響。例如,在梭羅的作品中,自然界及作者自己的內心一直是描寫重點。在梭羅看來,自然凝聚了整個社會的智慧,他認為人類應該拋棄世俗之事,真正融于自然,進而獲得智慧與平靜。但這種思想在網絡的推動下日漸被曲解為消極避世,更有甚者將之作為附庸文藝生活的標簽。
二、新媒體視角下梭羅作品傳播渠道的革新
(一)梭羅作品的音頻、視頻傳播
文本形式是文學作品的基本載體。隨著科技發展,音頻技術、視頻技術被相繼應用到文學作品的傳播過程中,為外國文學的傳播賦予了新生命。梭羅作品的受眾以青年為主,據統計,青年群體占總受眾的80%以上。除直接文本閱讀外,他們接觸梭羅作品最主要的途徑是各種影音節目。受眾可以直接收聽梭羅作品的有聲小說。此外,有關梭羅文學作品,尤其是《瓦爾登湖》的推介節目日益增多,例如中央電視臺科教頻道的《子午書簡》欄目、重慶衛視的《品讀》欄目。通過視頻節目,觀眾可以更直觀地了解梭羅及其作品。
在影音傳播過程中,原本嚴肅理性的文字信息被偏向感性的娛樂化的聲音和視頻信息代替。這種利用影音表達、訴諸情感的方式,刺激著受眾的感覺器官,使得部分晦澀難懂的外國文學作品更易被讀者接受理解。但是過分追求通俗易懂,往往導致外國文學作品的意義不能徹底被接受甚至曲解。因此,在制作外國文學作品的音頻、視頻時,需要聯系相關作品背景,利用理性解讀促進外國文學作品在中國的傳播與接受。
(二)梭羅作品的網絡媒體傳播
互聯網發展已經經歷了web1.0、web2.0、web3.0階段。web1.0本質是閱讀,web2.0本質是互動,web3.0本質是價值實現。在新的階段,互聯網技術,特別是互動、移動互聯網、大數據等都對外國文學在我國的傳播起到了推動作用。下面以web2.0時代虛擬互動社區網絡豆瓣為例,探究其對梭羅文學作品的影響。
豆瓣網是web2.0網站中具有特色的一個網站。網站提供“書影音”推薦、線下同城活動、小組話題交流等多種服務功能,它更像一個集品味系統(讀書、電影、音樂)、表達系統(我讀、我看、我聽)和交流系統(同城、小組、友鄰)于一體的創新網絡服務,一直致力于幫助都市人群發現生活中有用的事物。在該虛擬社區中,讀書頻道和豆瓣小組頻道是對梭羅文學作品推薦最多的兩個頻道。在讀書頻道,通過對關鍵詞“梭羅”進行搜索,可以搜索到梭羅所有被引進中國的文學作品,如《瓦爾登湖》《荒野孤舟》《在路上》等。同時,用戶可以對梭羅的各種作品進行打分或添加標簽。如2009年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的王家湘譯本《瓦爾登湖》,豆瓣用戶為該書貼上了“外國文學”“人生哲學”“隨筆”等標簽。用戶可以根據個人理解對本書進行短評、長篇書評,或對已有評價作出贊同回應。而在該虛擬網站的小組功能中,受眾可以根據個人的興趣愛好加入或新建小組,找到自己的歸屬,獲取自己希望獲得的信息。希望進一步了解或討論梭羅文學作品的用戶,可以在小組頻道中自由選擇加入或新建小組。在該虛擬社交網站的小組頻道中搜索“梭羅”,便可找到“梭羅與超驗主義”“梭羅點評”等小組。在這些小組中,用戶可以發表自己對梭羅個人及其作品的評價,還可以對相關問題進行咨詢提問,如:“在哪可以買到梭羅日記全集?”“誰翻譯的瓦爾登湖最棒?”
豆瓣網、知乎網等熱門虛擬社交網站大大增加了梭羅文學作品與讀者之間的黏性。網絡媒體的互動性、即時性、開放性特點打破了外國文學作品傳播的時間與空間限制,大大提高了外國文學作品的傳播效率,使得優秀外國文學作品能夠在短時間內被受眾閱讀甚至二次傳播,完成傳統傳播渠道幾十年所形成的傳播量。但我們也要看到,網絡評論有時會對文學作品的傳播造成負面影響。因此,在外國文學作品的傳播過程中,相關人員要及時發現負面評價,并做好對應的輿論引導,多發表有利于外國文學作品傳播的正面聲音,更多地傳播正確人生價值觀。
(三)梭羅作品的自媒體傳播
隨著微博、微信公眾號、短視頻媒體的發展,自媒體正逐步興起,并對外國文學在中國的傳播產生重要影響,主要表現在使外國文學向平民靠攏,使得全民閱讀成為可能。在自媒體時代,梭羅文學作品的傳播不再依賴報紙、書籍等印刷媒介,任何個人都可以依靠微博、微信、短視頻等渠道自由傳播。
值得一提的是,傳統媒體中存在著把關人。“把關人”這一概念最早是由美國社會心理學家庫爾特·盧因提出的,他認為群體傳播過程中存在著一些把關人,只有符合群體規范或把關人價值標準的信息內容才能進入傳播渠道。[3]外國作品在中國早期傳播的過程中也存在這樣的把關人,他們在傳播文學作品時會摒棄不符合自己政治或經濟利益的文學作品。例如,文化大革命時期,梭羅的文學作品被認為是資產階級的產物,與主流政治思想相違背,注定了梭羅的文學作品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遇冷局面。而在自媒體傳播過程中,不存在任何形式的把關人,人人都可以在自己的微博賬號、微信朋友圈、微信公眾號等場所自由發表專業或非專業評論,或進行轉發,實現文學作品的爆炸式傳播。
因此,自媒體的發展使得外國文學作品的傳播真正實現了平民化,傳統媒體中傳播者與受眾的角色邊界日漸模糊并實現相互轉化。梭羅作品的讀者同時也是其傳播者,在這種角色轉化中,外國文學傳播走向了欣欣向榮的局面。因此,在推動外國文學傳播時,我們可以建立相應的微博、微信公眾平臺等,定期定量發布與外國文學作品相關的影音、文字資料,并建立相關傳播機制。
三、結語
新聞傳播學與文學都是社會意識形態中的重要構成要素,新聞致力于捕捉社會生活中的熱點事件,文學則著重依據社會生活經驗進行再創造,二者同根同源,與社會生活密不可分。另一方面,新聞傳播與文學傳播都以大眾作為接收對象,致力于為受眾傳遞出有價值的信息,改變人們對于社會生活的認知與觀念,二者都隸屬于社會文化普及的必需品。[2]
“互聯網+”時代,傳播手段不斷創新。外國文學作品在中國的傳播應該順應時代潮流,尋找適合自己的傳播渠道,以更加多元的形式出現在讀者視野中。但在新媒體環境下,要注意對網絡信息的辨別及輿論的引導,預防負面輿論對外國文學作品的傳播造成的負面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