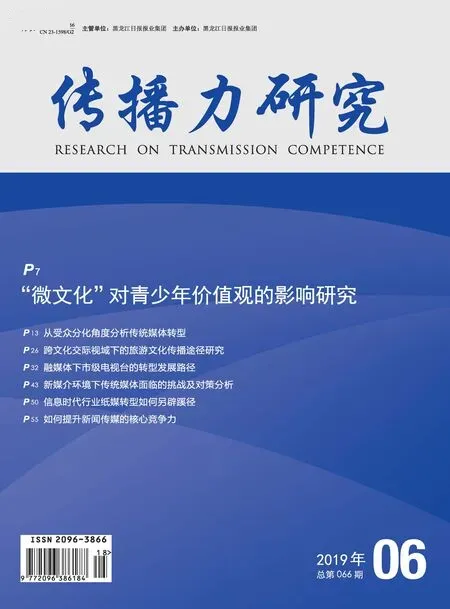輿情事件中公民記者角色定位
錢凱 上海大學(xué)新聞傳播學(xué)院
“公民記者”這一概念,最早起源于20世紀(jì)90年代的美國。美國“德拉吉報道”個人網(wǎng)站的創(chuàng)辦人德拉吉在1998年率先將克林頓丑聞公之于眾,引起了全美國的注意,因此也獲得了最早的“公民記者”稱號。
隨著移動終端的不斷普及,信息傳播無論是在渠道還是接受對象的數(shù)量上都有了很大的提升。傳統(tǒng)的大眾媒體處于主導(dǎo)地位的格局逐漸被打破,信息傳播越來越呈現(xiàn)出去中心化的特點。通過微博、微信這類的新媒體平臺,人們既接受來自外界的信息,同時也主動積極地以“公民記者”的身份參與到信息傳播的過程中。
一、輿情事件信息傳播特點及公民記者參與特點
持有智能移動終端,無論在何時何地,個人都能通過智能媒介所傳遞的信息讓自身體驗到事件的部分經(jīng)過。各類資訊平臺、個人社交平臺,能夠以文字、圖片、視頻等多種形式,或多或少讓受眾“在場”了解到事件的相關(guān)信息。而一些重大的社會輿情熱點事件,往往因為其突發(fā)性、受眾層廣大、涉及利益群體廣等特點牽動著更多受眾的情緒。在這種情況下,“公民記者”參與信息傳遞相較于傳統(tǒng)記者有了更多新的特點。
(一)信息發(fā)布平臺的多樣性
微信朋友圈的最顯著特點就是信息擴散基于一種“熟人關(guān)系網(wǎng)”。處于共同交際圈的朋友圈的話題會有一定的趨同性。輿情事件在微信好友之間傳播,提高了事件的可信度,增強了傳播的效果。微博也因其巨大用戶量讓信息能夠更加迅速的傳遞。微博熱搜榜,通過向用戶展示關(guān)注量靠前的事件,吸引用戶參與到微博設(shè)置的議程中來。輿情事件一經(jīng)引爆,通過微博熱搜榜,引來更多的點擊量和關(guān)注量,部分用戶也會參與到事件相關(guān)話題的轉(zhuǎn)發(fā)、評論甚至是發(fā)布原創(chuàng)內(nèi)容。微博發(fā)布的字?jǐn)?shù)被控制在140字,這種“短平快”的特點,也讓微博上的信息具有了更高的時效性。
(二)內(nèi)容更具時效性、個性化特點
相比于職業(yè)記者,公民記者在面對突發(fā)性事件時有更多優(yōu)勢。突發(fā)事件往往具有不可預(yù)測性和緊急性,相關(guān)新聞的報道則更應(yīng)該及時迅速。在職業(yè)記者難以第一時間趕到現(xiàn)場的時候,相關(guān)事件的當(dāng)事人或目擊者能夠提供第一手的信息,會讓新聞具有更高的價值。
“公民記者”也會推動更多個性化內(nèi)容的傳播。2017年麥當(dāng)勞改名“金拱門”事件,最早由自媒體“爆料濰坊”在2017年10月25日17:35分爆料。一時間,微博上涌現(xiàn)出了眾多對麥當(dāng)勞改名的吐槽和調(diào)侃:“KFC叫開封菜?”、“總感覺怪怪的,除了豬會拱,金也會拱……”僅在17:30-19:00之間,麥當(dāng)勞官方微博未作出回應(yīng)之前,“金拱門”相關(guān)的個人微博就有617條的發(fā)布量。著名央視的前主持人,張泉靈就在其微博上發(fā)布了“早上,猶豫了半天,金拱門還是開封菜,想了想最近長肉得厲害,忍痛只喝了杯白毛女咖啡。”這條微博也獲得了10w的點贊量。自媒體和一些微博大V既作為輿論領(lǐng)袖,又充當(dāng)“公民記者”,增強了更多個性化內(nèi)容的傳播效果。
二、公民記者及其報道存在問題
公民記者相比于職業(yè)記者,缺乏一定的專業(yè)素質(zhì),其發(fā)布的內(nèi)容難免存在問題。在輿情事件發(fā)生的時候,公眾的情緒極易受到事件本身的影響,缺乏理性的思考,陷入“沉默的螺旋”中,人云亦云。公民記者及其報道所存在的問題,會對社會輿情造成很大的影響。
(一)信息真實性難以把握
移動互聯(lián)時代,信息獲取和發(fā)布的渠道更加廣泛,“公民記者”能夠更加便捷地參與信息發(fā)布,然而網(wǎng)絡(luò)空間的開放性和匿名性也讓網(wǎng)絡(luò)信息的真實性難以甄別。在很多重大事件尤其是負(fù)面事件發(fā)生時,民眾會更關(guān)注事件所產(chǎn)生的原因,當(dāng)看似合理的解釋出現(xiàn)時,網(wǎng)民們會立刻將情緒轉(zhuǎn)移到所謂的原因上。在這個過程中,信息來源的“目擊者”,以及部分網(wǎng)絡(luò)媒體所充當(dāng)?shù)摹肮裼浾摺保菀鬃屖鼙娛プ陨淼乃伎级つ肯嘈啪W(wǎng)絡(luò)上“公民記者”的言論。
(二)營銷目的難以揣測
微信公眾平臺的低門檻,讓更多自媒體營銷號能夠利用內(nèi)容賺取流量,謀取利益。2019年初微信朋友圈大熱的爆款文《一個出身寒門的狀元之死》,通過“寒門”、“狀元”、“不合群”、“病逝”這些易容易戳中社會痛點的敘述制造了極大的懸念和沖突。也讓這篇文章在短時間內(nèi)收獲了10w+的閱讀量。然而第二天這篇文章卻因含有虛假信息遭到微信平臺的封禁。營銷號為了博取關(guān)注,不惜一味的拿社會痛點大肆炒作,甚至添加虛假的信息以達(dá)到更大的傳播效果。
(三)濫用權(quán)利易于侵犯隱私
互聯(lián)網(wǎng)讓信息檢索趨于便捷,然而不合理的使用則會引發(fā)“人肉搜索”等網(wǎng)絡(luò)暴力。在網(wǎng)絡(luò)上合理的發(fā)聲有利于行使監(jiān)督權(quán),然而濫用則有可能侵犯他人的隱私權(quán),嚴(yán)重的甚至?xí){到他人的人身安全。2015年5月3日,成都女司機被打事件在網(wǎng)絡(luò)傳開之后,網(wǎng)友不滿女司機的“路霸”行為,對其進(jìn)行大規(guī)模的人肉搜索,先后翻出她的駕駛違章記錄、個人身份信息,甚至是開房記錄,事件發(fā)展從而轉(zhuǎn)向惡劣的態(tài)勢。勒龐在其《烏合之眾》中指出:“群體不善于推理,卻急于行動。”在這一事件中,網(wǎng)民一味的侵犯他人的權(quán)利去捍衛(wèi)所謂的“公正”,實在是有失偏頗。
三、輿情事件中“公民記者”角色的正確定位
公民記者不同于職業(yè)記者,所受到的職業(yè)規(guī)范約束會更少,另一方面,在很多突發(fā)事件上,公民記者往往是臨時承擔(dān)起記錄現(xiàn)場、傳遞信息的責(zé)任,相比于職業(yè)記者,則會缺乏一定的專業(yè)技能和素養(yǎng)。然而在重大社會事件發(fā)生之時,公民記者能夠提供及時的、一手的信息,對職業(yè)媒體人來說,可以充分利用線索挖掘事實,對于受眾來說,也能夠借助公民記者提供的信息從不同角度來了解事實。
(一)公民記者應(yīng)提高自身專業(yè)性
在這個人人都能發(fā)布動態(tài)、傳遞信息的時代,遇到重大輿情事件,人人都能充當(dāng)“公民記者”的角色。公民記者應(yīng)當(dāng)明確自身的社會責(zé)任。尤其在重大的社會事件發(fā)生時,作為在現(xiàn)場的當(dāng)事人或旁觀者應(yīng)當(dāng)做到維護(hù)事實真相,不能虛構(gòu)事實、妄加論斷。另外,公民記者不能為了單純的制造轟動效應(yīng)而在挖掘信息的時候侵犯他人的隱私。
(二)職業(yè)記者應(yīng)合理利用公民記者
作為職業(yè)記者,應(yīng)當(dāng)將公民記者視為自己的互補。公民記者往往能趕在職業(yè)記者之前去發(fā)掘有關(guān)信息,職業(yè)記者應(yīng)當(dāng)充分利用公民記者的接近真相的優(yōu)勢為自己的采訪報道找準(zhǔn)切入口,豐富內(nèi)容。同時,職業(yè)記者應(yīng)當(dāng)充當(dāng)“把關(guān)人”的角色。對于“公民記者”所提供的信息,專業(yè)媒體及職業(yè)記者應(yīng)當(dāng)認(rèn)真核實信息的真實性,避免因虛假信息而引起不必要的負(fù)面輿情。
(三)受眾應(yīng)謹(jǐn)慎對待公民記者
對于一般受眾來說,也應(yīng)當(dāng)謹(jǐn)慎對待“公民記者”提供的信息。網(wǎng)絡(luò)信息繁雜,虛擬的社交平臺不能保證所有信息的真實性,對于網(wǎng)絡(luò)信息不能盲從。在重大輿情事件發(fā)生的時候,更應(yīng)當(dāng)全方位地了解事實的真相,而不是陷入“沉默的螺旋”之中。另外,網(wǎng)絡(luò)平臺也為每個人提供了平等發(fā)聲的權(quán)利,當(dāng)輿論走向極端的時候,更應(yīng)該有理性的聲音站出來,用事實解決公眾的疑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