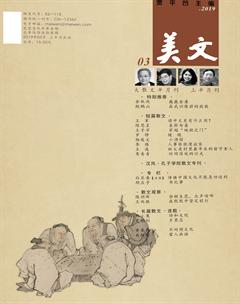不耐煩文化
黃集偉
『沒興趣,無利益,不參與』 來自作者李雅婷文章,語出作家朱天文,新近榮獲“華語文學人物獎”,在答謝詞里,朱天文援引漢娜·阿倫特的話,贊美“身處一個干凈位置”的青年學子,稱之。“沒興趣,無利益,不參與”:“那么大家要問了,是對什么沒興趣,無利益,不參與?我回答大家,對聲譽,對財富,對權勢。”朱天文的轉述很文學(分拆解說),但那溫婉里自帶確定和確信。
『實力派路人甲』 語出作者瘦駝文章標題《雜色狼,一個想改名轉運的實力派路人甲》。拋開文章主旨不說,這個“實力派路人甲”的矛盾造詞更為誘人聯想:它有鮮明的吃瓜底色,有不甘的內心激蕩,有不宜較真推敲的存在感,也有不易發覺的企圖心,很像我或你。
『劈你的雷正在路上』 來自百家號文章。上為歌手王心凌新專輯所收曲目之一,據說“歌詞意思就是懟網絡噴子。王心凌確實近些年,沒少遇到網絡暴力,這也算是正面懟黑了”。文章認為,從甜心教主,到以噴懟噴,王的人設改變稍顯突兀:“面對惡人,直接請雷,這樣的做法是《延禧攻略》的女主魏瓔珞的獨門神功……現在這種方法果然開始流行了,歌壇魏瓔珞——王心凌,也開始請雷了。”“請雷”,是多么霸悍的一種脆弱呢?
『含咪量』網絡熟詞,跟“抖音梗”之類近似,算是所謂流行文化影響力的派生詞。而所謂影響力,也常經歷路轉粉、粉轉路之類的跌宕起伏——在被人指摘與自我黑化間,還有恁多移步換景的維度,換個角度看,好多“梗”或“量”其實漏洞百出,沒人推敲也經不起推敲,呵呵而已。
『通過無盡的含混來言說那種確定性的力量』語出學者洛之秋微博。參加文學獎評獎,洛老師坦陳一己之好:“我最鐘愛的現在在《信徒》和《卜馬尾》之間搖擺,大概是因為這兩個文本其實很相似——透過一個老人的衰老和死亡來傳遞信仰的價值。大概與‘迷幻‘碎片和‘喪比起來,我還是更喜歡文學通過無盡的含混來言說那種確定性的力量”。末句中強調的“含混”與“確定”是很高級的標準,說它是小說的生存級底線,也不為過,不然,為啥還要寫小說讀小說?
『野奢』 來自作者潘姜汐熹、龔鑒文章。“野奢”一詞原為特色旅游主題詞(描述定位語),“野”極言旅游地自然原生狀(冷僻偏遠荒無人煙),“奢”極言景點吃住奢華(奢靡無度豪華獨享),這種反差比,成為此類旅游或個性化度假的噱頭和招牌。而正如兩位作者所說,當它的“野”野到基本沒有網絡信號、當它的“奢”奢到必須賒賬打白條時,“野奢”也不過是個宰人殺熟的招幌。
『小小的眼睛里充滿了大大的疑惑』網絡流行語,來自歌手李榮浩參加某真人秀節目后熱傳的表情包(文字部分),有人稱之為“黑人問號”(懵逼的尼克·楊)的本土實名制版,也有人稱之為小眼族勵志奮斗版。2018年,表情包語文在流行語文中占比躥升,它匹配了視覺化潮流,也跟現代人簡單粗暴即時滿足需求很搭,至于語境是否妥當、溢出語義是否尷尬之類,少人細究。
『不耐煩文化』 來自作者劉融本周文章。作者從“心情基調”切入,討論當代人“輕微煩躁,偶爾自燃”背后的“不耐煩文化”。作者沒將其簡單地歸結為浮躁,也沒將其歸結為壞事,而是小心翼翼地辨析“即時滿足”與“延時滿足”之間的人性更迭:即時滿足讓人歡呼雀躍,延時滿足讓人莫名不爽,“一邊說‘我一秒都等不了一邊用拖延癥浪費光陰”。跟即時滿足放大需求一樣,延時滿足映照出人格撕裂的日常:小妹啊,茉莉花炒蛋還上不上啊?
『 我可以當首富,但是沒必要』 2018網絡流行句式,亦稱“可以但沒有必要體”,原為某游戲主播口頭禪,熱傳后成為流行造句梗。樣板句如“我可以當首富,但是沒必要”“我可以原諒你,但是沒必要”“我可以回答你,但是沒必要”……此梗既是一種遮掩能力弱項的話術格式,也是一種慌張人格的自我撫慰,它超強的適用性和開放性,讓一些游戲玩家視其為裝逼神器。
『常叫他“呀”或“喂”』 來自媒體花邊新聞。前不久,一位名為“禤靐龘”的香港初中生在社交網站發文抱怨自己的名字難念、難寫,給自己的社交活動帶來很大困擾——迷信的父母“在他出生時,請算命師取了‘禤靐龘(xuān bìng dá)這個名字……同學因為念不出他的名字,常叫他‘呀或‘喂”。“禤靐龘”屬冷僻漢字,筆畫繁雜,“龘”四十八畫,“禤靐龘”三字總計一百零三畫。唉,禤靐龘快快上網吧,上了網,先給自己起個最最簡單的網名吧。
『沒毛病』 網絡熟詞,與其既有義項(沒問題)比,網絡義項的“沒毛病”既含有尬聊敷衍語的意味,也含有發量日稀、謝頂在即(沒毛是種病)的調笑意味。發量之類的調侃自帶歧視基因,在公共場域直言沒毛是病趕緊吃藥,太粗鄙。
『豎屏短劇』 來自媒體報道,“豎屏短劇”是匹配“抖音味”網劇的一種,因為無須橫倒手機,方便快捷,已成為近時一些消費者“通勤時最喜歡消磨時間的方式”。這類橫、豎屏幕的物理區隔真能帶來網劇內容品質的改變?我看懸。豎屏橫屏,人性還是人性,早年間,有導演嘗試圓形電影,終于不過是個玩票類嘗試,它對內容的質地與品質并無本質干擾。
『積極向上慫』 ?媒體對去年最流行文字游戲(求生欲測試)的一個形容,是個偏向樂觀的定義。求生欲測試本多發生于戀人之間,經媒體傳播后日漸大眾化,其標配模式是,“由女方拋出送命題,男方以角度刁鉆的回答表忠心”。將其定義為“情侶間一種積極向上的慫”。雖一廂情愿,可這類文字游戲本身,的確揭開了語文急智與邏輯、辭令與情感、體驗與表現、語境與語詞間微妙詭譎的那一面,想修煉說話水平,“積極慫”是個起點,還不低。
『死亡才是對生命最精準的教育』 來自作家武志紅公號文章,語出辯手邱晨。患病后,老奇葩辯手邱晨說,“死亡讓她學會了三件事情,而第一件事,就是明白了:‘死亡才是對生命最精準的教育……無論是死亡的日期,還是身患重病,還是我們人生當中躲不過的所有壞消息,我們只有看到它、面對它、甚至愿意談論它的時候,我們才有可能去對抗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