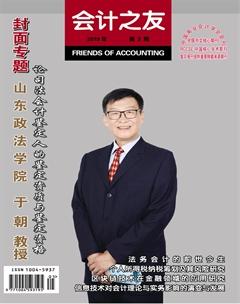避稅行為對企業投資結構偏向的影響研究
宋霞 鄒希佳
【摘 要】 以我國2006—2017年滬深兩市A股上市公司數據為樣本,探索避稅行為是否會導致企業投資結構偏向問題,并在此基礎上進行了產權保護制度、企業性質的異質性分析。研究表明,避稅行為導致了企業投資結構偏向權益性投資,且這種偏向現象在民營企業更加顯著,而強產權保護可以削弱這種偏向;2008年企業所得稅改革可以削弱企業避稅與投資結構偏向的關系。文章為企業避稅行為與投資結構關系的研究提供了新證據,對優化企業投資結構,加強企業稅收監管具有重要的實踐參考意義。
【關鍵詞】 企業避稅; 企業投資結構; 代理理論
【中圖分類號】 F27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4-5937(2019)05-0043-05
一、引言
自2012年以來,我國民間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高達60%及以上,貢獻了80%以上的就業、60%以上的GDP增速和50%的稅收。隨著市場經濟的迅速發展,我國企業的投資結構發生了顯著變化,權益性投資的發展尤為迅速[1]。2006年,我國上市企業權益性投資支出與固定資產投資支出比值平均為6.93,而到2017年該比值平均高達31.76,顯示出我國上市企業的投資結構顯著偏向權益性投資。盡管這種企業投資偏向現象十分常見,但是鮮有研究對其出現的原因進行探索,尤其是以企業避稅為視角,目前尚未有文獻進行實證分析。因此,本文基于代理理論,選取2006—2017年A股上市企業數據,探討了如下問題:企業避稅是否導致了投資結構的偏向?那么對固定資產投資和權益性投資影響的表現分別是什么?異質性條件對避稅和企業投資結構偏向的關系產生了什么影響?
本文的主要貢獻如下:基于代理理論,考察避稅行為對企業投資結構偏向的影響,構建了“企業避稅—代理沖突—企業投資結構權益性投資偏向”的完整邏輯框架;將產權保護進程引入對企業避稅和企業投資偏向關系的考察之中,以往投資研究往往會忽視地區產權保護制度差異帶來的影響,但實際上產權保護是企業投資的重要刺激因素;本文結論立足微觀企業投資視角,為企業投資結構升級、對企業的稅收監管和政府稅收政策的制定提供一定的實證證據和實踐參考。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企業投資一直是學術界最重要的研究對象之一,研究發現企業投資的重要影響因素之一是信息不對稱,主要是來源于經理人道德風險的升高和對其監督難度的增大[2],而企業避稅正是加劇內部信息不對稱的重要原因[3]。避稅通常被界定為企業的一項復雜財務活動,存在避稅動機的企業會通過降低財務信息質量躲避稅務當局的監管[4-6]。已有文獻研究發現稅收激勵對企業權益性投資的促進作用要顯著大于固定資產投資,也有研究得出相反的結論[7]:毛德鳳等[8]檢驗了企業所得稅改革和企業新增總體投資水平之間的正向關系,但企業所得稅改革對企業研發投資的影響比較小。
本文的理論分析從代理理論出發,認為由于企業避稅行為會同時增加內部的信息不對稱程度和自由現金流[9-10],所以經理人決策會偏離所有者的企業價值最大化目標,經理人甚至會因道德風險而產生過度擴張的動機。這種經理人行為不僅體現在企業投資總體增長,還可能會增加企業并購活動[11],這將表現為權益性投資的快速增長。從風險角度分析,企業避稅本身是一項風險活動,雖然強調避稅是利用稅法與會計準則之間的差異進行的財務活動,但是如果被證監部門或稅務部門裁定為避稅行為,必然影響企業的聲譽與股價,甚至造成處罰等損失,經理人成本會相應地增加。因此,為了規避公司行為引發的個人風險,經理人選擇將更多資金投入回報率較高的權益性投資,以期在未來獲取更多的回報。基于此,提出假設。
H:企業的避稅程度越高,企業的權益性投資支出越多。
需要注意的是,企業偏向權益性投資的投資結構可能與我國制度背景有很大關聯,因此存在兩個替代性解釋:企業受到地方政府稅收競爭的影響,投資需要在當地建立具有法人資格的子公司,會以股權投資的形式體現;我國稅收政策給予企業權益性投資所產生的關聯投資收益免稅優惠,企業會因此更多地進行權益性投資。本文將在穩健性檢驗中排除這兩種解釋。
三、研究設計
(一)數據來源
選擇我國2006—2017年滬深兩市A股上市企業作為研究對象,并進行以下樣本篩選:主要變量值缺失的樣本;金融行業樣本;樣本期間內ST等不正常企業樣本;當年虧損企業樣本。最后,共得到7 387個企業年度觀測樣本,并對主要變量按1%進行縮尾處理。名義所得稅稅率來自Wind數據庫,其他數據均來源于國泰安數據庫,研究采用Stata 14軟件進行數據分析。
(二)變量定義
1.被解釋變量:將企業投資結構分為固定資產投資和權益性投資[1],并采用其對數形式進行衡量。Ln Invest 1為固定資產投資支出,Ln Invest 2為權益性投資支出,均以自然對數形式表示。
2.解釋變量:采用會計—稅收差異(Btd)衡量企業的避稅程度[12]。Btd根據企業會計準則與稅法要求之間的差異,按兩者分別計算出的應納稅所得額之間的差異作為避稅指標。同時,也采用剔除應計利潤之后的會計—稅收差異變量(DDBtd)衡量企業避稅程度,采用總應計利潤對會計—稅收差異變量回歸所得的殘差平均值,DDBtd表示的是Btd中不能被應計利潤解釋的部分。
3.控制變量:首先,控制了與企業投資行為相關的變量[13],其中期初貨幣資金的自然對數(FCF)來表示企業的自由現金流狀況,銷售增長率(Salesrate)作為決定企業投資的關鍵因素也被作為控制變量。其次,控制了一般公司特征變量,包括資產負債率(Lev)、資產收益率(ROA)、托賓Q (Tobin's Q)、企業規模(Size)和企業年齡(Age)。此外,本文控制了上市企業的所得稅稅率(Rate)反映企業稅務決策情況的重要依據。最后,控制了年度(Year)和行業(Industry)變量。具體變量定義見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