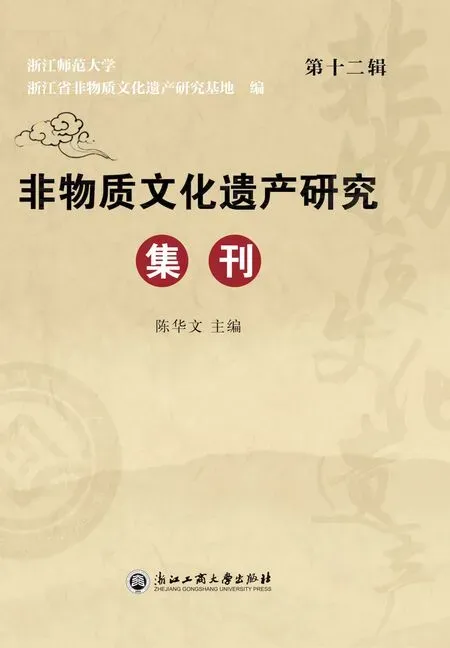“育俗于民”:當代藝陣組織與藝陣文化傳承發展
——以中國臺灣地區沙鹿晉武會為例
張鈺 林敏霞
(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四川成都 610207浙江師范大學文化創意傳播學院 浙江金華 321004)
在歷經戰火洗禮、文化運動、工業化城市化快速發展的沖擊后,近二三十年來,大陸持續處于復興傳統文化、重拾文化自信的熱潮中。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學熱”“文化尋根熱”次第登場,最終形成了波及大江南北的“民俗熱”(1)張士閃:《“順水推舟”:當代中國新型城鎮化不應忘卻鄉土本位》,《民俗研究》2014年第1期。。緊接著,伴隨2004年我國正式加入《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全國性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體系逐步建立和完善,保護措施迅速鋪開,并由此帶動民俗研究及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研究成為熱點,取得了豐碩的保護和研究成果。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轟轟烈烈的“非遺熱”中,不少非遺和特色民俗文化活動只是被“普查”并載入遺產名錄,或者只在配合官方活動需要時被展演。許多曾經深嵌于地方生活的民俗傳統,逐漸或已然消失于群眾生活。
此外,受“科學主義”等意識形態的影響,在多數大眾視野甚至學術研究中,不論是“民俗”或“非遺”,其語境仍隱含著屬于過去的、難以適應現代社會而需保護的、屬于少數人的消極含義。盡管傳統民俗的主體是占絕大多數的基本人群,即“我們的民俗之俗就是多數人的生活方式,我們的民俗之民就是社會的多數”(2)高丙中:《日常生活的未來民俗學論綱》,《民俗研究》2017年第1期。,但在日常實踐中,我們的“民俗”或“非遺”卻與民眾日常生活相割裂,許多民間文化生活的正當性仍然被貶低,民眾的日常生活仍然因不符合“現代”價值而被批判改造,民俗文化生存空間及傳承基礎處于萎縮和喪失的困境中。
我國臺灣地區素有“多神之島”之稱,島上民俗文化的發展在當下呈現出一派紛繁興盛的景象,然而其發展歷史中也曾歷經日據時代“皇民化”運動打壓,受到城市化、工業化、全球化、科技進步及政治因素等的影響,波折不斷。但與大陸不同的地方在于,中國臺灣的傳統民俗文化并沒有因上述原因衰退,反而日漸興盛,如媽祖繞境進香活動聲勢逐年浩大,島內神廟數目不斷增多香火不斷,以民俗藝陣為主題的電影取得年度票房冠軍,民眾自營創新民俗項目對外展演等等。其中,臺灣地區推行社區營造、地方特色文化保護等諸多政策的確是促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因素則在于當地普通民眾自信地認可傳統民俗在日常生活中的正當性與不可分割性,并因此自發信仰、實踐、傳承和創新。
藝陣在中國臺灣地區傳統民俗中極具代表性,廣泛分布于中國臺灣各地。它自宋元時隨閩粵移民傳入島內,通常與各路神靈、大小神廟及花樣繁多的祭祀活動伴生。藝陣作為與百姓日常生活及信仰緊密相連的民俗,自傳入后便在全臺灣的漢人聚居區星火相承、綿延至今。如今藝陣的展演、組織者多為地方民眾組成的社團協會,他們從自己的日常生活出發繼承、創新藝陣文化。筆者在中國臺灣交換學習期間對臺中沙鹿晉江社區的神靈繞境儀式及當地藝陣組織晉武會進行了調查,發現當下民間傳統文化發展運行有其內在生命邏輯,從而論證在當地政府引導傳統文化復興大方向的前提下,給予社會民眾自我選擇其文化生活的空間,對于民間傳統文化的傳承和發展至關重要。
一、當代中國臺灣藝陣與藝陣組織概況
(一)藝陣概況
“藝陣”是中國臺灣漢人的一種廟會節慶民俗。海峽兩岸漢族同文同種,追本溯源,“藝陣”源于古代“百戲”,宋明以來民間舞蹈發展形式多樣被泛稱為“藝陣”,又叫“社火”“出會”“走會”等,閩臺地區統稱此類民間舞蹈為“藝陣”。(3)鄭玉玲:《論臺灣福佬系民間藝陣及文化特征》,《信陽師范學院學報》,2010年第5期。三百余年間,大陸閩粵移民為求生計接連不斷冒著生命危險渡海登島,閩粵文化隨著人群遷徙而傳播至全島。艱辛的旅途和未卜的前途,使得早期移民們將信奉的神靈神尊隨身攜帶以求庇佑,“藝陣”作為神靈祭祀、年節慶典必不可少的儀式部分也由此渡海入臺,并衍生發展為現今臺灣分布最廣的民間舞蹈。在活動中人們為壯大聲勢、敬謝神靈,同時在艱苦的勞作生活間隙休閑娛樂,便常在祭祀隊伍前部設置歌舞雜技表演,即“藝閣”和“陣頭”,合稱“藝陣”。“藝閣”指用木板搭組平臺,加以裝飾,人抬或輪行的花車一類,于節慶熱鬧時做游行觀賞之用;現代藝閣多加以現代燈聲光電裝置裝飾,更具趣味。(4)謝國興:《宋江陣:臺灣廟會文化的特殊傳承》,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社會史研究中心編:《近代中國社會與民間文化——首屆中國近代社會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社會史研究中心,2005年,第17頁。“陣頭”則指迎神賽會中各種消災祈福、娛神娛人及增添熱鬧氣氛的儀式性與表演性團體。藝閣與陣頭一動一靜組成藝陣,共同服務于廟會慶典活動。在大陸語境里,“藝陣”相當于“年節慶典時民間傳統有組織的各類歌舞和雜技表演”。藝陣形式紛繁、種類多樣,依據表演內容、形式、功能及主辦者等可有不同分類。
藝陣有著多彩的表演活動和俗信內容穿插其間。如與藝陣中的“三太子”人偶交換奶嘴以求用其神力護佑家中孩童平安,“炸寒單”為求贖罪或驅散厄運,鉆入繞境媽祖轎底以讓神尊“踏身”而祛病消災等等,這些民俗活動帶給民眾娛樂放松和被神眷顧的慰藉。雖然隨著科技發展,現代社會娛樂方式花樣繁出,藝陣娛樂大眾的歷史功能有所淡化,但在全球化席卷各地、旅游業蓬勃發展的今天,藝陣文化保存了中國臺灣漢人傳統民俗文化的火種,同時不斷吸收現代因素使自己更適應大眾需求,在今天仍是中國臺灣民眾尋求內心安寧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是眾多“中國臺灣名片”中獨具特色的一張。
(二)藝陣組織概況
就筆者了解,“民俗藝陣組織”據業務范圍不同可以分為三類:一類即江泊洲在《中國臺灣傳統民俗藝陣之探討》中介紹的屬于中國臺灣民間普遍社群組織,其組成與當地民間宗教信仰有密切關系(5)江泊洲:《臺灣傳統民俗藝陣之探討》,《屏東教育大學體育》2006年第10期。。在傳統農業社會中各鄉多自有戲曲子弟或游藝陣頭,每逢地方上的廟會神誕、喪葬節慶或進香活動,這些陣頭就會出陣游行并沿街表演各項民俗技藝,使神圣的宗教活動融入世俗內涵。這類藝陣組織幾乎都為業余性質,附屬于社區廟寺,組織訓練費用由寺廟或地方鄉紳供應。
第二類是職業表演性質的藝陣組織。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隨城市化進程的加深,中國臺灣地區農業人口比重下降,鄉村人口流失,部分村莊無力維持原有陣頭組織的訓練,但又出于敬神及村落面子等考慮不愿在廟會中缺席,便選擇雇傭職業性藝陣組織參演各類儀式,對神對人都有個交代。(6)謝國興:《宋江陣:臺灣廟會文化的特殊傳承》,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社會史研究中心編:《近代中國社會與民間文化——首屆中國近代社會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社會史研究中心,2005年,第17頁。由此,帶動了此類職業性表演藝陣組織的快速發展。
本文所研究的“晉武會”并不完全屬于以上兩類,筆者將其歸為第三類:這類組織是對第一種傳統藝陣組織的發展。組織也由當地人業余自發組成,成員不靠藝陣維持生計,全憑信仰和愛好參與活動,可以進行相關藝陣表演并有持續訓練。這類組織雖有所在的社區或廟宇,同時又相對自由,可以應邀北上南下赴全臺各地或有償或義務進行表演;組織成員雖基本為社區成員,但也會吸納周邊社區對藝陣文化感興趣的青年;組織作用已經從傳統的附屬表演型轉而成為獨立運作的協調型,主要在神誕年節時協助村落宮廟組織相關活動、協調村內自有陣型、出面邀請雇傭其他藝陣及組織一些其他環節。組織運作費用由會員會費、應邀表演所得及捐贈(主要來自組織領頭人及部分村民)等幾部分組成。
以上三類藝陣組織雖產生于不同時代,但當下共存于中國臺灣的大小社區之中,共同為各自信奉的神靈服務;且在生活實踐中其分類定位并不固定,如晉武會也可受人聘請為其他社區活動做職業表演。
二、晉武會:一個當代藝陣組織
晉武會是服務于晉江社區的當地藝陣組織,屬于上述筆者所概括的第三類藝陣組織類型。晉江社區,又稱“晉江里”“晉江寮”,是中國臺灣地區臺中市沙鹿區大肚山麓下靜宜大學與弘光科技大學間的一個漢人聚居村落,西距中國臺灣海峽東岸僅數十千米,平面略成長方形,以晉武路為中軸線,居址在社區東部更為密集,西部則相對空曠,土地功能多與靜宜大學相關。村中及周邊耕地較少且多沙地,歷史上以番薯、花生及甘蔗為主要經濟作物。中國臺灣經濟轉型后,當地大規模甘蔗園荒廢,村中青壯年人多外出務工謀生或在村落高地開設觀景咖啡吧發展旅游觀光業。此外,向周邊大學學生、青年教師出租房屋也為該村主要謀生手段之一。
晉江寮社區人口年齡構成雖無具體數據,但從日常走訪和對晉武會會長的采訪及社區服務時的觀察可以概括得出:晉江社區現有土著居民以中老年人為主,青年人留居村中較少。(7)筆者在臺期間參與的晉江里“銀發族社區照顧服務”志愿者活動正是因為村中老人數目較多而青壯年人較少,老人長久缺乏溝通與活動,晚年生活缺乏活力太過冷清,才會邀請大學生進行志愿陪同服務。于活動中可以觀察到到場老人多在20余人左右,村中尚有不方便出行或不喜此類場合的老人沒有到場,考慮到晉江里村落不大,這個數目算較為可觀;此外采訪晉武會會長蔡俊明時他也提到由于晉江里青年人較少,晉武會雖主要服務晉江社區寺廟,但其組織成員有不少來自周邊社區。晉江社區內現有青年居民多為周邊大學租房暫住的學生,人數不少但多聚集于村落邊緣,與村落內部活動交集甚少。
村中有保安宮和土地廟兩座廟宇,分屬王爺信仰和土地公信仰,其中保安宮位于村落中部偏東地區,土地廟則偏于村落西南位于臺灣大道七段公路旁;日常啟門閉院及相關活動由每年選出的幾戶特定元老村民主持,輔以其他組織。晉武會便是晉江社區及其周邊居民自發組成專門統籌兩座廟宇所需藝陣活動的組織,它在晉江里保安宮一街之隔處有一處房屋作為組織基地,用以供奉玄天上帝、存放藝陣表演道具,兼為議事場所。
(一)晉武會的成立
晉江社區原就有日常處理宮廟相關事務的松散組織,只是行無名號、疏于管理,導致晉江的宮廟在與其他社區宮廟活動交流時十分不便。這是晉江民眾自發成立晉武會的一個地方性因素。
晉武會現任會長兼創始人之一蔡俊明出生于1987年,以裝潢家居店木匠為主業謀生。作為一個晉江本地人,他自小崇敬神靈,對民間信仰及傳統民俗十分感興趣,他對神靈保持“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但“又不過分迷信”的態度。他于2013年聚集身邊幾位而立之年又同樣喜愛藝陣民俗及民間信仰的朋友,每人出資100000新臺幣(約合人民幣20000元),整理村中組織基礎,成立了“晉武會”,初創者為會中元老,組織尊奉“玄天上帝”(8)中國臺灣的北帝,一般被稱為玄天上帝,簡稱上帝公。根據宋朝時代的民間傳說,玄天上帝原為一名屠夫,性情至孝,而以殺豬為業,直到晚年始悔悟自己的行業殺生太多,難積陰德,遂毅然放下屠刀,遁入深山修行。某日偶遇仙人告知“山中有婦人分娩,速去幫忙”,他急忙趕到河邊,果見一婦人抱嬰兒,請其代洗產后污物。但當他在河中洗濯時,卻見河中金光浮現,回首探視,婦人已不知所終。心中忽有所悟,認系觀音顯靈,以試探他修行的誠心,使得他更加堅定修行的決心。屠夫潛心修行多年,忽得神意暗示,欲除殺生之罪,須刀割己腹,取出臟腑洗清罪過。于是屠夫即赴河剖腹,任令腸胃流入河中(一說是屠宰所得的豬腸、豬肚),他改過修行的至誠終于感動上蒼,準其升天成仙,是為玄天上帝。,這也是晉江里當地的信仰傳統之一。晉武會即便在配合本村宮廟為“池府王爺”展開活動前,也會先行參拜他們供奉的玄天上帝。
“晉武”之名由神靈親自在蔡俊明所提供的多個草擬名稱中選中,“晉”代表晉江里,“武”則因為所奉的“玄天上帝”屬性武神。而晉江社區中部主路又恰好名為“晉武”,蔡會長認為這是神明的認同與護佑,以保晉江里一方平安。
(二)晉武會組織狀況及運作
晉武會為業余私人興趣社團,現有會員200余人,由于組織的地域性及神明“規定要當地人為其抬轎”的規矩,成員多為晉江本地樂于服務寺廟、參與藝陣活動的中青年及青少年。但由于晉江本地青年多外出務工,總數較少,周邊村社有志于此的愛好者也被吸納進來。成員總體以男性為主,女性較少,團體有統一的T恤作為制服且時常更新換代。晉武會組織結構較為完備,會長、副會長、財務等職位一應有之。
組織成立后,通過朋友介紹、自我報名、會長網絡社交媒體宣傳等多種方式廣泛吸納新鮮成員。采取會員制度,成員無償為組織服務。已工作成年會員每月繳納500元新臺幣(約合人民幣100元)作為會費用于組織日常運營;對民間信仰及藝陣感興趣的未成年人(以高中生為主)不需繳納會費即可入會,作為晉武會后備力量接受年長成員訓練,時間多在晚上7∶00—9∶00,內容為抬轎班等陣型表演。
組織開展的正式活動時間多定于休息日,以便成員能在不影響日常工作的情況下盡量參與。一切活動均非強制,會長會將活動信息公布在網絡群聊小組,自愿參與的成員依次報名即可。核心成員在活動前后均會在晉武會小院內聚會商討進程或總結經驗,活動淡季時也會三五天小聚一次喝酒聊天。考慮到成員白天各有主業,聚會議事也多選在工作時間之外。
組織通過line(9)中國臺灣流行的社交軟件,功能類似微信,用于線上即時通訊。群聊小組進行內部成員交流、通知和活動及時反饋,利用Facebook粉絲專頁(10)屬于Facebook的一個功能,類似微信公眾號,用于發布活動通知及總結等推廣性質的文章,并可與粉絲及其他相關組織實時互動。對自己的表演活動進行宣傳、發布活動信息、上傳活動影像并與Facebook上喜愛此類活動的網民及其他組織建立聯系。
(三)晉武會的具體職能
作為晉江社區本地藝陣組織,晉武會首先具備藝陣表演功能,能展演陣前游行神尊人偶扮演陣、抬轎班陣等基礎陣型;其次,組織也會不斷訓練成員將表演技能在組織內傳承。除了上述日常工作之外,它還在藝陣活動中發揮橋梁作用:與村中寺廟負責人商議活動時間和所需陣型,協同宮廟管理人員調動村中(如扶乩人等)非會員活動,聯系周邊乃至臺灣地區樂于參與本次活動的藝陣組織,協助聯系雇傭較為專業的藝陣表演團體(如南北管等專業技能要求較高的陣、車載舞曲表演女團)及在活動當天鎮守現場負責統領等。晉武會這類組織使村民信仰活動得以順利維系,同時又不會因為相關瑣事及彼此協調耗費村民過多的時間及精力,避免了因此而導致的民眾摩擦積怨、不歡而散,甚至最終放棄開展類似活動的困窘。
晉武會所在建筑原就是成員們假日聚會、培養感情之地,協會的成立聚集了更多志同道合的人在此一同實踐發展共同興趣,也拓寬了會員乃至晉江里藝陣活動的交友空間。成員們有了一塊專屬區域在固定時間一起排練,蔡會長認為這不僅能傳承傳統民俗保平安,還能鍛煉大家因工作而疏于活動的身體。
(四)晉武會與晉江社區的關系
晉武會成員多數是晉江里村民,其建筑本就坐落于晉江社區內,是社區的一部分,他們辛苦經營活動也是為了晉江里本地村民的共同信仰和儀式,如2016年11月12日池府王爺金身迎回繞境活動就由晉武會與社區陳主委共同協調組織,晉武會始終與社區其他機構一同為社區發展貢獻自己的力量。
不論是藝陣表演、活動組織還是四處助演,晉武會似乎始終呈現出正面積極的形象,但事實上它與許多臺灣地區的藝陣組織一樣,會員中有不少其實是社區“邊緣人”,如不愛讀書的輟學生、混跡街頭的不良青年甚至黑社會成員。在繞境現場,他們身著晉武會會服,頭發染成各種顏色,造型奇異,咀嚼著檳榔口牙血紅。他們原本是社區的不穩定因素,但晉武會將他們集合起來,借玄天上帝之口及組織會規對其進行行為約束,如活動期間不可飲酒鬧事之類。這些規定雖不一定被完全遵守,但鬼神的約束力和“集體表象”的作用是明顯的,在活動現場甚少有見晉武會會員飲酒,偶爾在街道拐角有一兩位偷飲者也并沒有因喝酒而耽誤活動。將活動安排在休息日也消耗了成員們非工作日的大量時間和精力,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更多不當行為發生。晉武會對晉江社區治安穩定的作用很難量化,但可以肯定的是,沒有晉武會,晉江里的治安一定不會更好。李亦園先生在《宗教的社會責任》中也肯定了宗教信仰對道德倫理及社會秩序的作用。(11)李亦園:《宗教的社會責任》,李亦園編:《李亦園自選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15-223頁。
另外,正如前文所述,保安宮、土地廟為村內公有宮廟,但配合他們展開活動的晉武會屬于私人興趣社團,他們參與宮廟活動,但兩者并無嚴格附屬關系。除宮廟活動外晉武會也會在村中空地搭建臨時宮廟舉行自己的活動,并會提前一周制作海報或邀請卡張貼于村內公告欄或會員家外墻,邀村民同樂,豐富社區文化生活,促進社區內部交流。
(五)晉武會與其他藝陣組織的互動
像晉武會這樣的民間組織散布于全臺灣大小村落,他們通過朋友介紹及臉書(Facebook)等社交媒體相互交流、互相支持彼此的活動。在池府王爺金身迎回繞境活動的藝陣表演中,臨近村鎮的藝陣組織便前來現場助演,更有團體從臺北臺南四面八方趕來支持。助演團體僅需參與表演,準備和清場均由晉武會成員處理。這種幫扶多為義氣相助,主辦者會盡力貼補車費和餐食。針對本次繞境的支援團體,蔡會長設計每團6000新臺幣(約1200元人民幣)來回租車預算,年輕人喜歡的檳榔每團3000新臺幣(約600人民幣),還提供香煙啤酒及午餐。盡管尊玄天上帝教誨晉武會成員于藝陣活動期間不許飲酒,但對友團則無此限制。本次活動最終檳榔消費超過20000新臺幣(約4000人民幣),啤酒消費約10000新臺幣(人民幣2000元),這筆費用由蔡會長先行墊付,有時也會有人贊助。
通過網絡與周邊乃至全臺各地藝陣組織進行聯系,邀請他們來捧場,豐富了現場陣型,壯大了活動聲勢,鑼鼓喧天才能讓神感受到社區最大的熱忱,因而更加護佑一方;不同團體身著不同色T恤作為隊服,彼此區別,也借此盛大場合自我宣傳,結交其他團體;各組織通過共同活動在現場直接交流,使藝陣文化的創新及時在各組織之間傳播與鞏固;各團體對于他人的支持彼此都有記錄,今日伸手相助更是為了明日自家辦事有求于人時能一呼百應,馬到功成;這種你來我往、相互支持促進了晉江里與周邊村落的地域聯系,促使不同社區間的民間信仰體系持續交流,受眾群體得以不斷擴大,同時強化著彼此的地緣凝聚力和認同感。
三、當代藝陣組織對藝陣文化傳承發展的表現
(一)扎根現代,樂于創新
不同時代、不同地域的人有不同的精神文化需求,相應便會產生不同的文化形式和內容。藝陣組織為了使得藝陣文化在新時代能夠持續獲得民眾的喜愛,不斷地將現代元素注入藝陣表演中。例如“難登大雅之堂”但為村民所喜愛的流行曲串燒“鋼管舞”表演車。據蔡俊明會長介紹,為吸引年輕人活躍活動氣氛,最初他們只是在藝陣團體中引入了電子琴演奏,后逐漸演變為車載演奏加伴跳,最后為保證表演者的安全才在車板上安裝“鋼管”,形成了如今活動熱場必不可少的“鋼管舞”表演車,深受年輕人喜愛。
更為典型的代表是火遍全臺甚至遠播海外的“電音三太子”。“三太子”原是繞境隊伍中打頭陣憨態可掬受人喜愛的孩童守護神,但隨著娛樂方式不斷發展,青少年早已不再靠觀賞藝陣游行取樂,也不再將“三太子”作為守護神信奉,失去市場的“三太子”一度從藝陣隊伍中消失。但熱愛“三太子”或依靠扮演“三太子”人偶為生的民間藝陣表演者不愿意就此放棄,多個團體不約而同地改造自己的表演方式,添加民眾喜聞樂見的現代流行元素,最終形成了古今結合、雅俗共賞的“電音三太子”,并一炮而紅。依然著傳統裝扮的“電音三太子”神偶騎重型機車、溜滑板表演雜技,伴隨當時流行歌星伍佰等人的電子音樂群跳霹靂舞,不停地與觀眾互動,將繞境變成嘉年華,聲勢浩大、奪人眼球,很快引起大批效仿,表演級別越來越高,從村落街頭到高雄世界運動會的開幕式,后來又相繼在臺北聽障奧運會、上海世界博覽會表演,甚至以青年學子身份進入人民大會堂與時任國家主席胡錦濤擊掌。(12)鄧琪瑛:《臺灣流行文化“電音三太子”中的青少年元素探析》,《青年探索》2013年第2期。在民間藝陣組織的努力下“三太子”打了一個漂亮的翻身仗,不僅表演形式創新重新翻紅,還以身處低谷但不屈不撓的熱血精神結合了青少年喜歡的流行文化,更給青少年以新的影響和激勵,“三太子守護神”的文化內涵也由此更新。
(二)社交媒體,聯絡宣傳
除了吸收現代文化要素創新藝陣的形式和內容,藝陣組織在信息社會中還通過充分運用現代社會媒體,幫助藝陣文化茁壯生長。
藝陣組織對現代社交媒體的運用是多層次的。組織內部即時通訊,保證信息傳達準確快速是活動順利開展的法寶。在晉武會對池府王爺金身迎回繞境活動的組織中,蔡會長通過line通知指令分配任務并及時接收各部問題反饋。晉武會組織成員平時通過自己的社交軟件交朋結友,發揮個人力量多點式宣傳團體吸納新成員。組織在臉書上成立粉絲專頁與其他類似組織互動,相互宣傳點贊支持并在活動時邀請其到場助威,類似于大陸微博網紅的“抱團”營銷。當然,藝陣組織的網絡影響力沒有網紅那么廣泛,但他們不完全重疊的粉絲群在一次次互動中不斷被交叉影響,由此擴大了互動中任何一方的影響力;透過社交媒體宣傳所產生的影響力也遠比舊式張貼公告、口耳相傳更大。增長的粉絲群是組織和藝陣相關團體潛在的新生力量,經社交媒體快速聯絡不同村落組織相互協助解決了活動人手不足的尷尬,同時促進不同藝陣表演之間的互補學習及創新內容傳播。
當代藝陣組織與影視媒體的聯合同樣推動著藝陣文化在年輕一代中重燃火花。電影《陣頭》改編自臺中九天民俗技藝團的真實故事:陣頭世家中與團長父親關系緊張的叛逆兒子陰錯陽差接下陣頭團長位置,但手下輟學生團員不服其帶領,對家陣頭團體虎視眈眈。主人公決定證明自己,背起鼓,帶著一幫年輕團員踏上環島之路,將時尚元素加入傳統文化,喚起中國臺灣陣頭文化新生機。電影獲得第49屆中國臺灣電影金馬獎提名的好成績,成為2012年中國臺灣票房冠軍。導演馮凱表示創作初衷是想拍一部中國臺灣人感動的正能量故事,調查中發現“陣頭”這種傳統文化的色彩,與神明、廟宇、中國臺灣人民的關系足以引起人們的共鳴。陣頭文化中人們尋找自己存在價值的過程體現出了足夠的戲劇張力。(13)時光網:《陣頭·幕后揭秘》,http://movie.mtime.com/155737/behind_the_scene.html。《陣頭》的宣傳效果不僅體現在票房和獎項,更深刻滲入中國臺灣當地年輕人的生活中,可以說它是促成晉武會成立的重要社會因素:影片原型九天民俗技藝團位于沙鹿區大肚山頂,晉武會所在晉江里位于沙鹿區大肚山腳。電影2012年上映大獲成功,晉武會則借助電影的成功在次年成立,并一直發展至今。
藝陣在此作為文化資源被搬上電影屏幕,不僅宣傳了藝陣文化,同時這種新的宣傳方式動員了更多的人重新認知和認同傳統藝陣文化。“民”與“俗”在新時代,在新的媒介空間進行著新的互融和發展。
(三)和諧社區,延續傳統
現代藝陣組織開展藝陣活動的過程中,在多個層面維系社區和諧,延續傳統。
首先,藝陣組織在進行每場藝陣活動前都要求得社區神靈的“同意”,以達到人與超自然神靈之間的和諧。一場繞境活動由卜問吉時路線、挑選所需藝陣種類、村民合力訓練、村中統籌協調組織等多個部分組成。活動時間及路線多由宮廟負責人和藝陣組織者共同商定,選出天氣穩定且最契合大多數人閑暇的日子(因而各類活動多在雙休日開展)、途經家戶數目最多的路線等。接著,于神尊面前擲茭(14)擲筊是人與神靈交流發熱的一種問卜儀式,普遍流傳于華人社會。儀式內容是將兩個約掌大的半月形,一面平坦、一面圓弧凸出之筊杯(一種尋求神靈指示的工具)擲出,以探測神鬼之意。凸面為“陰”,平面為“陽”,唯有一陰一陽為同意。請求批準,若神尊“否定”便將活動開始具體時間點順延五分鐘并再度詢問直至“同意”卦象出現,“神靈所好”的藝陣種類也要按這一程序來進行。通過“擲茭”獲得神靈的同意,是李亦園先生所說的三均衡中的與“超自然”的均衡,是人與超自然的和諧相處。信仰蘊含無窮力量,即便村民心知所謂“神的旨意”源自各方協調,但其畢竟經過上天批準。祭祀神靈、順利完成神靈滿意的繞境,能使虔誠的民眾獲得內心安寧,從而利于社區和諧。
其次,藝陣組織通過藝陣活動在很大程度上促使社區民眾之間的關系更為密切。單一個藝陣表演就有多變的陣型要求成員耐心協作共同排練,訓練中村民間信任感、配合度不斷上升;每一次成功開展活動都需要全村配合調度各項資源,且這一切都離不開藝陣組織的領導;加之藝陣團體對成員的教化與對社區治安的幫助,形成了社區居民之間、居民與組織之間及居民對藝陣文化的認可,有利于增進地區凝聚力及區域認同,推動社區營造發展。或許是民眾對城市化、技術發展所造成的分離本能的自反性,藝陣組織通過藝陣活動又把日漸分離的民眾有機地聯系在一起。
作為中介,晉武會承擔了溝通村民、配合宮廟負責人、聯系兄弟組織、雇傭職業藝陣團體等大部分對接事項,接受村民自愿的資助用于活動,不足部分通過會費或會長自掏腰包補貼,從而節約村民時間精力成本并極大減少鄰里間摩擦沖突,既提高了村民參與民俗活動的積極性又維護了社區和諧,村民自然沒有理由放棄對傳統信仰的尊崇。由此形成了有信仰—順利開展活動—內心獲得安寧感激神靈—進一步信仰并繼續開展活動的良性循環,保住了藝陣民俗賴以生存的信仰和受眾土壤。
再次,藝陣組織對和諧社區的作用還表現在前文提及的約束成員行為、減少社區不穩定因素這一方面。晉武會制定會規規范成員行為,原為社會“邊緣人”的成員們也在晉武會及其組織的活動中找尋自己的存在價值,獲得社會認同。平日里被視為不學無術、制造混亂的人可以通過為神靈服務來消解心中罪孽與無助,通過自我奉獻重獲社區成員的尊重,為自己在社區生活中找到合理位置,也將自己放入晉武會這樣志同道合的團體,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回歸社區,這幾乎是中國臺灣藝陣團體的共同特點。如電影《陣頭》講述——“臺中的九天玄女廟收容初中、高中的輟學生,組成九天民俗技藝團,剛開始因收容輟學生練民俗技藝,而被外界誤解是逞兇斗狠的團體,但團長許振榮堅持嚴格教育,要求學生需上學才能練鼓、跳陣頭,甚至訂定不能曠課、不能粗口的團規,讓許多不愛念書、血氣方剛的青少年改頭換面。”(15)時光網:《陣頭·幕后揭秘》,http://movie.mtime.com/155737/behind_the_scene.html。藝陣表演與信仰充實了“邊緣人”的日常與精神生活,幫助其找到人生意義,重回生活平衡。鄧琪瑛以“三太子”由頑劣到封神的轉變類比藝陣訓練對社區問題青年進行教化和約束的功能也是很好的佐證。(16)鄧琪瑛:《臺灣流行文化“電音三太子”中的青少年元素探析》《青年探索》,2013年第2期。
(四)年輕力量,薪火相傳
藝陣組織及其活動吸引著越來越多的青少年加入,并延續和發展藝陣文化。自小耳濡目染村頭廟宇頻繁的信仰活動、藝陣表演團體眾多的招募宣傳及各大高校復興傳統文化成立藝陣表演社團等等的日常氛圍,讓青少年人有更多的機會和渠道去接觸、了解、體驗、實踐乃至傳承這些自祖輩流傳至今的民俗文化。
藝陣表演人頭攢動又多設在雙休日等課余時間,自然吸引了好動的青少年;當地民間藝陣組織通過代代相承、口耳相傳、朋友介紹或社交媒體宣傳等方式不斷吸引新人加入;免費參與培訓、未工作會員免收會費制度對青少年而言也是一種優惠。在家長們看來,相較于泡網吧、夜店或飆車,參加藝陣組織和活動更有意義。另外前述的現代媒體傳播,也是吸引年輕人加入的一個很好的途徑。晉武會的蔡會長及其父親甚至認為,晉武會中青年輩出并無特殊原因,只是因為開設了臉書粉絲專頁、創辦了晉武會這樣一個平臺,有興趣的年輕人自然匯集而來。
青少年在藝陣組織內受到較為專業的陣型表演培訓又親歷繞境節慶等民俗活動,積累表演與組織的實踐經驗,了解現有活動的組織管理方式,長期不斷熏陶下自然而然成為藝陣文化的繼承人,使得藝陣及藝陣文化能夠代代相承。
四、育俗于民:引導民俗文化傳承發展的實踐邏輯
藝陣文化的發展以民間藝陣組織積極展演、兼容并包為主軸,也離不開社會生活中各因素綜合作用。首先是中國臺灣獨特的歷史、地理大環境。歷史上大陸移民在遷徙中國臺灣的過程中歷經苦難,依靠信仰維系意志,登島后又要與原住民及不同語系漢人械斗,爭奪土地、水源等資源以求生存。就自然環境而言,臺灣島地震、臺風及次生災害多發,生存環境并不穩定;經濟上,漁業自古便是中國臺灣人民賴以謀生的產業,出海捕魚風險極高,朝不保夕。生活中太多不以人類意志為轉移的風險和不可抗力促使民眾不斷舉辦各類祭祀活動供奉神靈,以祈求生活和平安定,從而促成了中國臺灣地區生生不息的信仰傳統,藝陣文化作為信仰活動的伴生品也隨之發展。其次,社會精英的推崇同樣不可忽視。身處全球化浪潮的沖擊之下,臺灣當局為維護地方文化特色,致力于社區營造、推行鄉土教育,從小學開始教育、宣傳、普及以各類藝閣陣頭為代表的傳統民俗文化(17)許雍政、石乙正:《茄定藝陣之考察》,《身體文化學報》2005年第1期。。當地精英如政商及演藝圈中人或為求心安或為選票作秀,逢年過節必往大廟上香祈福以彰顯自己內心虔誠,進一步鞏固了島內年輕群體對傳統民俗文化的認同。
但是藝陣民俗當下在中國臺灣地區如此興盛,最重要的因素在于以各類藝陣組織為代表的“人”的因素,這些人也正是構成社區的普通民眾,他們是與民俗相伴而生的,也是民俗文化所指向的人群。在他們的生活中,“所謂的民俗不是某種生活的殘留物,而是當時中國廣泛的生活狀況。那些東西不是遺留物,而是完整的生活現實。”(18)高丙中:《日常生活的未來民俗學論綱》,《民俗研究》2017年第1期。對于晉武會的成員而言,他們并不是在悲天憫人地搶救祖輩沒有未來的殘存,而只是按照習慣的方式生活,是遵循自己的興趣偏向,是實踐普羅大眾日常的一部分。他們主動投入閑暇時間與精力、充分發揮自身主觀能動性,將自己喜歡的現代因素與傳統文化融合創新以讓其更廣泛地傳播、為更多人接受;他們集合志趣相投的人為共同愛好出謀劃策,積極吸引更多人并致力于培育傳承人,他們努力協調民俗活動與左鄰右舍的關系,期望平穩順利又熱鬧地舉辦每一場活動。這些活動都是沿著民間傳統文化內在生命邏輯運行的,是在民眾日常生活中和在民與俗的互動中不斷形成和發展的。
藝陣組織客觀上推動了藝陣民俗承繼發展,但它不同于自上而下行政方式的文化實踐。藝陣組織對藝陣發展的推動是自下而上、自發的、主動的,而非自上而下、任務式的、被動的。在此系統中,“藝陣文化”其實可以被替換為“廣場舞”“書法”“長跑”等任何一種興趣行為,它們天然生長在日常生活的角落中,吸引情投意合的人來共同實踐。被定位為“興趣”的“藝陣民俗”也因此擁有同樣的氛圍:輕松、自由、有自己的歷史,并能自然延續發展。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實踐他們的興趣時,自然不會帶有“拯救”的焦慮與急迫,也不會懷著悲憫、俯視甚至歧視的偏見;外界對他們的繼承、展演、創新等行為也不會有過多干涉與界定,組織成員可根據愛好興趣決定自己的行動。這一切都源自較為寬松日常的文化生活空間。在這種相對寬松空間中,民眾的自發性文化實踐能力賦予民俗文化自己的生命力;民與俗相互交融,使民俗文化得到新的孕育、傳承和發展。
復興傳統文化一方面需要政府領導,需要各種政策的扶持,但更重要的是從群眾日常生活的實際出發,喚醒或者說實現廣大民眾對傳統文化及民俗的需要,激發民眾重新展演、傳承、創造傳統民俗的興趣熱情,做到育俗于民、順水推舟。因為民眾自己才知道什么是“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文化”,否則即便各種文化保護和發展的口號或政策遍布各地,也會因為與民眾日常生活脫節或誤會而產生“下有對策”、徒有表面的成效,延誤挽救傳統文化的良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