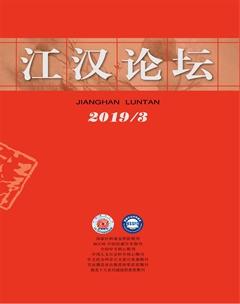工作壓力能促進知識型員工的創新行為嗎?
瞿艷平 李堅飛
摘要:企業員工創新行為是一個復雜且動態的過程,它包含了創新構想的產生、創新想法的推動和實施等過程;而知識型員工創新行為不僅受到諸如個體知識、智力、人格特征等個體因素的影響,還受到了諸如組織氛圍、組織支持等環境因素的影響,相比普通員工而言,知識型員工對影響要素的敏感性更高。從人與環境匹配的行為視角研究發現,員工自我認知與工作壓力之間存在顯著負向關系,工作壓力在自我認知系統的調節下與創新行為呈現顯著的負向關系;自我認知系統在工作壓力感與創新行為之間發揮了雙重動態效應,不僅對工作壓力感的形成有著顯著正向關系,還通過與工作壓力的交互效應,動態調適知識型員工的創新行為。作為企業實踐的參考,企業要在價值觀方面加強引導,在尊重知識型員工人格獨立與自主的同時,培養其自尊、自信、自愛、自強以及自豪感,促進知識型員工身心的健康發展。
關鍵詞:企業組織;知識型員工;自我認知;工作壓力;創新行為
基金項目:湖南省社會科學成果評審委員會重點項目“湖南地理標志農產品生產、消費與政策效應研究”(XSP18ZDI016)
中圖分類號:F272? ? 文獻標識碼:A? ? 文章編號:1003-854X(2019)03-0032-08
一、引言與文獻綜述
創新是現代企業生存與發展的必要條件,企業的創新能力是衡量一個企業發展潛力的重要指標,也是企業保持其競爭優勢和核心競爭力的前提條件。而在經濟全球化、一體化的今天,企業組織結構、工作任務體系以及商業競爭方式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企業對創新的需求日益高漲,僅僅依靠企業家和管理者的單源創新是難以適應企業發展的,企業對組織內部員工的創新能力也產生了越來越迫切的需求。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始意識到創新的基礎在于員工的創新,只有不斷發展和促進企業員工在當前工作情境下突破傳統技術、管理思維與方法的“枷鎖”,通過培育員工創新意識和創新行為去探索、尋找創新解決問題的方法與途徑,從而推動組織的創新變革,以此來保證組織的持續創新和基業長青。因此,對于知識型員工創新行為的研究正受到越來越多學者,尤其是社會學、心理學、管理學等社會科學領域甚至是自然科學領域學者的關注。
縱觀目前國內外文獻資料,影響員工創新行為的因素概括起來可以分為三大類:一是組織內外環境;二是員工個體因素;三是組織內外環境與員工個體因素的交互效應。
第一,員工個體因素。早期的學者更多將員工創新行為研究的重點放在員工個體因素上,認為員工個體的知識、潛能、智力、思維方式等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其創新的潛力與能力。Kirton提出了適應者—創新者理論,從適應者與創新者兩者表現出來的異質性闡述了員工個體對創新行為的影響①;Isaksen從系統化與直覺化兩種不同的員工個體解決問題方式對創新行為的結果進行了比較分析,認為員工個體直覺化的解決方式更容易促性創新行為的產生②;Scott和Bruce等人進一步豐富了Isaksen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不同的員工個體認知風格對其創新行為的產生有著顯著的影響③。隨著研究的深入,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將基于相對穩定的個體特質轉移到容易受外界影響的諸如個體的動機傾向、動態情緒以及創新偏好等心理屬性因素上來。Amabile提出了個體創新成分理論,就內部動機與外部動機對員工創新行為的影響進行了系統的探討④;Fredrickson 等學者也開始關注員工個體情緒、情感對創新行為的影響機制⑤。
第二,組織內外環境因素。管理學和社會學領域的學者認為除了個體自身的特質會影響其創新行為,工作本身也有著重要的影響。Bunce與West認為工作要求較高時會迫使員工改變現有的工作方式,為應對重的工作負擔而產生創新行為⑥。Janssen認為不能一味地提高工作要求,工作要求與創新行為兩者間的關系呈倒U型,中等強度的工作要求下創新水平最高⑦。Oldham和Cummings認為工作本身的設計會影響個體的創新表現,工作任務的挑戰性、復雜性及自主性會激發個體的創新行為⑧。隨著研究的繼續深入,學者們發現除了工作特征以外,個體所處的組織環境對創新行為同樣有著重要的影響。在組織層面,Damanpour等學者發現組織的戰略與組織的架構對創新行為有著一定的影響⑨。另一個比較重要的因素是組織創新氛圍。劉云和石金濤認為個體對工作環境的感知對激發其創造力有著重要的影響,形成良好的創新氛圍有助于創新行為的實現⑩。Oldham和Cummings認為在良好的組織創新氛圍中,個體常常能夠感受到來自組織對于創新的支持,這種情況下個體更容易表現出較多的創新行為{11}。類似的,Janssen認為這種對創新的支持還來自于直接的領導,且比組織支持的作用更加直接與顯著{12}。除了領導支持,學者們認為領導與下屬間的關系也會影響創新行為的發生。Scott和Bruce利用上下級領導—成員交換水平來預測創新行為,結果顯示了顯著的正向影響{13}。一般認為不同于交易型領導風格,變革型領導風格更能激發下屬的創新行為,而學者丁琳認為,交易型的領導風格同樣能夠刺激個體表現出創新行為。組織中常常存在以完成特定工作任務的團隊存在,團隊層次、團隊特征也會影響員工創新。
第三,員工個體與環境的交互作用。21世紀以后,越來越多的學者發現,影響員工創新行為的因素不能簡單地歸納為員工個體因素與工作特性單個因素上,提出了員工個體與組織內外環境交互作用引致了員工創新行為的產生,開始關注個體因素與環境因素的相互作用。Ford認為個體的創新行為并不是由個體特征決定的,也不是組織環境的單方面作用,而是通過個體與環境相互作用從而產生、推廣或實現新想法{14}。Choi利用價值觀匹配、能力匹配這種反映個體與環境交互的整體概念對學生的創造性展開調研,發現兩者可以很好地預測個體創新行為,且價值觀匹配的作用更為顯著{15}。
從目前國內外現有文獻來看,雖然學者們提出了大量的與員工創新行為有關聯的變量,但這些因素都過于籠統和模糊,存在幾個方面的不足:(1)在員工個體因素方面,更多文獻聚焦于員工自我效能感對創新行為的影響,將個體認知理解為個體在某種特定的情境中對自己能否做出某種特定行為的自信程度,或理解為完成特定任務的結果預期和效果預期,即班杜拉所提出的“自我效能感”,而將個體認知作為系統變量的研究相對較少,忽略了個體認知系統的復雜性和多維性。實際上,個體自我認知不僅包含了自信導向和預期導向的自我效能感,還包括自我概念、情緒、意識三種形式的結合,是自我評價、自我控制與自我體驗的有機融合。(2)在組織內外環境方面,現有文獻更多地集中在對員工工作績效的影響以及對工作壓力、創新行為的應對方式等方面的研究,而對工作過程中員工個體因素和組織內外環境給員工帶來的工作壓力與其創新行為的關系如何?是工作壓力抑制了創新行為?還是工作壓力驅動了員工創新行為,是否與員工的自我認知評價存在顯著關系?自我認知在工作壓力、創新行為之間扮演著何種關系等方面的研究相對較少。鑒于此,本文從行為交互的視角,將自我認知作為一個系統變量,研究其在工作壓力與企業知識型員工的創新行為之間的雙重效應,從而為國內這方面的研究作一些補充,也為企業在其知識型員工的壓力管理和激勵機制建設方面提出一些改進的措施和建議。
二、理論框架與假設提出
1. 自我認知系統與工作壓力的關系
關于自我認知系統與工作壓力的關系研究,目前學術界持有兩種觀點:一種是強調以工作特征為核心,認為影響工作壓力的因素主要是工作需求和工作控制,而與員工的個人因素沒有太多的關系。這種觀點的代表理論是Karasek提出的工作需求—控制模型及后來由此發展而來的工作需求—控制—支持模型{16}。另一種觀點強調以員工的個體特征為核心,認為只有在工作要求與員工的能力不相匹配時,員工才會產生工作壓力,其代表理論為French和Caplan于1972年提出來的個體—環境匹配理論,他們認為個人和環境相互作用是壓力產生的原因,而不是單獨的某一個因素或某一個個體特征{17};Leiter發現自我效能感的高低會影響個體應對工作壓力的方式{18}。
認知心理學理論認為,自我認知是個體對自我,包括自己思想、認識、情感、行為、個性特點以及人際關系等各個方面的認知、感受與調控。而實踐中,不論工作壓力來自于個人、組織還是環境,最終都表現為員工個體自我認知對其認知—感受—調控的結果。Robbin將壓力源分為三個層次:個人、組織和環境,他認為個體特征以及認知的差異決定著這三個壓力源能否最終造成現實的壓力感,比如個人認知、控制點、工作經驗等,并提出 “壓力源—壓力體驗—壓力結果”模型,闡述了與工作相關的壓力能導致工作不滿意這一心理癥狀{19}。
假設1:知識型員工自我認知系統與工作壓力之間存在顯著負相關關系,即隨著員工自我認知越強,環境對其工作狀態所帶來的影響水平越弱,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工作壓力越小。
2. 自我認知系統與員工創新行為的關系
早期學者Barron和Harrington的研究表明諸如“自信、廣泛的興趣、進攻性”等個人特質與其高創新性有關{20}。Feldhusen認為員工的創新行為包含三個方面:知識和技能、認知因素、人格因素,其假定兩個能力相同的個體,當面臨同一創新問題時,往往認為自己創新能力弱者,則行為動機較弱;認為自己創新能力強者,行為動機則較強,并將其根源歸結于個體對自我能力預期的不同引致的{21}。此后,顧遠來和彭紀生等國內學者就自我效能感對創新創造行為的影響機制進行了系列的研究{22}。在實踐中,個體創新行為的形成是一個高度復雜的過程,個體的認知因素不單是基于預期和自信的效能感那么簡單,而是一個融主我和賓我結合的系統概念,在外延上往往涵蓋了個體的自我概念評價、情緒調適以及意識融合等。認知心理學理論將自我認知歸納為自我評價、自我體驗和自我控制三個方面的內容和能力體系,由于知識、能力結構的差異,知識型員工的自我認知能力通常比一般型員工表現強烈,其在自我評價、自我情緒調適以及意識控制方面表現出相對有優勢,特別是其表現出來的創新欲望以及創新行為動機;同時自我認知能力愈強的員工,其對創新的行為動機愈強烈。
假設2:知識型員工自我認知系統與其創新行為之間呈現顯著正向相關關系,即員工自我認知越強,其創新行為付出的可能性越大。
3. 工作壓力與創新行為的關系
關于工作壓力與創新行為的關系,王雁飛等認為企業只有塑造良好的創新環境氛圍,才能夠有效地激發企業員工的創造動機與創新能力,除了組織環境的因素外,企業知識型員工的個人因素能影響其創新行為{23}。Cohen和Levinthal認為企業員工間個人情緒的變化會影響到周圍的其他員工,進而擴散開來,最終影響到員工的工作積極性和工作中的創新行為{24}。劉云和石金濤的研究表明,工作壓力這一組織環境中的負面因素是影響創新行為的重要影響因素{25}。從員工工作壓力源層面來看,Bunce與West認為工作要求較高時會迫使員工改變現有的工作方式,為應對重的工作負擔而產生創新行為{26}。Oldham和Cummings認為工作本身的設計會影響個體的創新表現,工作任務的挑戰性、復雜性及自主性會激發個體的創新行為{27}。正如中國俗語中所說“壓力越大,動力越大”,在中國的新生代身上存在一種較為典型的“證明自我”效應,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實現自己的新想法、新技術和新方法,以此贏得社會資本的青睞和網絡關系的構建。其實,創新本身就是一種緩解工作壓力的有效路徑,從主體負重的視角而言,行為主體有著強烈的參與創新的意愿與行為動機,這自然就形成了一個交互的內循環機制。
假設3:員工工作壓力與其創新行為之間存在邊界效應(倒U型結構關系)。在自我認知系統的調節下,處于兩個極端(極大、極小)的工作壓力,都會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或阻礙員工創新行為,而在一定工作壓力區間內,能對員工創新行為產生正向影響。
三、實證設計與分析
1. 變量測量
本文的問卷設計共包含四個部分,分別為自我認知量表、工作壓力現狀調查量表、創新行為量表及受訪者個人信息部分。在量表的設計和選取上,本文主要參考了相關理論及模型的測量方法,結合本文的實際調查對象和研究情況,在結合一線工作者、企業管理者及專家評審意見的基礎上,對量表的題項和描述進行部分修改,最終形成。
(1)員工的自我認知。自我認知是指個體對自己存在的察覺,包括對自己的行為和心理狀態的評價與認知。本文所采用的企業知識型員工自我認知調查量表主要參考了我國企業招聘時所廣泛使用的性格與職業匹配測試問卷及邁爾斯—布里格斯性格分類指標(MBTI測試問卷),分別從自我評價、自我體驗和自我控制三個維度加以測量,形成了12個題項的量表,該量表綜合考慮了企業知識型員工工作中的各種常見的表現,能夠真實地反映出知識型員工的自我認知能力。員工基于李克特五點計分法進行評價(“1”表示“非常不同意”;“2”表示“不同意”;“3”表示“不確定”;“4”表示“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最終用各測量指標的平均值作為知識型員工自我認知的測量值,數值越高,說明員工對自我的認知程度越高。該量表在本研究中的Cronbachs Alpha值為0.839,表明該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
(2)員工的工作壓力。工作壓力量表主要參考了羅賓斯提出的壓力理論模型及OSI工作壓力測量指標體系、曹靜用于研究員工工作壓力源的量表{28},量表共5個問題項。員工基于李克特五點計分法進行評價(“1”表示“非常不同意”;“2”表示“不同意”;“3”表示“不確定”;“4”表示“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最終用各測量指標的平均值作為知識型員工工作壓力感知的測量值,數值越高,說明員工對工作壓力的感知程度越高。該量表在本研究中的Cronbachs Alpha值為0.799,表明該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
(3)員工的創新行為。創新行為量表主要參考了Scott和Bruce{29}、Zhou和George{30}、顧遠東 {31} 等人的研究,將員工創新行為視為包含“創新想法的產生”、“創新構想的執行”的二維結構,將量表設計為包含創新想法的產生及創新構想的執行兩個維度、10個題項的量表。員工基于李克特五點計分法進行評價(“1”表示“非常不同意”;“2”表示“不同意”;“3”表示“不確定”;“4”表示“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最終用各測量指標的平均值作為知識型員工創新行為偏好的測量值,數值越高,說明員工對創新行為感知的程度越高。該量表在本研究中的Cronbachs Alpha值為0.817,表明該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
(4)控制變量。以往的研究表明,企業性質、工作角色和員工工作年限等都可能引起員工產生工作壓力和創新行為。為了排除其他相關變量對結果的影響,本文將員工的年齡、性別、學歷、家庭收入、婚姻狀況、工作年限和企業性質作為控制變量進行處理。
2. 數據的獲取與統計
為了檢驗本文所提出的理論假設,在抽樣時采用了廣泛抽樣以保證樣本的多樣性和科學性,同時也考慮了抽樣本身的便利性、可控性和真實性等因素,最終選取了來自某電機制造企業,含該企業電機銷售部及大電機車間、風電車間等電機制造車間及職能管理部門的員工。本文的數據收集主要采用的是問卷調查法,共發放問卷300份,問卷共回收268份,回收率89.33%,有效問卷240份。
在240份有效問卷中,以男性居多,共162人,占比67.5%,女性共78人,比例為32.5%。在年齡層次方面,以28—33歲人群所占比例最高,共100位,占比41.7%;18—23歲人群和28—33歲人群人數相差不大,分別為56人、50人。由此可以看出,在該企業基層員工平均年齡為25歲左右,呈年輕化態勢,其中男女比例為7:3,員工性別與年齡分布符合樣本分布。學歷方面,樣本數據中占比最高的為本科學歷,占總人數的58.3%(140人),其次則是大專學歷,占比35.8%(86人),高中及以下、碩士及以上所占比例較小,僅14人(5.9%)。大專及本科學歷累計占比達94.1%。在工作年限方面,樣本表現出較為均衡的分布,各個層次人數較為接近,平均工作年限為3—5年(62人,25.8%)。其中,一年以內的新員工人數為56人(23.3%),10年以上的老員工為28人(11.7%),可看出該企業知識型員工流動(離職、晉升)頻率不高,工作比較穩定。工作職務方面,受測樣本中基層員工與基層管理者(班組長)比例為8:2,人數分別為190人和50人,比例較為合理。
各變量的平均值以及相關系數匯總見表1。表1給出了主要變量的數據特征分析結果,包括統計描述、主要變量的相關系數以及標準差,從數據特征來看,變量之間具有較好的區分效度,適合作為樣本列入研究。
3. 假設驗證
本文采用SPSS18.0和LISREL8.7軟件對數據特征進行了層次回歸、多項式回歸和響應面分析方法來驗證前文所提出的假設。表2中列出了自我認知、工作壓力和員工創新行為之間關系的回歸分析結果。模型1考察的是員工創新行為與性別、年齡、學歷、工作年限以及所在單位類型等控制變量之間的關系,可以看出員工的年齡對其創新行為之間存在負向顯著關系(b=-0.113,p<0.05),即隨著員工的年齡越大,其創新行為往往越弱,這一實證結果在某種程度也印證了當前企業實踐中的一個普遍存在的現象與事實。
在模型2和模型3中,分別依據員工自我認知和工作壓力兩個變量與創新行為之間的關系進行了考察,發現員工自我認知與創新行為之間存在顯著的正向相關關系(b=0.337,p<0.001);而員工的工作壓力感知與創新行為之間沒有呈現出較為顯著的關聯(b=-0.006,p>0.05),這也驗證了前文所提出的假設1和部分驗證了假設3。模型4考察的是知識型員工自我認知與工作壓力兩個變量與創新行為之間的主效應關系,從模型結果可以看出,員工自我認知與創新行為之間存在顯著正向關系(b=0.357,p<0.01),而工作壓力感知與創新行為之間則存在顯著正向相關關系(b=0.063,p<0.05),這一結果從某種程度上證明了自我認知在工作壓力與創新行為之間起到了中介作用;在模型8中,我們獨立考察了自我認知和工作壓力的調節效應,將自我認知和工作壓力的乘積引入到模型中,由結果可以看出,自我認知對工作壓力與創新行為之間的調節效應是非常顯著的(b=-0.038,p<0.01),由此我們可以判定前文提出的假設2和假設3得以驗證。
四、研究結果的進一步討論
本文探討了知識型員工自我認知、工作壓力與創新行為三者之間的關系,前文中提出的假設均得到了驗證,進一步清晰了三者之間的關系。但在研究過程中我們發現了一些出乎意料的結論。例如,員工的自我認知不僅影響了員工的工作壓力感知,還在一定程度上調節了員工工作壓力與創新行為的關系,即自我認知在模型中扮演了雙重角色;自我認知和工作壓力在影響知識型員工創新行為的過程中是否存在邊界效應,即“過猶不及”效應現象。為了更加清晰地認識變量間的關系,以便為企業實踐提供更加具體的建議,下面做進一步的討論與分析。
1. 自我認知、工作壓力與創新行為兩兩變量間的U型關系
本文首先檢驗了工作壓力在自我認知的調節下與員工的創新行為之間的線性關系,發現在自我認知系統的傳導下工作壓力與創新行為呈現了正向的關系且顯著(b=0.063,p<0.05),說明在員工的自我認知調節下,工作壓力感知較強的員工所表現出來的創新行為強度要高于工作壓力感知較弱的員工;從另一個方面而言,可以認為自我認知較強的員工會呈現出一種通常所描述的“壓力就是動力”的行為動機,而對自我認知較弱的員工也許更多時候會出現“做好自己本分”的工作傾向。
許多學者提出“自我認知”與“工作壓力感知”存在強度邊界,即對自我能力(抗壓、處事等)評價過高往往會引致員工對創新行為的盲從,甚至出現盲干行為;而工作壓力過大也往往會導致員工的抗壓能力下降,進而引起不良的心理和行為反應。由于諸如此類邊界的存在,傳統理論認為自我認知、工作壓力與創新行為之間也許就不再表現為一種線性關系,而呈現出了U型曲線或者某種類型的二次函數。本文為了進一步驗證三者之間的復雜關系,引入“自我認知的平方”和“工作壓力的平方”兩個變量進入模型當中,進行討論與驗證。從模型5、模型6和模型7的結果可以看出,自我認知與創新行為之間、工作壓力感知與創新行為之間的U型關系的擬合結果要優于之前二者間線性關系的擬合結果。本文發現當工作壓力感知過高時,員工的創新行為要比工作壓力感知過低時的創新行為更強烈,且創新行為由低到高再由高到低。同樣自我認知過高時,員工的創新行為要比自我認知過低時的創新行為更強烈,且創新行為由低到高再由高到低。因此,在企業運作實踐中,要通過建立完善的員工職業生涯培訓體系,通過塑造學習型組織,科學引導員工的自我認知能力與水平,有效控制自我認知邊界,實現逐步地自我超越。同時也需要企業通過有效調適員工的自我認知水平,平衡企業工作壓力強度。保持員工的創新行為強度。
2. 自我認知系統對工作壓力、創新行為的雙重效應
(1)自我認知系統對工作壓力的交互效應。我們發現自我認識與工作壓力感知之間存在負相關關系,即員工的自我認知越高(包括自我檢查和自我控制能力),其所感受到的工作壓力越小。而從另外一個方面來看,工作壓力感知也在某種程度上調適著員工的自我認知。在企業中,我們發現自我認知能力強的員工,其抗壓能力往往表現尤為優異,自然面對同樣的工作壓力所表現出來的能力就越強,工作壓力感就會越弱;但同時在強工作壓力的環境下,員工也會不斷地調適自我認知,比如員工所表現的效能感往往會受到工作壓力感的強度呈現一種負向相關關系。因此,我們認為自我認知與工作壓力之間存在顯著的交互效應,員工個體通過不斷與環境進行交互,提升工作中的抗壓能力,也通過在工作壓力環境下不斷提升自我認知水平,實現兩者之間的能量交互。
(2)自我認知系統對創新行為的調節效應。自我認知不僅與工作壓力之間存在顯著交互效應,還在工作壓力與員工創新行為的作用機制中發揮著調節效應。較強的員工自我認知下,員工的工作壓力感對員工創新行為之間呈現出了負向的顯著關系,此階段的員工自我認知影響了員工所形成的工作壓力感,進而對員工創新行為產生影響。值得我們特別關注的是,前一階段的自我認知來自于員工對自我狀態的評估與認知,其對員工工作壓力感的形成產生了負向影響,而在這一階段中自我認知和工作壓力感兩者之間存在顯著交互效應。第二階段的自我認知是一個交互效應后的狀態修正值,其再次對工作壓力與創新行為之間的關系進行了調節。因此,我們認為,員工自我認知系統在其工作壓力感形成以及工作壓力感對員工創新行為的影響中扮演著雙重效應,且兩次所表現出來的狀態是一個后階狀態值。
可以推斷員工的自我認知系統、工作壓力和創新行為三者之間是一個動態演化系統,將員工自我認知系統作為供給變量,并以其作為序參量,以工作壓力作為控制參量,員工的創新行為可以呈現為一個二元非線性微分形式表達的演化模型。模型可以用式(1)表示。
SQ(X)=■=b1x+b2x2 (1)
式中:x為自我認知;t為時間;b1、b2為常量。在實際演化與發展階段中,受到個體學歷、態度、能力、性格等因素的影響,自我認知x是不可能無限制地增長,員工個體對工作壓力感總要使它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便穩定在某一水平,這就要求方程存在使x增加和減少的雙向作用機制。因此有下述表達式:
SQ(X)=■=b1x-b2x2 (b1>0,b2>0)(2)
為便于分析,令,b1=p,b2=p/k,可得:
SQ(X)=■=px(1-■x)(3)
式(3)為Logistic曲線方法,其中p為員工自我認知的修正速率;k表示在一定經濟社會環境和組織成本約束下工作壓力感的飽和量,即要素協調發展的閥值。
3. 自我認知系統中各子變量對工作壓力與創新行為的關系
人類的認知結構復雜而嚴密,是一個高度有組織的結構,這不僅取決于人類復雜的大腦結構,而且取決于復雜的外界環境和信息系統,因此人類的認知過程也是一個十分復雜的心理過程,它包括感覺、知覺、注意、記憶、語言、推理、判斷、決策。自我認知系統包括了基于認知的自我評價、基于情緒的自我體驗與基于意識的自我控制三個子變量,為了能更清晰地反映自我認知系統對工作壓力與員工創新行為的調節效應,分別將自我評價、自我體驗與自我控制三個系統子變量引入到自變量中,檢驗與工作壓力共同對創新行為的作用。具體回歸分析系數如表3所示。從回歸分析中可以看出,自我認知系統中的三個變量,除了自我體驗之
表3? 自我認知系統自變量、工作壓力與
創新行為的回歸系數
注:N=240;表中的Sn代表回歸分析中“工作壓力”變量的系數,Xn代表回歸分析中自我認知系統子變量的系數;*、 **、***表示在10%、5%、1%的水平下顯著。
外,自我評價、自我控制兩個子變量都調節著工作壓力與創新行為之間的關系,且呈現出了顯著的負向關系(b=-0.118,p<0.05;b=-0.101,p<0.01)。在中國情境下,創新行為更多來自于具有理性自我評價認知以及對自我意識有效調控能力的員工,對于知識型員工而言,由于知識結構和學習經驗的積累,其對自身性格、評價相對更偏向于客觀理性,在工作過程中,對“自我”意識的調控相對穩定,自然對其創新行為的激發和促進存在較強的正向影響。從另一個側面來看,知識型員工基于情緒的自我體驗,往往也會受到其知識理性的約束,受到一定程度的壓抑或隱藏,自然表現出來對創新行為的關系相對較弱。
五、簡要結論與建議
本文基于自我認知系統對工作壓力與知識型員工創新行為的調節效應分析,得出了三個方面的結論:(1)知識型員工自我認知系統與工作壓力之間存在顯著負向關系;(2)工作壓力在員工自我認知系統的調節下與創新行為呈現顯著的負向關系;(3)員工自我認知系統在工作壓力感與創新行為之間發揮了雙重動態效應,不僅對工作壓力感的形成有著顯著正向關系,還通過與工作壓力感的交互效應,動態地調適著工作壓力與創新行為之間的關系。同時,就自我認知系統、工作壓力以及員工創新行為三個變量兩兩之間存在倒U型關系進行了探討與驗證,研究結果顯示倒U型關系的擬合程度明顯優于線性擬合程度,也進一步驗證了自我認知、工作壓力“過猶不及”的假設。除此之外,本文在研究中還發現學歷、年齡對人—環境匹配下的創新行為存在顯著的影響,即不同學歷、不同年齡的員工個體在創新行為的選擇上存在顯著差異,尤其是對新生代、知識型員工的效應較為顯著,這也成為了下一步研究的側重點。
根據對企業員工自我認知、工作壓力對其創新行為的影響的實證分析,我們建議企業:(1)增強知識型員工自我體驗能力,提高知識型員工的滿意程度。企業要在價值觀方面加強引導,在尊重知識型員工人格獨立與自主的同時,培養其自尊、自信、自愛、自強以及自豪感,促進知識型員工身心的健康發展,幫助員工樹立積極向上的、正確的、與企業發展相適應的價值觀。(2)強化知識型員工的自我管理,增進其自我控制能力。通過幫助知識型員工樹立良好的職業道德、提升專業素養等能力,促進知識型員工對于理性思考問題、把握工作節奏、合理安排時間以及個人狀態的調整的能力。(3)在企業尤其是基層建設和諧的人際關系,創造一個良好的組織氛圍。(4)完善考核與激勵制度,并確保能夠得到正確的執行,物質手段與精神手段雙管齊下,努力達到“人盡其才”的目的,最終實現企業創新方面的長效發展機制。
注釋:
① M. Kirton, Adaptors and Innovators: A Description and Measure,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1976, 61(5), pp.622-629.
② S. G. Isaksen, K. J. Lauer & G. Ekvall, Situational Outlook Questionnaire: A Measure of the Climate for Creativity and Change, Psychological Reports, 1999, 85, pp.665-674.
③{13}{29} S. G. Scott, R. A. Bruce, Determinants of Innovative Behavior: A Path Model of Individual Innovation in the Workplac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4, 37(3), pp.580-607.
④ T. M. Amabile, Social Psychology of Creativity: A Componential Conceptualiz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3, 45, pp.357-376.
⑤ B. L. Fredrickson, C. Branigan, Positive Emotions Broaden the Scope of Attention and Thought-Action Repertoires, Cognition & Emotion, 2005, 19(3), pp.313-332.
⑥ D. Bunce, M. West, Changing Work Environment: Innovating Coping Responses to Occupation Stress, Work and Stress, 2003, 7(2), pp.189-212.
⑦{12} O. Janssen, Job Demands, Perceptions of Effort-reward Fairness and Innovative Work Behavior,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2000, 73(3), pp.287-302.
⑧{11} G. R. Oldham, A. Cummings, Employee Creativity: Personal and Contextual Factors at Work,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6, 39(3), pp.607-634.
⑨ F. Damanpour,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A Meta-analysis of Effects of Determinants and Moderator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6, 34(3), pp.555-590.
⑩{25} 劉云、石金濤:《組織創新氣氛與激勵偏好對員工創新行為的交互效應研究》,《管理世界》2009年第10期。
{14} C. M. Ford, A Theory of Individual Creative Action in Multiple Social Domains,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6, 21(4), pp.1112-1142.
{15} J. N. Choi, Person-Environment Fit and Creative Behavior: Differential Impacts of Supplies-Values and Demands-Abilities Versions of Fit, Human Relations, 2004, 57, pp.531-552.
{16} R. A. Karasek, Job Demands, Job Decision and Mental Strain: Implications for Job Redesign,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79, 24, pp.285-308.
{17} J. R. P. French & R. D. Caplan, Organizational Stress and Individual Strain, 1972, pp.30-67.
{18} M. P. Leiter, Coping Patterns as Predictors of Burnout: The Function of Control and Escapist Coping Patterns,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1991, 12(2), pp.123-144.
{19} F. C. Robbins,? C. A. Dequadros, Certification of the Eradication of Indigenous Transmission of Wild Poliovirus in the Americas, Journa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1997, 175(1), pp.281-285.
{20} F. Barron, D. M. Harrington Creativity, Intelligence, and Personality,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1981, 32(1), pp.439-476.
{21} J. F. Feldhusen, Creativity: A Knowledge Base, Metacognitive Skills, and Personality Factors, Journal of Creative Behavior, 1995, 29(4), pp.255-268.
{22}{31} 顧遠東、彭紀生:《組織創新氛圍對員工創新行為的影響:創新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南開管理評論》2010年第1期。
{23} 王雁飛、朱瑜:《組織社會化理論及其研究評價》,《外國經濟與管理》2006年第5期。
{24} W. M. Cohen, D. A. Levinthal, Absorptive Capacity: A New Perspective on Learning and Innovation,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0, 35(1), pp.128-152.
{26} D. Bunce & M. A. West, Self-Perceptions of Group Climate as Predictors of Individual Innovation at Work, Applied Psychology: An International Review, 1995,44(3), pp.199-215.
{27} O. Janssen & N. W. Van Yperen, Employees Goal Orientations, the Quality of Leader-member Exchange, and the Outcomes of Job Performance and Job Satisfac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4, 47(3), pp.368-384.
{28} 曹靜:《管理人員工作壓力源與工作倦怠的關系及其影響因素研究》,同濟大學2005年碩士學位論文。
{30} J. Zhou, J. M. George, When job Dissatisfaction Leads to Creativity: Encouraging Theexpression of Voice,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1, 44, pp.682-696.
作者簡介:瞿艷平,湖南商學院工商管理學院副教授,湖南長沙,410205;李堅飛,通訊作者,湖南商學院工商管理學院講師,湖南長沙,410205。
(責任編輯? 陳孝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