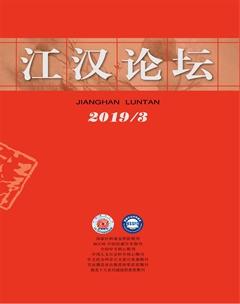文學獎與文學史秩序建構
記得在2017年紀念《收獲》雜志創刊60周年的慶典活動上,有幸躬逢慶典現場的我,曾經做過一個簡短的發言,旨在談論在當下時代到底怎樣才能有效辨別確認文學作品的優劣與否。至今猶記,我主要講了四個方面的意思。
第一,我從一種終極的意義上強調,一部文學作品真正的優劣與否,需要通過時間和歷史殘酷的淘洗與篩選。這一方面,學者劉小新關于何為“經典”的談論,可謂頗有啟示意義。劉小新指出:“‘經的本義是織物的縱線,后引申為經天緯地的宏大之義。劉勰《文心雕龍·宗經》曰:‘經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經或‘經典一般用來指稱宗教的主要典籍以及具有權威性的學術著作。文學經典是指那些具有極高的美學價值,并在漫長的歷史中經受考驗而獲得公認地位的偉大作品。在文學領域,這個詞的早期使用可以上溯到孔子刪詩,裁定《詩經》。文學史一般存在一個由‘必讀經典構成的體系,而經典體系通常被人們稱為社會歷史文化的寶藏,它們代表著‘某種不斷承傳的價值規范。”① 由對“經”字的考證出發,劉小新在得出何為經典的前提下,將視野回縮到文學領域,強調“文學經典是指那些具有極高的美學價值,并在漫長的歷史中經受考驗而獲得公認地位的偉大作品”。依照以上的界定,要想成為一部真正的文學經典,就必須同時滿足兩方面的要求:一方面是文學經典必須具備“極高的美學價值”,另一方面則是必須“在漫長的歷史中經受考驗而獲得公認地位”。如果說前一個要素與時間的因素無關,那么,后一個要素與時間因素之間,無疑存在著非常重要的內在關聯。所謂“在漫長的歷史中經受考驗”,很顯然意味著一部文學作品,只有在過去了數百年乃至上千年的時間淘洗篩選之后,依然存在于人們的關注視野中,依然能夠引起人們閱讀研究與討論的興趣,方才可以被看作是文學經典。既然是文學經典,那自然也就是思想藝術品質特別優秀的文學作品無疑。
第二,我特別強調了文學獎的重要性。一方面,我們無論如何都得承認,文學獎乃是一種典型不過的現代性產物。在有文學獎這一事物出現之前的漫長歷史時空中,文學早已經伴隨了人類很多很多年。與古往今來堪稱亙古的文學悠久存在史相比較,文學獎的歷史簡直顯得太短了。即以世界上目前最具影響力的文學獎諾貝爾文學獎為例,最早在1901年頒出第一屆獲獎作家,迄今也不過只有一百多年的歷史。但在另一方面,無論如何都不能不承認的一點是,在有了文學獎的現代社會里,那些能夠獲得各種文學獎項的作家作品總是要相對顯得優秀一些。這里的一個關鍵問題在于,大凡一個文學獎項都不會隨隨便便頒出,都會經過評委會認真而充分的討論與評選。也因此,在擁有了文學獎的現代社會里,衡量評價文學作品優劣與否的一個重要標準,就是要看它是否獲得過相應的各種文學獎項。
第三,是選刊的標準。在當下時代的文學場域里,各類建立在大量原創刊物基礎之上的文學類選刊的創辦,乃是一個相當引人注目的文學現象。《小說選刊》《小說月報》《中篇小說選刊》《長篇小說選刊》《中篇小說月報》《中華文學選刊》《長江文藝·好小說》《散文選刊》《詩選刊》,以及更具綜合性的《新華文摘》等,皆屬于業界有影響的文學類選刊。雖然很難絕對化,但相比較來說,在擁有了各類文學選刊之后,那些能夠脫穎而出被選刊所選載的文學作品,肯定比沒有被選載的作品優秀一些。
第四,恐怕多少帶有一點危言聳聽性質,我所要特別強調的,乃是《收獲》的標準。由文壇名宿巴金聯手靳以共同創辦于1957年的《收獲》,不僅是中國當代文學史上出現時間最早的一個大型文學期刊,而且也是辦刊水平最高的一個文學刊物。由于相當多的優秀文學作品尤其是小說作品都刊登在這個刊物上的緣故,在文學界,一向享有中國當代文學史的“半壁江山”或者中國當代文學史的“縮影”的美譽。在長達一個甲子的辦刊過程中,由于有一代又一代負責任的優秀編輯所付出的艱辛努力,《收獲》雜志得以保持了相對高的辦刊水準,可以說已經形成了獨有的思想藝術風貌。很多時候,只要嗅一嗅作家的文字,我們便不難嗅出其中的“收獲味”來。正因為《收獲》長期以來保持了如此難能可貴的一種思想藝術品質,所以,我個人的一種偏見就是,是否可以有作品發表在《收獲》雜志上,也同樣是衡量評價文學創作者成就高低的一個重要標準。當然,我清醒地意識到,在強調《收獲》雜志重要性的同時,我們也不能把這一標準簡單化和絕對化。而這,很顯然也就意味著,并不是所有沒能夠在《收獲》上發表過文學作品的作家,就都不是好作家。這一方面一個突出的例外,就是作家陳忠實。據我所知,陳忠實并沒有在《收獲》上發表過文學作品,但這卻不妨礙長篇小說《白鹿原》具備經典思想藝術品質。
在以上四點的基礎上,我在這里想要重點展開討論的,就是各類文學獎與文學史秩序的建構之間的內在關聯。應該注意到,除了為公眾所熟知的截至目前影響力最為廣泛的諾貝爾文學獎之外,世界范圍內其他各種文學獎項并不在少數。其中,英語世界的布克獎(現在已經擴展至非英語世界)、法語世界的龔古爾文學獎、西班牙的塞萬提斯文學獎、美國的普利徹文學獎、捷克的卡夫卡文學獎、以色列的耶路撒冷文學獎等,在文學界都有著相當大的影響力。退一步來看漢語世界,首先是由香港設立的以世界范圍內所有的華語寫作為評獎對象的紅樓夢文學獎,迄今已頒發七屆,其中,除臺灣與香港各有一位作家分別奪得頭籌之外,另外五屆的首獎獲得者,均為內地作家。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三地作家的基本寫作實力狀況。具體到國內,除了官方設立的茅盾文學獎與魯迅文學獎這樣最高的文學獎項之外,也還有帶有突出民間色彩的華語文學傳媒大獎以及郁達夫小說獎等獎項。
然而,在承認以上這些文學獎項的設立在很大程度上積極推動著文學事業的發展,參與著未來文學史秩序的建構的同時,我們也必須看到,由于這樣或者那樣的原因,一些文學獎項的評獎結果卻并不那么盡如人意,也存在著這樣或者那樣的遺憾與不足。即以公眾認可度最高的諾貝爾文學獎來說,反觀其百年的頒獎史,雖然說積極推動了諸如福克納、海明威、馬爾克斯、略薩等很多獲獎作家進入文學史殿堂的步伐,但也明顯留下了頗多遺憾。諸如喬伊斯、普魯斯特、卡爾維諾、博爾赫斯、納博科夫以及魯迅等文學史上一眾大家的未能獲獎,尤其是如托爾斯泰這樣的文學巨匠與這一獎項的失之交臂,就更是諾貝爾文學獎頒獎史的明顯缺陷。
諾獎之外,其他文學獎項的不足與遺憾也大都顯而易見。比如,我個人有幸參加了最近兩屆“茅盾文學獎”的評選。依照評獎規則,兩屆評獎共產生了十部獲獎作品。對于這兩屆茅盾文學獎的評選過程,我的總體評價是最不“離譜”。任何評獎,第一,不會絕對公正;第二,評獎結果不可能沒有爭議。這兩屆“茅獎”的評獎結果,同樣也有爭議,但同之前的幾屆相比,我認為這兩屆應該屬于最不“離譜”的評獎。最初的幾屆“茅獎”爭議較少,是因為當時的長篇小說創作尚未形成為一個引人注目的文學現象,長篇小說創作數量相對較少,并且由于改革開放剛剛開始,我們的作家、評論家思想解放程度還不夠,自由與民主的意識也較為薄弱,再加上對權威的盲從與膜拜,很少對評獎結果進行反思。近年來,我們的文化環境、文化語境都發生了變化,所以每屆結果出來爭議都很大。例如第三屆茅盾文學獎,共評出了五部作品,分別是《平凡的世界》(路遙),《少年天子》(凌力),《都市風流》(孫力、余小惠)、《第二個太陽》(劉白羽)和《穆斯林的葬禮》(霍達),爭議就比較大。除了路遙名至實歸,凌力與霍達差強人意之外,另外的兩部作品很顯然算不上出色,能夠獲獎的確顯得相當勉強。還有第四屆,有一部山東作家劉玉民的長篇——《騷動之秋》,但除了在列舉“茅獎”獲獎作品的時候會提到它之外,好多人根本就不記得曾經有過這么一部獲獎小說。像這樣的一種評獎,就是比較 “離譜”的。據我的了解,圈里的作家、評論家對第八、九屆茅盾文學獎總體的一個評價,就是認為它是最不“離譜”的兩屆評獎。到現在為止,十部長篇小說還沒有一部差到慘不忍睹的地步。大家都覺得這十部作品均達到了相當高的思想藝術水平,是應該獲獎的。丘吉爾曾經說:“資本主義制度不是最好的制度,但它是目前人類所能找到的最不壞的制度。”我們在這里簡單地套用一下丘吉爾的話,不能說這兩屆評獎就是最完美的評獎,但它從根本上說卻是最不“離譜”的。也因此,假如我們承認第八、九這兩屆相對靠譜的茅盾文學獎的評選,積極有效地參與到未來文學史秩序的建構過程的話,那么,諸如第三屆茅盾文學獎評選因其不盡如人意而遠離了理應公正客觀的文學史建構,也就是其題中應有之義。
在看到文學獎評選過程中所存在著的各種不足與弊端的同時,我們也必須注意到文學獎自身一種雙刃劍效果的存在。所謂雙刃劍效果,就是指文學獎這一現代性的產物,自打它生成出現以來,在強有力地以其刺激性助推著文學事業良性發展演進的同時,卻也有著不容輕易忽視的負面效應。具體來說,我們這里所強調的負面效應,就是指有不少作家會在文學獎的巨大光環面前陷入到某種不應有的迷失狀態之中。更進一步說,這些作家的迷失,乃具體表現為他們往往會把文學獎干脆就當作文學本身,把文學創作事業不無簡單粗暴地理解為為文學獎而寫作。毫無疑問,一旦作家只是一味地滿足于為文學獎而寫作,那么,其寫作功利性色彩的具備,就是無可置疑的一件事情。既然是功利性寫作,那么,很大程度上也就會嚴重背離文學本身的精神高尚性。從這個層面上說,我個人認為作家王蒙參照新飛冰箱的廣告語“新飛廣告做得好,不如新飛冰箱好”所提出的“文學獎固然好,但不如文學本身好”的說法,其真理性色彩的具備,也就自然不容輕易否認了。
作者簡介:王春林,山西大學文學院教授,山西太原,03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