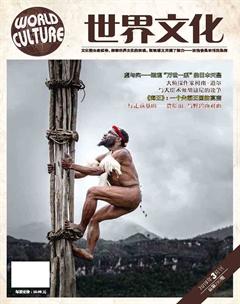虛與實
王秀娟

2019年1月2日,日本皇室依照慣例舉行了一年一度的新年朝賀。據報道,截至當日下午,共計超過15萬人涌入皇居,其中有很多人一邊揮動著手中的日本國旗,一邊高呼“萬歲”。朝賀活動的聲勢之所以如此浩大,是因為今年是85歲高齡的明仁天皇最后一次發表新年致辭。日本明仁天皇在1989年1月7日裕仁天皇去世之后登基,年號 “平成”,在位至今整整30年。早在2016年的一次視頻講話中明仁天皇就曾經流露出想要退位的意向,2017年6月日本國會表決通過了專門適用于明仁天皇的退位特別法案。直到2017年12月8日,才正式確定退位時間為2019年4月30日。屆時,明仁天皇的退位將成為近兩百年來日本天皇的首次“生前讓位”。
從神話傳說中的神武天皇到即將退位的明仁天皇,日本共計經歷了125代天皇。自上古時代世襲至今,日本的天皇制度堪稱世界上歷史最為長久的家族統治,“萬世一系”的說法不無道理。明治維新之后,1889年近代日本頒布的首部憲法《大日本帝國憲法》更是將“萬世一系”直接寫入法典。憲法第一章第一條就開宗明義“大日本帝國,由萬世一系之天皇統治(大日本帝國ハ萬世一系ノ天皇之ヲ統治ス)”。相反,中國自古就有“勝者為王敗者寇”、“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說法,歷史上懷揣過“帝王夢”的人不計其數,就連《西游記》里的孫悟空都戲言,“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唐代李氏王朝滅亡之后,朝代更迭更是一度如走馬燈一般頻繁。比鄰而居的島國日本自古以來在政治、經濟、文化等等各個方面都深受中國文化的影響,可天皇家族的“萬世一系”又是緣何能夠“固若金湯”呢?
神授王權——天皇的神格化
眾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日本裕仁天皇曾在1946年元旦發表過著名的《人間宣言》。宣言否定了天皇作為“現世神”的性質,宣告天皇是僅具有“人間性”的普通人。那一刻,裕仁天皇用一紙詔書打破的是一個被所有日本人世代信仰的千年神話,即所謂“天皇是神的后裔,具有神性”。由此倒推,日本天皇一直以來都不是人,而是以“神”的身份而存在。
關于天皇的“神格”由來,日本最早的神話古籍《古事記》中有詳細的記述。從天地開辟、國土生成、諸神誕生,到第1代神武天皇的降生,以及截至第33代推古天皇之前歷代天皇的家譜和主要經歷,《古事記》闡明了日本天皇家族的神性緣起和天皇制度的確立鞏固。其中,日本皇室將天照大神,即日本神話傳說中的太陽神奉為自己的祖先。母神伊邪那美因生火神去世之后,父神伊邪那岐赴黃泉國追尋自己的妻子。尋妻無果的伊邪那岐倉皇逃離黃泉國,在滌除污穢洗刷左眼時化生出了天照大神。伊邪那岐委派作為三貴子之一的天照大神司理天界高天原。后來,天照大神派自己的天孫瓊瓊杵尊去管理人界葦原中國,即日本本土。第1代神武天皇正是瓊瓊杵尊的曾孫。
當然,成書于712年的《古事記》本身是由太安萬侶編纂,天武天皇親自審定。其編寫目的就是為了宣揚皇統的權威性,考察歷史不足為據。天武天皇在奈良時代末期,經過“壬申之亂”奪取政權之后,成為日本歷史上第40代天皇。登上皇位之后的天武天皇強烈地意識到只有高度的中央集權才能夠使國家堅如磐石,而強調皇權統治的正統性、唯一性就是其中一項重要舉措。《古事記》和另一部古書《日本書紀》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應運而生的。兩本書雖然在編寫形式上存在差異,但內容上多有重合。

事實上,從傳說中的初代神武天皇到第14代仲哀天皇,并未得到相關的歷史考證。不僅如此,關于這些天皇的相關記述還存在很多不合常理的疑點,被學界普遍認為有意編造的成分居多。歷史上真正能夠找到存在依據的,最早只能追溯到第15代應神天皇。而且,“天皇”的稱號也并非從開始就一直沿用至今。據史書記載,日本的“大和政權”是在3世紀中期,以日本本州中部地區為中心興起的一支由地方豪族構成的聯合政權。發展到5世紀初,逐漸開始崛起,在征服各部之后,建立起日本列島上第一個統一的國家政權。大和政權最初的首領并非稱呼“天皇”,而是“大王”。當時的“大王”雖是世襲君主,但是并沒有絕對的實權,政權實質掌握在勢力最大的中央豪族手中。直到7世紀初推古天皇時代,受中國儒家思想的影響,才真正改“大王”為“天皇”。第33代推古天皇成為日本最早使用“天皇”稱號的日本君主,同時,她也是日本歷史上第一位女天皇。推古天皇時代頒布了“冠位十二階”和“憲法十七條”以打破之前依靠門第壟斷朝政的氏族制度,從而強調了天皇統治的中心地位。有關日本天皇最早的文字記錄則是第41代持統天皇在689年頒布的《飛鳥凈御原令》。從593年推古天皇即位至1192年鐮倉幕府建立,是日本古代天皇制確立、發展的重要時期。此過程中,“天皇作為天照大神的后裔”成為日本君權神授的依據,為天皇制度的延續起到了保駕護航的作用。
當然,“君權神授”并非日本獨有的政治理論。在古代很多國家的君主為了鞏固權力都會宣稱自己是受天命派遣,來管治世人的。類似的例子俯拾即是,中國周朝武王伐紂時就號稱“受命于天”,之后自稱“周天子”,古埃及的法老同樣稱自己是“太陽的兒子”,古巴比倫漢謨拉比王則自詡“月神的后裔”等等。同是神授王權,天皇制度在日本能夠延續至今未遭遇根本性的顛覆,自然還有很多其他因素的作用。
萬世一系——天皇統治的虛與實
“二戰”之后,戰敗的日本在美國的主持下建立起新的議會民主制度。過程中,依照日方的強烈要求才將天皇作為象征性的國家元首保留下來。1947年頒布施行的《日本國憲法》(又稱“和平憲法”)規定由國民直接選舉產生的國會是國家權力的最高機關,天皇不具備任何獨立的政治權力,有關國事的一切行為,都必須得到內閣的建議和承認,由內閣對其負責任。由此,天皇的權力從明治維新之后的鼎盛轉而再次徹底架空。有人不理解,為何是架空而不是廢除。仔細考察一下日本歷史,就會發現這種“非常態”似乎才是日本歷史的“常態”。
早在天皇制度確立之初,593年推古天皇即位之后,立侄子廄戶皇子為皇太子(即圣德太子),進行攝政,通過“冠位十二階”和“憲法十七條”的頒布鞏固中央集權。645年中大兄皇子在鏟除蘇我氏之后,扶植孝德天皇上位,同樣以皇太子的身份攝政,并模仿中國制定了最初的年號“大化”,推行“大化改新”。大化改新之后,日本逐步確立起律令制國家,經過奈良和平安初期,天皇的權力被推向了鼎盛時期。有趣的是即使在統治權威集中在皇族的時代,“攝政”現象也是屢見不鮮。 “統而不治、治而不統”的政治形式自始就成為各方勢力博弈之后的一種較為穩妥的統治方式。這種“統”、“治”分離的政治生態既為日后天皇權力的喪失埋下伏筆,同時也為天皇制度的延續化解了根本性的危機。
平安時代中期,藤原家族得到嵯峨天皇的信賴,并利用與皇室聯姻的機會,鞏固政治地位,日本開始進入“攝關政治”的階段。858年藤原良房以清和天皇外祖父兼臣子的身份首次攝政,成為日本歷史上皇族以外的人第一次實質性的攝政。從此,天皇家族“治”理國家的大權開始旁落。進入11世紀,藤原道長先后將4個女兒都嫁入皇室成為皇后和皇太子妃,實現了他在朝廷專權30年。其子藤原子賴又作為后一條、后朱雀、后冷泉三位天皇的外祖父攝政關白長達50年。就這樣,“攝政關白”連續把持日本“治”的權力近200年。
直到12世紀初,藤原賴通的女兒沒有誕下皇子,繼承皇位的是與攝關家族沒有血緣關系的后三條天皇。后三條天皇想要打破藤原家族的專權,開始啟用有學識之人。之后的白河天皇也是不甘心看到大權旁落外戚,有意奪回政權,于是開始通過“院政”的形式進行一系列抗爭。所謂“院政”,就是天皇成年之后為擺脫攝政關白的控制,有意將皇位讓于他人,退位為太上皇。作為太上皇在居所設立“院廳”,任命官吏,總攬國政。由于“院廳”擁有攝政、關白之上的權威,受到被藤原家族壓制的部分貴族的擁護。“院廳”主要依靠地方武士集團來實現與藤原家族的對抗。但后期,隨著源、平兩大武士集團的相互爭霸,“院廳”就像墻頭草一般不斷改變依附的對象。天皇家族開始出現內部分裂,最終形成“大覺寺統”和“持明院統”兩統迭立的局面。
1193年鐮倉幕府建立以來,天皇逐漸淪為傀儡的角色。尤其是經過后醍醐天皇的“建武中興”,天皇家族非但沒有能夠恢復皇統,反而淪落成一文不名的沒落貴族,只能靠武士領主的施舍度日。之后的室町幕府和德川幕府雖然對天皇家族采取了在經濟上的扶持政策,但均出于“挾天子以令天下”的目的。表面上公家與武家共治,但實質上是武家獨大。幕府時期,日本的實際統治者是武士階層的最高代表“征夷大將軍”,虛君政治長達682年。

19世紀中葉,歐美列強企圖敲開日本的國門,實行鎖國政策的幕府政治開始動搖。天皇成為倒幕派渡過危機的一根救命草,1867年12月日本發動政變,推行“王政復古”。德川幕府最后一位征夷大將軍德川慶喜被迫宣布“奉還大政”,明治天皇重新掌權。明治維新之后,天皇權力達到歷史巔峰,日本也因此走上一條窮兵黷武之路。裕仁天皇在位期間更是發動了罪惡的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給亞洲各國人民帶來沉痛的災難。
“二戰”之后,日本在以美國為首的盟軍總部的外力作用下進行了民主改革,最終并沒有廢除天皇制度,而是建立起現代天皇制度。如今,天皇僅作為日本國家和國民整體的象征而存在,充當名義上的國家元首,其履行的職責也大多屬于形式上、禮節性的。
歷史證明,日本天皇在國民心目中長期形成的神圣地位,以及自古以來 “統”、“治”分離的政治形式,維護了天皇家族 “萬世一系”的“統”帥權威。盡管曾經作為昔日君主專制的封建集權象征、日本窮兵黷武的軍國主義根源,但是,不可否認天皇已然成為日本民族精神的象征、倫理思想的因子。天皇制度能夠保留至今,皆因扎根日本社會的天皇信仰無可撼動。
天皇信仰——根植日本社會
2009年10月30日至11月1日, NHK電視臺輿論調查部門與日本報道局社會部曾經進行過“即位20年,有關皇室的民意調查”。調查對象為3313名20歲以上的日本人,其中收到2043人,即62%有效回答。調查結果表明,其中70%的國民對皇室持關注態度, 85%的被受訪者認為現任天皇履行了憲法規定的象征意義。關于廢止天皇制度的問題,85%的受訪者認為應維持現狀,繼續將天皇作為國家的象征。僅有6%的人主張廢止天皇制度,8%的人認為應賦予天皇政治權力。事實證明,直至今日皇室家族和天皇制度的發展仍舊是日本大多數國民關注的焦點之一,人們對皇族普遍抱有一種親切之感,甚至在國際友好和與國民接觸等方面充滿各種期待。
美國人類文化學家魯思·本尼迪克特的經典著作《菊與刀》借用“菊”和“刀”兩種不同性格的意象來象征日本人和日本文化的矛盾性格和雙重性。其中,“菊”正是日本皇室的家徽。本尼迪克特在書中明確指出日本不可能廢棄天皇制度。“沒有天皇的日本根本無法想象”,“日本天皇作為日本國民的象征,是日本人宗教生活的中心”,“即便是戰敗,十個日本人里依舊還是會有十個人繼續崇拜天皇”。因此,不論是作為神道教的“現世神”,還是放棄“神格”,走下神壇的國家象征,日本天皇始終是一個與普通人不同維度的存在。天皇信仰已經深深地扎根于日本的國民意識當中,滲透在國民生活的方方面面。

日本國歌《君之代》,“吾皇盛世兮,千秋萬代;砂礫成巖兮,遍生青苔”,盡管在1999年才得到法律意義上的認可,但實際上作為國歌沿用已經有上百年的歷史。歌詞唱的就是天皇家族“萬世一系”的長治久安。此外,歌舞伎、能、狂言、劍道、茶道等等很多領域至今仍然依照“家元制度”的形式來傳承。這種制度強調的是家族之間的主從關系、父權家長之下的支配關系,而這些內容從根本上來說都是源于日本人對天皇的信仰、對權威的崇拜。還有日本人的集團意識和勤勉精神無一不與天皇信仰存在密切聯系。作為一個資源匱乏的島國,日本需要一個精神領袖來激發和維系國民的向心力。久而久之,天皇作為國家象征逐漸成為全體國民的一種精神依托和心理習慣,從而也就變成了一種集體無意識。
皇室的危機與化解
天皇制度的“萬世一系”并不代表日本歷史上沒有圍繞皇位爭奪的明爭暗斗,也不意味著天皇家族人丁興旺足以保證一脈相承上千年。相反,這兩方面的危機一直困擾著日本皇室家族。
尤其在鐮倉幕府之前,權力爭奪經常伴有血雨腥風的紛爭。例如,上文提及過的第33代推古天皇是在朝廷大臣蘇我馬子消滅了物部守屋,又暗殺了對其不滿的崇峻天皇之后,被推舉即位的。第40代天武天皇是與大友皇子叔侄之間對峙之后,經過“壬申之亂”擊敗對方登上皇位的。歷史上的女天皇,大多也是為了化解危機而采取的權宜之計。翻閱日本歷史,會發現但凡是女天皇即位之前必定伴有皇權爭奪。為了調停紛爭、避免流血沖突,往往暫時推舉女天皇上位,先由他人攝政,待到皇太子長大成人或是有其他合適的人選繼位時,再主動讓位。日本歷史上先后共計有八位女天皇,她們是推古天皇、皇極天皇、持統天皇、元明天皇、元正天皇、孝謙天皇、明正天皇、后櫻町天皇。因此,這些女天皇通常也被稱為“過渡天皇”。只是,不論天皇是否擁有實權,皇權繼承權問題都與普通人無關。普通人沒有人能夠取代得了天皇,也不會有人想到要取代天皇。另外,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日本人對血統的信仰。日籍華裔作家陳舜臣在他的作品《日本人與中國人》中就明確地指出,“日本文明的源頭就在于‘對血統的信仰”,而血統信仰的頂峰便是“天皇家族”。
日本天皇家族為保持血脈的純正,在歷史上很長一段時間里一直主張在皇族內部進行通婚。第一代推古天皇就嫁給了同父異母的哥哥敏達天皇,后來的皇極天皇也是先后嫁給叔伯高向王和舒明天皇。裕仁天皇和香淳皇后也是皇室通婚的典型。通婚制度盡管保證了日本皇室的血統純正,但也給他們帶來了很大的問題。歷史上的第25代武烈天皇無后而終,在他去世之后,皇室近親里已經找不到能夠繼承皇位的合適人選。第26代繼體天皇是當時的朝臣費盡周折,在遙遠的越前國尋找到的應神天皇的5世孫。一方面是由于爭權奪位的相互殺戮,另一個方面就是因為近親通婚造成的生育力低下。
歷史的車輪總是周而復始。依照現行的《皇室典范》,皇位應由皇室家族的男性后裔繼承。然而就在十幾年前,日本皇室曾面臨長達41年里沒有男嬰誕生的殘酷現實。日本天皇的皇位一度面臨后繼無人的窘境。尤其是2001年12月1日皇太子德仁與太子妃雅子的長女愛子出生之后,皇位繼承問題成為各界熱議的焦點。為避免皇脈斷絕,當時的政府內閣甚至已經開始醞釀修改《皇室典范》,以允許女性皇室成員繼承皇位。直到2006年9月6日,明仁天皇的次子秋筱宮親王的王妃紀子通過剖腹產誕下一名男嬰,現代版“ 女天皇”之爭才告一段落。小王子悠仁親王的出生,拯救了深陷窘境的皇室家族,也為日本國民打了一針強心劑。當時,日本全國上下一片歡騰,東京的主要報紙均發行號外,在街頭鬧市免費發放。

事實證明,天皇制度已經深深地扎根于日本的國民意識之中,并非當初的一紙詔書就能夠揮之而去的。2019年明仁天皇的退位對于日本和日本人而言都將意味著一個時代的結束,新的時代即將開啟。199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時,明仁天皇和美智子皇后曾對中國進行過一次正式友好訪問。那也是中日兩國交流史上日本天皇首次、也是迄今為止唯一的一次訪問中國。當時,明仁天皇專門前往西安碑林博物館,在65萬多個漢字當中查找自己的年號“平成”的出處,最后終于找到“地平天成”4個大字。日本歷史上,有很多位天皇的年號都取自中國的古書典籍,例如,“元祿”出自《文選》中的“建立元勛,以歷顯祿,福之上也”。“明治”出自《易經·說卦傳》中的“圣人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治。”“大正”出自《易經·臨卦》中的“大亨以正,天之道也。”等等。今年5月1日58歲的皇太子德仁將繼承皇位,屆時會選定什么樣的年號,作為新一代天皇在中日兩國交流史上又會書寫怎樣的歷史,不禁讓人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