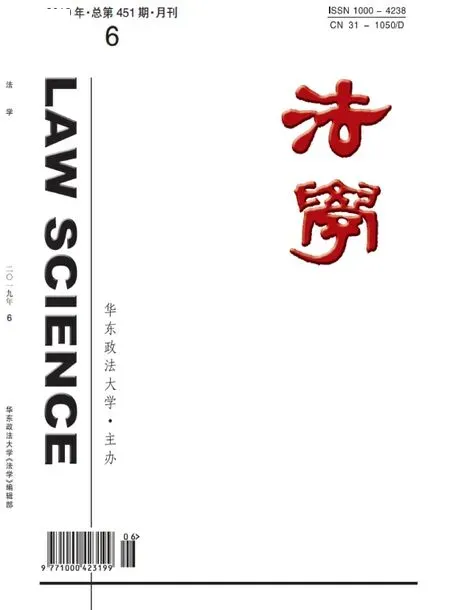夫妻債務規范的層次互動體系
——以連帶債務方案為中心
●劉征峰
夫妻債務問題不僅是當下的學術熱點,更是社會大眾和立法者所關注的焦點,這尤其反映在對《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法釋〔2003〕19號,以下簡稱《婚姻法解釋(二)》)第24條的爭論上。最高人民法院在2017年2月對該條司法解釋的補充規定(法釋〔2017〕6號)并沒有從根本上平息論爭。僅在隨后的“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期間,就有45位全國人大代表聯名提出5件建議,要求對該條司法解釋進行審查”。〔1〕《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法制工作委員會關于十二屆全國人大以來暨2017年備案審查工作情況的報告》。有鑒于此,2018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發布了《關于審理涉及夫妻債務糾紛案件適用法律有關問題的解釋》(法釋〔2018〕2號,以下簡稱《夫妻債務司法解釋》),對《婚姻法解釋(二)》第24條所確立的夫妻共同債務認定標準進行了根本性調整。
由于《婚姻法解釋(二)》第24條所帶來的聚焦效應,目前我國學界對夫妻債務規范的檢討與反思多集中在債務性質的認定方面,立法建議也往往局限于此。〔2〕代表性論文參見冉克平:《夫妻團體債務的認定及清償》,《中國法學》2017年第5期;葉名怡:《〈婚姻法解釋(二)〉第24條廢除論——基于相關統計數據的實證分析》,《法學》2017年第6期;孫若軍:《論夫妻共同債務“時間”推定規則》,《法學家》2017年第1期;但淑華:《對〈婚姻法解釋(二)〉第二十四條推定夫妻共同債務規則之反思》,《婦女研究論叢》2016年第6期;夏吟蘭:《我國夫妻共同債務推定規則之檢討》,《西南政法大學學報》2011年第1期。當然,亦有部分學者同時討論了夫妻債務的性質認定和清償規則。〔3〕代表性論文參見曲超彥:《夫妻共同債務清償規則探析》,《法學論壇》2016年第11期;張馳:《我國夫妻共同債務的界定與清償論》,《政治與法律》2012年第6期。然而,這些偶見的討論仍然欠缺一種體系視角。這種體系視角不應局限于債務規范內部,而是應當擴展至整個夫妻法定財產制。在某些情形下,討論還應擴展至整個民法。那種將夫妻財產制的效力局限于夫妻內部的建議〔4〕持這種觀點的代表性論文參見A.Verbeke,Naar een billijk relatie-vermogensrecht,TPR 2001,391-393;賀劍:《論婚姻法回歸民法的基本思路:以法定夫妻財產制為重點》,《中外法學》2014年第6期;劉征峰:《論請求權體系在法定夫妻財產制中的優越地位》,《月旦民商法雜志》總第50期(2015年12月)。固然有其學理上的合理性,但這需要大大突破我國現行夫妻法定財產制的基本框架,轉向德國法上的增益共同制或者瑞典法和丹麥法上的延遲共同制,勢必造成立法繼受傳統的斷層,會產生巨大的社會成本。此外,從此次我國民法典編纂所采“既不推倒重來,也不照單全收”的原則來看,在夫妻法定財產制上另辟蹊徑的可能性并不大。有鑒于此,本文對夫妻債務規范的探討在婚后所得共同制的基本框架下展開。這一基本框架指向婚姻對夫妻財產權屬狀態的影響。在將夫妻雙方財產權屬狀態的變化作為婚姻效力的前提下,本文嘗試從積極財產、消極財產和責任財產的牽連性視角梳理夫妻債務規范體系的脈絡層次,并以夫妻連帶債務方案為中心,探討規范層次互動原理的具體應用。
一、夫妻債務規范體系中“視同無婚姻原則”及其實施進路
(一)夫妻債務規范“中立性”視角下的“視同無婚姻原則”
在我國法定的婚后所得共同制下,法律必須同時處理積極財產和消極財產(即債務)的問題。由于婚后所得共同制采納了一種物權的方案,造成了夫妻內部關系與外部關系的牽連。〔5〕同上注,賀劍文。婚后所得共同制面臨的最大難題是如何平衡外部第三人與夫妻雙方內部的利益。這一難題主要體現在夫妻債務規范的設計上。首先,在價值判斷層面,優先保護配偶利益或者外部債權人利益實際上都并不是一種妥當的選擇。雖然價值論層面的利益平衡設想并不必然對應某種外在體系,但至少從合目的性視角為外在體系確立了基本的指向。如果說“利益平衡設想”過于抽象,只是一種方法而不具有實益,那么不妨將這一抽象的判斷外顯為一項相對具體的原則,即夫妻債務規范的中立性。其次,從比較法來看,幾乎沒有實行婚后所得共同制的國家將這一原則作為一項實定法原則予以明確規定,但其反映了這些國家在夫妻債務規范立法上的共性。夫妻債務規范的中立性意味著“債務人的婚姻狀態既不應當給債權人帶來好處,也不應當給其帶來不利”。〔6〕同前注〔4〕,A.Verbeke文,第392頁。“婚后所得共同制在保護婚姻關系中經濟地位相對較弱一方利益的同時,不應降低對債權人的保護,債權人的地位不應弱于債務人無婚狀態。”〔7〕繆宇:《美國夫妻共同債務制度研究——以美國實行夫妻共同財產制州為中心》,《法學家》2018年第2期。質言之,即使債務人已經結婚,在處理外部債務關系時應以債務人若無婚姻時的利益保護為基準。
如果我們否認婚姻在財產方面的外部效力,將“協力共享”的理念具體化為請求權,那么這一原則的實現毫無難度。但如果我們承認婚姻會影響夫妻雙方的財產權屬狀態,對這一原則的堅持則會使得相應的規范體系變得尤為復雜。一方面,債權人和債務人在財產法律關系中以抽象人面貌出現,債務人是否已婚通常并不構成債權人需要考察的一項因素。另一方面,婚姻在積極財產層面所產生的共有及準共有效力影響了個人的支付能力,并最終影響了債權的實現。這種影響對債權人而言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負面的。于前者,本無責任財產的債務人通過婚姻的這一效力提升了支付能力。于后者,對夫妻共同財產貢獻較多的債務人的支付能力因婚姻的這一效力被削弱。在一般情況下,“債務人應以其財產全部負其責任,財產形成債權的一般擔保”。〔8〕王澤鑒:《債法原理》第1冊,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31頁。在責任財產不當減少并危及債權人債權的實現時,債權人可通過行使代位權或者撤銷權實現對債權的保全。然而,即使婚姻削弱了債務人的支付能力從而導致債權不能實現,債權人也不能行使撤銷權。由此,法律必須在債法所規定的債務清償一般性規范之外另行確立債務清償特別規范。在此,法律追求的只是一種“視同無婚姻”的效果,并不能從規則上直接將其擬制為無婚姻。法律不可能在既已承認積極財產外部性的同時,又否定消極財產的外部性。從這一角度來看,“視同無婚姻原則”是結果意義上的。當然,由于對這一原則的貫徹存在巨大難度,即使是這種結果意義層面的利益平衡,也只能是一種相似,而非等同。法律只能通過合理的規范體系使債權人和債務人的利益平衡達到與債務人婚姻不存在時相似的狀態。
(二)單純夫妻債務性質劃分方案的弊端
就積極財產而言,法律重點關注的問題是其性質的劃分。出于一種邏輯對稱的直覺,我國法律意圖通過消極財產(債務)的性質劃分貫徹上述原則,經歷了從擴張夫妻共同債務到限縮夫妻共同債務的轉變過程。
1.擴張夫妻共同債務的進路
擴張夫妻共同債務的進路意圖通過進一步放寬夫妻共同債務的認定標準強化對債權人的保護。《婚姻法解釋(二)》第24條采納了這一進路,即為了保護債權人的利益,將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形成的債務原則上推定為夫妻共同債務,除非債權人與債務人明確將其界定為個人債務或者債權人知道夫妻雙方實行的是分別財產制。相關司法實踐表明,該條款但書所列情形極少出現,即使存在,也往往難以證明。與此相配套的是,一旦被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則夫妻雙方應當以包括其個人財產和共同財產在內的所有財產承擔連帶清償責任。這一進路偏離了《婚姻法》第41條所預設的“原為夫妻共同生活”的前提,將夫妻共同債務的認定標準簡化為“婚姻關系存續期間”。這被學者形象地稱為“時間推定規則”〔9〕同前注〔2〕,孫若軍文。或“利益分享推定制”〔10〕參見官玉琴:《夫妻共同債務認定的法理基礎及離婚婦女財產權益保護》,《中華女子學院學報》 2016年第6期;同前注〔2〕,夏吟蘭文。。通過擴張夫妻共同債務并輔之以無限連帶清償責任的方式填補婚后所得共同制的上述漏洞又產生了新的問題。“對于債權人來講,連帶債務是最為有保障的多數人債務形式。”〔11〕王洪亮:《債法總論》,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493頁。但對于非直接負債方配偶而言,即使債務與其利益無關,也可能就整個債務承擔清償責任。這一進路對債權人極為明顯的優待完全背離了前述中立性視角下的“視同無婚姻原則”。
當然,我國法在擴張夫妻共同債務的同時還配套了債務清償順序規范和內部追償規范,然而這兩項配套都無助于從根本上消除擴張夫妻共同債務的進路所帶來的過度優待債權人的弊端。就債務清償順序而言,根據《婚姻法》第41條的規定,夫妻共同債務應先以共同財產清償,再以個人財產清償。這對債權人的權利形成了一定程度的限制。〔12〕對這一限制合理性的討論,參見尚志東、張西、王文信:《婚姻法不宜設定以夫妻共同財產清償共同債務》,《人民司法(應用)》2009年第1期。在普通的連帶責任中并不存在這種清償順序的限制,債權人可以選擇最易于實現債權的財產獲得清償。〔13〕參見我國《民法通則》第87條和《民法總則》第187條。這種清償順序的限制并不是補充責任,因為共同財產本身沒有人格。雖然從表面來看,“共同體既是債權人,也是債務人”,〔14〕See Jo Carrillo,Understanding California Community Property Law,LexisNexis,2015,p.227.但“夫妻共同體沒有法律人格是共同財產制最重要的原則,共同體不擁有財產也不能負擔債務”。〔15〕See Lee Hargrave,Community Property Considerations in Law Suits by and against Spouses,57 La.L.Rev.439 (1996).從責任主體的角度來看,以夫妻雙方共同財產清償實際上是夫妻雙方作為共有人或者準共有人的清償。事實上,這種清償順序的限制并不能將某些財產隔離在責任財產之外,不會對債權人實現其債權產生實質影響,其作用僅局限于減少內部追償的繁瑣,對于過度優待債權人所致利益失衡的修正意義微弱。
就內部追償而言,其乃連帶債務對內效力之重要方面。追償有賴于債務人內部分擔比例之確定。〔16〕參見林誠二:《民法債編總論:體系化解說》,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481頁。與一般連帶債務不同的是,此種追償以身份關系的消滅為前置要件。只有在夫妻身份關系消滅時雙方的債務承擔比例才能確定。《婚姻法解釋(二)》第25條采納了這種意見,將離婚協議、裁定書、調解書、判決書所確定的債務承擔比例作為最后追償的依據。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審理離婚案件處理財產分割問題的若干具體意見》(法發〔1993〕32號,以下簡稱《離婚財產分割若干意見》)第17條關于“夫妻雙方約定由個人負擔的債務應由一方以個人財產清償”的規定主要是在追償層面被適用,除非第三人明確知道該約定。在司法實踐中,由于一方配偶常常已無償債能力,另外一方配偶在償債之后所取得的追償權往往難以實現,內部追償規范的實質修正意義同樣微弱。
2.限縮夫妻共同債務的進路
由于以《婚姻法解釋(二)》第24條為核心的擴張夫妻共同債務的進路存在上述嚴重弊端,導致司法實踐中損害非直接負債方配偶利益的現象層出不窮,最高人民法院在2018年最終放棄了繼續修訂“時間推定規則”的想法,而是另辟蹊徑地發布了《夫妻債務司法解釋》。該解釋大幅限縮了夫妻共同債務,將夫妻共同債務局限于雙方共同簽字及事后追認所形成的債務、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負債務以及債權人能夠證明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者夫妻共同生產經營或者基于雙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其他債務。這一限縮方案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前述第一種方案所帶來的過度優待債權人的問題,但可能會產生其他問題。且不論債權人證明非日常生活需要之外債務用途之難度,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負責人在答記者問中對“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產經營”的解釋明顯采納了一種限縮立場,〔17〕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負責人認為,夫妻共同生活所形成的債務系由夫妻雙方共同消費、支配,或者用于形成夫妻共同財產,或者是基于夫妻共同利益管理共同財產產生的支出。夫妻共同生產經營主要是指由夫妻雙方共同決定生產經營事項,或者雖由一方決定但由另一方授權的情形。參見羅書臻:《妥善審理涉及夫妻債務糾紛案件,依法平等保護各方當事人合法權益——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負責人就〈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涉及夫妻債務糾紛案件適用法律有關問題的解釋〉答記者問》,《人民法院報》2018年1月18日第3版。這意味著相當數量的債務即使與“家庭共同利益”相關,也無法被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而應按照個人債務處理。然而,我國對個人債務的責任財產范圍缺乏明確的規定。個人債務可以從其個人財產中獲得清償在我國沒有爭議,但個人債務能否以共同財產清償則存有爭議。《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法(辦)發〔1988〕6號,以下簡稱《民通意見》)第43條規定:“在夫妻關系存續期間,一方從事個體經營或者承包經營的,其收入為夫妻共有財產,債務亦應以夫妻共有財產清償。”在《婚姻法解釋(二)》發布后,該條文常常與《婚姻法解釋(二)》第24條同時適用,作為認定夫妻共同債務的依據。實際上,從夫妻共同財產作為某項債務的清償基礎并不能當然推斷出其為夫妻共同債務。易言之,以夫妻共同財產清償只是在性質上認定夫妻共同債務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從我國法將夫妻共同債務之清償責任界定為無限連帶責任來看,承擔責任的財產不僅包括夫妻共有的財產,而且包括雙方的個人財產。
上述問題的關鍵在于是否只能在一項債務被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的情況下才能以夫妻共同財產清償。如果對這一問題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將“可用共同財產償還債務”作為夫妻共同債務的獨占性特征便是妥當的。從《離婚財產分割若干意見》第17條的文義來看,它并沒有回答能否以夫妻共同財產清償個人債務的問題。立法和司法解釋對這一問題的語焉不詳為相關司法裁判的亂象埋下了伏筆。〔18〕參見楊治、王云霞:《夫妻個人債務執行疑難問題研究》,《法律適用》2011年第1期。這種亂象尤其反映在對夫妻共同財產的執行中。部分法院認為,債權人有權請求執行負債方配偶在共同財產中一半的財產權益。〔19〕參見“方蘭為與王欣、葛峰申請執行人執行異議之訴案”,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2016)皖民終587號民事判決書;“張濤與聞偉龍執行異議案”,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2017)粵執復175號民事裁定書。亦有法院認為,夫妻共同財產的分割僅限于法定情形,債權人無權請求執行夫妻雙方共同財產。〔20〕參見“瞿賽珠與薛偕發、陳惠松申請執行人執行異議之訴案”,云南省高級人民法院(2016)云民終619號民事判決書。還有法院認為,在夫妻關系存續期間,雖然配偶一方無權對單項財產進行分割,也不享有按份共有份額,但債權人可以請求執行夫妻共同財產。如一方配偶認為其利益受損,可以在夫妻共同財產的分割中要求多分財產以補償其損失。〔21〕參見“賀道俊與張小偉、張光耀、張光明案外人執行異議之訴案”,湖北省棗陽市人民法院(2017)鄂0683民初4769號民事判決書;“楊麗華與常州市武進區廣信農村小額貸款股份有限公司、葉民執行異議案”,江蘇省常州市武進區人民法院(2015)武執異字第14號民事裁定書。在實踐中多數法院采納了第一種意見,認為可以用負債方配偶從共同財產中可分得的份額清償其個人債務。〔22〕參見“楊俊華與邢雙全執行異議糾紛案”,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2105號民事裁定書;“張越與孫亞平、付健、徐州博匯工程機械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執行異議案”,海南省高級人民法院(2016)瓊執異9號民事裁定書;“王以紅與浙江麗水農村合作銀行城南支行、黎偉平案外人執行異議案”,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2010)浙執異終字第2號民事判決書。
照此理解,在執行程序中自應適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民事執行中查封、扣押、凍結財產的規定》(法釋〔2004〕15號)第14條的規定,夫妻任何一方均可提起析產訴訟,債權人也可以代負債方配偶提起析產訴訟,用分割所得的財產清償個人債務。在不涉及第三人的情形中,對夫妻共同財產的分割應適用《婚姻法》第39條、第47條以及《離婚財產分割若干意見》第8條的規定。司法實踐普遍采納了均等分割原則,極少給予婦女和子女照顧。然而,關鍵的問題是非負債方配偶能否以《婚姻法》第47條的規定對抗債權人。如果承認該條規定的對外效力,那么債務人可能故意實施相關行為,少分或者不分財產,不當減少責任財產,留下巨大的漏洞。但如果不承認這一分割基準,那么是否意味著《婚姻法》所確定的分配原則均不具有對外效力呢?如果不認可其對外效力就應當適用《民通意見》第90條所確立的分割規則,原則上均等分割并考慮共有人的貢獻度。但該條文但書部分已經明確規定夫妻共同財產的分割適用《婚姻法》的規定。故而,在限縮夫妻共同債務范圍的前提下,這一問題似乎很難得到解決。
即使均等分割夫妻共同財產,也會背離《民通意見》第43條所隱含的“積極財產、消極財產與責任財產相互牽連”的基本框架,既可能會導致對夫妻共同財產貢獻較多配偶一方的責任財產大幅減少,也可能使對夫妻共同財產貢獻較少配偶一方的責任財產大幅增加。由此形成的債權人劣勢或者優勢實際上均有違中立性視角下的“視同無婚姻原則”。
從以上分析不難發現,無論是擴張夫妻共同債務的方案還是限縮夫妻共同債務的方案均存在諸多問題和弊端。單純在債務性質認定層面進行“或有或無”式的限縮或者擴張都無法應對現實復雜情形中劇烈的利益沖突。
(三)層次互動方案的提出
如前所述,單純依靠債務性質劃分無法有效實現利益平衡,要么債權人的利益受到優待,要么夫妻一方的利益受到優待。這主要是由于在債務性質劃分層面,實際上只有夫妻共同債務和個人債務兩種選擇,無法進一步類型化作業以實現更細的區分。既然單純依靠債務性質劃分無法有效解決內部和外部的利益沖突,那么能否在夫妻債務規范體系的其他層面進行類型化處理呢?要回答這一問題,應當首先分析夫妻債務規范體系的層次。整個夫妻債務規范體系包含對內和對外兩個面向,對外以清償責任為核心,對內則以追償權為核心。法律需要用一種方法確定對外清償和對內追償的范圍。債務性質劃分是一種可行的方式,它可能同時具有內外兩個方面的意義或者只具有某一方面的意義。例如,在美國那些采用“管理人制度”(managerial system)的州,“用以清償債務的責任財產范圍取決于對共同財產的管理和控制權,而非取決于債務形成的原因”,〔23〕See Charlotte K.Goldberg,Community Property,Wolters Kluwer,2013,p.371.但“債務性質劃分在確定夫妻間的追償請求權時十分重要”。〔24〕See William A.Reppy and Cynthia A.Samuel,Community Property in the United States,Carolina Academic Press,2004,p.432.值得注意的是,進行債務性質劃分主要不是出于對積極財產性質劃分的邏輯對稱考慮,而是出于上述實用目標的考慮。在債務性質劃分規范之外,債務規范體系還應包含責任財產范圍規范、清償順序規范和追償規范等實體法內容。此外,處于實體法和程序法交界地帶的證明責任分配規范同樣具有重要意義,尤其是其中的事實推定規范通過一種抽象的風險分配緩和實體法規范的弊端。〔25〕參見[德]漢斯?普維庭:《現代證明責任問題》,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6頁。囿于篇幅,本文的討論主要集中于前述四個層次的規范。
所謂夫妻債務規范的層次互動,是指在“視同無婚姻原則”之下,通過上述四個層次規范的巧妙配合,進行細致的類型化處理。當然,從層次互動視角出發并不會得出唯一的解決方案,而是存在多種解決方案。但無論是哪一種解決方案都必須建立在一種體系融貫的思考之上。例如,如果采納《夫妻債務司法解釋》發布后的方案,就必須通盤考慮個人債務的清償問題。如果欠缺對這一問題的考慮,該司法解釋將導致矯枉過正的后果,危及債權人的利益。總體而言,層次互動存在兩個基本方向:一是適當擴張夫妻共同債務的范圍,但需要在清償規范層面根據夫妻共同債務產生的原因對其責任財產進行一定的區分和限制;二是限縮夫妻共同債務的范圍,但需要在清償規范層面對個人債務的責任財產進行適當的類型化區分。當然,正如前文所述,這種體系性考量不應局限于夫妻債務規范內部,而是應當擴展至積極財產規范,并融通債法(尤其是其中的多數人債務規范)和物權法(尤其是其中的共同共有規范)。之所以進行這種擴展性考量,是因為婚后所得共同制所產生的共有或者準共有狀態,“不僅影響到了共有財產所有權的法律制度以及共有人之間的關系,而且涉及到第三人,特別是債權人”。〔26〕[法]弗朗索瓦?泰雷、菲利普?森勒爾:《法國財產法》,羅結珍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715頁。從這一角度來看,夫妻債務規范同時會涉及到家庭法、債法和物權法。
二、連帶債務方案下夫妻共同債務的界定
在婚后所得共同制下,對債務性質進行劃分必然會涉及對夫妻共同債務和個人債務內涵的界定。雖然概念是進行性質劃分的前提,但鮮有實定法對這兩項概念作出明確的界定。由于夫妻共同債務和個人債務的互斥性,只要對其中一項概念作出界定即可。法國學者從對內視角將夫妻共同債務界定為最終應由夫妻共同清償的債務。〔27〕See Katharina Boele-Woelki,Bente Braat and Ian Curry-Sumner (eds.),European Family Law in Action Volume IV: Property Relations between Spouses,Intersentia,2009,p.404.意大利學者從對外視角將夫妻共同債務界定為可以用共同財產清償的債務。〔28〕同上注,第405頁。兩者的概念界定均建立在債務性質劃分的效果之上。
然而,從效果出發對概念進行界定的弊端在于它無法涵蓋債務性質劃分的依據,對債務性質進行劃分需要基于債務產生的原因。從直觀感受來看,夫妻共同債務是為夫妻共同利益所負的債務,而個人債務是為夫妻個人利益所負的債務。但這種直觀感受實際上并不能涵蓋所有的情形,也是不準確的。更為合理的區分標準是基于債務形成時債務人以何種面目出現,并由此進行大的類型區分。如果夫妻雙方以抽象人(persona)的面貌出現,其與債權人的關系,應依財產法(尤其是債法和物權法)規范具體判斷。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連帶債務與夫妻共同債務等置的前提下,債務在性質上依財產法規范可能被認定為連帶債務,從而形成夫妻共同債務。其他債務則可依其用途而被轉換成夫妻共同債務,這些用途與夫妻身份存在密切關聯。
(一)依性質而成的夫妻共同債務
在判斷某項債務依其性質是否應被劃歸夫妻共同債務時,應回到多數人債務的體系上去。有學者認為夫妻共同債務并非連帶債務,而是獨立于連帶債務的多數人債務形態。〔29〕參見繆宇:《走出夫妻共同債務的誤區——以〈婚姻法司法解釋(二)〉第24條為分析對象》,《中外法學》2018年第1期。此種觀點存在一項前提,即我國法上的多數人債務體系承認按份債務和連帶債務之外的第三種形態。從整個民法體系來看,我國法并沒有承認此種多數人債務。這一立場從《民法通則》開始即得到了很好的堅持。《民法通則》第86條、第87條僅規定了按份債務和連帶債務,并未規定其他類型的多數人債務。《物權法》第102條更是從根本上否認了在《民法通則》所規定的兩種多數人債務形態之外另設形態的可能性。按照《物權法》第102條的規定,除非法律另有規定或者第三人知道之例外情形,均應按連帶債務處理。然而,《婚姻法》對此并未作出特別的規定。2017年頒布的《民法總則》第177條、第178條維持了按份債務與連帶債務的二分法。有學者認為《合伙企業法》第38條、第39條可以作為我國法承認第三類多數人債務的例證。〔30〕參見前注〔11〕,王洪亮書,第504頁。但合伙企業作為獨立的民事主體,與單純的共同共有體存在明顯的區別。共同共有體本身并不會獲得獨立的法律人格,也不能享有民事權利能力。〔31〕參見薛軍:《〈物權法〉關于共同共有的規定在適用中的若干問題》,《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07年第6期。這實際上也是《民法通則》在規定個人合伙時采用連帶債務立場的重要原因。〔32〕參見我國《民法通則》第35條。
對于夫妻共同債務的性質,我國法也一直采納連帶債務之立場。《婚姻法》第41條關于“共同財產不足以清償的,由雙方協議清償,協議不成時,由人民法院判決”的規定實際上不能對外部債權人產生當然的約束。《婚姻法解釋(二)》第24條、第25條更是明確采納了連帶債務的立場。〔33〕參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審判第一庭編著:《最高人民法院婚姻法司法解釋(二)的理解與適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228~229頁。《夫妻債務司法解釋》維持了前述立場。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在“王社保與呂國華、劉明桂債權確認糾紛案”中將夫妻共同債務的責任財產范圍限定于直接負債方配偶的個人財產與共同財產的觀點〔34〕參見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2014)蘇民再提字第0057號民事判決書。實際上背離了現行法關于夫妻共同債務就是連帶債務的立場。事實上,要不要單獨設立協同債務或者共同共有債務這一類型的意義是存疑的。就本文所論的夫妻共同債務而言,問題的關鍵并不在于債權人是否應同時向夫妻雙方提出清償的請求,也不在于以共同財產向債權人承擔共同共有債務后再以個人財產承擔連帶債務的區分,而在于如何根據債務形成的原因對需要用以清償債務的責任財產范圍進行合理的限制,共同共有債務或者協同債務并不能擔此重任。這是由于它并不能像按份之債那樣限定個人所需承擔的責任范圍。從這一角度來看,增設共同共有債務的意義微弱。
從夫妻雙方依據財產法規范所形成的夫妻共同債務的種類來看,其既可能是意定之債,也可能是法定之債。婚姻并不消解夫妻雙方的法律人格,他們作為民事主體所形成的各類連帶債務均應被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但并不能從締結婚姻的意思表示中解釋出債務人與其配偶形成了并存債務承擔的合意,并由此對債權人承擔連帶責任。夫妻在共同生活或者共同生產經營過程中,依據財產法中的規范對第三人負連帶債務并不罕見。如果夫妻雙方對第三人所負債務根據財產法中的規范已被界定為連帶債務,自無必要再作相應的用途考察而可以徑直被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這一過程的實現難度遠低于經由債務用途考察而進行的轉換性認定。
值得探討的是,夫妻雙方通過共同意思表示或者其他原因所形成的按份之債是否應當屬于夫妻共同債務。從《夫妻債務司法解釋》第1條之文義來看,夫妻共同意思并不局限于形成連帶債務這一層含義,而且還包含雙方通過共同意思表示形成按份之債這一層含義。如果作此解釋,則意味著某些類型的債務根據財產法是按份債務,根據身份法又是連帶債務,唯一可能就是此類型的債務根據其用途而進行了性質上的轉換。但實際上,并非所有基于共同意思所形成的按份債務都存在“家庭日常生活”“夫妻共同生活”“夫妻共同生產經營”等用途。在堅持連帶債務與夫妻共同債務同義互換的立場下,不應將無法進行用途轉換的按份債務直接擬制為夫妻共同債務,而應將其定性為個人債務。
(二)依用途而成的夫妻共同債務
依用途而成的夫妻共同債務是指在性質上不能依據財產法規范被界定為連帶債務,但根據該債務所含用途,能依據家庭法規范將其擬制為連帶債務的債務。這一擬制性轉換的合理性來源于婚姻對夫妻雙方責任財產的影響。當然,其中還包含了對家庭團結性予以維持的抽象立法目的。按照原型,其可以區分為原為按份之債而依用途被擬制為連帶之債以及原為單一之債而依用途被擬制為連帶之債兩種類型,實踐中爭議較多的是后者。
關于這一擬制所依據的債務用途,學說上主要存在“家庭利益”“家庭生活所需”“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等三種標準。自1980年《婚姻法》以來我國法就此長期采納共同生活標準。〔35〕參見我國1980年《婚姻法》第32條、2001年修訂后的《婚姻法》第41條。《婚姻法解釋(二)》第24條被批評的一項重要原因正是其偏離了我國立法長期以來堅持的基于共同生活用途之性質轉換標準,改采時間標準。雖然《夫妻債務司法解釋》區分了“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標準及其他共同生活標準,但是這種區分主要反映在證明責任的分配上。質言之,該司法解釋實際上采納了共同生活標準。共同生活標準的外延比“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標準的范圍要廣,但比家庭利益標準的范圍要窄。需要注意的是,“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夫妻共同生活”“夫妻共同生產經營”等標準在本質上都是一種客觀視角,而非主觀動機。易言之,判斷一項債務的性質是否應當根據其用途進行轉換之基準并不在于夫妻一方或雙方負債時的主觀動機,而是在于一種理性第三人視角,即理性第三人如何理解債務的性質。
1.“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標準的家事代理權本質
就“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標準而言,根據《夫妻債務司法解釋》起草人的意見,其實際上對應的是日常家事代理權所能涵蓋的范圍。〔36〕參見程新文、劉敏、方芳等:《〈關于審理涉及夫妻債務糾紛案件適用法律有關問題的解釋〉的理解與適用》,《人民司法(應用)》2018年第4期。家事代理權在當代是否有存在的必要本身即存爭議。在我國臺灣地區,由于已有關于夫妻應就家庭生活費用所生之債負連帶責任的規定,有學者建議廢除日常家事代理權之規定。〔37〕參見陳棋炎、黃宗樂、郭振恭:《民法親屬新論》,三民書局2011年第10版,第151~152頁。實際上,家事代理制度并不能從民法代理的法理中獲得有效的解釋。〔38〕Vgl.Jauernig/Budzikiewicz BGB,§ 1357 Rn.1-2.正如林秀雄先生所言,“無法從日常家務互為代理之結果,而導出夫妻應就家庭生活費用所生之債務負連帶責任”。〔39〕林秀雄:《民法親屬編第六講——婚姻之普通效力》,《月旦法學教室》總第76期。按照代理之法理,代理人法律行為之效果應當直接歸屬于被代理人,而非代理人與被代理人負連帶責任。從要件上看,家事代理并不要求具有代理之意思,亦不要求顯名。〔40〕Vgl.BeckOK BGB/Hahn BGB,§ 1357 Rn.4;林秀雄:《親屬法講義》,元照出版公司2018年版,第120頁。如夫妻一方以另外一方的名義實施法律行為,在符合代理要件時,應適用代理的有關規定。在德國,關于家事代理權的法律性質存在兩種不同的觀點。爭議的焦點在于非締約方配偶能否依據家事代理權的規定直接成為合同當事人。〔41〕參見[德]迪特爾?施瓦布:《德國家庭法》,王葆蒔譯,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87頁。如果非締約方配偶能直接依據家事代理權的規定成為合同的一方當事人,則將嚴重破壞合同的相對性,并產生解釋上的難題。在荷蘭,雖然承認夫妻雙方對家庭生活債務的連帶責任,但是并不承認非締約方配偶能自動成為合同的一方當事人。〔42〕同前注〔27〕,Katharina Boele-Woelki 等編書,第169頁。從比較法來看,將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負債務的清償責任界定為連帶責任日趨普遍,〔43〕典型者如《巴西民法典》第1644條、《韓國民法典》第832條、《日本民法典》第761條、《奧地利民法典》第96條、《荷蘭民法典》第1:85條、《保加利亞家庭法典》第36條。當然亦有少數立法例不將其作為連帶債務,而是作為一種按份債務處理,典型者如《意大利民法典》第190條。且與法定夫妻財產制并無直接關聯。
在我國,情況則有所不同。我國學者通常將《婚姻法》第17條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法釋〔2001〕30號)第17條作為家事代理權的規范依據。從體系定位的角度來看,這兩個條文皆為共同財產制下的規范,家事代理權應為夫妻共同財產制之內容。它們實際上是對《物權法》第97條關于共同共有人處分共同財產規范的調整。法律作此調整的目的既是為了應對現實生活需要,也是為了保護第三人。只要是夫妻在日常生活范圍內的處分,就不構成無權處分,第三人無需援引《物權法》第106條有關善意取得的規定。只有在處分的對象包含積極財產和消極財產兩方面內容時,家事代理制度之立法目的才能實現。雖然當今的家事代理制度之立法目的已經發生了重要的變化,但將其概括為“喪失了保護婦女的原有功能,而完全淪為保護債權人的工具”〔44〕王戰濤:《家事代理的共同核心與更優規則:以〈關于夫妻財產關系的歐洲家庭法原則〉為考察對象》,《財經法學》2018年第2期。是不準確的。家事代理權更是為了維護日常生活便利與家庭團結的需要。〔45〕在德國,根據聯邦憲法法院的意見,保護債權人的利益并非家事代理權規范的首要乃至唯一立法目的。立法者同時也考慮到了婚姻義務實現的問題。Vgl.BVerfGE 81,1 (7).但如前所述,家事代理并不會使得非締約方配偶當然成為合同當事人,家事代理僅產生一種責任承擔意義上的連帶。法律實際上是將“夫妻應當共同分擔家庭生活費用”這一對內的權利義務外化。從歐洲家庭法學會對歐洲主要國家家庭法的比較研究來看,絕大多數立法例均涉及為家庭日常生活所負債務的特殊處理規則。〔46〕See Katharina Boele-Woelki (ed.),Matrimonial Property Law from a Comparative Law Perspective (Huwelijksvermogensrecht in Rechtsvergelijkend Perspectief),2000,Stichting ter Bevordering der Notari?le Wetenschap,in the Series Ars Notariatus C111,Kluwer,2000,translated by Hans Warendorf,p.25.這些特殊處理規則與家事代理制度密切相關。“無論這些法定的代理權是基于明示的規則還是基于被代理配偶的責任,在家庭共同生活的范圍內,另外一方配偶均受法定代理效果的約束。”〔47〕See Katharina Boele-Woelki et al.,Principles of European Family Law Regarding Property Relations between Spouses,Intersentia,2013,p.80.此處所謂“法定代理效果”主要體現在夫妻共同債務的認定及清償上。質言之,家事代理制度為此類型債務性質的轉換提供了正當性基礎。
2.為其他“家庭共同利益”所負債務的性質
值得注意的是,我國相關司法解釋并沒有明確規定“家庭共同利益”標準。對《夫妻債務司法解釋》中“共同生活”“共同生產經營”的解釋不應局限于文義。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妥善審理涉夫妻債務糾紛案件的通知》(浙高法〔2018〕89號)即對《夫妻債務司法解釋》第3條中“共同生活”“共同生產經營”的含義進行了擴張解釋。其中,“共同生活”包含雙方共同消費支配和用于形成夫妻共同財產兩種情形。“共同生產經營”則要根據其性質和夫妻雙方在其中的地位綜合判定。“共同生活”和“共同生產經營”只是“家庭共同利益”的典型形態。將“共同生活”“共同生產經營”等同于“家庭共同利益”實際上是擴張了夫妻共同債務的范圍,以緩和廢除“推定論”后對債權人保護的不利。
不過,對家庭共同利益的判斷并非易事。容易判斷的一種類型是,根據“鏡像原理”,凡是為取得、管理、處分共同財產所生的債務就應當被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如果為取得、管理、處分共同財產所生的債務根據財產法規則(如《物權法》第102條)已經被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自無判斷是否為家庭共同利益的必要。“鏡像原理”體現了“哪里有權利,哪里就有責任”(Ubi emolumentum ibi onus)的觀念。就我國法而言,為取得、管理和處分《婚姻法》第17條及相關司法解釋規定的共同財產所生債務屬于典型的為家庭共同利益的情形。
然而,到底是應從取得經濟利益還是從取得法律權利的角度理解“家庭共同利益”呢?如果將其局限于取得經濟利益,則可能導致家庭共同利益所能涵蓋的范圍被大大限縮。有學者認為,應當進行一種事實性的審查,考察債務所生利益是否實際共享。〔48〕參見李洪祥:《論夫妻共同債務構成的依據》,《求是學刊》2017年第3期。這實際上會嚴重限縮對共同債務的認定。例如,夫妻一方在生產經營活動中面臨風險,可能并不能實際取得經濟利益,但將其排除在外并不合理。如果將其局限于取得法律權利,有可能會產生另外一個問題,即負債所獲得的法律權利并不能直接體現為經濟利益,甚至有損于夫妻雙方的共同經濟利益。例如,夫妻一方從第三人處受讓債權,雖然獲得了作為標的物的債權,但該權利由于債務人缺乏支付能力可能難以具體化為經濟利益。我國司法實踐傾向于采用經濟利益標準,但并不以最終獲得經濟利益為標準,而是強調獲得經濟利益的可能性。例如,在判斷擔保債務是否屬于夫妻共同債務時,無論是持贊成還是反對的觀點,多采納了是否有助于獲取經濟利益這一立場。因承擔保證責任所產生的追償權最多只能填補保證人的經濟利益損失,而無可能從中直接獲取經濟利益。按照這一理解,似應將其排除在“家庭共同利益”標準所能涵蓋的債務之外。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雖在《關于夫妻一方對外擔保之債能否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的復函》(〔2015〕民一他字第9號)中采納了這一立場,但在對該案的分析中又指出,應當根據夫妻一方是否從對外擔保中獲取經濟利益判斷以夫妻一方名義所承擔的保證債務是個人債務還是夫妻共同債務。〔49〕參見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夫妻一方對外擔保之債不屬于夫妻共同債務》,載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審判第一庭編:《民事審判指導與參考》2016年第1輯,人民法院出版社2016年版,第118頁。
最高人民法院在其后審理的相關案件中實際上采納了“間接獲益可能說”,即使保證人缺乏從保證中直接獲益的可能,也可能因為間接獲益而屬于為“家庭共同利益”的情形。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在“王瑯與李文龍、謝凱、成都歡娛互動科技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糾紛案”中認為,夫妻一方為自己擔任法定代表人及大股東的公司債務進行保證所生的債務屬于夫妻共同債務。其理由在于公司的經營狀況會直接影響保證人的個人獲利,進而會影響夫妻共同財產。〔50〕參見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752號民事裁定書。類似案件參見“李大紅與安英杰、寇淮案外人執行異議之訴案”,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申2908號民事裁定書;“張秀萍與田瑜、河北旭躍實業集團有限公司、曾海生、徐躍全、郝文杰、河北利嘉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河北鑫源順發化工化肥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糾紛案”,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44號民事裁定書。在另外一起涉及債務加入的案件中,最高人民法院同樣采納了這一立場,認為作為加入債務人的夫妻一方實際參與債務人的經營活動,與夫妻雙方的利益存在關聯,因而維持了原審法院的判決。〔51〕參見“徐靜娟與華偉明、許洪標、許逸文、德金投資有限公司、北京清大德人科技有限公司、鄧崇云民間借貸糾紛案”,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1516號民事裁定書。對于夫妻一方所生侵權之債、不當得利之債、無因管理之債或者公法上的債務(如稅款、罰款),同樣應當以間接獲益可能性作為判斷基準,但在具體判斷上有所差異。以實踐中較為常見的侵權之債為例,如果侵權行為與家庭共同利益之間存在密切關系,則應將其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典型者如出租車司機交通肇事所生債務。〔52〕參見吳曉芳:《〈婚姻法〉司法解釋(三)適用中的疑難問題探析》,《法律適用》2014年第1期。在此類情形中,侵權行為本身不可能給家庭帶來經濟上的增益,而是會招致損失,但是與侵權行為有關的職業活動具有一種經濟上的增益可能性。
如果采納家庭共同利益標準,可能涉及的一項解釋難題是,夫妻雙方撫養前婚所生子女或者非婚生子女所形成的債務實際上與夫妻雙方共同的家庭利益無關。但出于保護未成年人的需要,將其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較為合理,但是否應當拓展至其他類型的血親扶養則不無疑問。《離婚財產分割若干意見》第17條采納了血親扶養的立場,將夫妻一方履行撫養、贍養義務等所負債務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不過,在夫妻共同債務就是連帶債務的前提下,可能會產生矯枉過正的后果,使得無法定扶養、撫養、贍養義務的配偶一方承擔過重的責任。清償后的追償機制只能緩解這種或有或無式的困境。“間接獲益可能說”實際上已經為寬泛解釋“家庭共同利益”創造了基礎,如果再進一步增設其他類型,其妥當性殊值懷疑。
值得對比的是,在美國四個實行共同債務制度的州出現了擴張解釋“家庭共同利益”的傾向,被學者批評過于保護債權人。〔53〕See Andrea B.Carroll,The Superior Position of the Creditor in the Community Property Regime: Has the Community Property Become a Mere Creditor Collection Device?,47 Santa Clara L.Rev.1,19 (2007).而在美國這幾個州,除了“共同生活需要” 產生的債務等極少例外情形外,非負債方配偶的個人財產并不會被用以清償夫妻共同債務。而在我國,一旦被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夫妻雙方就將承擔連帶清償責任,因此,應當更為謹慎地處理擴張解釋“家庭共同利益”的問題。基于類似的考慮,我國法同樣不宜效仿諸如法國、匈牙利、比利時以及美國亞利桑那州、新墨西哥州、華盛頓州〔54〕同前注〔47〕,Katharina Boele-Woelki等書,第252頁;同前注〔24〕,William A.Reppy、Cynthia A.Samuel書,第445頁。所采用的夫妻共同債務推定模式,鏡像積極財產性質不明時的推定規則,〔55〕See Frédérique Ferrand,The Community of Acquisitions Regime,in Katharina Boele-Woelki,Nina Dethloff and Wener Gephart(eds.),Family Law and Culture in Europe: Developments,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Intersentia,2014,p.47.將不能被證明為個人債務的債務全部推定為夫妻共同債務,而是應適當加重債權人的舉證責任,以降低被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的可能性。易言之,在性質不明時,應根據債務形成原因的差異分配舉證責任。總體而言,考慮到連帶債務的嚴苛性,以及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形成的夫妻共同債務對非負債方配偶可能產生的巨大負擔,對于后一種類型的夫妻共同債務的判定應當至少采納一種限縮立場。但如前所述,這種限縮或許會不利于對債權人的保護。
不難看出,在連帶債務與夫妻共同債務等置的前提下,解釋“家庭共同利益”的范圍并實施轉換會經常面臨兩難境地。這主要是由于對處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范圍之外但尚屬于“家庭共同利益”范圍之內的這部分債務,家事代理權已經不能夠為其性質轉換提供正當化依據。唯一可尋找的正當化依據只能是前述積極財產、消極財產與責任財產三者之間的牽連性。〔56〕不僅是婚后所得共同制,各類夫妻法定財產制基本上都是以積極財產、消極財產和責任財產之間的牽連性為構建框架的。例如,在一般共同制中,作為理想原則,任何一方配偶的無論是在婚前還是在婚后的債務都應當被認定為共同債務。這正是由于在積極財產層面,除了特別財產外,婚前與婚后的財產都視為共同財產,對夫妻各自的責任財產產生了根本性影響。當然,法律也可基于公平原則對此理想框架進行某些修正。See Isidor Leob,The Legal Property Relations of Married Parties: A Study in Comparative Legislation,The Law Book Exchange,2004,p.75.易言之,婚后所得共同制對責任財產的影響形成了對債務性質進行轉換的必要。但這種牽連性只能為將夫妻共同財產納入為“家庭共同利益”所負債務的責任財產范圍提供支撐,而不能為將非直接負債方配偶的個人財產納入夫妻共同債務的責任財產范圍提供合理性論證,或有或無式轉換之正當性基礎存在嚴重問題。
三、連帶債務方案下個人債務的雙重類型
(一)個人債務類型區分的必要性
在堅持夫妻共同債務等同于連帶債務的立場下,一旦被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則無法對用以清償該債務的責任財產進行限制。易言之,在此立場下,無法根據債務產生的原因進行進一步區分和類型化處理。這也是我國目前夫妻共同債務規范體系無法有效平衡債權人保護和配偶保護的重要原因。《婚姻法解釋(二)》第24條被詬病的重要原因正是其過度強化了對債權人的保護。過度保護最為明顯的表現在于直接負債方配偶用以清償夫妻共同債務的責任財產可能遠遠超過其若未婚時可提供的責任財產。從比較法來看,在實行婚后所得共同制的歐洲國家和美國的部分州,通常而言,如果債務根據其性質本不應由配偶雙方承擔連帶責任,則只有在基于特殊法政策考量的例外情況(如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負債務)下,才能以非直接負債方配偶的財產清償債務。夫妻共同債務與連帶債務等置并不是一種最佳方案,在立法例上也極為罕見。將夫妻共同債務與連帶債務等置的問題集中表現為對于既不屬于財產法上的連帶債務,也不屬于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負的債務,非直接負債方配偶也可能要承擔連帶清償責任。這部分債務主要是指依據其他“家庭共同利益”標準轉換而形成的連帶債務。法律只能通過縮小夫妻共同債務的范圍降低非負債方配偶承擔連帶清償責任的可能性。相比之前的時間轉換標準,《夫妻債務司法解釋》所確立的用途標準已經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個人債務和按份債務被轉換為連帶債務的可能性,但司法實踐所面臨的兩難境地仍然存在。部分學者提出將夫妻共同債務之責任財產局限于直接負債方配偶的個人財產及共同財產的改革方案。〔57〕代表性觀點參見裴樺:《夫妻財產制與財產法規則的沖突與協調》,《法學研究》2017年第4期;龍俊:《夫妻共同財產的潛在共有》,《法學研究》2017年第4期;何麗新:《論非舉債方以夫妻共同財產為限清償夫妻共同債務——從(2014)蘇民再提字第0057號民事判決書說起》,《政法論叢》2017年第6期。但從目前的趨勢來看,立法和司法均無突破多數人之債二分法的動力,這一方案的可行性較低。與其如此,倒不如將與“家庭共同利益”相關但不符合“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標準,且在性質上不屬于連帶債務的債務整體移入個人債務處理。
與夫妻共同債務不同,個人債務可資利用的工具更為廣泛,尤其是在責任財產規范層面能夠根據債務發生的原因進行類型化區分。這些工具的密切配合能夠有效解決“什么性質的財產負擔什么性質的債務”這一夫妻債務規范體系的核心問題。
在責任財產范圍層面存在兩項顯而易見的共識。其一,負債方配偶的個人財產應當被納入責任財產的范圍。其二,個人債務的責任財產不應涵蓋另外一方配偶的個人財產。對于夫妻共同財產是否應當納入個人債務的責任財產范圍以及在多大比例上納入則存在明顯的爭議。當然,這種比例上的區分也為類型化處理個人債務奠定了基礎。按照“視同無婚姻原則”,似乎應當將用以清償個人債務的責任財產擴展至該方配偶對夫妻共同財產的貢獻份額。婚姻既不應當成為債務人逃避責任的手段,也不能為債權人在責任財產層面獲得優待提供合理的支撐。
但從比較法來看,并非所有的立法例均采納了這一標準,而是大致存在三種方案。第一種方案是原則上允許個人債務從整個共同財產中獲得清償,菲律賓采此例。〔58〕See The Civil Code of the Philippines,§ 163.第二種方案是原則上只允許個人債務從其在共同財產的份額中獲得清償,俄羅斯采此例。〔59〕Ct.142 CK.第三種方案是不考慮一方配偶對夫妻共同財產的貢獻份額,而是直接將特定比例的共同財產納入責任財產范圍,美國新墨西哥州和瑞士采此例。〔60〕See New Mexico Statutes Annotated,§ 40-3-10 (A).美國新墨西哥州關于個人債務責任財產范圍的規則相對復雜。在個人財產不足以清償時,應以負債方在共同財產中的份額清償,如果不足以清償,則以除家庭住宅外共同財產一半的份額清償,如果還不足以清償,則以其在家庭住宅中的份額清償。《瑞士民法典》第234條將婚后所得共同制作為一種約定財產制,規定一方配偶可以一半的共同財產清償個人債務。在堅持夫妻共同債務與連帶債務等置且將為“家庭共同利益”所生的債務納入個人債務范疇處理時,無法通過一種方案獲得滿意的解決,有必要對個人債務進行進一步的區分。
(二)與“家庭共同利益”相關的個人債務
對于為“家庭共同利益”所生的債務,其責任財產范圍應當擴展至整個共同財產。易言之,這一類型債務的責任財產包括直接負債方配偶之個人財產以及共同財產。與此相關的是,法律不再面臨通過限縮解釋“家庭共同利益”限制夫妻共同債務范圍的壓力。在此方案下,應當適度放寬對“家庭共同利益”的解釋,但是否應當將精神利益納入不無疑問。從比較法來看,對“家庭共同利益”的認定往往存在寬泛的解釋,不僅僅局限于經濟利益。在葡萄牙,對家庭共同利益的認定“不僅僅局限于物質利益或者經濟利益,而且可能包含道德利益和精神利益”。〔61〕See Guilherme de Oliveira,Family and Succession Law: Portugal,Wolters Kluwer Law & Business,2012,p.193.在雙務合同(尤其是各類服務合同)中,如果第三人之對待給付使家庭獲得了精神利益,原則上應將其界定為“家庭共同利益”。與此相對,在缺乏對待給付義務的單務合同情形,考慮到家庭并不能從中直接獲得精神利益,原則上應將其排除在“家庭共同利益”之外。典型者如《離婚財產分割若干意見》第17條規定的“資助不具有法定扶養義務的親友”所形成的贈與合同。在侵權行為所生債務情形中,類型更為復雜。如果侵權行為并不發生在具有經濟利益增益可能性的活動中,那么能否一概排除“家庭共同利益”范疇呢?作為美國實行共同債務制度典型的亞利桑那州,法院在“Reckart v.Avra Valley Air案”中認為:“金錢利益在判斷共同利益時并不是必需的,娛樂消遣活動會給家庭共同體的利益帶來一般性的好處,共同財產應當被用以清償配偶一方在實施這些活動時所產生的侵權責任。”〔62〕See Reckart v.Avra Valley Air,509 P.2d 231,1973 Ariz.App.LEXIS 589,19 Ariz.App.538.在該案中,丈夫為了獲取飛機駕駛執照以便帶家人外出度假,在此過程中因過失導致飛機受損。這種解釋方法存在明顯的擴張傾向,更有利于保護債權人,但并未超過必要的限度。更具爭議的是夫妻一方所實施的侵權行為無論是在主觀目的上還是在客觀利益上都與家庭共同利益無關的情形。在“Clayton v.Wilson案”中,丈夫雇傭租住在他家的未成年人整理院子并在此過程中實施性侵,華盛頓州最高法院認為丈夫的行為發生在管理夫妻共同財產的活動中,夫妻共同財產應當被用以承擔侵權責任。〔63〕See Clayton v.Wilson,168 Wn.2d 57,227 P.3d 278,2010 Wash.LEXIS 63.這種觀點實際上過度拓寬了家庭共同利益的含義,為了保護債權人的利益過度犧牲了非負債方配偶的利益,并不可取。
總體而言,即使將與“家庭共同利益”相關且在性質上不屬于連帶債務、在用途上不屬于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債務移入個人債務范疇處理,將其責任財產限定于直接負債方配偶的個人財產和共同財產,也不宜過分擴大“家庭共同利益”的外延,而應將其局限于“間接經濟獲益可能性及精神獲益可能性”的范疇。對于精神獲益可能性的解釋標準應當較經濟獲益可能性更為嚴格。
(三)其他類型的個人債務
對于除此之外的其他類型個人債務,應將其責任財產局限于貢獻份額。典型的其他類型個人債務例如夫妻一方婚前所負擔的債務、婚后因取得或管理個人財產所負擔的債務以及其他因實施與“家庭共同利益”無關行為所負擔的債務。對前兩種個人債務應當考慮諸如夫妻一方婚前所負擔的債務是否用于婚后家庭生活,婚后管理個人財產之收益是否歸屬于共同財產,婚后管理個人財產是否有助于家庭共同利益等因素。例如,對性質上雖然屬于個人財產的職業活動用具進行修理所生債務應屬于為“家庭共同利益”所生之債務。對于非為“家庭共同利益”所生債務,其責任財產范圍自應包含負債方配偶的個人財產。除此之外,實行共同財產制的國家普遍承認此類型個人債務的債權人有權從共同財產中獲得清償,但存在前述立場上的差異。由于我國現行法將為“家庭共同利益”所負債務置于夫妻共同債務處理,個人債務實際上僅指非為家庭共同利益所負債務。我國司法實踐關于共同財產對個人債務的清償責任問題存在較大的分歧。最高人民法院在近年來審理的相關案件中只是確認了個人債務可以從夫妻共同財產中獲得清償,另外一方配偶的相應份額亦應得到保護,但并未明確何為配偶的相應份額。〔64〕參見“劉成英與海南聯商物業管理有限公司、海口市擔保投資有限公司、張春田、周海誠、肖四美案外人執行異議之訴案”,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3819號民事裁定書;“周鳳珠與青島威邦貿易有限公司、周春海案外人執行異議之訴案”,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3915號民事裁定書;“張靜與高天云、張佳勛案外人執行異議之訴案”,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2083號民事裁定書。對此的合理解決方案是:在外部關系上,按照雙方對財產的具體貢獻份額處理;在內部關系上,按照《婚姻法》所確定的原則處理。故而,貢獻份額并不等于夫妻一方在婚姻關系終止時實際可分得的份額。貢獻份額既可能少于也可能多于在婚姻關系終止時可分得的財產。即使一方因隱藏、轉移、變賣、毀損夫妻共同財產,或因偽造債務企圖侵占另一方財產而在婚姻關系終止時未分得財產,也應當將其對共同財產的貢獻份額作為清償其個人債務的責任財產。
是否有必要對個人債務作婚前或者婚后的區分呢?域外立法例中確實存在這種區分。例如《立陶宛民法典》第3.110條和第3.112條將婚前個人債務的責任財產范圍局限于負債方配偶的個人財產及其在共同財產中的份額,而將婚后所形成的個人債務之責任財產范圍擴展至負債方配偶的個人財產以及整個共同財產。美國統一州法委員會制定的《統一夫妻財產法》亦采納了這一區分立場,對于婚前形成的或者婚內形成但可歸因于婚前行為,且與家庭共同利益無關的個人債務,其責任財產范圍為負債方配偶的個人財產以及若不存在婚姻情況下該方配偶在共同財產中的份額;〔65〕See Uniform Marital Property Act,§ 8 (b)(iii).而對于婚內形成的個人債務,其責任財產范圍為負債方配偶的個人財產以及共同財產中一半的份額。〔66〕See Uniform Marital Property Act,§ 8 (b)(iv).這些規定與《立陶宛民法典》存在明顯的差異。此類區分可能產生對婚后所形成個人債務的債權人之過度優待,違背“視同無婚姻原則”。例如,雖然另外一方配偶可根據《立陶宛民法典》第3.115條主張補償,但負債方配偶通常已經陷入困境,無力進行補償,這一規則實際上損害了非負債方配偶的利益。至于是否應當將侵權或者犯罪所生的債務單列,則涉及法政策判斷問題。歐洲家庭法學會在《關于夫妻財產關系的歐洲家庭法原則》中對侵權或者犯罪所生的債務進行了特別處理,即使此二類個人債務負債方配偶的貢獻份額不足共同財產的一半,債權人也可以從一半共同財產中獲得清償,這主要是為了保護侵權或者犯罪行為的受害者。〔67〕同前注〔47〕,Katharina Boele-Woelki等書,第272頁。不過,此項理由是否真正足以突破“視同無婚姻原則”值得探討。此種規定實際上是在負債方配偶的侵權行為或者犯罪行為與家庭共同利益無關的情況下,讓非負債方配偶承擔責任,違背了前述責任與利益一致的原則。
四、連帶債務方案下的債務清償順序和內部追償關系
(一)清償順序
此處所言的債務清償順序并不同于民法上補充債務中的清償順序。“補充債務是不同主體之間的債務承擔關系”,〔68〕李中原:《論民法上的補充債務》,《法學》2010年第3期。而此處所言的清償順序并不針對主體,而是針對特定的財產,主要是指個人財產和共同財產之間的清償順序。當然,它還涉及個人財產上夫妻共同債務和個人債務的清償順序以及共同財產上兩種債務的清償順序。就我國現行法而言,《合伙企業法》第42條、《婚姻法》第41條均為針對特定財產的清償順序限定條款。值得注意的是,清償順序的限定并不影響對債務性質的認定。《婚姻法》第41條對夫妻共同債務中責任財產清償順序的限定并不影響該債務的連帶債務性質。這種清償順序上的限制意味著后順位財產的權利人享有先訴抗辯權,這種先訴抗辯權并不阻卻對主體全部財產的執行,而是阻卻對特定財產的執行,這與保證債務中的先訴抗辯權不同。
那么,這種針對財產的清償順序限制的意義何在?一個顯而易見的動因是順序規則降低了后續糾紛發生的可能性。亦即,順序規則減少了內部追償的發生,在一定意義上簡化了法律關系。例如,如果法律規定為“家庭共同利益”所形成的個人債務應先從共同財產中獲得清償,再從個人財產中獲得清償,相當比例的追償將不會發生。值得探討的問題是順序規則是否會對債權人造成重大不利。雖然順序規則對債權人的選擇自由形成了一定的限制,但從債權最終實現的角度來看,并沒有對其造成過度限制。總體而言,設定債務清償順序的限制明顯利大于弊。
基于這樣的考慮,即使是夫妻雙方根據財產法規則所形成的共同債務亦應受到這種清償順序的限制,即先以共同財產償還,再以個人財產償還。對夫妻共同債務責任財產清償順序進行規定的國家以葡萄牙〔69〕Art.1695CC.為典型。如果承認在夫妻共同債務中債權人應當承受這種限制,那么作為一種對等,無論個人債務是否與家庭共同利益相關,債權人都應當承受這種限制。如果債權人拋棄對先順位財產的追償,比照補充債務之法理,后順位財產權利人有權主張其僅應對先順位財產不足以清償的部分承擔責任。
(二)內部追償關系
配偶間的追償關系源于一方配偶對外承擔了超過其依據內部關系所應當承擔的責任份額。《婚姻法解釋(二)》第25條承認了一方配偶在承擔超過離婚協議或者人民法院的法律文書確定的債務承擔比例責任時的追償權。實際上,內部追償關系是夫妻債務規范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追償關系的目的是平衡夫妻內部的利益。是否存在內部追償關系決定了對債務的清償是最終意義上的還是臨時性的。〔70〕See G.Baeteman,The Original System of the Code Napoléon in Belgium and Holland,in Albert Kiralfy (ed.),Comparative Law of Matrimonial Property: A Symposium at the International Faculty of Comparative Law at Luxembourg on the Laws of Belgium,England,France,Germany,Italy and the Netherlands,A.W.Sijthoff,1972,p.8.大體而言,追償發生在以下兩種場合:一是在夫妻一方的個人財產被用以清償夫妻共同債務時,其有權按照雙方約定或者法律規定的債務承擔比例向另外一方追償;二是在夫妻共同財產被用以清償一方的個人債務時,另外一方有權按照雙方約定或者法律規定追償。在夫妻共同財產被用以清償共同債務,或者個人財產被用以清償個人債務時,并不會出現內部追償問題。易言之,這種追償既可發生在清償夫妻共同債務場合,也可發生在清償個人債務場合。
在夫妻共同債務場合,依據《民法總則》第178條的規定,實際承擔責任超過自己責任份額的連帶責任人,有權向其他連帶責任人追償。除非雙方存在單獨的約定,原則上夫妻雙方應當平均承擔責任。有疑問的是,如果債務系由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轉換而來,責任份額應當如何確定。夫妻雙方都有義務撫養家庭,但撫養義務之實現方式應視具體情況而定,綜合考量夫妻雙方的經濟能力、家務勞動貢獻等因素。如一方承擔了養老育幼和日常家務的主要部分,另一方以個人財產清償了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而形成的債務,則后者無權追償。
在個人債務場合,追償既是為了“維持共同體的物質基礎”,〔71〕薛寧蘭:《中國民法典夫妻債務制度研究——基于財產權平等保護的討論》,《婦女研究論叢》2018年第3期。也是為了防止夫妻一方通過個人債務不當減少共同財產,損害另一方在夫妻共同財產中的利益。如前所述,在本文所主張的方案中,個人債務區分為為家庭共同利益所生債務和非為家庭共同利益所生債務兩種類型。于前者,此類債務在內部關系上應由雙方分擔,但非直接負債方配偶的分擔存在一定的限制。如果在清償債務時無夫妻共同財產,直接負債方配偶以個人財產清償,其是否有權追償呢?對此,應當堅持此類型債務的最終責任不能超過共同財產的原則。在直接負債方配偶以個人財產清償債務后,如果婚姻繼續存在,則其可從將來獲得的共同財產中取得補償。如果在清償時,雙方已經離婚,則直接負債方配偶不能向另外一方追償。對于后一類型的個人債務,如果負債方配偶以其在共同財產中的份額清償,則另外一方配偶有權追償,要求其補足共同財產中的相應份額。在離婚后,如果非負債方配偶以其分得的共同財產承擔了此類型債務的清償責任,則其可直接向負債方配偶追償。
就追償權產生的時間而言,有意見認為,應將其限制在所得共同制終止時更為合理。〔72〕參見冉克平:《論夫妻共同債務的類型與清償——兼析法釋〔2018〕2號》,《法學》2018年第6期。歐洲國家立法例普遍采此種意見。〔73〕同前注〔47〕,Katharina Boele-Woelki等書,第326頁。這背后隱含了與將婚姻作為時效不完成情形的相似考量,即維持家庭的和平與團結。〔74〕Vgl.BGH NJW 1980,1517.當然,域外立法例亦有堅持追償不以財產制終止為前提者。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為了督促享有補償權的配偶及時行使權利,法律規定了3年的時效期間。〔75〕See California Family Code,§ 920.美國威斯康辛州亦有類似的規定,不僅允許權利方配偶在婚內提出補償,而且將時效確定為1年。〔76〕See Wisconsin Statutes,§ 766.70.就我國而言,將所得共同制之終止作為追償行使的條件更為合理。首先,我國法并未明確將婚姻作為訴訟時效中止事由,實踐中亦有爭議。〔77〕參見楊巍:《民法時效制度的理論反思與案例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359頁。與無行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為能力人和其法定代理人的關系不同,婚姻并不導致人格吸收,也不影響行為能力,更多是出于維持親密關系的倫理考量。〔78〕See Reinhard Zimmermann,Comparative Foundations of a European Law of See-Off and Prescrip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p.140-141.在法律沒有明確將婚姻作為訴訟時效中止事由之前,只有將財產制終止作為追償的條件,才能有效維持這種倫理上的團結。其次,由于共同財產的浮動特征,只有在婚后所得共同制終止時才有最終確定共同財產價值并進行清算分割的必要。追償同樣具有終局清算意義,將追償權的產生時間限定于此將更具效率。
五、結論
雖然夫妻分別財產制在制度科學性面向上更為簡潔與清晰,更有利于促進交易安全和效率,也反映了當今社會人格獨立、兩性平等的趨勢,代表了一種發展方向,〔79〕參見林秀雄:《夫妻財產制之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41頁。但一國應采用何種法定夫妻財產制并非純粹科學性判斷,還雜糅了民眾觀念與繼受傳統等因素。至少在我國此次民法典編纂中,立法者尚未展現出廢除婚后所得共同制的意愿。一旦承認婚姻具有改變夫妻雙方財產權屬狀態的效力,婚后所得共同制就無法擺脫處理夫妻債務問題的難題。由于夫妻財產制中的積極財產規范對夫妻一方或者雙方對外承擔債務的責任財產造成了影響,法律必須在消極財產層面綜合評價各方利益,建構合理的規范。作為一項總體目標,夫妻債務規范體系既不應當優待也不應當損害債權人的利益,而是應當盡量趨近夫妻雙方無婚狀態下的利益格局。夫妻債務規范體系的核心是在對外關系上解決一方或者雙方的債務應由何種類型財產承擔責任的問題以及在對內關系上解決應由何種類型財產承擔終局責任的問題。前者涉及債務性質劃分和責任財產范圍的問題,后者涉及內部追償問題。由于我國法目前將夫妻共同債務與連帶債務等置,將單個債務人無法償還債務的風險轉嫁給婚姻共同體中的另外一方配偶,對非直接負債方配偶的約束過于嚴苛,故而只宜將夫妻共同債務限定于依財產法規范在性質上屬于連帶債務以及根據“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轉換而成的連帶債務兩種類型,而將與“家庭共同利益”相關但不屬于上述兩種類型的其他債務移入個人債務進行處理,并以此為標準區分兩種類型的個人債務,確定各自的責任財產范圍。這是在夫妻共同債務與連帶債務等置前提下最能體現本文所主張的夫妻債務規范層次互動觀的方案。